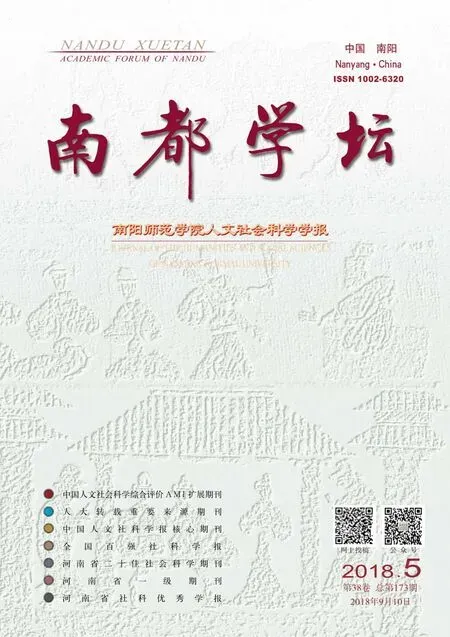汉镜中的“求仙路”
——以汉乐府为参照
2018-01-23时嘉艺
时 嘉 艺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求仙长生观念是汉代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从先秦模糊的神仙思想到汉代有意识地运用神仙寄托理想,体现了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延长寿命的期盼,无论是帝王贵族还是士人百姓,对生命的渴望从未消减。本文从两汉铜镜铭文入手,分析镜铭中神仙长寿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而将镜铭与汉乐府诗歌相联系,分析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群体中出现的求仙长寿观念,从而全方位还原当时世人思想的图景。
一、两汉镜铭中的求仙长寿思想
以长生不死为主要特征的求仙观念,历来影响到各个阶层的群体,从帝王贵族、士人阶层到普通百姓均以不同的方式祈祷神仙降福,以求长寿。这一观念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两汉铜镜铭文的阅读,可以从另一角度窥见该思想的面貌及时代情景。
(一)西汉早期
西汉初年,刘氏政权新建,文臣武将渴望得到封赏,并盼望子孙后代能延续这种富贵。至吕氏专权,吕氏外戚也抱有同样心态。由于铜镜的使用者多为中上层,故而铜镜铭文的撰写也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求富贵长寿类的镜铭开始萌芽。
包含长寿内容的镜铭,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固定书写形式:一是“大乐富贵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1]①本文所引铜镜铭文主要来自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编《汉镜文化研究(下)》图录部分,故下文征引只标明图版序号,不再赘述。(图号14);二是“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乐未央”(图号38);三是“寿如山,西王母,谷光憙,宜系(孙)子”(图号37);四是“服者君卿,万岁未央”(图号51)。还有一些镜铭,在这几种形式的基础上稍加变动,大同小异。此时镜铭多为综合性铭文,即求长寿的思想并非主体,而是富贵思想的附属。由于贵族阶层在掌握统治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封王拜相,故镜铭大多刻有“大乐富贵”“富贵如言”,也有“服者君王”“服者君卿”等为镜宣传的用语。人们既然拥有了富贵,便期望富贵可以延续下去,于是强化了对延年益寿的渴望。在西汉早期,统治阶层的求仙思想并不浓重,由于政权初建,他们更注重实用层面需求,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发展生产,没有太多精力关注求仙之事。仅在文帝时期,有方士新垣平以升仙术蛊惑文帝,后又被文帝处死,这件事也并未掀起更大波澜。民众更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生活重心,无暇顾及虚无缥缈的神仙追求。故而仅有少量镜铭中提到神仙“西王母”,并只把它作为长寿的符号进行展示,没有突出神仙崇拜的重要性。
(二)武帝时期至西汉后期
经过文景之治,社会财富得到积累,至武帝时期,国库积蓄充足,国家实力雄厚,中央集权得到加强,面对盛世局面,武帝和热衷求仙的秦始皇一样,自然期望拥有永恒的生命,将手中皇权延续下去。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2]381,为投统治阶层所好,求仙长生之说应运凸显。
这一时期,长寿类镜铭得到发展,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些变体。例如“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延年千岁,幸至未央,常以行”(图号60),“镜以此行,服者君卿,所言必当,千秋万岁,长毋相忘”等(图号61)。这些镜铭相较此前内容不变,篇幅加长。由于武帝中后期战争频仍,多征徭役,综合性铭文中求富贵、求长寿内容减少,相思离别类比重增加。
如果说战国齐威王和宣王、燕昭王及秦始皇的求仙思想是一直影响后世的隐流,武帝的追仙求寿思想则更推动了这股浪潮。此外,由董仲舒开创的新儒家思想,融合阴阳五行因素,创造天人感应理论,也为西汉后期及王莽时期的求仙思想奠定了基础。在西汉中后期,出现了全篇以长寿为主的“铜华类”镜铭,基本形式为:“清练铜华,杂锡银黄,以成明镜,令名文章,延年益寿,长乐未央,寿敝金石,与天为常,善哉毋伤。”(图号104)“湅治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长年益寿去不羊,与天长久而日月之光,千万旦而未央。”(图号105)这一类镜铭希望在“毋伤”“去不羊(祥)”的基础上实现寿如金石的愿望,与天地同寿能享受更长久的欢乐。另有一则镜铭,内容比较特殊:“日有喜,月有富。乐毋事,常得(意)。美人会,竽瑟侍。贾市程,万物正。老复丁,死复生。醉不知,酲旦星(醒)。”(图号111)其中“老复丁,死复生”意指人在年老之后可以再变年轻,死去之后还可复生,将人们对生命的渴望由不断延续的线性结构,推向了轮回结构。
(三)王莽时期
自王莽居摄年间到新莽王朝建立,王莽亦重视求仙长寿。王莽为文母太后起庙“长寿宫”。《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第一任皇后王氏死后,郎官阳成修献上符命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3]3561王莽便以此为名广泛选取女子充入后宫。又有人说黄帝因建华盖而成仙,王莽便制造九层华盖,并命拉车人呼喊“登仙”。
这一时期,长寿类镜铭内容明显丰富:一方面,镜铭中的长寿思想,从求个体长寿向群体长寿发展,多出现双亲长寿、子孙长寿的内容,希望子孙世代繁衍,是对长寿的更高期待。例如“福熹进兮日以前,食玉英兮饮澧泉。驾交(蛟)龙兮乘浮云,白虎引兮上泰山。凤皇集兮见神仙,保长命兮寿万年,周而复始兮八子十二孙”[4]。另一方面,长寿思想与神仙思想相融合,形成求仙以达长寿目的的铭文。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尚方类”。内容分为两种:一种是“尚方作竟(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非(徘)回(徊)名山采芝草,浮由(游)天下敖四海,寿如今(金)石得天道。”(图号145);另一种是“尚方御竟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上有仙人高敖(遨)祥(翔),寿敝(比)金石如侯王兮”(图号146)等。其中“尚方”是官署名,执掌帝王所用器物的制作。王莽曾被赐封为新都侯,篡位后又定国号为“新”,故“尚方作镜”“王氏作镜”“新家作竟”,均表示官府制镜。该类镜铭或完整呈现了神仙的饮食、活动等日常生活状态,或融入神兽元素,使神仙生活场景更为丰富,生动的画面感也与铜镜背面的神兽花纹相互参照。二是“上大山”类。有“上华山,凤皇(凰)集,见神鲜(仙),保长命,寿万年,周复始,传子孙,福禄进,日以前,食玉英,饮澧(醴)泉,驾青龙,乘浮云,白虎弓(引)”(图号164)等。其中“上华山”也可更换为“上大山”。“食玉英”指食玉屑求长寿,当时人们不懂食玉的危险,不但未得长寿而反受其害。东汉以后就不再出现“食玉英”的铭文。
在西汉末年的求仙思想中,最重要的是西王母崇拜。汉代成哀平时期,皇权旁落,外戚专权,奸佞当道,造成政局不稳,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民不聊生,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民需要某种信仰作精神寄托。据《汉书·哀帝纪》记载,“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3]290。民间出现集体祭祀西王母的事件。至新莽政权时期,为巩固自身政权统治的合法性,王莽注重谶纬、祥瑞与符命之说,也借助于民间西王母信仰运动为自己夺得政权制造理论依据。他重提民众传行西王母诏筹事件,将该事件赋予新的意图,《汉书·元后传》记载王莽诏令:“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钦承。谨以令月吉日,亲率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玺绂,以当顺天心,光于四海焉。”[3]3450王莽认为西王母为“历代为母”的图谶,应验着所谓太皇太后既是汉政权的太后,现在又是新莽政权的太后,即赞同王莽夺汉称帝。
由于王莽在位时间不长,在镜铭中大量出现西王母形象,大约是从东汉开始的。西王母长生不老,掌管不死之药,在西汉中期之前,一直作为统治阶级祈求长生的祭祀对象,而到了西汉后期,西王母形象下移,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主神,具有消灾避祸、赐福天下的神性功能。另有东王公作为西王母的“对偶神”出现。镜铭内容多为“永康元年,正月午日,幽湅黄白,早(造)作明镜,买者大富,延寿命长,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位至公侯,长生大吉,太师命长”(图号179)等。镜铭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处于“公侯”的高位,这种“世俗化”“平民化”的叙述,是便于民众理解的表现形式。
(四)东汉时期
在新莽末年至东汉时期,随着青铜材料的丰富和制镜技术的成熟,铜镜也不仅限于贵族使用,民间铸镜业渐趋普及。汉章帝时期出现手工业重心从官方到民间的重大转移,全国出现大量造镜中心,例如会稽郡的治所山阴(浙江绍兴)、江夏郡(治所湖北安陆)、广汉郡(治所四川广汉北)、蜀郡(治所四川成都)等地。从镜铭中也可以看到更多民间思想。
在镜铭的记录中就显示出更加丰富的造镜主体,例如“朱氏明竟快人意”“杜氏作竟四夷服”“吕氏作竟自有纪”等。其中“朱氏”“杜氏”“吕氏”是造镜工匠的姓氏。镜铭的思想也更加多样化,除了一贯延续的长寿主题、西王母主题,综合类镜铭增多,求富贵高官与求仙长寿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镜铭多有“均宜高位,位至公侯”(图号179)、“买者大富”(图号183)、“男则封侯,女即侍王。久服长饰,位至三公”(图号187)、“作吏高迁车生耳”(图号192)等内容,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阶层之间流动加强,普通百姓建功立业成为可能,镜铭内容为迎合民众思想而显得功利化、实际化。东王公、西王母的神性功能也更加复杂,不仅可以保佑世人长生,也可以保佑升官富贵、平安吉祥,总之,满足了民间大部分的精神需求。神仙信仰呈现出“民间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两汉镜铭中求仙长生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得知,神仙长寿思想的出现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从西汉时期的初步萌芽到武帝时期进一步发展,在新莽时代得到巩固,及至东汉达到顶峰,而后由于时局动荡又渐渐衰落。中国的求仙思想中即使有幻想的神仙部分,其落脚点也往往与现实紧密结合。人们对长寿的追求从最初对生命的渴望,发展为诉诸神仙世界,在东汉中后期又回归到对现世享乐的追求。
二、镜铭与汉乐府的对读
从历时性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人们思想的演变规律,而从共时性的视角也能够发现各个社会层面对神仙类思想的理解亦各有不同。汉乐府和镜铭可以视为代表贵族、士人、民间不同层面的文学形式,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以发现不同文本思想上的共通和差异之处。
(一)内容对读
镜铭作为一种韵文体,一方面有其自身独特性,另一方面又是诗歌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诗歌、辞赋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乐府中反映神仙信仰的诗歌可划分为三种:贵族乐府、文人乐府与民间乐府。反映西汉贵族神仙信仰的乐府诗有《郊祀歌》《铙歌》《八公操》。民间乐府中有《董逃行·吾欲上谒从高山》《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吟叹曲·王子乔》《步出夏门行》《善哉行·淮南八公》《艳歌·今日乐上乐》等。文人乐府中与求仙保身思想有关的是《引声歌》和张衡的《同声歌》[5]《汉诗》卷六,178。
从汉初到武帝时期,求仙活动主要集中在贵族阶层。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命人创作《郊祀歌》十九章,目的是祭祀天地诸神,包含浓厚的求仙长生思想。例如《赤蛟》中“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5]《汉诗》卷四,154可以看出帝王对永生的希冀。同时期镜铭中记载了相似内容,如“见日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延年益寿,敬毋相忘,幸至未央”(图号92)等 。由于西汉的铜镜多供给中上层使用,镜铭思想即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体现,二者意蕴共通。在《铙歌》十八曲中,《上陵》一曲歌咏仙人降临,赐下金芝、甘露,使人们得以延年益寿,其末句点明愿景“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5]《汉诗》卷四,158;《上之回》记录武帝到达回中的情景,其中有“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5]《汉诗》卷四,156;《远如期》中也有“远如期,益如寿,处天左侧。大乐万岁。与天无极”[5]《汉诗》卷四,161等祀颂之句。这些句子都表达了追求长生极乐的心情。除皇帝之外,宗室贵族也同样热衷求仙,《八公操》表现淮南王刘安希望八公下凡向他传道,“悠悠将将天相保兮”[5]《汉诗》卷一,99是祈求上天降福。许多镜铭内容从这些乐府诗句中脱胎而来,如“延年益寿,长乐未央,寿敝金石,与天为常,善哉毋伤” 等(图号104),这些乐府诗与镜铭是贵族求仙思想的真实写照。
《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3]1553从武帝到东汉中叶,是汉乐府诗进入民间乐府时期。这类乐府诗歌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为求取仙丹;一为游览仙境。
《董逃行》主要讲董生面圣,奉长生不老之药的故事。云:“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5]《汉诗》卷九,264与同时期镜铭“生如山石富且昌,□□富贵受命长”(图号182)可互相参照。《董逃行》“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中的“玉兔”“虾蟆”物象多与不死之药有关,在镜图中就有“蟾蜍举盘献药”的图式。《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吟叹曲·王子乔》与《董逃行》近似,都描写方士历经千难万险将仙丹奉给主人,祝颂主人“延年寿命长”,这些诗歌可能为民间方士所作。汉乐府中也有普通人为长生求得仙药的描述,如《善哉行》中“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之句即是。
《善哉行》《步出夏门行》《艳歌》主要记录游仙过程和仙界景观,在仙界参驾“白鹿”“六龙”,见到“王母”“王子乔”“姮娥”。这些仙界人物在镜图中也都有出现。在神仙类作品中会有一些共同的意象群,无论是诗歌还是镜铭,相同的意象总是频繁出现。“仙人”类有东王公、西王母、王子乔、姮娥,“仙禽神兽”类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白鹿”“六龙”,“神物”类有“灵芝丹药”等,这些主题词构成了汉代求仙诗的主体内容,在镜铭和镜图上都能得到印证。
东汉中叶以后至建安时期,文人乐府有张衡的《同声歌》等。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张衡接受南阳太守鲍德的邀请,出任南阳主簿,其在诗中以妾自比,以君比鲍德,“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希所见,天老教轩皇”,以求仙诗的形式,抒发自己对鲍德真挚的崇敬之情。《琴操》中又有“避世守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直当”,该诗表达的是回避朝堂、以求隐居的心境。在文人乐府中,求仙诗表达的内涵已经扩展,以求仙的形式展现现实主义的内容。
《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篇目也涉及神仙思想,其创作年代可能已不是东汉,应属魏晋,但也可视为此类思想的余波,而其中表现的内涵已经完全改观。《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回车驾言迈》均表现出求仙失望的思想,感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说明士人已经意识到生命转瞬即逝,不可强求,也不再寄托于仙人赐予的长寿,认为“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
此外,汉乐府诗歌中常有祝颂套语出现,胡应麟曾云:“乐府尾句,多用‘今日乐相乐’等语,至有与题意及上文略不相蒙者,旧亦疑之。盖汉魏诗皆以被之弦歌,必燕会间用之。”这些套语多为祝寿词,有“陛下寿万年”(《射乌辞》)、“令我主寿万年”(《临高台》)、“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等。由于音乐表演方式的要求,在乐调结束常见套语、重复等现象,这种用法与镜铭中反复出现的套语如出一辙。
通过对乐府诗歌和镜铭内容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阶层求仙思想的发展脉络。贵族阶层的求仙诗作在祭祀、宴饮场合使用,叙述内容程式化。《郊祀歌》中大多书写神灵从显现到降福的全过程。历代帝王都渴望永恒的生命,借助方士提供的服丹、养气之法以求长寿,这种思想代代流传,在王朝兴盛时尤甚。贵族阶层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士人的创作,士人创作既为统治阶层服务,又传达自己的思想。东汉时期,士人渐渐从寻求不朽存在的幻想中惊醒,转入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即使披着求仙外衣的《同声歌》《引声歌》,其实也是自我情感的表达。这种思想在魏晋进一步升华,士人在声称求仙的同时又十分清楚升仙的渺茫,意识到人寿的长短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借助神仙或者任何外在力量,在短暂的生命面前,现世的功业与享乐显然更加重要,从中可以窥见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子。至于民间层面的思想则更为实际,民间乐府诗反映的社会现象和观念比贵族乐府、文人乐府更加真实真切。东汉以后的镜铭就是民间思想的反映。在国运衰微的王朝末年,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惶惶不安的百姓需要西王母以“救世主”的形象存在,带给人们精神寄托。百姓也依据自己的需求与喜好,赋予西王母更多的神性功能,并想象西王母的神仙生活:“石氏作竟世少有,东王公,西王母,人有三仙侍左右,后常侍,名玉女。云中玉昌□□鼓,白虎喜怒毋央咎,男为公侯女□□,千秋万岁生长久。”(图号174)此类镜铭的出现既说明造镜工艺的进步,也说明神仙思想在民间流传广、影响深。“惟此明镜,焕并照明。本出吴郡,张氏元公。百湅千辟,分别文(章)。对距相向,朱鸟凤黄。天神集会,祐父宜兄。男则封侯,女即侍王。久服长饰,位至三公。曾(增)年益寿,其(师)命长。”(图号187)综合类的镜铭显示出民间思想的重点从求仙转移到求长寿、求富贵,实用主义色彩更浓。
(二)结构对读
无论是求仙类的诗歌还是镜铭,在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上,都呈现出固定的模式。《郊祀歌》十九章是汉武帝时期为郊庙祭神而创作的一组朝廷乐歌。既属朝廷乐歌,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它们凝聚的不是个人声音,而是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本结构的安排必然呈现某种秩序。《郊祀歌》中各诗篇按一定顺序配合形成组诗,《郊祀歌》的前两首《练时日》《帝临》叙述了神灵的到来,《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在四季轮回中展开祭祀,组诗末《赤蛟》与《练时日》形成内容上的照应。除了组诗的结构安排,诗篇内部也呈现出秩序,例如《练时日》一篇,记录了神灵从远方而来的全过程:“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班)裔裔。灵之至,庆阴阴,相放(仿)佛,震澹心。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5]《汉诗》卷四,147这个顺序是固定而不可随意更改的。同理,《赤蛟》中的“灵已醉”“灵既享”“灵将归”[5]《汉诗》卷四,154记录了神灵享用祭祀的过程。
镜铭的结构安排也另有一种秩序。秩序在西汉早期三言、四言镜铭中体现较少,镜铭多注重相邻两句间的紧密联系,而不会注意整篇的结构安排。例如“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乐未央”(图号38),前两句中“天”“地”相对,“富贵”之后,祈求“长乐”,而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不会有太多联系。这个时期镜铭的结构特点为句序安排更加灵活,可以调换,结构松散。“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乐未央”中几句的顺序,在另一组镜铭中就会略有不同,“清练铜华,杂锡银黄,以成明镜,令名文章,延年益寿,长乐未央,寿敝金石,与天为常,善哉毋伤”(图号104)。原本放在句末的“长乐未央”被置于句中,而“与天为常”(近似“与天相寿”)被放在句末。由于镜铭本身短小,不会有足够的空间展开叙述,个别句序的调整,并不影响整篇镜铭的理解。而到了七言诗中,镜铭也具有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句子之间联系紧密,例如“尚方御竟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上有仙人高敖(遨)祥(翔),寿敝(比)金石如侯王兮”(图号146)一首,先叙述处于四周方位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再叙述中间方位受到保佑的子孙,再描写高高在上的仙人。另一篇“上华山,凤皇(凰)集,见神鲜(仙),保长命,寿万年,周复始,传子孙,福禄进,日以前,食玉英,饮澧(醴)泉,驾青龙,乘浮云,白虎弓(引)”(图号164),完整展现上华山遇到仙人,求到长生之法的过程,随着完整叙事结构的形成,句子间的顺序也不会再随意改动。比诗歌模式性更强的镜铭,已经完全形成了固定模板,模板不会轻易改动,虽然铜镜出土数量众多,镜铭模板却是数量有限的。
三、“道门乐府”与镜铭中的道家文化
经过两汉的发展,神仙长生信仰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上层贵族、士人还是下层民众,都对神仙长生信仰有着各自的解读。上文中提到的求仙长生类乐府诗歌,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称其为“道门乐府”,例如《日出入》是汉代的郊庙歌词,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通过赞美日神无限的生命,感叹人世今生的短暂,显示出祈求永恒而不得的强烈生命意识与随乘龙以遨游的“天乐”情怀。《长歌行·仙人骑白鹿》《董逃行》等诗是求取仙药的主题,表现“延年寿命长”的愿景。《艳歌》《陇西行》等诗重在描述游仙的经历,是对神仙境界的幻想。诗歌中用铺排华丽的语句描绘神仙世界,向人们展现神仙生活景象,渴望成仙与劝仙劝道是其主题,神仙长生信仰正是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乐府诗歌外,铜镜铭文也从文学的视角为两汉道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佐证,与乐府诗歌相比,镜铭更能反映道家文化在全社会尤其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性,为思想史和哲学史呈现新的资料。
西汉初年,统治者崇尚清虚无为的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融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受到推崇,加之大一统思想下,汉武帝渴望皇权得到延续,这些汉代思想文化呈现出的交叉性与复杂性促成了黄老学说与神仙信仰的结合,黄老学说日益向养生、求仙的思想靠拢。《汉镜文化研究》中录有王纲怀《西汉早期镜道家文化概说》一文,其中提出铜镜铭文中崇尚天地自然永固不死的思想、表达人们期盼长寿的愿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道家文化的反映。例如镜铭中常出现“与天地相翼”(图号6)、“与天相寿,于地相长”(图号38)、“与天无极”(图号58)等内容。“与天”一词,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为“与天同道,故天与之”,“翼”在《尔雅·释诂》中的含义为“敬”。该类镜铭传达出对天地的敬畏,希望得到天助,以求得与天地同寿,这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神仙长生思想的演变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虽然在西汉早期表现神仙不死思想还较为少见,这一点上文已经论证,因为此时人们较多关注现实生活,故而神仙思想还不是主流。但经过武帝时期对鬼神之威的借助,确实达到了加强皇权的作用,在西汉中后期,与神仙思想直接相关的镜铭就十分丰富了,追求长寿、成仙等思想被道家所吸收,成为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神仙信仰在道家文化中的作用、王莽时期神仙信仰与谶纬神学的结合,加之天灾人祸、政治危机的背景,人们期盼救世神仙出现,以上几种元素,共同构成神仙信仰宗教化的发展契机,促进了道教的形成。在东汉末年,道教造神运动兴起,道教对以往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进行改造发展,东王公、西王母的主神地位受到动摇,多神局面出现。镜铭出现“众神见容”“天神集会”等内容,伯牙、黄帝、王乔等仙人形象被纳入其中,体现出道教的多偶像神崇拜。东汉时期的铜镜中,还存在一种三段式神仙镜群,通过对其花纹和产地的分析,学者指出该类铜镜与五斗米道关联密切,铜镜即是佐证宗教史的重要材料。神仙信仰虽然只是道教形成的众多前提条件之一,但是纵观道教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其实也是神仙信仰的理论化、宗教化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定型成熟,铜镜又被赋予驱邪、占卜等新的含义,是对其鉴容功能的引申化。
四、小结
镜铭作为一种简单的实用性文体,同时也是承载文学、思想的一手史料,反映社会生活的另一面镜子,铜镜是文本记录和历史记忆的统一场,从政治制度、文学文化视角都可以重新审视器物上的文字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通过上文对汉镜铭文演变的梳理以及与同时期汉乐府诗歌的对读可以发现:汉代的求仙长生思想在不断发展,西汉初期以帝王贵族为主流,至武帝时期,普通士人和平民百姓也参与到求仙大潮中,神仙信仰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王朝盛衰,人们也为神仙信仰不断注入新的观念,汉代不同阶层的求仙态度也对魏晋神仙观念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