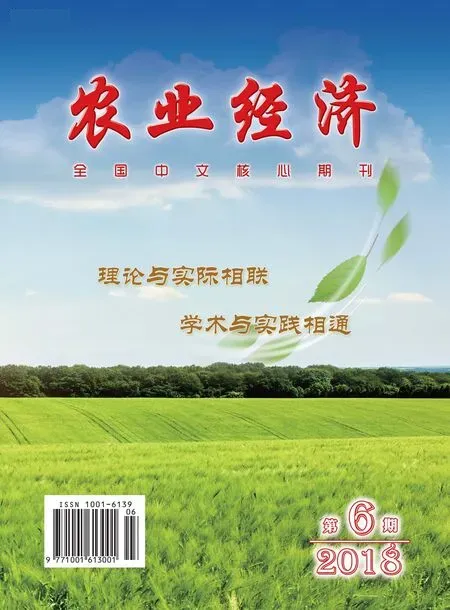以农产品价格不规律变动为视角窥探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冲突与协调
2018-01-23◎吴琼
◎吴 琼
一、从农产品价格不规律变动分析农业竞争秩序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经常会出现短时间不规律变动的现象。而“农产品市场每一次轮番上涨都是以某种或几种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为先导的”[1],由于粮食连续减产,2003年一年,小麦和稻谷的涨价超过30%,导致多种肉类及相关农场品价格普遍上涨;2006年1-6月份,猪肉价格上涨接近一倍,而8-12月,大豆、玉米的价格也开始出现持续上涨;2009年1-6月,生姜、大蒜等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而在之后的两个月,棉花、早籼稻、大豆等农产品也开始轮番涨价。而从2010年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价格不规律变动始终没有停止,不仅如此,诸如“蒜你狠”这种现象在全国大范围反复出现。[2]探究其背后的原因,除了表面的涉农因素外,其背后蕴含的非农因素也不得不考虑。而非农因素中,产业法规制的空白与竞争法规制的缺失不可否认也是造成此种现象的重要原因。竞争秩序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构成要素以及市场运行模式,一旦失控,无论任何形式的市场,其公平与效率都无法得到有机的配置。因此,在产业政策框架下建立一套产业法与竞争法协调融合的联动机制,以此来保障二者目标的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
二、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冲突原因分析
(一)价值目标的冲突
竞争法和产业法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但是,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规制重点、实施方式、调整手段和作用机制却存在明显不同。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法律化的产物和竞争政策的核心体现,是以维护自由竞争秩序为出发点,通过限制市场主体滥用支配地位、不当合并、联合限制竞争等行为,防止自由竞争带来的垄断和失序,把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基石;产业政策则是通过扶持或限制某些特定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对特定产业的扶持或限制,比如设置行业准入标准,就有可能在产业间形成不公平、不自由的竞争,与反垄断法的目标、价值取向和基本制度发生冲突。特别是经济转型和后发展国家,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的,客观上要求推行产业政策,而一些产业政策的采用会挤压、替代甚至是破坏市场竞争机制,产业政策的推行与竞争法整体的目标和理念发生了背离。
(二)立法上的冲突
农业是第一产业,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工业、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因而农业被誉为“产业之母”。农业的基础性以及农业生产机制所特有的高风险性、依赖性等弱质特点,决定了农业是个非全竞争性的产业。因此,各国政府一般均通过制定农业政策,对农业实行不同程度的保护来扶持农业发展。从广泛意义上讲,农业政策属于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同其他产业政策一样,农业政策也是通过政府的扶持与引导来推动农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从而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农业政策一般允许国家对农产品设立保护价格、给予财政补贴或者直接参与农产品收购。表面上看这与反垄断法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但出于对农业的维护和对农业政策的兼容,反垄断法认可农业的垄断地位,并依据农业政策设置反垄断法对农业的适用除外制度。对于农业组织的部分豁免,最早由美国在1914年的《克莱顿法》予以规定。《欧共体条约》第36条(现为《欧盟运行条约》42条)规定欧盟的农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其依据为欧共体委员会1962年通过,2006年修改的《关于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使用特定竞争规则的条例》(26号条例)。我国《反垄断法》56条规定:“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但不得不说,在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下,缺少对农产品竞争的有效监管立法。
(三)执法机构与产业监管的冲突
政府对于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手段,然而调控的宽度深度问题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市场始终会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和政府产业监管的双重监管。由于我国从80年代开始对于市场的调控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过程,竞争法与产业法在运行中的交叉问题始终不容忽视,反垄断执法机构与产业竞争监管部门之间在角色定位上,管辖权,管辖范围上都存在一定的冲突。而在农业产业中,这种冲突更多的表现为是执法经验和制度范围的缺失,主要是因为现有农业法律体系本身缺少有效的市场监管,而反垄断法对于农业领域采取适用除外规定。结合近些年价格的不规律上涨,监管缺失是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以农村合作社为代表的农业组织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等存在着错误的理解和不当利用,也正因为如此在立法的缺失导致监管的不力。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具有的易腐性所导致的仓储问题和运输问题,使得农村小规模经营者对于收购商,批发商等中间商的依存度很高,进而导致其为了降低风险,防止市场行情的急转直下,小规模农业生产者通常会选择大规模的批发商、收购商或者农产品公司签订长期订单以规避风险。虽然2007年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有相关规定,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加之反垄断法56条的农业豁免中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不清晰,使得在执法角度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断层局面。[3]而且由于缺少农业竞争监管机构和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联动,使得相关竞争法律规范在农业领域很难发挥作用。
三、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冲突的路径
(一)坚持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
虽然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路径上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二者在目标价值上是殊途同归的。在经济发展从无到有进而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协调路径无疑更能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因为其目标更为精准,犹如一记强心针直达病灶。然而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阶段,不难看出竞争法律规制市场更符合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经济发展初期,产业政策法可以利用税收,财政等多种产业政策促进幼稚行业的优先发展。虽然产业法反映的是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体现了明显的事后干预,但有时甚至是背离市场机制的。相比较而言,竞争法通过立法手段建立市场秩序,促进各行业平稳有序高质量发展,其更能为产业发展营造整体优质环境,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福祉。[4]这方面日本的大量经验可以为我国借鉴。因此,我国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协调必须是以市场作为核心和基础,产业政策法以建立公平市场秩序,维护经济稳定,并且和竞争法产生联动效应作为基本原则。
(二)完善反垄断法豁免除外制度适用范围和界定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和适用除外制度是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交叉点,其本质就是对原本属于反垄断法规制范围的,但为了特定时期某一经济产业目标能高速发展而产生的垄断行为不受法律规制的行为,从而划定竞争法与产业法的范围,以实现经济目标和其他社会目标的和谐统一。具体体现在第5条、第7条、第15条、第2条、第29条、第55条和第56条,并且对与大多数的自然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产业监管机制。而第56条农业豁免条款,虽然规定某一具体行业,但内容过于原则和概括,具体表现在:首先,明确界定“农业”的范围。广义的农业还应包含林业、畜牧业、种植业等。其次,限定适用除外的对象。要将适用除外的对象限定为农业直接生产者及其组织,非农业直接生严者组成的组织或联合体不宜确定为适用除外对象。第56条的规定中,农业生产者是明确的,而“农村经济组织”的表述易将农业销售、仓储、加工、运输等组织均包含在使用范围中。第三,农业适用除外要限制条件。《反垄断法》第56条对农业适用除外没有规定任何的限制性条件,没有将严重限制、扭曲竞争的行为和可能造成价格过度提高等不良后果的限制竞争行为排除在外,使农业适用除外貌似没有限制。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法对农业及其合作社的适用除外都有明确限制条件,而不是绝对的,甚至都设立了适用除外的“安全阀”,以防止农业及其组织滥用垄断地位。
(三)竞争执法机关和产业监管部门的管辖权协调
竞争执法机关与产业监管的管辖权配置应该坚持共同管辖为原则,专业管辖为例外。因此专业主管部门应与综合性竞争执法机关建立专业系统的联动机制,这是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重要保障。以农业产业为例,根据《农业法》27条,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农产品市场竞争,同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作为反垄断执法机关之一,负责查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因此,可以考虑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体系框架内,在反垄断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完成产业竞争监管,并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专业管辖,以形成联动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目标与竞争政策在执法领域的价值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