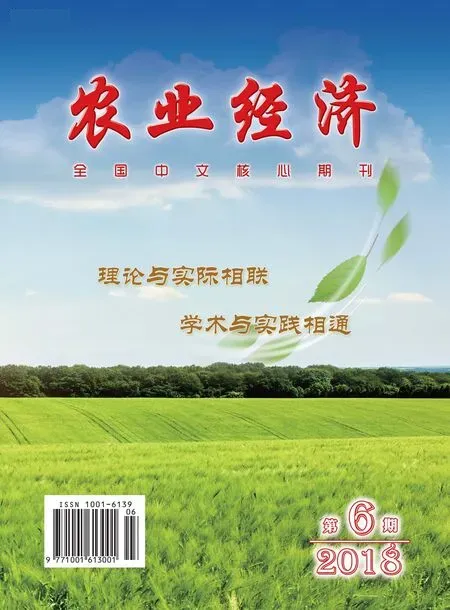新常态下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
——基于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2018-01-23潘万历
◎潘万历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持续增长,2015年增加到约7880美元。按照2015年世界银行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标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进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但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这时国内需求、产业基础和对外经济关系均形成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到了经济起飞的临界点。[1]但纵观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非所有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发展容易陷入瓶颈期,如果不能及时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便有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目前,我国在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一方面,我们要调整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如何推动农业的结构调整,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增收问题。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四年关注“三农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当前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三十年的特征,“三农”问题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比较突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占总人口近一半的农民的收入,从而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等收入阶段,是一个非常严峻和现实的问题。
日本是少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一。在农业问题上,日本也曾面临着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使农民脱贫致富等问题。日本是一个岛国,人均耕地少,农业生产条件比较恶劣。在二战结束初期,由于军人复员以及城市疏散人员大量涌入农村等原因,农村剩余人口和潜在的失业问题曾成为国家的重大问题。[2]面对战后复兴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抓住从1955年开始的高速增长机遇,用相对较短的时间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使城乡差距不断缩小,1975年农民收入甚至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因此,借鉴日本农民的增收经验,对推动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提高农民收入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期促进农民增收的经验
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进行了农地改革,改革到1950年基本完成,消灭了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推进了农村社会的民主化。1950年日本进入复兴期,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也随之启动。在如何解决农村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上,日本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提高农村边际生产率。二是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采取各种措施,增加他们的收入。最终达到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一)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关于目前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争议数量从几千万到1亿左右不等。[3]但是,不管数量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耕地上所需的劳动力会随之下降。此时,如果多余的劳动力继续依附在土地上,不仅会降低边际生产率,影响整体收入的增加,还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将过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这也是农业劳动力的再配置过程。
战后日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贯穿其整个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加上战后复员军人等纷纷涌入农村,致使农村人口急剧膨胀。日本通过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和就地转移的方式,较快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成为发达国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
首先,重工业和中小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日本政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并采取不同的方式引导劳动力转移。在工业迅速发展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重工业发展较快,1961-1969年,日本的机械、钢铁和化学工业都成倍增长,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4]在这期间,日本政府主要依靠重工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960 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列有农村劳动力动员计划,计划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中转用243万人,[5]以农业劳动力来填补二、三产业劳动力的缺口。当经济增长放缓,传统工业无法继续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时,日本政府便转而利用引进中小企业转移劳动力。1971年日本颁布了《农村地区企业导入促进法》等法规,引导中小企业以及大企业的分公司在农村地区建立工厂。这种临近转移方式可以有效防止农村人口过多流入大城市,避免“大城市病”的发生。
其次,日本政府通过在农村发展特色产业就地转移劳动力。日本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传统耕地作业所需劳动力大大减少,政府在扩大农业生产、保障粮食自给率的同时,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促进特色农产品的加工和利用,在全国形成了“一村一品”运动①一村一品是指以村为基本单位,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推进规模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几个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例如,大分县开展“一村一品”运动20多年来,共培育出有特色的产品336种,其中产值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有126项,产值达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15项。[6]通过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使第一、二、三产业有机结合,既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消化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概而言之,日本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方式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农业人口已经降至10%,与欧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
(二)通过农业保护、农村社会保障等促进农民增收
除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外,日本政府通过农业保护、农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促进包括兼业农户②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为第一兼业农户,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为第二兼业农户。、专业农户在内的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
由于日本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的耕地条件较差等原因,日本农业比较脆弱,政府对其的保护意识也相对强烈。日本的农业保护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以减轻税收负担为中心的农业发展政策。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实行地税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7]战后,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实现粮食自给,日本继续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主要包括直接财政补贴和价格支持。日本政府对一般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项目、农业生产资料的购置实施财政补贴,农户只负担很小的一部分费用。日本通过对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的农户进行补贴,促进了农地流动,扩大了规模经营。
此外,日本政府还几乎对所有的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日本政府于1961年制定了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标的《农业基本法》,为实施农业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到1965年,日本已成为工业化国家中农业支持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政府对农户补贴的力度也逐渐加大。1986年,世界各国政府发放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而日本一国就高达400亿美元。从农户的年收入来看,农户年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各种补贴。[8]通过农业保护政策,农户的收入增长效果明显,收入由1960年的平均41.1万日元增加到1994年的709.3万日元,增长了16.3倍。[9]
此外,日本政府还逐步制定、完善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了经济基础。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国民年金法》,将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60年代,以农村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障为支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日本进入了“国民皆保险”的时代。1971年日本政府开始设立农民养老金基金,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补充。[10]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保障了农民的生活,避免了“因病致贫”、“老无所依”现象的发生,从另一个侧面稳定了农民的收入。
为了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提高农业经营的稳定性,日本还设立了农业保险制度。1947年,日本专门制定并实施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此后又多次对其进行修改,放宽并扩大了强制加入的条件和范围。此外,农业保险的费用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负担。农业保险对于稳定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日本的增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就地致富的方式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这给我国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借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日本经验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二是兼业化程度高。
1955年至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此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转移的时期。1955年至1970年的15年中,农村劳动力人口从1600万减少到1000万,下降了37.5 %。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1.0%降为19.3%,下降了21.7%。70年代石油危机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开始下降,从50、60年代的年均60万人下降到年均40万人。[11]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及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新常态”下经济产业机构的不断优化将带动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要结合自身实际,合理、有序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以此填补二、三产业所需新增劳动力的缺口。同时借鉴日本经验,通过立法等方式完善工业布局,积极引导中小企业以及大企业的分公司在临近农村的地区建立工厂,让农民就地致富,避免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大城市病”问题。
(二)提高农民兼业化水平
兼业化程度高是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大特点。1960年至1980年,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户数量从207万户减少到62万户,减少71%,第二兼业农户则由194万户增加到303万户,占总农户数的65%。[12]可见,兼业是日本农村劳动力流出的主体形态。兼业农民类似我国的农民工,但是日本兼业农民具有较高的工作技能,他们在保留农地的情况下,通过进入城市从事工作获取农业以外的收入。这种兼业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传统的重农思想、落叶归根以及农村土地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外出工作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由此造成了日本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同步性,阻碍了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化,从而影响了规模农业的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开展技能培训的方式,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适当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三)加强农业保护,发展特色农业
日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有效供应,长期以来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主要包括直接财政补贴和价格支持。日本政府对一般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项目、农业生产资料的购置都会实施财政补贴,这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当前,我国正积极推动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鼓励有能力的农户承包土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可以在农田基建、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提高补贴力度,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实现农民增收。
同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曾大力推进“一村一品”运动,通过培育特色农产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方式促进了农民增收,这与我国当前所提倡的特色农业相吻合。我们可以开展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推进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通过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一条龙产业化发展,使第一、二、三产业相结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
四、结语
中日两国在“三农问题”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借鉴日本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我们现阶段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农民增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虽然日本所推行的农业政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基本消灭了城乡差距,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许多问题。例如,由于少子化以及青年人不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等原因,造成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严重,农业面临着后继无人、农地荒芜化的问题。日本对农业的保护措施,虽然保证了农民的稳定增收,但忽视市场规律、过度保护也造成了某些农产品的过剩危机。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不断增加的农业预算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愈发成为日本财政的沉重负担。因此,我们在借鉴其有益经验的同时,也要吸取教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