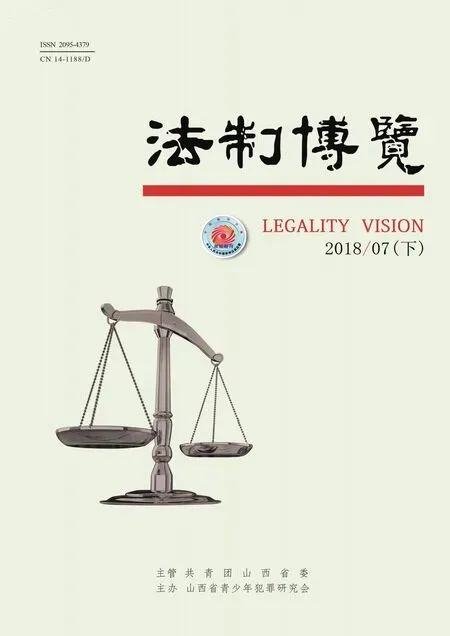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法中礼与法关系的演进
2018-01-22宋一楠
宋一楠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中国古代礼与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代“法”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对刑罚的裁判与实现上,而礼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规范,强调等级尊卑,要求人们发自内心地去遵守。礼法关系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经过秦及汉初的艰难发展,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代又结合在一起。[1]
一、夏商周礼治制度下的礼法混一
法律产生受宗教、道德的极大影响。法律与道德、宗教由混合到分化,是其进化的普遍规律。中国法“法出于礼”的特点也印证了这一现象。
早在夏商,从祭祀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礼文化已逐渐演变为一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用以区分贵贱亲疏的规范秩序。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称为“周礼”。这种制度既包含了强制手段也包含了非强制手段,是礼与法的混合,仅就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礼与法律无异。这时的礼混杂了其他很多形式的社会规范。此时的“法”也无后世所称法律的含义,《尔雅·释沽上》:“法,常也。”指常循之法式,也即习惯,更能体现法律特征的其实是“刑”。
而至于礼与刑的关系,如晋大夫叔向描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所谓的“事”,就是违礼的情况。说明西周实行的礼治存在着“失礼入刑”的原则,礼和刑皆是礼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刑是维护礼的手段之一,当时并没有独立的、相对稳定的刑罚体系,刑是依附于礼而存在的。[1]礼刑的结合也体现了礼法的混一。之后随着统治阶级司法经验的丰富,西周中期定《吕刑》,特定违礼的情形和相应的刑罚开始能够大致对应,“法”的概念也逐渐同刑罚及相关制度相结合,在与礼分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二、春秋战国时期礼法的分离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礼治制度式微。礼崩乐坏下,儒法两家提出各自的社会治理主张,一个主张德治和仁政,一个主张法治和刑罚。但其实无论是儒还是法,其思想内核都脱胎于西周的礼治,是经过扬弃,从中分化出来的礼和法。
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突出传统礼治体系中的德礼教化,形成儒家之礼。法家强调礼治中的“政刑”,主张用强制、严苛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郑子产铸刑书、晋铸刑鼎、李悝制法经、商鞅变法,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律实践活动都使原来依附于西周礼治体系的刑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法家之法。[1]
礼法分离,各自对西周礼治进行继承与革新,但尽管如此,二者文化的实质核心并非对立,对立的只是它们的社会治理主张。法家不排斥礼所蕴含的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区分,不仅如此,反而力图以法律来建构尊卑有别的差别性社会。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可见,法家反对的只是儒家所主张的无用的礼。同样,儒家也不否认政刑在国家治理上的作用。《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所反对的也仅是法家试图用刑罚来治理社会的主张,认为这样治标不治本。
儒法两家的对立在秦朝时达到顶峰。秦覆亡后,汉承秦制,在基本沿袭秦朝法律制度的同时,逐渐开始重视儒家之礼的教化作用,礼法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
三、西汉中期及之后礼与法的结合
汉代虽基本承袭秦朝法制,但汉代统治者开始将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汉武帝时期开启礼法结合的端倪,其中董仲舒所倡导的“春秋决狱”,即是指运用经典《春秋》所载事例及其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用“礼”来进行“法”的裁判。董仲舒所提的儒家理论,与春秋初期的儒家大不相同,是一种已被改造了的以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他主张德刑并用,侧重于儒家德治教化的统治原则。以礼入法,礼法结合,是这一时期礼法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
所谓的礼法结合,即是指以礼作为法的指导思想,礼所蕴含的伦理道德、纲常规矩成为法必须体现的道德精神。法家之法中对秩序、规则的注重,再无发扬之余地,因为法律、刑罚的适用可以根据礼的解释而变化。礼法结合首先以“以礼为主”为前提。这一转变的原则在后世历代中都不断被确认与加强。魏以“八议”入律,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唐代《唐律疏议序》载:“夫礼,民之防也,刑,礼之表也。二者相须犹口舌然。礼乐禁于未萌之前,刑制于已然之后。”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
礼法的结合诞生了一种绝佳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制度,人们的思想由礼来直接规范,行为由以礼为原则的法来规范,礼法共同为社会的稳定服务,礼法关系的演进在这一阶段愈趋稳定,直至清末外来的冲击迫使这一制度开始近代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