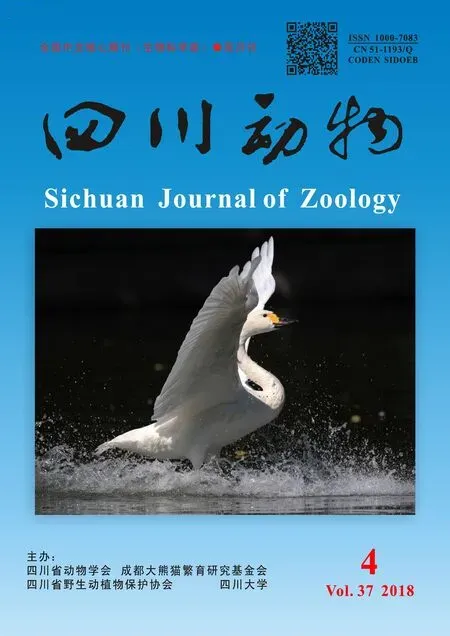鹿科动物声音通讯的研究进展
2018-01-22左智力杨萍陈渝倩刘洋
左智力, 杨萍, 陈渝倩, 刘洋*
(1.成都动物园,成都610081; 2. 上饶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鹿科Cervidae是偶蹄目Artiodactyla中物种数量仅次于牛科Bovidae的第二大科,分布遍及北半球、南美洲和东南亚(Gilbertetal.,2006)。根据交配制度,可将鹿科动物分为2种类群:一种为独居鹿类,一般为一夫一妻制或存在轻微的一夫多妻现象,通常具有领域性,如白尾鹿Odocoileusvirginianus、赤麂Muntiacusvaginalis、西方狍Capreoluscapreolus等;另一种为一夫多妻的群居鹿类,通常一只雄鹿会占有一个“后宫群”,有后宫防御现象,如黇鹿Damadama、马鹿Cervuselaphus、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等(Reby & McComb,2003a)。但是婚配制度作为进化稳定策略,在鹿类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可塑性(张建军,张知彬,2003)。
所有鹿科动物都要依赖视觉、嗅觉和听觉线索进行交流,有时还会整合各种信号以强化反应,例如,通过听觉、嗅觉和视觉进行个体识别或优势炫耀(曾治高等,2001;Lingleetal.,2007a;宁继祖等,2008)。声音交流比视觉交流受障碍物的限制较少,也不会受光线影响;虽然声音信号不如化学信号持久,但传递距离可远可近,比化学信号更灵活(Marler,1977),因此,声音交流作为一种非常高效的交流方式,在鹿科动物群体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鸣叫类型
与其他哺乳动物类似,鹿科动物发声的主要意义包括社会交流及竞争、母子互动、警戒和繁殖等(Bradbury & Vehrencamp,2011),典型鸣叫类型有发情鸣叫、警戒鸣叫交流鸣叫和求救鸣叫。
1.1 发情鸣叫
发情鸣叫是鹿科动物性成熟个体展示发情状态而发出的特定鸣叫声,主要用来吸引异性或激发配偶同步发情,以达到交配为目的。在繁殖季节,喜群居的鹿类雄性间争夺配偶激烈,同性竞争导致它们进化出较明显的两性异形,拥有形状复杂的角和性展示,同时声音高度发展,雄性利用显著且耗能的发情鸣叫展示自身的发情状态以吸引雌鹿(Reby & McComb,2003a;Capetal.,2008)。发情鸣叫在群居鹿类的成功繁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直接结果是给雄鹿带来更多的交配机会,给雌鹿提供选择配偶的依据,最终使更强壮的雄鹿成功繁殖,从而提高进化适合度(李春旺等,2001)。由于缺乏激烈的繁殖竞争,独居鹿类通常被认为缺乏与发情相关的特定大声鸣叫(Reby & McComb,2003a)。总体上,国内外学者对独居鹿类的研究远不及群居鹿类,这导致对其行为习性的了解有限。关于独居鹿类是否存在多样化的发情鸣叫类型,还需更多研究证实。
1.2 警戒鸣叫
鹿科动物在遇到潜在危险或竞争者时会发出大声的警戒鸣叫,起到反捕食或保卫繁殖领域的作用(Vannonietal.,2005)。大部分警戒鸣叫为吠叫,而美洲鹿族Odocoileini和驯鹿属Rangifer是喷鼻息(Capetal.,2008)。独居鹿类发出警戒鸣叫主要是作为“制止追逐的信号”,但偶尔在遇到潜在的领域竞争时也会发出警戒鸣叫(Rebyetal.,1999a)。群居鹿类则主要在受到其他物种入侵干扰时,向入侵对象发出警戒鸣叫(李春旺等,2001;宁继祖等,2008)。
1.3 交流鸣叫
交流鸣叫在社会性动物中比较普遍,不同交配制度以及不同年龄性别的鹿类在视觉交流受阻时,或者为了表达某种情绪时,都会通过声音交流来维持彼此间的互动(Atkesonetal.,1988;付义强等,2008)。某些独居的成年雄鹿在求偶时,会对雌鹿发出轻柔、简短的鸣叫,雌鹿有时也会鸣叫回应,但这种鸣叫并不仅限于性互动(Oli & Jacobson,1995)。因此,这种声音被定义为交流鸣叫而非发情鸣叫(Reby & McComb,2003a)。而群居鹿类的交流鸣叫主要用于繁殖期群主与“后宫群”以及“后宫群”内的雌性之间保持密切联络(Feighnyetal.,2006;付义强等,2008)。鹿类母子交流鸣叫的作用是当母亲与幼仔分开时进行定位和识别(Atkesonetal.,1988;Minami & Kawamichi,1992;Vaňková & Málek,1997)。鸣叫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会暴露发声者的一些重要信息,鹿类母子互动鸣叫的音量通常较低,这可能与降低捕食风险有关(杨承忠等,2012)。
1.4 求救鸣叫
鹿科动物在遭受极大痛苦,如被捕食者攻击或者受伤严重时会发出求救鸣叫(Richardsonetal.,1983)。发声时嘴部张大,声音持久、响亮、尖锐且失控,传播距离很远(Vannonietal.,2005)。不同种类的雌鹿听到幼仔求救鸣叫的反应不同,有的不论求救者是否为同类或其后代都会前来帮助,有的除非求救者是其刚出生几个月的后代才会前来救援(Lingleetal.,2005)。对于同类或后代求救鸣叫的识别能力不同,是导致雌鹿出现不同反应的原因,而进化出不同的声音识别能力可能与权衡反捕食防御好处与代价有关(Lingleetal.,2007b)。
2 发声机制
哺乳动物的发声可以用声源-过滤器理论来阐述(Taylor & Reby,2010)。声音的产生来自于声源的振动,然后被声道过滤(Pitcheretal.,2014)。根据声源-过滤器理论,动物的发声基频由喉头声带振动产生的源信号决定,但源信号在经过声道(包括咽和口或者鼻腔)时,受到声道的滤波作用,使频域中不同频率的能量重新分配,一部分频率因为共鸣被选择性放大从而产生共振峰频率,最终通过口和/或鼻孔传播出去(Fant,1960)。
大多数陆生哺乳动物喉头紧紧地附着在头骨底部,声道长度受头骨大小限制(Fitch,2000),因此缺乏复杂的声道控制,只能利用嘴唇和下颌控制嘴型和口腔张开情况来调节共振峰(Shipleyetal.,1991),发出声音的共振峰缺少变化。而某些雄性群居鹿类可以像人类一样移动喉头(Fitch & Reby,2001),发声时通过降低喉头的位置改变声道长度,可以大幅度改变声音的共振频率(Reby & McComb,2003b),从而发出复杂多变的叫声吸引异性或者与同性竞争。基频受声带的长度、纵向应力和组织密度影响(Titze,1994),因此,不同的基频对发声器官的形态和动物的身体素质有不同要求。产生低基频叫声需要较低的声带张力、较大的肺压和较大的声门波,而高基频叫声需要强大的肌肉力量(拉紧声韧带)和较大的肺压(克服发声阈值压力)(Titze & Riede,2010)。
3 声音包含的信息
对鹿类声带的生物力学研究发现,其粘弹性会随激素水平和发声行为而改变(Riedeetal.,2010),另外,声带还对睾酮高度敏感,随着雄性睾酮水平升高而变长(Beckfordetal.,1985),而且声音信号的编码方式不仅受发声器官的控制,动物身体的各方面情况也影响发声(Taylor & Reby,2010;Charltonetal.,2011)。因此,鹿科动物的声音能向竞争对手和潜在的交配对象反映其竞争能力,例如,体型、体质量、年龄、激素水平、社会地位等(Pitcheretal.,2014;Liuetal.,2016)。
3.1 形态学信息
非人哺乳动物的声带振动和声道共鸣可以独立变化(Fitch & Hauser,2002)。因此,基频或共振峰频率可以提供与发声动物相关的形态学信息(Reby & McComb,2003a)。声带或者声道长度可能跟体型有关,从而分别影响基频或共振峰频率(Fitch & Hauser,2002;Reby & McComb,2003b)。雄鹿发声通常受性选择影响,通过声音可以评估发声者的体型和身体状况等与适合度有关的信息(Andersson,1994;Vannoni & McElligott,2008;Titze & Riede,2010)。发出或者维持反映身体素质的“诚实”声音信号代价昂贵,只有身体状况良好的动物才能负担(Grafen,1990)。另外,声音包含与发声者固有特征相关的某些信息,由于生理或者身体的限制不能伪造(Maynard-Smith & Harper,2003)。
3.2 生理信息
发声特点例如声学参数、鸣叫率等,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会发生变化,这反映了发声者在生理状况上的改变(Lietal.,2001;Briefer,2012)。短时间内雄鹿可以通过提高鸣叫率向附近的雄性展示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动机状态(McElligott & Hayden,2001;Pitcheretal.,2014),而长时间内雄鹿也可以通过鸣叫质量判断鸣叫者的身体损耗情况(Vannoni & McElligott,2007)。
3.3 社会地位
性选择鸣叫除了体型信息,还能传递其他反映雄性适合度的间接指标信息,雄鹿的社会地位可以由各种声学参数体现(Vannoni & McElligott,2008;Liuetal.,2016)。发声的持续时间也是基因质量的判断指标,时间越长说明遗传质量越优秀,证明其具有更高的交配成功率(McComb,1991)。因此,高等级雄鹿可能在交配前几周就开始发出发情鸣叫,用长期的繁殖投资来确保交配成功(McElligottetal.,1999)。
4 雄性竞争和雌性选择
由于声音包含个体的身体状况、竞争能力、动机和疲劳度等遗传和非遗传信息,基于声音信号的性选择会影响雄性竞争和雌性选择的结果。雄鹿会根据听到的竞争者叫声情况判断加入或放弃竞争(Clutton-Brock & Albon,1979)。雄性竞争者和发情雌性的数量、雄性竞争者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鸣叫者的竞争积极性和性欲(Komersetal.,1997;Naultyetal.,2013)。例如,雄性黇鹿的竞争结果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地位,优势顺位是决定繁殖行为的关键因素,3~5岁个体参与繁殖的次数随社会地位变化而变化(Komersetal.,1997)。雄性黇鹿还可以通过发情鸣叫实时评估竞争者当前的繁殖状态,并马上确定需要采取的竞争策略,例如,早期的发情鸣叫通常具有较高的鸣叫频次,表示竞争者处于较好的繁殖状态,当雄鹿听到高频次的鸣叫回放时,相比低频次的鸣叫回放,会更快进入专注状态,且保持更久的注意力(Pitcheretal.,2014)。雄性麋鹿发情期鸣叫的声学特征,例如共振频率、共振峰的间隔和声音强度都与其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可以作为雄性竞争能力的有效指标(Liuetal.,2016)。
雄性的叫声对雌性的繁殖状态也有影响,雄鹿及其鸣叫的存在能促进雌鹿发情和排卵(McComb,1987;Hosacketal.,1998)。雌性还可以根据声音信号评估雄性的繁殖质量,以此作为选择配偶的依据,从而提高自身的繁殖成功率(Andersson,1994)。例如,鸣叫频次高的雄鹿竞争能力强,等级较高的雄鹿通常具有更高的生存率和繁殖成功率,因此,雌性偏爱鸣叫频次和社会地位较高的雄性(McComb,1991;McElligottetal.,2002)。马鹿发情鸣叫的共振峰频率也可作为性选择的依据,例如,最小共振峰频率受声道长度的限制,当喉头最大限度接近胸骨时,鸣叫声中共振峰频率最小,随着体质量和年龄的增加,其解剖结构限制了喉头的向下运动,从而使得最小共振峰频率可作为判断竞争对手和潜在配偶的依据(Reby & McComb,2003b)。发情鸣叫具有较高基频的雄性也可能具有遗传优势,因此,发情期雌性马鹿还偏爱具有较高基频的雄性鸣叫(Rebyetal.,2010)。
5 声音与识别
5.1 种内识别
鹿科动物的大部分叫声包含足够的声学信息,因此,声音信号的接收者可以通过叫声区别后宫群主和附近的其他雄性、已建立的邻居和闯入的陌生者,或者完成母子识别(Vaňková & Málek,1997;Rebyetal.,1999b,2001)。但不是所有的声音信号都包含足够的身份信息,某些鹿类如马鹿、白尾鹿、黑尾鹿O.hemionus幼仔的叫声就不能被准确识别,母鹿必须要借助近距离接触和嗅觉信号才能成功识别其幼仔(Vaňková & Málek,1997;Lingleetal.,2007a)。
5.2 种间识别
大多数动物能通过鸣叫进行物种识别,并对来自同类的声音信号具有更强烈的反应(Andersson,1994;范艳珠,方光战,2016)。动物对非同类声音信号的低接受度可作为一种合子前生殖隔离机制,但出现杂交现象的雌鹿对同类、杂交个体和非同类异性的发情鸣叫并未表现出严格的同类偏好(Wymanetal.,2011,2014,2016)。对非同类和杂交个体的声音信号具有一定接受度可能会影响雌性的交配偏好,从而加快杂交导致基因渗入(Smithetal.,2014)。
6 研究方法
研究鹿类声音通讯的方法,一类是结合功能解剖学进行研究。例如,发声与雄性马鹿、黇鹿的可移动喉头以及在驯鹿R.tarandus发育过程中出现的腹侧可膨胀喉气囊的关系,就是通过解剖、X光成像、计算机层析分析等方法证实的(Fitch & Reby,2001;Freyetal.,2007)。此外还有通过解剖分析鹿类声带长度、年龄和体质量之间的关系(Reby & McComb,2003a),以及录音分析鹿类声学参数与体质量、年龄等因素之间的关联(Reby & McComb,2003a)。之后又发展出基于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利用模型模拟鹿类声道发声,寻找鸣叫的声学参数与发声器官以及肌肉力量等形态学上的关系(Riedeetal.,2010;Titze & Riede,2010)。
另一类是结合行为学进行研究。例如,先利用录音结合行为观察记录,再用录制好的清晰鸣叫进行回放,根据动物的反应验证鸣声的含义和功能,对某种鹿类的鸣叫进行初步描述性研究。确认某种叫声的含义后,可以对研究对象同时播放同一类型但来自不同个体的声音,探讨发声特点中响度、音高、速率或基频对行为响应的影响,从而判断其声音偏好或者声音识别能力。研究雌性性选择偏好时,可以通过在雌鹿阴道内放置浸满醋酸氟孕酮的海绵,8 d 后再肌肉注射氯前列烯醇,12 d后取出海绵,并肌肉注射马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诱导雌鹿发情和排卵同步化(Rebyetal.,2010;Wymanetal.,2016)。针对雄鹿的发情鸣叫,还可以根据动物不同的社会地位、动机和生理状态比较分析各类声学参数的差异(Pitcheretal.,2014;Liuetal.,2016)。
还有一种方法是结合行为学及系统发育学对鹿类的声音通讯进行研究。例如,将雄鹿的18种发声特点转换为数字矩阵,以此构建鹿科动物的系统发育关系,并比较雄鹿的发声特点与其分子系统发育关系的一致性,结果显示,雄鹿的发声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系统关系(Capetal.,2008)。虽然现阶段采用此种方法进行的研究较少,但是随着各种鹿类行为学和鸣叫基础资料的补充积累,今后此类方法能挖掘出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7 研究展望
虽然关于鹿类声音通讯的研究对其发声机制、声音识别、性选择等内容都做出了阐述,但是诸多环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哺乳动物交流的声音信号受到选择压力(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影响,各种复杂的驱动力,如栖息地的声音环境、种群密度、交流距离等导致鹿类的发情鸣叫在种间差异很大(Titze & Riede,2010),即使亲缘关系很近也不相同,如同为鹿属Cervus的马鹿为低频吼叫(Clutton-Brock & Albon,1979)、加拿大马鹿C.canadensis为类似于军号的高频叫声(Struhsacker,1968)、梅花鹿C.nippon则为呜咽声和嗥叫(Minami & Kawamichi,1992)。还有前面提到的警戒鸣叫也具有一定的种间差异。到底什么因素是鹿类叫声进化的主要驱动力?目前还缺少相应研究。
其次,鹿类的母子声音识别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某些鹿类(如驯鹿)可以仅通过声音完成母子识别(Espmark,1971),而某些雌鹿却无法仅通过声音识别后代,还需借助触觉和嗅觉信号才能完成识别过程,虽然已有研究认为这种声音识别能力的不同是鹿类幼仔声音信号的个体差异导致(Vaňková & Málek,1997;Lingleetal.,2007a),但鹿类幼仔声音差异度的进化选择压力还知之甚少。
最后,同种鹿类在不同的生境、种群密度和食物资源条件下,婚配制度会出现变化。例如,驼鹿Alcesalces在多数情况下是一夫一妻制,但在高种群密度的开阔生境也会集群生活(Geist,1990)。豚鹿Axisporcinus在野外是独居生活(杨德华,马德惠,1965),但是在食物充足的圈养条件下,也可以集群生活。鹿类婚配制度的可塑性是否对其声音行为有影响,这也是今后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