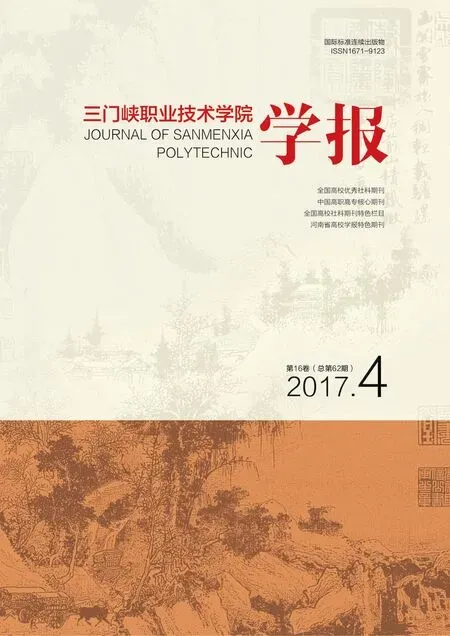略论汉唐灾异认识论之嬗变
2018-01-19◎杨凯
◎杨 凯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汉唐时期,灾异学说是天人感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当时人们把自然或社会中的危害现象都称之为“灾异”。然而实际上,“灾”和“异”分别有不同的含义。董仲舒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1]欧阳修说:“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蝗之类是也。异者,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是已。”[2]由此可知,所谓“灾”是指水灾、旱灾、蝗灾等直接危害人类的自然灾害;所谓“异”,是指当时人眼里反常的事物,包括日食、彗星等违背自然正常秩序,超出人们理解范围的现象。
对于汉唐灾异认识论的研究,古已有之。清代赵翼在《汉儒言灾异》[3]中已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今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灾异学说。如黄肇基《汉代公羊学灾异理论研究》[4]分别对董仲舒、公羊学、何休的灾异学说进行阐述和比较研究。王保顶《汉代灾异观略论》[5]探讨了灾异的实质、功能与意义。桂罗敏《灾异与秩序——<汉书·五行志>研究》[6]认为,《汉书·五行志》是西汉灾异学家为维护社会秩序,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将人事与灾异一一对应,并将其标准化的一个文本。然而学界对于唐代灾异学说的研究还较少,对于汉唐灾异学说的传承与整合的研究更加少见。
笔者认为,汉唐灾异认识论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灾异与人事的联系渐渐弱化;祈禳措施被淡化,官方转而寻求更务实的减灾措施;唐代灾异学说受到外来宗教的挑战,其地位和汉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一、从天人相感到阴阳常理:灾异与人事的联系逐渐弱化
《汉书·五行志》是最早对先秦两汉灾异现象系统总结的正史资料。这份史料不仅是对该时期灾异解说的集结和汇总,更是将灾异与人事分别纳入阴阳五行结构,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形成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灾异学说体系。理论上,两唐书《五行志》基本继承了这种灾异学说体系。其大致结构可以归纳为以下表。

两唐书《五行志》灾异学说体系表
《汉书·五行志》基本上严格按照这个灾异学说体系来解释灾异现象。如记载春秋鲁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刘歆以为上阳施不下通,下阳施不下达,故雨,而木为之冰,雾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以为冰者阴之胜而水滞者也,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7]这个推演过程大概可以概括为“木——木不曲直——恒雨——极阴——大臣受迫害”,可见其中灾异—人事对应关系是十分明确的。仅在《汉书·五行志》中,类似的灾异记录及解释有四百多条,可见当时人们将灾异与人事联系得何等紧密。
然而在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灾异与人事的对应关系逐渐开始弱化。如贞观十一年(637)洛阳发生水灾,唐太宗要求群臣极言直谏。中书侍郎岑文本上书说:“水之为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8]所谓“阴阳常理”,可以理解为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将水灾的成因归纳为自然规律而非人事使然,并且否定水灾是天谴,这本身就是灾异—人事对应关系弱化的表现。永徽四年(653),同州冯翊县有陨石坠落,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少师于志宁认为:“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自为之,未必关于人事。”[8]开成四年(839)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上忧于形色。宰臣曰:‘星官奏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8]此则史料中宰臣所说的“天时当尔”,与于志宁所说的“物自为之”,类似于岑文本“阴阳常理”的解释,都强调了灾异发生的客观必然性,而割裂了灾异与人事的联系。又如,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火,延及天堂,京城光照如昼,至曙并为灰烬。则天欲避殿撤乐,宰相姚璹以为火因麻主,人户不谨,非天灾也,不宜贬损。”[8]虽说“人护不谨”也可以说是人的因素,但实际上是把君主的责任推卸给他人,强调火灾并非“天灾”,君主不必自责,从而脱离了天人感应的窠臼。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衹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3]唐代当然属于“自汉以后”的范畴,但若将“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的结论置于唐代,尚觉过于绝对化。实际上,翻阅唐史史料时,还是可以发现很多证明灾异—人事对应关系存在的例子。只是相对于汉代而言,这种对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弱化,而为更加多元的灾异解释方法所代替。不可否认的是,唐人基本继承了汉代的天人感应学说,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有所保留和修正。
二、应对灾异:祈禳措施被淡化,官方采取务实的减灾措施
有证据证明,汉代君主对待灾异十分敏感。当灾异发生时,他们总会颁发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答天谴,并且采取一系列祈禳措施。据学者统计,汉代君主因灾异而颁发罪己诏达40次以上[5],采取的祈禳措施包括:大赦、进贤、求谏、赐爵、赐帛、禁杀奴婢、释放后宫、弛苑囿之禁、致祭宗庙、削减宫廷用度、禁卖酒等等。如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诏:“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贤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9]又如顺帝时“灾异屡作”,公车征郎凯上疏:“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是以灾害屡臻,四国未宁……若欲除昭祉,顺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9]又如桓帝建和三年(119)九月日食出现,诏“郡国不得卖酒。”[9]
汉代在应对灾异时所采取的祈禳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有安稳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对于大规模的破坏严重的自然灾害而言,很难说这些措施有什么实际的减灾作用。祈禳措施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对不可知的自然之力的敬畏,一方面又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失序所预兆的社会失序的惊恐。然而到了唐代,随着人们对灾异的认识进一步发展,这种恐慌情绪逐渐被理性所代替。因此祈禳措施渐渐被淡化,官方转而寻求更加务实有效的减灾措施。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七月,天降大雨,洛水暴涨,有人建议中宗关闭坊市北门以祈晴,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今暂逢霖雨,即闭坊门,弃先圣之明训,遵后来之浅术,时偶中之,安足神耶?……岂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神灵;暂闭暂开,便欲发挥神道。必不然矣,何其缪哉!至今巷议街言,共呼坊门为宰相,谓能节宣风雨,变理阴阳。夫如是,则赫然师尹,便为虚设;悠悠苍生,复所何望?”[8]其后,八月戊申,诏:“河南洛阳百姓被水兼损者给复一年。”[8]在灾异学说体系中,五行中的“水”对应方位中的“北方”,在水灾发生时闭坊市北门本来是常见的祈禳措施。然而官方对此弃而不用,只是免除受灾区域一年的赋税徭役,以缓解灾情的影响。
开元四年(716)五月,“山东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既除不得,为害滋深。’宰相姚崇报之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卒行埋瘗之法,获蝗十四万投之汴河。”[8]姚崇驳斥倪若水的“蝗是天灾,自宜修德”之说,积极组织捕蝗,有效控制了灾情的发展,百姓受益。这足以表明,唐代时灾异学说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开始被打破,一些开明的士大夫采取巧妙的方法化解传统思维习惯的藩篱,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应对自然灾害。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关中发生旱灾和蝗灾,诏:“自顷以来,灾沴仍集,雨泽不降,绵历三时,虫蝗继臻,弥互千里……遍祈百神,曾不获应,方悟祷祠非救灾之术,言辞非谢谴之诚……除诸军将士外,应食粮人诸色用度,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罢,以救荒凶。”[8]官方以诏书形式直言祈禳措施的失效,并且明确指出祈禳并非救灾之术,态度可谓鲜明。与其寻求神灵的庇佑,倒不如节省财政开支,以赈济灾民。既然在应对灾异时,相对于汉代而言,唐代更加注重救灾减灾措施,而非祈禳。那么,唐代的自然灾害救济是否真的切实有效呢?对此,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如潘孝伟认为,唐代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减灾行政管理体制,他在《唐代减灾和当时政治经济之关系》[10]中指出,唐代的灾荒救济措施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毛阳光在《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11]中认为,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基本都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灾害救济中去,并且能够取得良好的实效。笔者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唐人应对灾异的观念发生变化。曾经存在的许多祈禳措施可能反而会拖慢救灾的进程,于是被逐渐忽略,被更加务实有效的减灾救灾措施取代。唐人对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客观,灾异认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受到来自佛教的挑战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便屡次被君主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同样地,本土的阴阳五行灾异学说虽然一方面限制了君主行为,但另一方面又为君主神化自己的权力提供了依据。这两种学说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很可能有冲突对立的方面。在这时,统治者对二者的抉择,往往对两种学说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垂拱二年(686),“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则天以为休征,名为庆山。荆州人俞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隔,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诚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灾祸至。’则天怒,流于岭南。”[8]俞文俊根据阴阳五行灾异学说解释地震“山踊出”的现象,认为这是对女主居位的天谴,结果被流放。这说明在唐代,灾异学说对君主的约束往往有失效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同样是对于地震现象,灾异学说认为这是以下犯上、阴胜阳的灾异,而佛教却将其认定为祥瑞,是佛法无边,众心虔诚的表现。如天宝十三载(754),密宗大师不空在开元寺主持佛教仪式,“是日道场地震,空曰:‘群心之至也。’”[12]又如,圣历二年(699)十月,武则天请高僧法藏在佛授记寺讲解《华严经》,当时洛阳地震,而当时的记载是,“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13]
当阴阳五行灾异学说与佛教学说发生矛盾的时候,武则天经过权衡,终于决定选择后者。载初元年(690),万年县霸陵乡又有山踊出。官方立刻将其认定为佛教圣山——衹阇山。张说《为留守作贺崛山表》云:“万年县新出庆山醴泉,乃有天竺真僧于春首献状,若以梵音所记,此是衹阇山。”[13]
联系前文所引的史料,武则天当政的垂拱二年(686)和载初元年(690)分别发生了两次“山踊出”的现象,第一次在新丰县,第二次在万年县。武则天先是运用阴阳五行灾异学说来解释新丰县的“山踊出”现象,根据山周围出现的“龙凤之形,禾麦之异”的池子,将其认定为祥瑞,命名为“庆山”,结果遭到臣僚的反对,武则天面临“阴胜阳”“女主擅政”的政治舆论压力。其后,万年县再次发生“山踊出”现象,武则天吸取上次的教训,改用佛教学说来解释,将此山认定为佛教圣山“衹阇山”,以作为其德政的表征,巧妙地化解了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带来的舆论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恰好在武则天革唐为周、登基称帝后不久,其借助佛教进行政治宣传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如学者孙英刚所言,“佛教的传入不但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也为统治者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工具。一些过去被视为上天对君主统治进行警戒的‘灾异’,在佛教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中,被去灾异化,甚至转化为表彰统治者的祥瑞。”[14]这一方面说明,君主在强化中央权力时,自主选择有利于自身的学说来解释灾异现象;另一方面又证明,在某些时候,传统的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已经不能适应君主强化自身权力的需要,有时反而陷君主于不利的舆论环境,自然容易遭到废弃甚至排斥。新的外来学说体系如佛教学说体系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灾异解释方式,而且很可能更迎合君主集权的需要,于是更受君主的青睐。由于官方的态度转变,阴阳五行灾异学说的发展遭遇曲折。
四、结论
大致勾勒阴阳五行灾异学说的发展脉络,其源头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鼎盛阶段则在两汉时期。自汉代至唐代,阴阳五行灾异学说的内部结构渐渐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处的地位也也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人事—灾异的对应关系逐渐弱化。汉代形成的体系化、结构化、类型化的阴阳五行灾异学说一定程度上被唐人分解,并且在运用时掺入时人的解释,如“天时当尔”“物自为之”“阴阳常理”云云,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导致阴阳五行灾异学说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异。其次,两汉以来,依据阴阳五行灾异学说所采取的种种祈禳措施部分遭到忽略甚至废弃,官方转而寻求更加务实有效的救灾减灾方案。那些致力于沟通天人、自省修德的祈禳措施,有时反而会对救灾减灾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而在唐人的灾异应对方案中逐渐被淡化。第三,本土的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受到外来宗教学说的严重挑战。武周时期对两次“山踊出”现象的不同解释即是支持此论点的明证。为了强化自身权力,武周政权前后分别采取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和佛教学说来解释两次“山踊出”现象,结果前者遭遇失败,后者获得成功。阴阳五行灾异学说不仅没有帮助武则天实现原初设想的的神化权力的目的,反而使其陷入“女主居阳位”不利的政治舆论环境。而佛教学说巧妙地化解了来自灾异学说的压力,自然为武周政权采用和大力宣扬。
简言之,到了唐代,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依然存在,只是相较于汉代而言,影响程度减弱,影响范围缩小,影响过程中还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最后,笔者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对汉唐时期的灾异认识论进行比较,但极力避免线性的历史发展逻辑,并不认为灾异认识论的发展遵循从低级到高级的简单直线轨迹。本文揭示灾异认识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但并不由此对汉唐时期的文化形态进行价值判断。笔者认为,须将灾异认识论的发展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须充分考虑历史背景因素的影响,以及灾异认识论发展所遵循的内在逻辑。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对这一问题获得一个比较客观清晰的认识。
[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M]王权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黄肇基.汉代公羊学灾异理论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
[5]王保顶.汉代灾异观略论[J].学术月刊,1997(5):104-108.
[6]桂罗敏.灾异与秩序:<汉书·五行志>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2.
[7]班固.汉书:卷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刘昫.旧唐书:卷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范晔.后汉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潘孝伟.唐代减灾与当时政治经济之关系[J].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4):19-24.
[11]毛阳光.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1):53-64.
[12]赞宁.宋高僧传:卷一[M].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董诰等.全唐文: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孙英刚.佛教对阴阳灾异说的化解:以地震与武周革命为中心[J].史林,2013(6):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