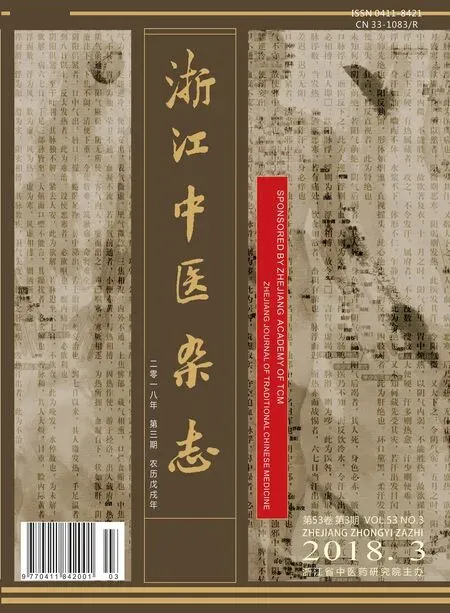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肠道菌群与中医学相关性研究进展
2018-01-19官彗婧阎小燕
官彗婧阎小燕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而无器质性病变的功能性肠病,临床大多患者伴抑郁或焦虑症状[1]。该病根据临床症状分为腹泻型、便秘型、腹泻便秘交替型、未分型四型[2]。我国IBS发病率约为15.9%,其中以腹泻型为主[1]。近年来,肠道微生态变化在该病中的地位日益引起重视,许多研究[3-5]结果表明,与健康人相比,腹泻型IBS(IBS-D)患者粪便中非优势菌的数量增多,而乳酸杆菌属及双歧杆菌属等优势菌数量减少。肠道菌群通过肠-脑轴的3条途径(免疫、神经内分泌和迷走神经途径)形成肠道菌群-肠-脑轴,影响人体信号分子的合成,以及神经递质的浓度,从而影响人体神经兴奋性及神经元传导速度,以此调控肠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活动[6-8]。
1 病因病机
中医学根据IBS-D主症,将其归之于“泄泻”“腹痛”等范畴,多见大便稀溏,腹痛即泻,泻后痛减,常因情绪紧张或忧伤而发生或加重。本病病位在肠腑,但与肝、脾、胃、肾密切相关,主要病因病机乃为感受外邪、饮食不节、情志失畅、病后体虚、先天不足等导致脾失健运或脾虚湿盛,升降失调,大小肠传化失常,清浊不分,而成泄泻。可分为肝郁脾虚证、脾虚湿阻证、脾胃湿热证、脾肾阳虚证[9]。亚洲人群IBS-D患者大多存在排便不爽之感[1],乃因脾虚无以化湿,湿性重浊粘滞,留恋大肠所致。IBS-D患者泄泻多伴随腹痛[1],《医方考》言:“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肝责之实,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肝气横逆犯脾,运化失常,气机郁结,故腹痛则泻;便后气机得畅,则泻后腹痛暂缓。可见本病主要责之于肝脾二脏。
2 中医学与微生态学
2.1 中医藏象学说与微生态学的相关性: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微生态学尽管理论产生时间相距甚远,但研究发现二者理论存在惊人相似之处,其中微生态学与中医藏象学说渊源颇深。
中医学认为该病病位主在大肠,大肠有传化糟粕和主津之功。大肠正常生理功能仰赖于气机调畅使传导有力,津液充足使润燥有功。而大肠气机的调畅及津液的输布又依赖于胃之通降、肺之肃降、脾之运化、肾之蒸化和固摄,而其关键在于气机升降枢纽——脾胃。现代研究认为肠道微生态与中医学脾胃关系密切。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统血,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而其功能之根本乃“主运化”,现代医学认为肠道菌群不仅具有对饮食分解和吸收的作用,亦可随着因饮食而改变的肠道微环境进行自身适应性调节,从而激发机体的调控机制,促进机体对营养成分的利用[10]。
中医学认为情志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研究[11]证实IBS中医证型与抑郁、焦虑等因素具有独特的关系。其中肝主疏泄的功能使之多与情志病相关,微生物学角度的“肠道菌群-肠-脑轴”及“菌心说”恰与上述中医学观点相对应。可见IBS-D中医发病机制与现代医学肠道菌群学说机理不谋而合。
2.2 IBS-D中医辨证分型的肠道菌群特点:不同IBS-D中医辨证分型的肠道菌群特点亦有差别,目前仅有对于脾胃湿热证与脾气虚证的初步研究[12]:与正常人群相比,脾胃湿热证患者革兰阳性杆菌比例明显下降,而革兰阴性杆菌及革兰阳性球菌比例明显上升;肠道菌群密集度及肠道菌群多样性无明显差异。脾气虚证患者与湿热证患者革兰阳性杆菌相比,比例明显升高;湿热证患者肠道菌群密集度明显高于脾气虚证;两者的菌群多样性无明显差异。
3 中医药治疗的影响
关于中医药治疗IBS-D的研究众多,但大多为对其临床疗效的观察报道,极少有深入到对患者症状改善机理的研究。对疗效机理的研究中又有部分以免疫细胞及因子、胃肠激素、脑肠肽受体等为靶点,涉及到肠道菌群的研究极少。
IBS-D脾虚证患者治疗后酵母菌明显下降,与正常人群无异,双歧杆菌、乳杆菌、拟杆菌、消化球菌明显上升,但仍明显低于正常组[13]。IBS-D脾胃湿热证患者治疗后肠道革兰阳性杆菌、双歧杆菌、乳杆菌、消化球菌明显上升;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阳性球菌、肠杆菌、肠球菌明显下降,肠道菌群密集度无明显上升,肠道菌群多样性无明显改变[13]。关于IBS-D肝郁脾虚证的研究,采用痛泻要方加米雅BM治疗后,肠道菌群中双歧杆菌、乳酸菌量上升,大肠杆菌和肠球菌量下降[14]。罗文佑[15]用痛泻要方加减治疗后,或因临床样本量采集较少,虽然数据显示治疗后双歧杆菌有上升趋势,大肠杆菌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但并无统计学意义。
此外,防风归肝脾膀胱经,具祛湿止痛之功,可升散脾之清阳,研究证明其水煎液[16]亦可调节肠道菌群,改善IBS-D临床症状。神曲归脾胃经,有消食和胃之功,研究表明水煎液治疗后,患者粪便中乳杆菌明显增多,双歧杆菌增加,肠杆菌减少[17]。
4 结语
目前IBS-D发病率较高,且发病几率逐年增长,其中以肝郁脾虚证最为高发[18]。本病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本病病因的未明确性使本病病机及治疗的研究迫在眉睫。中医药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疗效日渐明显的优势,使得中医学对于本病病因病机及其治疗疗效的机理的研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学者们对肠道菌群对于人体各系统、组织、器官影响及其机理的研究日渐深入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以肠道菌群为基础的人体免疫、神经、激素的调节网的理论,也使得肠道菌群的深入研讨成为趋势。对于中药治疗该病疗效与肠道菌群的相关性,现代医家少有研究。因此,我们应结合趋势与优势,继续深入探讨:中药治疗IBS-D疗效显著,是否因其对肠道菌群具有一定影响;IBS-D各中医辨证分型是否存在肠道菌群的差异;中药治疗后,肠道中哪些菌群的变化致使患者症状的改善;肠道菌群改变致使患者症状改善的机理又是如何等等;都值得大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以上深入研究不仅可为中医药治疗本病疗效的靶点所在提供有效证据,而且也为中医药治疗本病疗效的优势提供有力依据。
[1]Quigley EM,Fried M,Gwee KA,et al.World Gastroenterology Organisation Global Guideline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A Global Perspective Update September2015[J].Journal of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2016,50(9):704.
[2]Rome Committee.Rome Ⅲ criteria[J].Gastroenterology,2006,141(130):1459.
[3]李小萍,王巧民,褚源,等.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目标菌群的分析[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14,49(5):653-658.
[4]Carroll IM,Ringel-kulka T,siddle JP,et al.Alterations in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J].Neurogastroenterol Motil,2012,24(6):521-530,e248.
[5]李刚平.中国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菌群的特点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
[6]Cryan JF,Dinan TG.Mind-altering microorganisms:The impact of the gut microbiota on brain and behaviour[J].Nat Rev Neurosci,2012,13(12):701-712.
[7]Hsiao EY,McBride SW,Hsien S,et al.Microbiota modulate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neuro developmental disorders[J].Cell,2013,155(7):1451-1463.
[8]Mayer EA,Savidge T,Shulman RJ.Brain-gut microbiome interactions and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J].Gastroen-terology,2014,146(6):1500-1512.
[9]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诊疗共识意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7):795-796.
[10]王欢,曾奥,曹蓉,等.七味白术散调节肠道微生态的物质基础[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14,22(13):1773-1777.
[11]赵黎君,刘庆生.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证型与心理因素的研究[J].浙江中医杂志,2012,47(7):475-477.
[12]江月斐,劳绍贤,邝枣园,等.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脾胃湿热证与脾气虚证肠道微生态初步研究[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05,15(2):1-3.
[13]江月斐,劳绍贤,邝枣园,等.加味苓桂术甘汤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肠道菌群的影响[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06,16(6):7-9.
[14]孙旭,蔡淦,王文健.肠易激综合征中西医结合治疗前后肠道菌群状况观察[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4,2(5):340-342.
[15]罗文佑.痛泻要方加减治疗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肠道微生态的影响[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0.
[16]齐绍云,蔡洁毅,周龙艳,等.防风对PI-IBS模型大鼠肠道菌群及丝氨酸蛋白酶信号的影响[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15,26(6):790-796.
[17]庄彦华,杨春辉,杨旭东,等.中药“神曲”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菌群的调节和临床疗效的研究[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05,17(1):41-43.
[18]刘康毅.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证候规律及临床特征调查[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