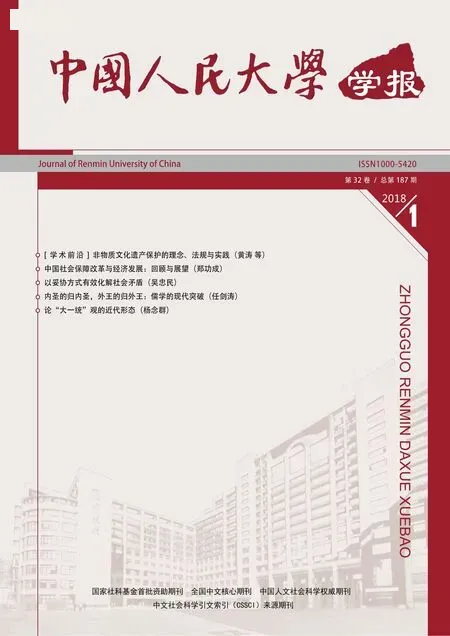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中“私”的观念类型
2018-01-19闫润鱼
赵 竞 闫润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私”观念一直是思想家们用以评判道德伦理和实际政治的一把标尺,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它有过相对独特的设想或建构,致使其本身成了一个庞大的观念丛。因此,想要获得关于“公”“私”的较为完整的观念图像,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类型的概括和分析。由于“公”不仅相对于“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而且以其符合天道或天理的价值而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这就使研究者们大多将关注的笔墨聚集在了“公”上,而“私”则在不经意间成为被悬置的对象。其实,若缺少对由“己”生发的“私”的类型进行学理上的区分和辨析,就很难真正理解“公”“私”对举的不同语境和内涵。
一、关涉“利”/“欲”之“私”
尽管“公”“私”概念很早就被人们对举使用,但它们的各自出现则有早有晚,相对于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的“公”而言,“私”的出现要晚些。“私”最初表达的含义大多与“己”相关,除了与“己”有着血亲关系的私亲之人外,还表示“己”之情感和欲求,诸如私欲、私情、偏私等。这些由“己”而生发的“私”,都属于实然层面的表述,内中并不包含抽象的价值含义。*刘泽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战国以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公”“私”的所指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原本相对于周王室是“私”的诸侯国、相对于诸侯国是“私”的大夫之家,在战乱或冲突中,不时会上演由“私”变“公”的反转剧。与这个过程相伴,人们对由“己”生发的“私”也开始发生观念和态度上的变化,私人欲求和利益开始受到关注。比如,人们对“私”田的重视,竟会导致“公田不治”现象的出现。
儒学创始人都肯定人们逐利行为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基于这种判断,孔子劝告统治者应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则强调保护私利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理由就是“民有恒产然后有恒心”。孔孟虽然寡言“公”“私”,但他们对人之“欲”、民之“利”、民之“产”的讨论,已经赋予私利、私欲以合理性,这也为后世学者援引原始儒家为“私”正名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孔孟关注的“私”是一种实然的存在,他们在意的是如何在国之利益与百姓利益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度,内中并不包含与“正”“义”有多少关联的价值倾向。例如孟子认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虽然民之私产被“制”所规范,但“制民之产”的目的则很直接,那就是要满足民的基本生存需求。
法家也没有赋予私利以价值上的内涵,在他们的相关议论中,“私”只关涉个体利欲,“公”则表示由国家和国法所代表的整体性利益。“民之欲富贵也,其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在他们看来,个体对利欲的追求不仅是与生俱来的禀赋,也是可以为君主和国家所利用来实现其统治霸业的。管子提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子·国蓄》)商鞅也提出了“利出一孔”(《商君书·壹言》)的耕战体制,认为君主只要鼓励民专心务农,就既可满足其在官职和爵位方面的欲求,也可使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私利、私欲虽然由“己”生发,但它们却并非一定与“公”处于对立地位而被认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贬抑,与“公”对立的只是违背国家和法律的那部分“私”。
在先秦思想家中,荀子所论的“私”具有比较鲜明的价值倾向。比如,他对春秋末期“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吕氏春秋·举难》)现象的针砭,就为“私”打上了狞邪、违背天道和礼乐的不良特性。除此之外,荀子还直接将私利与公义对立起来,认为“明分职,序事业……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公”与“私”不是用来指称某种实然状态的存在,而是与“道”和“邪”关联在一起,强调的是“以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的合道义性。
二程和朱熹延续了荀子将公私与义利、道义相联系的论说,并进一步将天理人欲引入公私义利之辨。朱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理有气,并且理先于气,“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熹:《朱子语类》卷一,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物在形成之时,就有“形气之私”,“私”代表了万物之间存在的差异。程朱还将性理与善恶相联系,认为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就是“天理”,这种需求是所有人都同一的,“公则一,私则万殊”*程颐、程颢:《二程集》,14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因此,天理就是“善”,也是最大的“公”,而超越基本需求之外的人欲,则是“私”,也是“恶”。既然万物只有一个理,那么人顺应天理就自然是“大公”“无我”。假如不是出于“无我”的“公心”,那么,即使所做事情的结果符合了“公利”,也还是“私”。在《四书集注》中,朱子曾言:“私,谓燕居独处,非进见请问之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他对“私”的这种判断与传统经学有所不同,朱子真正关注的是个体在内心深处或心念发动之际是否体悟到“仁义”的意蕴所在。如此一来,不仅由“己”之个体生发出来的欲求,甚至个体的内心活动和动机也都成为必须要加以规范的对象。显然,程朱是将由己生发的私欲、私利做了不同面相的区隔:一是满足基本生存欲求、符合天理之公的“私”;一是越出基本生存之外必须“去”的“私”。
宋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商思想的变化,事功和私利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对象,以至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功利思潮。崇尚功利的人们并没有否定天理,也没有将人的动机和欲求分为不同层次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将追求私利、谋利都看作是人情之自然,并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解释私利对于国富民生的重要性。比如李觏认为:“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李觏:《李觏集》,3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叶适批评理学家津津乐道的“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是“全疏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陈亮进而从功利的角度肯定汉高祖、唐太宗“禁暴戢乱,爱人利物”*陈亮:《陈亮集》,卷二十八,27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的功业,认为功利心并不妨碍道义的实现。事功学派虽然未像程朱等人那样通过哲学思辨的方式去论证“私”的正当与否,却也承袭了孟子“民有恒产然后有恒心”的思想,最大限度地赋予了私利、私欲以合理性。
晚明以来,为“私”的正名首先从承认人有自私之心开始。李贽将“私”作为人的动机来解释其与为学、为圣之间的关系,他分别举治田、治家和治学为例来说明“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李贽:《藏书》,5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陈确同样从经验角度解释人的自私之心与有为、成圣之间自然且符合天理的关系,即古人成贤成圣的结果也是由其最初的私欲、私念所推动的。与宋儒多以有意为之亦是“私”的看法不同,陈确认为:“彼古之所谓仁圣贤人者皆从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极者也。而可曰君子必无私乎哉!”*陈确:《陈确集》,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即使是圣贤,在其行动之际也是由“私”之心念所发动的,那种绝对无私的“公”、离欲而言的理是不存在的。除了功利的解释之外,王夫之还从理欲一元的角度去论证“私”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人的私欲也是“大公之理之所凝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418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礼和天理“必寓于人欲可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91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从而将私欲纳入天理之中。从事功学派到明清学人,欲望不断地从个体的情欲、私心扩展到“财货”“富贵”等涉及生存欲、物质欲、所有欲的层面,天理不断地将人欲吸纳进自身,“私”也不断地被解释为“公”。如果说宋学是努力使个体克服私意而成圣的话,那么晚明李贽等人更加关注的则是个体在生存层面所拥有的原初欲求和动力。
在先秦诸子的论说中,私利作为基本的生存欲求一直是被肯定的。但随着战国以来“公”“私”之间冲突的不断加剧,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成为学人们的普遍关切。在理学家那里,虽然民之私利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具有合理性,但作为个体的“己”、己之内心的“私”,却被纳入了天理人欲的义利公私之辨中,成为被“去”的对象。经由功利学派为“私”的正名努力,“私”不仅重新回到原始儒家对“己”之“利”与“欲”的认可上,还进而扩展了与“权利”/“权力”相关的新界域。
二、关涉“权利”/“权力”之“私”
私利、私欲由“己”生发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他人或“公”毫无关联。实际上,这种欲求一旦产生并通过个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就不再是只关涉个体的“私”,换言之,它已然进到了与所有或占有相关的“公”领域。当然,这个意义上的“公”,并非那种内涵了天道的“公”,而是指由多数的“共”所形成的相对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例如“公室”、“公田”等。《诗·大雅·大田》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里的“公田”,是指井田里的中区部分,耕作由大家共同承担,收成上缴王室,“私”则表示井田里的收成归耕种者所有的部分。而在《周礼·大司马》的有关议论中,“公”“私”也与占有权相关。所谓“大兽公之,小禽私之”的“公”“私”,表示的就是处理涉及“共”的事务时,什么规格的东西必须交给部落由全体共享、什么可以留归家庭或个人由私人占有。
法家鲜有对“公”“私”的价值评说,在他们那里,不论是官是民,都必须要以国家的法度与利益为依归,要“以吏为师”。不过,由于“公”是官府处理公共事务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本义就在于“背私”,所以“公”与“私”是呈决然对立状的。“公”之外的所有存在都是“私”,且都有可能妨害到“公”,包括博学和孝亲之类也不能外。*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虽然法家并未将己之私利看作是邪恶的存在,但却通过无处不在的“公私对立”,将个体权利几乎抹杀殆尽。民虽然可以追求个体私利,但国法除了奖励耕战之外,并没有为其提供获得的保障途径。
伴随着“公”与“私”逐步发展成为一对规范性概念的过程展开,它们的所指也由占有关系扩展到了处理公共事务和君王治理天下应秉持的原则问题。由于“公”表示君王、官府、朝廷以及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务,所以像《曲礼》中所说的“公事不私议”这种看似描述性的、用于指称各自所属领域的所谓“公事”“私议”,却因“公事”涉及多数的“共”而拥有了至上性。“私不议公”,表明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必须奉行公私分明、私不害公的原则。既然“公”获得如此的价值内涵,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私”,便由最初表示领域的概念,无形中被赋予了与“偏”“邪”等相连的价值含义。
实然层面的“公”通过与道、义相联系而获得了超越性的抽象价值。作为与这种意义上的“公”相对的“私”,则多指效法天道的“无私”。诚如子夏问何谓“三无私”时孔子所答:“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效仿天道的“无私”有两个方面:一是“生民”,即保障民的私利;二是“均”,使民利共享。就“生民”这一目的来说,有一个自然的、以生民为目的“天之公”。由于“公”实际上由君王、官府代表着,那么,治理天下假如名实不符,做不到“生民”,满足不了民的生存权利,就要被判为偏私。同样,做不到均平共享,也将被视为“私”。只有在民的占有问题上很好地体现了“无私”原则,那才是“公”。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道家和墨家的议论中。《庄子·大宗师》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希望统治者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不要背离天地的无私之德。墨子也强调:“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法仪》)总之,经过先秦诸子的论说,“天”统一了“三无私”,成为“公”的化身。
晚明以来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也谈天无偏私的话题,但他们的目的则偏重于为“私”的生存权和私有权进行辩护。他们强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王的一家一姓之“私”,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重于万民之“私”。君王专权既是一家一姓之“私”,也是对“天之公”原则的背离。而万民之私,不论是作为“天之公”的目的,还是能体现“共”的价值,都享有至上的正当性,都是理所当然的“公”。与朱子所谓“万物各得其所”、“君臣父子各得其宜”的分配观不同,顾、黄等人更属意于不受礼分制约的占有关系,“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一,2、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视不均为“私”。通过颠倒君民在公私关系上的承载地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将宋明以来天理之公的道德哲学问题转换为关注万民之私的社会性权利问题,并就此埋下了否定君主专制之私的权力问题引线。*例如,梁启超认为:“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梁启超卷》,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又如,何启等人认为:“合人人之私以为私,于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各得其私者,不得复以私名之也,谓之公焉可也”。参见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41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清中后期,魏源所论的“公”“私”就直接与政治参与勾连起来。不同于晚明学人,魏源并不认为上古三代在用人上能很好地体现“公”的价值,因为“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贵袭,贱以贱袭,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这种独享政治当然是“私”。而后代的选官制度,随着世官向贡举的改变,使文化精英获得了“学而优则仕”的参政机会,这种政治情形方可称得上“公”。基于“三代私而后代公”*的评判,以及士大夫群体因忌惮明末党祸之争而普遍将结党看作偏私的现状,魏源认为“心有公私,迹无胡越”*,强调文人精英应当保持内心的公私界限,不要因官务阴暗而泯灭,并且以“皇皇者华,周爰咨诹”(《诗经·皇皇者华》)为例讨论了政治生活的合法边界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君王既要广泛征询“庶民之首”(即社会政治精英们)的上书建言,以促成“公议无不上达,斯私议息”风气的形成,也要给予百工、庶人以进言权,效法“古圣人听言”的态度,“不问其疏近,并不问其公私,而惟其理之是非”*魏源:《魏源集》,60、61、36、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以有效克服政治参与上的偏“私”之弊。
由于面对的政治情境有所不同,魏源在三代官制究竟是“公”还是“私”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同于晚明学人的评价,并为后世不拘泥于三代而重在根据时势变化来进行公私评价开了先河。实际上,魏源依然延续了明末清初思想家对如何优化政治过程的思考。比如,倡导“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顾炎武,虽然主张实行在魏源看来是“私”的世官之制,但他关注的则是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希望通过扩大地方守令之权,以实现君臣共治天下的“公”。
同样,冯桂芬也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将君王与民众上下相隔看作是“私”:“《尧典》曰‘师锡’,师者众也。《礼》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者,亦众词也。”*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冯桂芬卷》,2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显然,冯桂芬将“公”等同于“众”“共”,公论、公举的合法性来源于“众”所代表的多数。能够集合民众的意愿、能够根据众人的意见选贤、能够与众人共同议政的通上下情之“公”,是魏源、冯桂芬等人理想的政治形态。同时,郑观应还将用人上的“公”“私”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认为君民隔阂之私必然导致“权分力弱”,无法巩固民心,抵御外侮,从而提出效法三代乡举里选和泰西投票公举的方式,通过选出能够代表民众意愿的贤者,“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任智勇、戴圆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郑观应卷》,8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来实现上下交泰,君民一心,从而强民力、张国威。
虽然无论是顾炎武、黄宗羲还是魏源,他们对“公”“私”的诠释都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这一核心问题,但其论说已经掀开了将“公”“私”置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中进行思考的新篇章。
三、关涉“私亲”/“公法”之“私”
由“己”生发的“私”,不仅因其关涉占有或如何占有的问题而归属“权利”/“权力”范畴,更因与血缘亲疏远近有关而与伦理相涉。传统中国的基本生活空间和领域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宗族。正因为如此,先秦诸子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说大都以孝亲为开端,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表明此点。
在“亲亲”“仁民”“爱物”的展开过程中,所谓“公”与“私”,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存在。以“家”为例,相对于国与朝廷,它是“私”;相对于大的宗族来说,它还是“私”;但相对于“己”之个体而言,则成为“公”。诸如“父母存,不有私财”(《礼记·曲礼》)、“子妇无私货、无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礼记·内则》)等说法就表明,父母与子女相对,父母是公,子女为“私”,有父母在,子女就不应该保留私人财产。家庭间的这种“公”“私”关系,除由财产占有的实态体现外,还因对远近亲疏不同的人抱持不同的情感而有所区分。《仪礼·丧服传》称:“昆弟之义无分焉,而有分者则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在这里,父子情、兄弟情都是顺乎自然之情,因此可以被视为“公”。不过,后来程颐对哥哥的生病儿子与对自己的生病儿子给予不同牵挂所做的解读,则揭示出伦理之“私”实际上存有情感上的等差:第五伦对自己儿子的牵挂是发乎自然之情,因而是“公”;而对哥哥的儿子,即使一夜探望十次,也是一种刻意的大公无私,其行为不及牵挂儿子那样出于本心自然,所以还是“私”。当然,对超出小家庭之外的宗族和乡里的关注,所谓“公”“私”又有另一番论说。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统治者为了禁止结党营私,是特别反对士大夫结群的,但仔细观察则可发现,对于以私亲为基础的宗族间的团体行为,则不仅不予禁止,相反还给予鼓励。官方通常认可宗族内部的一些规则和习俗,并将其纳入帝国治理的范畴之中。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如何处理以私亲为基础的家庭宗族伦理与国家法律教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由“己”之“私”扩展到家之“公”,是家庭成员间亲亲的内在要求。而君臣、君民之间的公私关系,则是尊尊与教化的体现。私亲与政教绝非谁一定要先于谁的关系,含有这两层关系的“公”“私”结构,实质上是立体的而非“差序格局”式的。
“孝”的伦理和道德来源是血缘私亲以及由此生发的情感关系,但人们对此所做的不同解释却影响到不同时期的政教法律和风俗变化。“亲亲相隐”这个恒久不衰的论题,涉及公法与亲私的关系问题,即国家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干涉私人生活。传统公私观念在这一问题上并非采取“一刀切”式的处理方式。以《论语》中孔子回答“子为父隐”问题为例,叶公对孔子说: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里,叶公和孔子对于什么是“直”的理解显然大为不同。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之间的亲“私”情感是“直”,也是符合礼的规范的,因此,也就不能被视为以私情妨害公法。而叶公则认为只有“子证”其父之过才算得上“直”。面对亲私与公法的冲突,孔子虽然优先考虑了前者,但也并不意味着他肆意放大了私亲的边界或无视法律和公权的存在。同样,注重后者的叶公也并非于私亲不顾。实际上,这里关涉的是“齐之以礼”与“齐之以刑”在尺度上的把握问题。源自私亲之情的孝亲伦理,作为维系传统社会人伦和礼法秩序的基础,与公法和公权力之间并非是对抗和不容的关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只有在“礼”有所不化的地方才适于“刑”之。在儒家的议论中,大体而言,在不涉及家庭之外的领域、不涉及家庭之外的人时,主张以私亲为大;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即涉及家庭以外的公领域时,则主张以公义灭私亲。*陈乔见:《公私辨》,2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那种不分对象、不论领域的所谓大公无私或大义灭亲之举,实际上被判定为是对人情和礼乐教化的背离。
除了父子相隐的私亲与公法问题之外,私亲和教化、私亲与秩序之间也会存在冲突。报私仇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在民间,一直是被默许的行为,但若冤冤相报无了时,整个社会必将永无宁日。因此,在以孝亲伦理为尊的社会,如何处理私亲与公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历代哲人持续关注的话题。以父弑子该当何罪为例,基于“父者,子之天也”(《仪礼·丧服传》)、“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经·圣治》)的认知,儒家并不认为父弑子必须获罪。不过,东汉时期《白虎通》引《孝经》的相关议论,则将父子关系放在了天地、政教之下,认为所有人都既由父母生养,更由王者教化;既受私亲伦理规范,更受政教法律制约。*陈壁生:《孝经学史》,9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据此理解,人因私而仇杀的行为就不应被允许,因为仅以孝亲的名义默许弑子或报私仇,就是置天、置教化于不顾。即使在最密切的父子之间,亦当遵循公法的判决,若父弑子,亦当诛。
虽然私亲是最自然、最切己的情感,但却并不因此而理所当然地可以置于其他存在之上。汉虽然以孝治天下,但在引经义进行裁决时,也特别关注到该将私亲伦理放置何处的问题。私亲与政教、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关系,既复杂难辨,也直接影响着传统社会的治理秩序。
从古代的私己、私亲,直至近代的“私国”,“私”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的范畴。对“私”观念进行类型划分和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其形成和变化的语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挖掘其不断变化的解释力。由“己”生发而来的“私”,在封建制度瓦解以前是内涵于制度中的实然概念,鲜有价值内涵。而当这种制度无法再为“私”提供规范时,“私”便被赋予了“邪”“非礼”等负面意义。由血缘构成的私亲,在商鞅的实验中变成了不合礼法的“私”。受包括魏晋佛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两宋时期形成了直面个体的理学传统,由“己”生发的“私”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分裂,并被纳入了天理之公的话语中。明末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通过为“私”正名,将“私”诠释为符合天理自然之“私”,并将万民之私转化为天下为公的基础和根据,使“私”再度回归实然。除了受纵向的时间因素影响外,关涉范畴不同的“私”也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当它指向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时,往往被指独占天下。而当其相对于大同社会的经济理想时,则被指土地不均、贫富悬殊等。显然,要呈现公私之间立体的、完整的图像,就必须廓清不同语境下“私”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