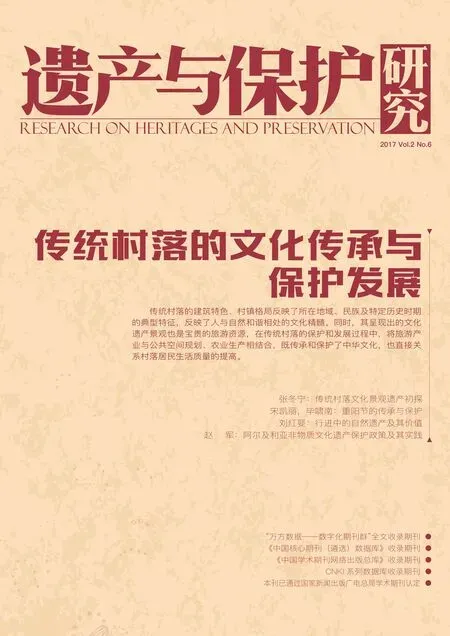考古技术在中俄首次联合搜寻二战时期苏军遗骸中的应用与前景
2018-01-16王赫
王 赫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015年5月12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双方开展首次送苏军烈士“回家”的活动。“中俄首次联合搜寻在中国境内牺牲的苏军烈士遗骸活动”的启动仪式在牡丹江市穆棱县下城子镇举行。这是中俄双方首次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牺牲的、苏军烈士遗骸进行的搜寻行动。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考古队应俄方邀请,参与了本次搜寻工作。在本次搜寻工作中,搜寻队伍成员包括来自俄方的6名档案学、地质勘探、医疗鉴定方面的专家和11名勘探队员,以及我校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9名师生。在本次搜寻活动中,考古学调查与发掘技术的运用,为搜寻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文将对比两国考古学技术的差异,为田野考古学技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一点思路。
1 历史背景与搜寻经过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正式约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布从即日起,苏联正式对日宣战,次日凌晨,苏联驻远东部队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统帅下,跨过边境线,向中国东北挺进,对盘踞东北14年之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打击,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直接促成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性的灾难正式进入了历史。牡丹江地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地,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火的洗礼[1]。
苏军的意图是用约58万苏联红军从东、西、北3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向心突击,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等,意图切断关东军与关内日军及在朝鲜日军的联系。牡丹江市位于牡丹江下游,周围黄金原煤等战略资源富足,这里是日本关东军驻扎的核心区域。为抵抗苏联红军的进攻,同时向东保护哈尔滨这一重要战略防御枢纽,日本关东军在这里集结,这一地区便成为了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腹地的第一道关卡。
1945年8月9日上午,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五集团军跨过国境,向绥芬河发起进攻。揭开了牡丹江战役的序幕。牡丹江战役共包括4场战斗,分别为绥芬河战斗、桦木车站战斗、挺进牡丹江和血战东宁。战斗异常惨烈,双方损失惨重。火烧山位于黑龙江穆棱县柳毛村,这是日军为抵抗东线苏军设置的第二道防线。由于苏军的猛烈攻势,日军节节退败,通信全部中断,位于穆棱县的关东军因没有接收到日本天皇投降的诏书,与苏军垂死抵抗。1945年8月19日,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五集团军190步兵师与日关东军124师在此展开激烈战斗,共413名苏军将士阵亡于此[2]。
2012年8月,柳毛村农民刘光临偶然在火烧山上发现一块腿骨并进而发现4具完整遗骸。经中俄双方学者鉴定,该4具人骨均为在火烧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这次发现引起了俄方学者的高度重视。
2015年5—6月中俄联合搜寻队在火烧山区域,通过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确定墓葬位置,并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手段,对烈士遗骸进行提取、保存、运输,出色完成了这一跨国合作项目。这也为今后双方在考古学研究上的更深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考古调查发掘方法在搜寻中的应用
在本次中俄联合搜寻活动的搜寻队中,俄方队员包括档案学、地质勘探学、医疗鉴定、野外搜寻、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共计17人,而中方队员主要来自黑龙江大学考古队。在此次搜寻工作中,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中俄双方的考古学在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因此使用的方式也略有不同。
2.1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
在搜寻的准备阶段,俄方提供了1:10万的地图,是1906年绘制的。地图中记录了在这片土地上埋葬的第一方面军第五集团军190步兵师112团、58团和158团的军官和士兵。少尉以上的单独埋葬,少尉以下的集中埋葬。这些官兵被埋葬在32 m2的范围内,加上年代久远等客观原因,搜寻的难度非常大。
搜寻队员希望选择一种短时间内可以对大面积区域进行搜查的方式,区域系统调查这一简单高效的理论成为了搜寻队员的首选。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最早起源于西方,起初目的是服务于聚落考古,并研究古代社会的系统性的抽样调查方法。
20世纪50年代,部分西方考古学者认为仅通过类型学方式研究考古学遗存,无法反映古代社会,认为考古学应该是通过遗存研究古代社会规律,掌握人类生活的一门学科,进而促成了新考古学的诞生,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应运而生。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北京进行讲座,聚落考古的模式开始进入国内考古学者的视线;1989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一文中提出聚落考古学的重要性。1990年后以北京大学为首,国内开始进行聚落考古学研究,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也正式被引入中国。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中俄联合搜寻活动中的使用,极大地缩小了搜寻难度。通过这一具体的理论方法,搜寻队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搜寻更大空间,在疑似地点进行标记,之后运用探铲确定遗迹范围。
2.2 考古钻探方法
考古钻探是考古学的重要调查手段之一,是为了初步确定埋藏于地下的遗迹范围的一种手段。主要使用探铲向地下打孔,通过带上来的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判断遗存的埋藏情况。
探铲(图1),又称为洛阳铲,相传洛阳铲最早出现于清朝的河南洛阳地区,是盗墓贼通常使用的工具之一。20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亲眼目睹了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况,受到启发,最早将其运用于安阳殷墟、偃师商城等古代遗址的发掘当中,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洛阳铲经过了我国考古学者的改进后,广泛地使用于我国的考古工作当中。
经过我国考古学者的努力,洛阳铲的种类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多,铲头被分为土铲、破砖铲、泥沙铲头和筒子铲4大类。土铲即普通铲头,主要使用于大多数土壤情况下,是考古探查最常使用的工具;破砖铲,这种铲头适用于土铲因碰到较硬石块而无法进行探测的情况;泥沙铲,这类铲头适用于土质松软的沙土地,泥沙铲的铲头是在土铲铲头两侧增加护翼,以解决其他铲头无法将沙土带上地表的问题(图2);筒子铲,这是一种新兴的铲头,适用于普通铲头无法带出如水一般的泥沙而设计的。

图1 探铲

图2 包曙光老师向俄罗斯学者展示探铲使用方式
使用洛阳铲时,身体站直,两腿叉开,双手握杆,置于胸前,铲头着地,位于二足尖间,用力向下垂直打探。开口到底,不断将探铲头旋转,四面交替下打,保持孔的圆柱形。否则探不下去,拔不上来,将探铲卡在孔中。打的探孔要正直,正是不弯,直是不歪。打垂直孔也并不十分容易。测验探孔的正直弯曲,可以拿电筒之类,借助光线,垂直从孔口往下照,光线射到孔底,则探孔是直的;如果光线射到孔壁下不去了,则探孔是弯的,必须修整工具后再打。打弯的探孔在拔铲时是很费劲的,双手拔杆时也可以将肩头顶靠接杆借力上拔[3]。
结合区域系统调查方法,搜寻队员在疑似区域进行拉网式打探,每10 m打一个探孔,根据土质土色对于疑似埋葬区域进行细致探查并做标记。最初,俄方搜寻队员对于洛阳铲的精确度存疑,仍采取打探沟的方式进行搜寻,费时费力。经过几天的共同工作和实践的检验,我们使用的洛阳铲的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俄方搜寻队员也开始接受这种简单高效的方法,并主动要求学习。这是联合搜寻活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两国考古学技术交流的一个重大突破。
2.3 中俄双方的考古学调查发掘方法对比
在遗骸埋葬地点的发掘过程中,搜寻队员首先通过打探的方式确定墓葬位置,之后俄方队员对墓葬区域布下1 m×1 m的方格,根据揭露情况进行扩方,同时按照发掘深度,将一定深度作为一个人为地层,进行记录。这种发掘方式与国际上采用的考古学方法相同。
中国考古学方法分为两种体系:旧石器发掘方式与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发掘方法相同,采用国际通用的发掘方法;新石器及之后的发掘方式大多数采用5 m×5 m探方进行发掘,部分大遗址采用10 m×10 m探方进行发掘。发掘方式遵循地层学的方法,按照地层进行揭露。
笔者在2016年对俄罗斯考古遗址的实地考察发现,俄罗斯的田野考古发掘遵循国际通用的考古学方法。首先,根据一定深度划分人为地层的方式方便记录,由于俄罗斯纬度较高,地层的土质土色较难区分,利用这种方式有利于在不易区分地层的情况下出土遗物遗迹的记录,也方便之后的修正。其次,采用1 m×1 m的小规格探方更加便捷,对于已经确定了位置的遗迹,发掘可以减少很多无用做功。最后,保留遗物下方埋藏介质的方式,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遗物出土的位置关系,利于发现其内在规律。
相比较我国的考古学技术,从调查、发掘到整理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程序。各类遗迹的发掘方式,包括不同时期的发掘方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并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高科技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考古发掘工作中,如无人机航拍,全站仪、RTK精准测量,CAD绘图,3D建模等,中国的考古学技术越来越规范化、科学化、先进化,我们的考古学已经迈向了世界一流水平。但是一个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停滞于自己的小圈子当中,需要有国际大视野,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相互学习,寻求共同提高。中俄两国的考古学技术手段各自存在优缺点,只有相互取长补短才能寻求考古学更高层次的发展。2.4 考古学调查发掘技术在搜寻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本次联合搜寻活动中,考古学技术手段成为搜寻工作的强大助臂。实践证明,考古学发掘方法已不仅仅局限于考古这个小框架当中,而是有了广阔的使用空间。首先区域系统调查与考古探测相结合,短时间内对大面积区域进行调查,真实地还原该区域的地层情况。这对于搜寻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的搜寻工作由于时间、人力资源有限,无法对大面积的区域进行短期高效的调查,区域系统调查与考古探测的加入,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搜寻工作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次,考古发掘方法的引入,为本次搜寻提供了强大的后期保障。一般来说,与本次搜寻性质类似的活动中,会出现因没有科学完整的体系,且由于工作人员不细致而破坏遗物的情况。作为考古挖掘则此情形绝不允许发生,由于考古工作的性质决定,考古发掘工作对于人骨的提取、保存、运输等有一系列完整的流程,这正是搜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3 联合搜寻工作成果
搜寻成果如图3所示,在为期一个月的搜寻工作中,中俄联合搜寻队走遍了火烧山及其周围32 m2的所有区域。共发现了5具有确切名字的苏军烈士遗骸。另外还发现了至少3具苏军无名烈士的残骸,仅发现几段肢骨而无头骨。除此之外,还搜寻到苏军使用的钢盔、弹片、枪架、子弹、衣物残片和勺子等近50件遗物。这些遗物与烈士遗骸一并移交给穆棱市外事办和民政局。

图3 搜寻到人骨与部分遗物
4 总结
本次联合考古搜寻活动,共历时1个月,顺利地完成了既定任务,让长眠于此的苏军烈士回家。同时两国学者相互交流,令我们看到了考古学调查与发掘技术发展的广阔前景。
俄罗斯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陶米恒说:“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正如所言,在这次联合搜寻活动当中,考古学技术手段大放异彩,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时代在进步,一门学科也应该顺应时代而发展,不应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当中,而这次活动正好为考古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考古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带动其他学科的进步,考古学从今以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可以实实在在为民众服务的。
其次,这次活动促进了两国考古学者的密切交流,学科在交流中发展,两国学者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这对于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时至关重要。经过这次合作,中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16年我校考古队应俄方邀请,赴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对伊万诺夫卡河口墓地遗址进行共同发掘,进行更深入地交流。正如俄罗斯学者杰尼斯.沃尔科夫所言:“俄国人用左眼看阿穆尔河,中国人用右眼看黑龙江,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可睁开双眼共同开拓这片考古研究圣地,过去的一小步如今已经成为一大步,愿我们的合作如奔腾流逝的黑龙江水,滚滚向前,不断开拓进取,勇攀高峰”。
最后,合作与交流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相信通过这次合作,中俄双方已经敞开了合作的大门,未来两国的考古学事业一定会在合作中更加辉煌。
[1]孙晓,陈志斌.东方的落日:苏联紧急出兵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5.
[2]苏亮.血战牡丹江:日本军国主义的“滑铁卢”[J].安徽文学月刊,2008(9):251-253.
[3]洪昀,王辉.洛阳铲在取土场勘探中的应用[J].工程与建设, 2014 (3):32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