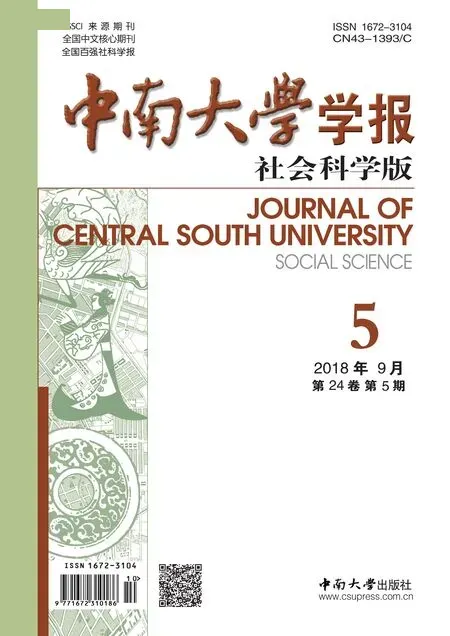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视野下文学批评者的政治体验
2018-01-14毛郭平
毛郭平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文学批评者的政治体验
毛郭平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晋中,030619)
作为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验是人们对政治环境、政策法规的深刻体认与感悟,既包含着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也包含着人们对政治价值的探寻。对文学批评者政治体验的探讨,就是试图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还原那些被遮蔽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特别是批评者的政治关怀。文学批评者的政治体验是各种权力渗透的结果。文学批评,就是批评者将自身的政治体验与文学文本相结合,在阐释文学所要表达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一种介入现实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政治体验不断被修正的过程。文学批评对宏观政治的强调会造成政治体验的“单一化”,对微观政治的强调又会形成政治体验的“多样化”,这两者都会造成文学批评者政治体验的“过剩”。
文学批评;政治体验;权力;现实介入;修正
政治体验是人们对政治环境、政策法规的深刻体认与感悟,既包含着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也包含着人们对政治价值的探寻。我们对文学批评者政治体验的探讨,就是试图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还原那些被遮蔽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特别是批评者的政治关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总是从文学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揭示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作者的体验而展示出来的观念、感情及其价值取向。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文学作品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 式”[1](9)。然而,当文学批评越来越倾向于借助逻辑推理及观念预设,以技术化的手段和程序化的方式来对作品进行评析的时候,有关文学与社会、政治的体验势必被那些抽象的概念所挤压,从而造成对事物认知与体验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磨损。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并非简单地将一切文学作品当成一种政治概念的论据,因为这样会造成文学批评仅仅成为政治问题的延伸,从而弱化甚至忽视了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存在的必要性。文学批评中的政治体验应该是多样的,既包含某一群体的政治体验,也包含个人化的政治感受,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顺应或者悖逆关系。
一、权力融入的政治体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政治方向的强调,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当我们提及文学批评中的权力渗透的时候,就意味着从宏观视野进行文学批评的同时,仍有诸多微观因素值得我们去考察。比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内涵的不断丰富与修正就表明了文艺领导者对文艺及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的基本看法的调整。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类型,如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规定了文学表现现实的不同方法,这种规定本身并非完全是现实主义自身的理论发展使然,而是由于权力建构的结果。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差异在于两种创作方法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政治倾向,或者说两者暗含着不同的政治立场;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出,虽有解决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理论困境的意图,但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中国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摆脱苏联影响的努力[2](225)。当然,这些概念都是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着意识形态,也就承载着权力。
那么,文学批评者在使用某一概念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对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乃至政治情感的顺应或者悖逆,同时也就接受或者拒斥了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巴金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热烈地表达了对新社会的赞美,“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用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来歌颂、描绘我们时代的英雄,发挥高度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人们不断地前进”[3](184)。文学想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文学家思想改造的理论指导,并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认同,即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和政治需要的光辉作品。然而,巴金的这种文学批评观落实到文学实践中,并没有达到现实主义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在冯雪峰看来,巴金的作品存在着世界观的问题,其立场和观点仍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这恰恰决定了巴金作品中对现实表现的乏力。“两结合”是文艺创作方法、评价方法,其本质是一种文艺政策,因此,批评者在使用“两结合”的时候,一方面是接受了“两结合”所蕴含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用“两结合”所暗含的权力去管控别人。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是否合乎“两结合”这一标准去评价他人或者被他人评价,同时,每个人也都依托这一概念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体验。郭沫若对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有深刻的体验,他认为这一方法的独特性就体现在“革命”二字上,并将其上升到认识论层面,试图在现实与作品之间架起一道有关“世界观”的桥梁。对此提出质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则认为,“世界观”或者作者的政治立场至关重要,能否拥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作品的现实性及其现实效果。当然,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单靠一些空洞的热情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冯雪峰在谈及丁玲的小说《水》时,就指出这部小说以概念取代了对人民大众丰富生活的描写,以旁观者的姿态想象地表达着所描摹对象的情态,漠视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人的艰难困苦与奋起反抗的思想感情。因此,我们感受到的并非生动的画面和让人惊心动魄的人民力量,而是一种淡漠的感情与公式化的表达方式,这也反映了丁玲与生活的距离[4](156)。冯雪峰对丁玲《水》的评价,实际上强调了对现实的描绘不应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而是能够体现出作者本人深潜到人民生活中去,并切实表达自身对现实的体验。邵荃麟也对那种鼓吹主观主义而回避矛盾的假浪漫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推进现实主义的深化[5](399)。邵荃麟的这一提法是对农村题材小说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思考,并将自己的政治体验融入“中间人物论”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些主张与“两结合”所暗含的权力形成了一定的抵牾,最终必然被主流文艺观念抛弃。值得注意的是,邵荃麟的文艺主张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强调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须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需求。如果我们将现实主义作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词,却没有深入到它自身的历史演变轨迹之中,就有可能将之作为一个意义恒定的概念,从而遮蔽了这一关键词所隐含的不同观念,特别是忽视了意识形态在关键词内涵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胡亚敏认为:“给关键词下定义只是一种有限的本质探寻,追求完美的定义可能是一个陷阱。关键词的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静止的,我们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界定这些关键词,而对其意义的认识不可能有终点的,它们的含义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向未来开放。”[6]将现实主义当成一种认识论,那么这种认识论必然会随着历史场域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致使有关现实的内涵不断延展。
总体而言,每种与文化和社会相关的概念都有“权力”的预设,要求使用者承认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政治倾向,那么使用者也会将自己的政治体验融入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中的政治要求。其实,对现实的考量并非试图要找到一个抽象的还原论,即探寻所谓绝对的、抽象的、带有同一性的现实,而是需要把现实当成一个过程,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它的未完成性。因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政治实践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总体性特征。或者按照罗骞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7]。文学批评中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可以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两结合”将现实主义中的抒情合法化,使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理解更为具象化,同时也为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条符合中国政治现实书写的路径。对“两结合”的阐释,批评家所援引的典范就是毛泽东的诗词。有学者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艺主张,为知识分子抒发个人情怀留下了相当的空间。如果现实的概念因为在政治情势的变迁中体现为一个空洞的能指的话,那么,浪漫主义则会将那种可能被现实遮蔽的个人化的东西表达出来。尽管这种情感本身依然是某种“志”的言说,但其通过一种直白的抒情方式,多少能减少因为现实主义的各种规则所带来的言说困境。也就是说,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有助于作者和批评者在预设的政治空间里表达自己的体验与认知,同时也为批评者摆脱抽象概念而进入人的心理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参照。不过,这种创作方法或者政治限定,为文学的政治化叙述提供了异质性的因素[8](141)。我们在对某一文学现象进行评析的时候,总会把这一文学现象的外围作为我们评述的参照对象,即便这一对象本身并没有被有意地突显出来。因此,现实概念的发展,既可以认为是其自身内涵的不断丰富,也可以看作是自身不断受到挑战的结果。当然,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变化与人们的体验发生了变化有直接的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创作者突破自身的政治局限。比如在政治上作为“正统派”的巴尔扎克突破了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描写了“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是怎样一步步堕落并滑入深渊的,并对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刻的嘲笑。这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9](683−68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文学批评中美学的和历史的要求,就是对现实主义最根本的规定。鉴于此,文学家才能写出切身的政治体验,而批评者也能通过文学作品领悟其中的精髓。
不过,当我们对一个思想框架或者体系信任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完全用理性的方式对其进行反思,这往往使得我们的思想全都被纳入一个由经验和权威支撑起来的信念体系。反映在文学批评上,则表现为我们会用这种信念体系作为我们评价的潜在尺度,继而将其当作我们的真切体验,并且试图纠正与此相违的任何东西。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如果这种信念体系做出适当的更新,可能会引发我们认识、判断和体验的混乱。有学者指出:“在共同体成员的主观态度和忠诚还没来得及调整之前,新的共同体就已经事实上(即客观地)出现了。它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异议和反抗、疏离和矛盾心态将人性——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挤压得四分五裂。”[10](325)应该说,我们所研究的事物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一旦我们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对现实政治的感受和体验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就必然在事物与思维方式之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既可能是自身造成的,也可能是外部的力量所造成的,但最终却落在了个人身上。胡风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试图在革命话语所要求的规范化行动中,仍旧执着于个人化的“主观战斗精神”,特别是在新的环境中,他在整风会上的沉默、对“讲话”的态度问题等,均表明了他与这个时代、特别是政治环境的错位,由此也影响了其理论阐释路线甚至人生轨迹。对国家来说,知识分子需要服从和维护政治的权威,自觉地表达对政治的认同。不过,一旦将政治机械化、庸俗化地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标准的话,那么,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对政治的诠释和阐发非但无益于发挥政治认同和政治动员的功能,反而会削弱文艺的政治影响力,其结果必然是影响知识分子对这类政治的认同。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对阶级政治的疏离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有的学者看来,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态度,形成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周期性震荡”。但是,这种周期性震荡使得知识分子始终徘徊在专业研究的周边,既要充分考量政治的可能需要,又要强调专业的发展趋向。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他们仍担心可能存在的政治压力,致使知识分子陷入了新的焦虑当中。这一焦虑可通过两种方式来排遣,即要么告别专业领域,寻求相对平淡的生活,要么随大流,丢掉独立思考的习惯,放弃自身的价值和责 任[11]。沉迷于平庸的流行思想抑或抛弃理想主义精神,都是文学工作者与批评者政治体验的外在表现。每个人都会对政治现实做出自身的判断,但这一判断是否公之于众,则需要通过他的行为来判断。人们总是生存在一个有着各种秩序的社会之中,因而也总是对当下的秩序安排表达着认可或者不满,这种内心的感悟并非是秩序可以完全规划的。
二、指向现实行为的政治体验
马克思指出,哲学的使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同样,具有鲜明社会批判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批评者将自身的政治体验与文学文本相结合,在阐释文学所要表达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一种介入现实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的重要方式。瞿秋白就把文艺当成改造世界的一种有力武器。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会作用于人的意识当中,从而悄悄地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在帮助人们认识现实的同时又改变着现实。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充分发挥文艺的这种功能,服务中国革命事业[12](346)。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文艺活动既是对现实的阐释,也是改造现实的辅助手段。但整体而言,文艺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即通过影响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激发人们改造世界的意识和观念,并最终指向现实行为。在文学批评中,批评者总是会在考虑现实政治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政治体验,依托文本所表达出来的意象,揭示文学创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从而把文学与现实若隐若现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并影响文学创作的趋势和立场。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文学中的“政治体验”,毛泽东就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他还特别指出,要想做教师,首先得做学生——人民群众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工作者不要自身的感情。冯雪峰就强调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深通生活”,体会和注意到了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并认为文艺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认识现实,并引导自身的热情到实践中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作家和批评家有敏锐的感觉和判断,特别是要有一种艺术性的情感[13](190)。因而,从文学文本到现实行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着力研究和阐释的方面。文学批评者的言说方式与内容,与自身的政治体验有着紧密的关联。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袒露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本身与其亲身体验有紧密的关系。“我二十一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14](701−702)当面临死亡时,瞿秋白对自己的过往所进行的一番历史性总结,表达了内心的复杂感受。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角色以及其所完成的政治工作,由于两种政治观或者人生观的矛盾冲突,让其无所适从,并把自己所从事的政治事业当作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其实,通过瞿秋白在苏联的游学经历以及其对苏俄文学的深刻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瞿秋白过于敏感的气质与其现实的政治体验,决定了他对文学的评价也必然是个人化的。他指出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小说表现了当时俄国社会中的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远离人民,却又不愿与政府同流合污;有改变现实的渴望,却又不愿付诸行动,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犹豫不决,被社会放逐,最终显得“多余”。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真实表现[15](177)。对“多余人”惺惺相惜的评价与其说表达了批评者对这类人的同情与认可,不如说是对自身遭遇的悲悯与理解,因为瞿秋白早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14](700)。立足于个人化的视角,文学批评者会将个别化的体验融入对作品的分析与阐释中,此时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带有浓郁个人体验的言说手段。
与之不同的是,在过于强调集体利益至上的时代潮流中,个人性的体验往往会被挤压,或者说个人化的感受被集体感知所替代,相应地,文学批评所表达出来的政治体验的“集体性”特征就较为明显。田汉评价《风云儿女》时,就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指出,《风云儿女》描绘了青年男女面对紧迫的政治形势如何从软弱转变为勇敢反抗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然而,电影本身却违背了这一政治主题,为此,他说,“我丝毫没有意思要孤立地刻画一出‘从风云莫测的变幻中演成的人生悲剧’来加以欣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使人民流离颠沛,是一种必然的民族运命,不是什么‘风云莫测的事件’,一定得唤起人民跟这种运命做斗争。处理这种现实斗争决不能用什么‘风云莫测、变幻无常的手法’。”而导演对剧本的非政治性演绎,造成了观众对《风云儿女》政治主题的忽视,也就削弱了剧本本身的政治力量,无法让观众得到启迪[16](199)。文学批评植根于现实社会,其实是依托于批评者对现实政治的体验。每个社会的统治阶层都试图将自己的政治观念当成人民的意志来宣传和执行,违背于此的都要受到批判。田汉基于对现实政治的体验与对政治理想的预期,对《风云儿女》做了政治情势需求下的解释。可以看到,田汉的文艺批评与同时代其他人的文艺批评并无本质不同,即在分析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的时候,必然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革命豪情,一是旧中国人民的不幸,有违于这两者的,必然是“非政治的”,也就无法鼓舞人民。主流意识形态所使用的观念在田汉的这段话中有明显的体现,那就是对相关概念的大量引用。这些概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以及处理现实状况的方法、立场,通过反复地言说,也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现实的一种潜在的标准。为此,概念连同其所隐含的体验一并成为人们的自觉感受,并将其作为评判现实生活的一把标尺。
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的宣传确实激发了人们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特别是通过想像的方式让人们把一切当作真实的情况来感受。只是一旦遇到与这种期望的现实不符的情况,或者另外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的宣传替代旧有宣传的时候,人们原有的体验必然会发生迁移。反映在文学批评方面,则表现为批评者会在批评的过程中对各种预期的现实与所体验到的现实进行一番比对。瞿秋白在狱中回顾自身的经历,认为无法解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自身的绅士意识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自已是书生的角色。书生习惯于天马行空地想像世界,所获知识仅仅停留在书本层面,缺乏对现实的真正感受与理解。原想通过各种概念来掌控世界,但一旦面对世界的时候却显得百无一用[14](716)。仅仅依靠抽象名词来感知社会现实,必然会使得知识分子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并把这些名词所蕴含的东西当成现实来感知。不过,一旦遭遇真正的现实政治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不得不审视书本上、理想中的“现实”政治了,不得不权衡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从而萌生自己无用之念。只是碍于“体面”,只能勉强着做“文人”,挣扎着扮演各种角色[14](715)。巴金的无政府主义观念尽管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理念有些抵牾,但其对现实政治的感知却是顺从了社会发展的潮流的,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时代政治体验所要求于他的行为。因为时代政治对人们的要求并非指出应该做什么,而是必须做什么。诚如刘象愚等人指出的,“政治话语在功能上专门化了:它的品格在本质上是审议的,总是指向质询,要做什么?怎么做?与此相应,它的修辞也是有特色的:指向争辩与必要的字斟句酌,政治的语言具有特别强的‘述行’感,实际上,总是用祈使语气来表达。这一审议—祈使的实践,就确定的资源说,缺少它自身缺少的东西,根本不在仅仅是文化的,而是强制的:政治话语在体系上与力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认可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论这力是通过国家机器还是通过群众的反权势行动发挥作用的”[17](31−32)。尽管政治话语有助于知识分子维护或者重建预设的政治意识形态,但也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这些术语的引导下来对文学进行批评。文学批评者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架构与这种政治体验有关,但政治体验往往是既有与个人经历相关的独特性的政治体验,又有时代潮流所催生的共同的政治体验。我们看到文学批评中的批评方法、术语、行文逻辑总有时代政治的影子,这恰恰说明了文学批评试图描写这些政治体验,并将其作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和支撑力。
不过,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中,微观政治体验确实对文学批评干预现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通过作品发掘出来的生态政治、身体政治、媒介政治、空间政治、食物政治、服装政治等,催生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审视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然而,这些不同立场的批评只不过是人们对切身生活的某些政治方面的诉求,甚至可以认为,这只是人们在放弃了像革命政治、阶段政治那样的宏观政治诉求之后,在微观政治方面所追求的一些具体的政治愿望。因为,每一个事件的解决都不可能单单靠这一事件本身来完成,它需要在各种关系中来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微观政治的各种诉求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野。然而,如果将这些不同立场的批评都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框架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性质,即把一种激进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批评变成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批评,而这种包容性所产生的张力就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泛化,甚至暗中削弱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和社会批判性质”[18]。两相比较,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政治形态的研究,一方面要坚持文学理论形态的学科性和体系化,以确保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逻辑性,另一方面,文论研究要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使得文学理论真正来源于现实的文学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归纳或者演绎。只有这样,方能做到“从特殊到一般”,确保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的学科性和现实指涉性,从而有利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真正的现实穿透力。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增强干预现实的力度,那就需要“文学批评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并“通过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 界”[19](221)。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需要批评者深入现实生活,表达出属于自己的真正体验。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更有现实感染力,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只停留在观念中,而是被批评者真正认同。
三、被修正的政治体验
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政治体验不断被修正的过程。对概念的使用及其意义的赋予,实际上都是各种权力及相关制度在文学批评中的渗透以及个人对这一渗透的不同感受的结合。但总体而言,这些概念包含了人们的多种政治体验,同时有关这些概念的文学批评总是有意无意地帮助维持和加强相关政治制度的种种假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及文艺工作者应该加强思想改造。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体验他们的真实情感,并转移到他们的政治立场上去。这一要求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全面的实施。我们通过作家与批评家们的文本言说,可以看到他们有关政治的认识与感悟。郭沫若在1949年的文代会上说:“文艺上的战线,和政治上的一样,有着不同的阶级,就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和政治上的情况一样,如果只有团结,没有批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是不能巩固的。文艺界应该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作风。”[20](42)将文艺情况与政治情况相比较,要求文艺批评上的“民主作风”。郭沫若在批评方法和理论上顺时而动,1959年在答《人民文学》编者问时就借用了毛泽东有关鲜花与毒草的辨别标准,认为文艺应该服从政治利益,创作活动也应该为这一利益服务。“合乎这些标准的就可能产生出香花。不合乎这些标准的就一定产生出毒草。因此,这六项标准不仅是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指路碑,而同时也是产生香花或者毒草的分水岭。”[20](304)作为党的文艺领导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的把握必须准确,同时也需要将之贯穿到对文学的指导与批评上。相应地,作为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政策和国家相关政治动员的要求下,也表达了自身的政治体悟。柳青就认为:“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改造自己也是这样,要热爱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要表现这个制度的本质关系,只要看到我们这个制度,不满意的都会满意。这是我多年的体会。”[21](35)在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号召之下,文艺工作者在表达对新的社会的歌颂的同时,也将改造思想作为自觉的内在追求。柳青认为作家要想让艺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就必须去“三个学校”深入学习:生活的学校,即要深入到人民群众斗争生活当中;政治的学校,即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方针政策;艺术的学校,即向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学习[21](40)。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这种传统也会从党内延伸到党外。巴金的政治立场就有从无政府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恰恰印证了巴金思想的不断调整。但是这种转变并不能作为其兴奋的理由,反而成为不断挖掘自身“狭小”的资源,成为探讨自身挥之不去的落后与缺点的依据。巴金在自己的文集序中就反复说道:“我过去那些作品中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只有感到愧悚。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我的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无色!”[22](26)这种内疚感并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政治认识与感悟。巴金在1962年的短篇小说集序中坦承自身的罪责,“我得向读者告罪:我没有写出旧中国的全貌。”[22](30)这种自我批评是巴金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表现,也表明了其政治体验的变更。同样,那些很早就参加革命宣传的作家也在对照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田汉就曾在编选文集的时候对自己的不足进行了一番历史追溯:在较早的时候,是靠着年轻人的正义感和冲劲来从事创作的,后来在党的感召和教育下,用文艺活动来从事革命工作,由于要及时有效地反映现实斗争,很多作品缺乏认真研磨,从而显得粗糙,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满意。“当一九五O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不积极的。我怀疑那样的东西在人民日益提高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23](418)汉的创作尽管一直是在党的领导和要求下进行,但其所作的反省,恰恰说明了文艺中所表达的政治体验,不得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满意”这一要求下做出适当的调适,即从“急就章”到“精雕细琢”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者对自身的作品进行自我解剖,就连那些从事文学编辑的人也不得不对自身工作中的不足进行自我反省。冯雪峰在谈及《红楼梦》研究时,就曾做过一番检讨。他说,最初在看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时候,只是把它看成是纯粹的“学术性”的东西,也仅仅从文字表达的顺畅上去考虑稿子,没有认识到其中还有有违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因素,还有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13](263)。这些文艺工作者的不同政治体验是自觉的、自愿的,更是在新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以及参与现实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政治体验的修正,是知识分子个人改造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不过,里面的经验教训需要吸取。
应该说,这种对往昔的评价与作者早期对自身的剖析理路是一致的,即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那种宏观政治对个人主体所应承担角色的限定。有学者认为,中国革命政治在塑形个人与集体及其关系方面就呈现出一种悖论,即中国革命一方面将每个人从传统的文化政治境遇中抽取出来,让其变为一个单独存在的个体,旨在变成不受各种关系束缚的原子。另一方面,又借助新的理想目标旨在让其形成共识,从而又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使得中国革命通过生产出来的个体有可能解构集体,而生产出来的集体又无形中制约着个体,形成一种矛盾对立状态,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关系。“个人/集体一直纠缠在社会主义的文学——文化想象之中,并构成了这一想象的某种内在的紧张。”[8](152)中国革命中个人与集体内在关系的张弛的最终解决方式,往往是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高度来加强对个人行为方式的规约,特别是加入了对个人行为的道德化评判。不过,个体往往在来不及建立个人意识的时候就已经被卷入了另一个集体之中了。当然,这种被卷入存在一个被认定的环节。也就是说,这种归属感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外在的建构,而自身是无法言说的。当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宏观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感受及其所诱发的心态也会发生相应的更替。有学者就比较过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感和新时期兴起的政治感的差异,他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例,认为前者处于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之际,而后者则是处于中国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之后。这两种政治现实决定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不同政治体验。如果说前者催生了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话,那么后者则由于历史境遇的差异,产生了不同于前者的政治感[2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多元价值观和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盛行,生命政治开始凸显。在当前颇有市场的文化研究中,生命政治的发掘与整理相当流行。对生命政治的发掘固然揭示了人们被异化的现实,但这种现实却伴随着娱乐之风加剧了我们对政治的恐惧心理与对生命的麻木感。我们已经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究其原因,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随的迷恋,使个体缺乏一种自我认知,无法体味到内心的真正渴望和要求。无论个人抑或集体都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中,迷失了自身的感受,从而将一种外在所赋予的或者教会我们的观点当成自己的切身感受。就是说,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人们,很难分清哪些是自己的真正感受,哪些是别人让其那样感受。这就使得有关过去与当下的评价是否具有“当下性”的意义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可以说明的是,当我们做出评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根据我们自身的身份变化作出了无违于时代的总体的政治体验。而那些试图带有个人化色彩的政治体验往往会在总体的时代政治体验中被边缘化。
四、政治体验生产的过剩
特定的政治环境往往会对其成员的政治体验产生深刻的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政治理想都与这个社会所主张的政治观念及政治实践有关。
在文学批评方面,批评者往往会在某一政治要求的框架下体验生活,或者说连同体验方式及其对象本身都是被规定了的。因而,文学批评中的政治体验就可能走向同一性,从而有可能形成对其他政治体验的遮蔽,最终形成“单一”化的政治体验。而这种单一化的政治体验又会在文学批评中被不断地生产出来,造成“单一化”政治体验的过剩。冯雪峰认为,文艺必须要敏捷地表现现实,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我们必须研究政治,研究国家政治形势和国家工业化建设,也研究国际形势,并且把这种研究成为日常的学习。只有从政治的学习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从亲身参加的人民斗争生活的学习中,使自己的政治水平提高到一个政治家的水平,才能全面地认识我们伟大的现实而真实地描写 它。”[13](7)即首先要研究政治,其次要学习马列主义,最后是要参与到人民的生活斗争当中。这三个方面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政治水平。而只有立足于较高的政治水平之上,才能更好地反映现实。作家要体验政治理论的深刻内涵,同时还不能用概念的手段去理解现实,去体验社会,否则表达出来的认识只能是原地踏步。冯雪峰进而指出批评家存在的问题,认为批评家们大多无法深入到轰轰烈烈的现实斗争中去,也缺乏应有的关注度和责任心,因而与现实失去了紧密的联系,也就缺乏亲身体验。批评家即便思考问题也是远离了时刻变化的现实生活,执着于苦思冥想,“我们的思想感情不是时刻都敏感地和实际斗争共鸣,时刻为每一个实际斗争的发展所激动。另一方面也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常常以许多概念来代替了自己的思想,甚至代替了自己的行动”[13](45)。冯雪峰有关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论述,与周扬、郭沫若等文艺领导人关于文艺政策的论述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只不过是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述而已。为此,就有可能形成思想的一体化(包括对思想的诠释与体验的同一化)。情感氛围与政治环境也会影响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效果。托克维尔在强调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时就指出,一方面作家们通过作品向人民灌输了各种思想,这就充当着国民的启蒙先生;另一方面,作家们也会将自己的性情、情绪、嗜好、气质传递给国民,使得国民完全继承了他们的优缺点,以至于大革命来临之际,国民会把他们从文学中所承袭的各种感受直接挪用到政治中去[25](187)。因此,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及文学批评中所表达出来的对政治的理解及其言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其他人。并且这种批评或者自我批评模式具有示范效果,致使每个批评者都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同时也会将这种政治见解在适当的时候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因而,普遍性的政治言说方式及言说内容共同形成了特定时期的政治场域,在这种场域中,形成了集体的或者带有意识共同体的特征。就是说,政治场域的相似性必然会把有关政治的体验塑形成带有普遍性的观念,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趋同化、模式化。
如果说文学批评的政治体验倾注于对宏观政治的表述,那么诸如“国家”“革命”“经济”“阶级斗争”等具有隐喻性的现代性政治话语就暗示着对我们的要求。同样,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微观政治倾向也在制造着类似的隐喻。詹姆逊将叙事当成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学批评就成了一种政治性的暗示。正如批评者将文学当成微观政治的发源地,在不断阐释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陷入政治无法自拔。富里迪说:“对无力感的意识,或者社会学家描述为‘自主力丧失’的状态,从一些不断增强宿命感的文化势力那里得到持续不断的动力。正如我们关于历史冻结的讨论已经提到的那样,一种流行的情绪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通过彼此之间及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命运。人类不再是历史推动者,而且实际上已被重塑为客体的角色,对他们而言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偶然的,是受到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操纵的。人是不可信赖的,不能再指望他们会富有责任感地生活——这是众多政策档案的预设。将成人当成小孩对待的倾向灌注于整个政治阶层。个体不再被视作‘政治人’,甚至连‘公民’都算不上。今天的政治词汇表强调突出了公众的被动和无力。我们中有的是受排斥者、易受攻击者(潜在的受害者)、受害人、遭欺凌者、受人庇护者、最终用户、消费者或利益共持者,但却没有作为政治动物的人。”[26](63)其实在不断地对政治的挖掘过程中,一切似乎都成了政治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政治无意识。然而这种解读本身就包含着其自身的另一种倾向:取消政治。因为每个人不再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只能是被动地迎接可能性政治的到来。从微观政治角度展开文学批评,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被压抑或者被剥夺的政治体验。这些批评所提供的政治体验种类繁多,不过却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接受范围,最终造成体验的过剩。
对宏观政治的强调会造成政治体验的“单一化”,对微观政治的强调又会形成政治体验的“多样化”。前者是因为在文学批评中反复呈现,形成了单一化政治体验的过剩;而后者则是因为文学批评中的政治体验过于繁琐,是一种体验的真正过剩。如果剔除微观政治给我们带来的无力感这一消极因素,那么,政治体验的多样化应该是人们面对政治现实的正常选择。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学批评不只是“文学”的批评,而是要借助文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我们通过文学批评能够认识和改变的世界首先是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批评者的政治体验就是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的重要参照对象。
[1]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文宝,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2] 旷新年.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3] 巴金. 巴金全集: 第19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4] 冯雪峰. 冯雪峰论文集: 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 邵荃麟. 邵荃麟评论选集: 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6] 胡亚敏.“概念的旅行”与“历史场域”——《概念的旅行——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导言[J]. 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41−44.
[7] 罗骞. 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N]. 光明日报, 2015−5−27(14).
[8] 费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0] 莱斯利·里普森. 政治学的重大问题: 政治学导论[M]. 刘晓,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11] 孟繁华. 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6): 146−159.
[12]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13] 冯雪峰. 冯雪峰论文集: 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4]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16] 田汉. 田汉全集: 第18卷[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17] 弗兰西斯·马尔赫恩.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M]. 刘象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8] 胡亚敏.“理论仍在途中”——詹姆逊批判[J]. 外国文学, 2005(1): 33−37.
[19] 胡亚敏. 中西之间: 批评的历程[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0]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第17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21] 柳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79.
[22] 巴金. 巴金全集: 第17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23] 田汉. 田汉全集: 第16卷[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24] 贺照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变奏与“政治”的变奏[J]. 美术馆, 2010(2): 184−202.
[25]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6] 弗兰克·富里迪. 恐惧的政治[M]. 方军, 吕静莲,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literary cr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MAO Guop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experience is a profound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which includes people’s political feelings and attitudes, as well as people’s pursuit of political values. Exploration into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literary critics is to try to restore the obscured political feeling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especially the political concern of the critics.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literary critics is the result of infiltration of various powers. Literary criticism means that critics combine his own political experience with literary texts, and provide us with a political idea and a way of life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expressed in literature.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s actually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correcting political experience. The emphasis on the macro politics of literary criticism will cause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micro politics will for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both of which will cause the “excess” of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the literary critics.
literary criticism; political experience; power; reality intervention; amendment
2018−04−07;
2018−06−2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11&ZD078)
毛郭平(1979—),男,山西洪洞人,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批评,邮箱:mgpsxr@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19
I01
A
1672-3104(2018)05−0162−09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