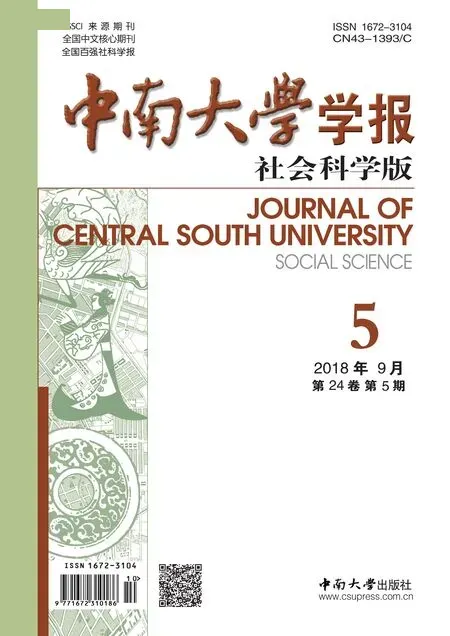康德统觉理论中的主体知识问题
2018-01-14唐红光
唐红光
康德统觉理论中的主体知识问题
唐红光
(长沙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03)
在对待主体知识问题上,康德试图通过批判理性心理学的主体学说来表明扩展主体知识的企图是徒劳的。理性心理学构建主体知识的合理性依据是统觉概念。通过统觉概念不能推导出任何主体的先天知识,并且正是对统觉的误解才形成了关于主体知识的幻象,消除这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限制了主体知识的扩展。先验统觉的功能性特征决定了它作为先验自我意识只指示主体实存,不表象主体,不能构建主体知识。主体表面上似乎拥有关于“我”的知识,实质上只是一些关于客体的自我知识。在先验观念下,康德借助统觉概念达到了区分先验主体与经验自我的目的,在理论层面真正解决了主体知识问题。
康德;理性心理学;统觉理论;主体知识
长期以来,研究者在诠释康德的统觉理论时往往限于客体的知识建构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康德提出统觉概念的最初目的就是要解决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核心问题,即主客体如何统一,而作为人的心灵最高认识能力的“统觉”为此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统觉理论时不免会将焦点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以探明统觉建构客体知识的原理及作用。
然而,自20世纪末开始,以德国学者Klemme和美国学者Ameriks为代表所主张的“主体哲学”[1]“心灵理论”[2]使康德的统觉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他们重新审视“先验谬误推理”的主题,并提供给读者解读统觉理论的另一个新的维度——主体。于是,如何将主体知识问题置于康德的整个统觉理论中加以考察变得尤为重要,也亟待澄清。本文将遵循“统觉构成主体知识的限制性条件”这一基本立场,既从反面厘清康德批判、诊断主体知识问题的理路,又从正面阐释他限制主体知识的解决之道。展开这些讨论之前,我们先了解下主体知识问题的由来及其能够成为康德的统觉理论批判对象的原由。
一、主体知识问题及合理性依据
早期现代哲学家将哲学的发展转向认识论,不可避免地触碰到关于主体的系列问题。如:主体是否实存?我们如何知悉(意识)它的实存?我们能否获得关于它的知识?众所周知,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心理学家对上述问题持肯定、积极的态度。笛卡尔首次确立由主体出发去研究认识论的原则,采用普遍怀疑的方法确定了不可怀疑的关于主体的实存。莱布尼茨则将主体学说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基于他自己的单子论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主体的先天知识的学说。
在对待主体知识这个问题上,康德试图通过批判理性心理学的主体学说来表明扩展主体知识的企图是徒劳的。所以他对理性心理学家的一整套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梳理。
在康德看来,支撑理性心理学家获得主体先天知识所依赖的唯一性原则就是“我思”,并且他们把“我思”作为研究主题是合理的。首先,“我思”表象能够把灵魂与肉体这两种对象区别开来。思维的“我”(灵魂)是内感官的对象,其本质就是从事思维活动,是经验我思,构成经验心理学的研究主题。肉体的“我”是外感官的对象,其活动发生在外部空间,能够被物理手段所测量、观察,构成物理学的对象。而先验我思虽然自身不掺杂任何经验性的要素,却能将关于“我”的灵魂表象与肉体区分。主体唯有借助先验我思才能不仅思维对象(外感官),也能思维这个思维自身(内感官)。合理的心理学必须首要把心理对象和物理对象进行区分,这无非只能有“我思”能胜任这个角色。其次,“我思”能够对经验心理学起一个范导性的作用,并形成独立的一门科学。尽管先验我思所产生的表象必然会出现在内感官中,经验心理学研究的又是灵魂在内感官中产生的现象,但我们可以不考虑经验心理学中的经验维度,仅对先验我思单独加以研究,继而仅仅从“我思”作的概念推论出一整套的主体的先天知识。综上,理性心理学家可以唯一地以“我思”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主体学说的做法是可行的。
理性心理学单纯由“我思”的概念能推导出关于主体的哪些先天知识呢?拥有主体的先天知识实质上就是:作为主体的主词先天地联结着相关的谓词。康德认为,理性心理学家所推导出来的关于主体的先验谓词都是杂乱的,必须对它们“正位”,继而把它们置于一个逻辑的体系中。他通过考察发现,理性心理学家在考察灵魂(主体)时已经把它作为某个东西来对待,那么就已经将其当做实体了,所以正位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关于“实体”。依照他自己的范畴表以及“前溯推论法”①,实体的范畴属于关系范畴,之前分别是质的范畴、量的范畴,以及模态范畴。质的范畴就是“单纯性”,量的范畴是“单一性”,模态的范畴是“可能性”。于是,关于灵魂的四组先天综合命题就是:灵魂是实体;就其质而言灵魂是单纯的;就其所在的不同时间而言灵魂在号数上是同一的,亦即单一性(非多数性);灵魂与空间中可能的对象相关[3](290)。
二、主体知识产生的根源:对统觉的误解
康德批判理性心理学的主体学说最为关键的工作就是诊断他们为什么会犯错,并且这种错误的推论还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不可消解的幻 觉”[3](288)。下文我将按照康德本人惯常的一般到个别的思维路径,先指出四个谬误推理之间存在的共同错误,再以“单纯性”为例特别地去说明主题。
(一) 先验谬误推理的一般错误
从形式逻辑看,“实体性”“单纯性”“人格性”“观念性”——先验谬误推理都犯了“四名词”推理错误,进一步从认识论上进行探究的话,它们则犯了范畴的“先验——经验”用法混淆的错误。
由于先验谬误推理是以三段论的推理形式出现,所以康德将其纳入一般谬误推理之中考察,并认为先验谬误推理和逻辑谬误推理一样犯了“语言形态的诡辩”[3](345),即“四名词”错误。以《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的第一谬误“实体性”为例,大前提是:“凡是只能被思考为主词的东西也只能作为主体而实存,因此也就是实体”,小前提是:“现在,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仅仅作为本身来看,只能被思考为主词”,结论是:“它也只作为一个主体、也就是作为实体而实 存”[3](295)。大前提中的“凡是只能被思考为主词的东西”与小前提中“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这两个“存在者”表面看起来是指同一个东西,但其含义实质上发生了变化。大前提中的这个存在者既可以作为单纯的思维与意识的统一性的主词来思考,也可以作为在可能的直观中被给予来思考,而小前提中的存在者只能作为思维与意识的统一性这一意图被思考,因此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表面意义一致的名词由于修辞格的诡辩使它在上述两个前提中含义出现了歧义,进而得出了一个本不应该推导出的结论。这种三段论推理把小前提的条件归摄到大前提中,而大前提中的两个词与小前提中的两个词的含义却都不相同,这样一来,整个的推理过程中实质上就出现了“四名词”。
形式逻辑上的错误有着认识论方面的依据。主词“思维的存在者”即“我思”已经被康德解释为伴随其他一切表象的纯粹自我意识,它是给予一些表象综合统一性的自我意识,并构成了客观经验的必要条件,也是范畴运用的必要条件②。理性心理学家却想要把范畴反过来运用于这个“思维的存在者”身上,必然会导致范畴的误用。这样,理性心理学家在谬误推理过程中混淆了范畴先验——经验的运用。因为在康德看来,大前提是对范畴在其条件方面仅仅作一种先验的运用,但小前提和结论却是在归摄于该条件之下的那个灵魂方面作一种经验性的运用[3](89)。说一个范畴作先验运用,就是指它的运用超越了可能的经验或者说没有注意到经验对其的限制。说大前提中的实体范畴作先验的运用,就是因为它的运用独立于把认识的对象归摄于概念之下的形式条件。此时的范畴被称为“单纯的范畴”,这种范畴的运用脱离了可能的经验,在康德那里就被界定为非法的或者说误用。范畴作经验性运用必须借助时间的图型。在“原理分析论”中,康德一一揭示出每一个范畴是如何借助由先验想象力所产生出来的时间图型而与感性事物打交道的。这种作经验性运用的范畴也被称为“图型化的范畴”。因此,从认识论看,先验谬误推理的错误在于,理性心理学家在推理过程中对“单纯的范畴”与“图型化的范畴”作了非法的过渡,即,我们可以推导出所有先验的主词可以是先验的实体,但不能保证某个个别的经验的主体也属于经验的实体。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探究会发现:理性心理学正是出于对统觉的误解才造成了先验与经验的混淆,其推理只能停留在小前提之上的结论,即,作为思维的存在者的“我”是先验意义上的实体。
(二) 根本错误源于对统觉的误解——以“单纯性”为例
康德通过以下的三段论方式论述理性心理学家关于“单纯性”的谬误推理。
这样一种东西,它的活动永远不能被看作许多活动的东西的合作,它就是单纯的。
现在,灵魂,或者思维着的我,就是这样一个 东西:
所以就如此如此[3](312)。
大前提是对“单纯性”的定义。对于“单纯性”,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就是“没有部分”“不可分”。“实体是单纯的”可以被看作莱布尼茨的“单子是不可分的”重述。因为在他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就应当具有无限性和不可分性的“权力”,真正的单元是绝对不可分解的[4]。莱布尼茨用这个命题去反驳唯物主义[5]。他认为,如果像唯物主义那样认为思维的东西可以是物体或者机器,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可分的,但一直可以无限可分下去的东西自然就无法解释知觉现象了。所以实体必须是单纯的。
康德对大前提的处理显然是吸收了莱布尼茨的思想,认为这个定义自身表达了形式逻辑的自明性。他的理由是:当某个东西不能被看作许多活动的东西的协作,那么我们仅依靠理性的推理,而不需要借助任何的直观就可以推导出那个东西是单纯的。因此,大前提在康德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康德是否也接受小前提呢?他借一个思想实验转述了理性心理学关于单纯性的论证,并表明自己的立场。理论心理学的相关论证有两个重要节点。①思维只有依附于一个单个的主体才是可能的。假设我们把思维的内容都孤立地分散开来,例如,把一首诗分成若干个词,分散在不同的思维存在者那里,每一个思维者都获得了思维的一部分(即组成诗的部分词)。但不论这些词如何组合在一起,要是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在同一时间内能意识到这些词构成的整体,这些词的部分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思维。所以每个东西如果真正地能够被我们所思维,就要求我们主体必须意识到所有的部分构成了一个表象(思维)。换言之,思维需要一个单个的主体。②思维的部分既然必须预设一个单个的主体,那么这个思维者就不能是复合物,思维的主体必须是单纯的。
针对理性派的论证,康德认为他们关于①的推论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推论就建立在统觉的先验统一性原理之上②。我们为了能够思维,就必须综合地将思维中复杂的内容综合在一个单个的思维中,这些表象必须属于一个统觉的统一,因此必须需要一个单个的主体。但康德认为关于②的推理是有问题的,“因为由多个表象所组成的思想的统一是集合性的,而且按照单纯的概念来看既可以与在这方面共同合作的那些实体的集合性的统一发生关系(正如一个物体的运动就是它的一切部分的运动的复合一样),同样也可以与主体的绝对单一性发生关系”[3](313)。康德指出,理性心理学家的推理建立在后一种的基础之上,却忽略了前一种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可以赞成理性心理学家的推理,即思维的特征要求必须有一个单个的主体,但不能由此进一步推论出,这样的一个主体本身必须是“绝对的单纯的”“不包含任何相互外在的杂多的东 西”[3](297)。这种情况下的主体也可能是复合的。因为对于思维(如关于一首诗的思想)的统一虽然不能被解释为不同思维者不同的思维(构成诗的词)的联结,但这也绝不意味着这样的思维者自身(思维诗歌的主体)不能是复合的存在者。Sellars从语义学角度将这里的道理一语道破,“作为诸思维的主体的‘我’是一个复数性(思维所依赖的主体其自身是复合的),并不等同于作为诸思维的主体是复数个‘我’(思维依赖于不同的主体)”③。
因此,康德将这个谬误推理的错误归结为对统觉的“我”的本性的理解上:“有一点是肯定的:我通过这个‘我’任何时候都想到了一个绝对的、但却是逻辑上的主体单一性(单纯性),但并非这样一来我就会认识到我的主体的现实的单纯性。”[3](315)也就是说,理性心理学单纯从“我”概念的分析只能得到“逻辑上的主体单一性”,而不能得到“主体的现实的单纯性”。逻辑上的单一性就是一种绝对的单纯性,即我思的综合活动仅仅是单一的活动,而不能包含其他的活动。然而,现实的单纯性,是对经验材料进行统一的单纯的活动,包含了杂多性的内容。理性派试图通过对思维存在者进行抽象的分析就推导出关于该存在者自身内在所具有的性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6]。
康德继续对这个错误的推理进行诊断:“显而易见:如果有人想要表象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他自己就必须置身于这个存在者的位置,因而必须用他自己的主体去置换我所要考虑的客体(这是在任何别的一种研究中都没有的事),而我们之所以对于一个思想要求有主体的绝对统一,只是由于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说:我思(我在一个表象中思维杂多东西)。”[3](314)“我思”与经验对象不一样,就经验对象而言,由于它自身就处于外部感性直观之中,所以“我思”可以对其进行思维。但是,当我们对“我思”进行研究的话,就必须运用我们的反思能力,即将主体置换成客体思”。问题是:我们虽然通过反思将“我思”“变成了”客体,实质上它并不能成为真正客观的实体,因为这个过程仍在主体之中进行,“我思”不可能获得一个外部直观。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谬误的根源在于:统觉的“我思”没有自我直观。
康德对这个谬误的最终结论是:我们可以有条件地接受这命题,“但‘我是单纯的’则无非意味着:‘我’这个表象并不包含丝毫杂多性,而且它是绝对的(虽然只是逻辑上的)单一性”[3](315)。我们可以说“我是一个单纯的实体”,但“单纯的”并不是指经验的意义,这种单纯性并不是如理性心理学家那样将其运用到现象中,如他们认为某物单纯的就是不朽的。
三、主体知识的消解:先验观念论下统觉的主体无法被认识
虽然虚假地产生主体知识的幻觉是出自我们人类的理性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要我们有效地揭示出这种幻觉的先验根据,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去理解、对待统觉的应有之义,我们便能警惕产生主体知识的妄想。如果说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只能称得上是消极的处理主体知识问题,还停留在诊断问题的症结阶段,那么是否还存在一种正面、彻底的解决方案呢?康德最终是如何基于自己的统觉概念真正有效地解决了关于主体的先天知识问题呢?
(一) 主体实存的自明性
关于主体的实存问题,康德赞成理性心理学家的那种经由思维通达主体实存的路径,即我们通过自己的思维就可以意识到主体的实存。但在具体涉及主体实存的自明性问题上,即思维自身通达主体的实存是否还需要逻辑推理时,康德批判了笛卡尔派的观点。与笛卡尔派不同,康德认为我思本身就蕴含着实存,并不需要逻辑的推理。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个有名的脚注中,康德说:“‘我思’正如已经说过的,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并且自身包含有‘我实存’这一命题。”[3](303)紧接着,他又说:“因此我的实存也不可能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被看作是从‘我思’这个命题中推论出来的(因为否则就必须预设这个大前提: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而是与‘我思’命题同一的。”[3](303)这样一些表述都表明,康德主张:当我们说“我思”的时候就意味着它隐含着“我思”的实存性命题——“我在”,我们关于主体的实存直接是由统觉概念自明呈现的,无需其他任何逻辑的推定。
当然,“我思”的命题涉及的实存并不是模态范畴中的“实存”的范畴。“实存”的范畴“并不与一个不确定地被给予出来的客体相关,只与一个我们对之有一个概念、并且想知道它是否也被置于这一概念之外的客体相关”[3](303)。实存性的范畴虽然不像其他非模态范畴可以作为某个物的谓词,但与那些范畴的运用一样,我们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关于规定的对象的概念。当我们想要决定是否有一个现实的对象符合这个概念时,实存性的范畴就生效了。而我思的“实存”命题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我们关于我思的“我”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思维存在者的概念,只是拥有“一个不确定的知觉”“某种只是被给予一般思维的实在的东 西”[3](303)。因此,实存的范畴并不能运用到这样一个“不确定地被给予出来的客体”,即我思中的“我”中。“我的实存”中的“实存”与实存的范畴是不一样的。
(二) 先验统觉的自指示功能
如果说主体的实存是一种自明性的事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先验统觉指向先验主体进而可以建构关于主体的先天知识?康德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原因可以通过先验统觉的自指示功能得以说明。
首先,先验统觉指向主体的方式并不是借助于将某种属性归于拥有该属性的主体进而意识到该主体,因为对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来说,“通过自我这个简单的表象,并没有什么杂多的东西被给予”[3](91)。思维的自我本质上是“空”的,它不能提供直观杂多给主体。这意味着我们对主体的意识并不是以将它包含的直观杂多或者某属性归入主体来进行,而是以其他一种特殊的方式。其次,既然这个“我”不提供杂多,那么主体能够得到说明的方式是“先验的”。康德对此有直接的论述:“但显而易见,依存性的主体通过与思想相关联的这个我只是得到了先验的表明,而丝毫也没有说明它的属性,或者说对它根本没有任何一点了解或知悉”[3](315)。“先验的表明”明确了统觉的自我意识指向主体的特殊的方式。我们能够通过意识自己的(综合)行动来指向自己,并进一步意识到“我”就是这种行动的主体。当我以这种方式,即“通过与思想相关联的这个我”指向自己时,没有任何关于我如何显现的东西呈现给自己,我们不能获得关于我自己的任何属性特征。最后,康德将这种统觉的意识指向主体的确切方式称为“表示”而非“表明”:“因为,在我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中,一切都处于连续的流动之中,而没有任何常驻的东西,也许(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说的话)除了那个单纯的‘我’之外,之所以如此单纯是因为这个表象没有任何内容,因而没有任何杂多,因此它也显得是在表象、或不如说在表示一个单纯的客体。”[3](332)我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并没有表象某主体,而只是“表示”,这种指示主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对主体进行进一步描述,也无需借助对主体属性的知悉方式指向该主体。
当代著名学者Shoemaker将这种特殊的指称自己的方式称作“无确认的自指”(self-reference without identification)。他认为,这种关于“我”的自指功能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不受我们对第一人称代词进行误识的影响[7]。Shoemaker就此援引维特根斯坦对“我”的用法分析。维特根斯坦将日常语言中关于“我”的用法分成两种:一种是“作为对象的用法”(如“我长高了六英尺”),一种是“作为主体的用法”(如“我牙疼”)。前一种情况涉及对某个个别的人、“对象”的确认,因为我们是针对“我”这个确定的对象作出的判断,一旦将“我”误判为其他人,关于“我”的用法就会出错。但后一种情况并不涉及具体的人,而将个人限定在关于“我”的判断中也将变得无意义。所以Shoemaker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作为主体的“我”是免疫于对具体的个人的确认的,这种特征是先验统觉的自指示功能的独特之处。
先验统觉的自指特征表明:对实存的意识与对实存某物的属性的意识是不同的。在康德看来,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前者的地位还优于后者。当我们试图对“我”进行认识时,我们只是围绕着它不断地打转,“因为我们如要对它作出任何一个判断,总是不得不已经使用了它的表象”[3](291)。我们要想认识任何关于我们的谓词,即任何关于我们的认识,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有一个“我”在认识。换言之,我为了能够把相关的谓词归于我自己,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是独立地先于认识的实存者。
所以真正说来,任何判断都包含先验统觉的运用,是后者间接的表达。任何关于“我”的判断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直接表达“我思”,而是预设了它,“所以诸范畴的主体不可能由于它思维到这些范畴就获得一个关于它自己作为诸范畴的一个客体的概念;因为,为了思维这些范畴,它就必须把它的纯粹的自我意识作为基础,而这个自我意识却正是本来要加以说明的”[3](302−303)。先验自我意识并不是像经验自我意识那样关于我的任何判断的直接表达,它不是直接意识。这个特征决定了,我对任何对象都可以作判断并自发地运用到这种意识,这些对象可以是上帝,世界,我自己[8]。
(三) 先验观念论与主体知识问题
我们通过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仅仅意识到“我”的实存,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个体似乎又都拥有关于“我”的知识呢?或者说,对“我”实存的意识如何能够与拥有“我”的知识协调一致?
康德在他的先验观念论立场下对上述问题作了回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两处对他的观念论理念进行阐释。一处是:“但我所理解的对一切现象的先验观念论是这样一种学说概念,依据它我们就把一切现象全部看作单纯的表象,而不是看作自在之物本身,因此时间和空间就只是我们直观的感性形式,却不是看作自在之物本身的客体独自给出的规定或条件。”[3](324)另一处是:“我们在先验感性论中曾充分地证明了:一切在空间和时间中被直观到的东西,因而一切对我们可能的经验的对象,都无非是现象、即一些单纯的表象,它们正如它们被表象出来的那样,作为广延的存在物或变化的序列,在我们思维之外没有任何以自身为根据的实存。”[3](404)从这两处引文可以看出,先验观念论是涉及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分学说,并特别地涉及时间和空间在此观念下应如何理解的问题④。基于先验观念论,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而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因为现象既然是向我们主体显现的对象,那么现象背后必定有一个显现者,这个显现者自身就不能被认识。对于时空,康德就强调它们是我们主体固有的主观观念,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的属性。我们主体正是通过时空先天观念接受自在之物,并由后者刺激我们的感官产生了感性表象,继而由知性的纯粹概念(范畴)去思维这些对象就形成客体知识。自在之物则是那些不能借助时空观念提供给主体的东西,我们却可以借助范畴思维它,所以自在之物不能被认识,但它必须被断定。自在之物的概念从根本上保证了由时空接收到的感觉材料具有实在性。
按照这种理论,主体知识问题便可以通过对“我”进行现象——自在之物的二分得到解决。在范畴先验演绎中有这么一段话:“但正在思维的这个我如何与直观到自身的我(凭借我至少还能把另外一种直观方式设想为可能的而)区别开来,却又与后者作为同一个主体而是等同的,因而我如何能够说:我,作为理智和思维着的主体,把我自己当作被思维的客体来认识,只要我还被通过这客体在直观中给予了我,不过与其他现象一样,并不如同我在知性面前所是的,而是如同我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3](103)这段引文有两点需格外注意。其一,康德明确将“我”区分为客体的我与思维的我,即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先验主体。以统觉与主体实存、主体知识之间发生的逻辑关系来看,我们通过先验统觉可以意识到“我在”(即“我”的实存),但没有任何关于“我在”的知识。然而一旦先验统觉开始规定我的实存时,就意味着它开始要把“我”当作一个对象试图去认识,继而使得我可以借助内感官/经验性统觉去规定我的实存,其结果是,我不仅能够经验性地意识到这种实存,还将这种实存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心灵状态的主体呈现给我自己,形成“我对自身所显现的那样”的知识。因此,对我的实存的规定才意味着我们能获得关于自己具体的确定的知识,这种情形下的经验自我是一个被规定了的实存,处于时间中,是受因果作用的。这样一种自我是由一个人的所有的表象状态构成的,包括感情,行动等[9]。先验自我/先验主体只是一般表象的形式[3](291),是认识的主体,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的规定。
其二,经验自我与先验主体仍然是“同一个主体”。这里涉及对康德先验观念论进一步的理解。如果我们将现象——自在之物的区分理解成现象、本体是两种不同种类的对象,进而分属不同的世界,就可能会误解康德的本意[10]。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它解释成“一个世界”“双重视角”的理论,即,虽然现象是知识的对象,自在之物是独立于我们知识并实存的对象,但这两种对象仍是同一个东西[11]。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个物。当我们用现象的眼光看它时,它就是时空中的对象,当我们转而用本体的视角看待它时,它就是缺少时空形式而存在的对象。只有这样的解读才能合理地解释康德为什么将两个不同名称的“我”又归于同一个主体。
四、结语
通过对康德统觉理论中的主体知识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主要揭示出:①理性心理学构建主体知识的合理性依据是“我思”的统觉概念;②他们之所以自认为能够获得关于主体的先天知识根源于对统觉的误解;③统觉的先验自我意识所指向的主体仅仅意味着主体的实存,并非主体的先天知识,而康德本人对主体知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应该在先验观念论的视角下被理解。统觉就是解锁主体知识问题的一把钥匙,它构成了主体知识的限制性条件。因为我们既然通过统觉的概念不能推导出任何主体的先天知识,并且正是对统觉的误解才使我们形成关于主体知识的幻象,那么,消除这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限制了主体知识的扩展。先验统觉的功能性特征决定了它作为先验自我意识只指示主体实存,不表象主体、不能构建主体知识。我们表面上似乎拥有关于“我”的知识,实质上只是一些关于客体的自我知识。所以,在先验观念下,康德借助统觉的概念(先验统觉和经验性统觉)达到了将先验主体和经验自我相区分的目的,在理论层面真正解决了主体知识问题。
虽然主体知识问题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谬误推理中,但正如文中呈现的那样,先验演绎中的相关统觉思想(如统觉原理),即积极构建客体知识方面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在这里只是对统觉理论中的一个方面,即主体知识问题作出的探索性工作,如何全面、彻底地澄清统觉理论内部结构的思想承接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66. 所谓“前溯推论法”,即给定某物之后,追溯它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康德看来,只有这样的一种综合方法才能保证由实体性范畴出发推导出的其他先验谓词能够产生先天综合命题。
② 康德在范畴先验演绎中提出了统觉的先验统一性原理,也就是关于“我思”的著名命题:“‘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可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里面被表象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叫直观。所以直观的一切杂多,在它们被发现于其中的那同一个主体里,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参见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9.)
③ Sellars的原文是“the subject of thoughts, the ‘I’, is a plurality’’ is not the same as “the subject of thoughts is a plurality of ‘I’s’’. 文中括号里内容系笔者所添加。参见Sellars W. Metaphysics and the Concept of a Person[C], in Essays in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Dordrecht: Reide, 1974: 239.
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先验观念论是康德哲学的基本立场,而非只针对时间和空间。康德在这里只提时间和空间,是因为他在先验感性论里对时间和空间的主观观念性和经验性实在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因而借此表明他的观念论立场。
[1] KLEMME H. Kants Philosophie des Subjekts[M], Hamburg: Meiner, 1996.
[2] AMERIKS K. Kant’s Theory of Mind: an Analysis of the Paralogisms of Pure Reas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3]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 莱布尼茨. 新系统及其说明[M]. 陈修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9.
[5] WILSON M. Leibniz and Materialism[J],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4, 3(4): 510−511.
[6] KITCHER P. Kant’s 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3.
[7] SCHOEMAKER S. Self-Reference and Self-Awareness[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8, 65(19): 556.
[8] CARR D. The Paradox of Subjectivity: The Self in the Transcendental Tradition[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2.
[9] BROOK A. Kant and the Mind[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91.
[10] CLEVE J. Problems from Kant[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
[11] ALLISON H.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2−45.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in Kant’s theory of apperception
TANG Hongguang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Kant, by criticizing rational psychology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tries to indicate the futility of attempting to expand the Subject’s knowledge. Concept of apperception is the rationalization basis for rational psychology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s knowledge. We cannot induce any subject’s innate knowledge through apperception; misreading apperception leads to illusion about the Subject’s knowledge, and eliminating this misreading is restricting the extending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in some sense. The functional feature of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determines that it denotes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ject as transcendental self-consciousness,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the Subject or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s knowledge. Seemingly, it includes the knowledge about “me”, but essentially, it is only self-knowledge about the Object. Under the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Kant, by achieving the aim of differentiating transcendental Subject from experiencing self by means of apperception, solves in theory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Kant; rational psychology; theory of apperception; the Subject’s knowledge
2017−12−15;
2018−04−15
长沙学院人才引进科研基金项目“康德‘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中的统觉思想”(SF1611)
唐红光(1985—),男,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长沙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心灵哲学,联系邮箱:thg@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04
B516.31
A
1672-3104(2018)05−0026−07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