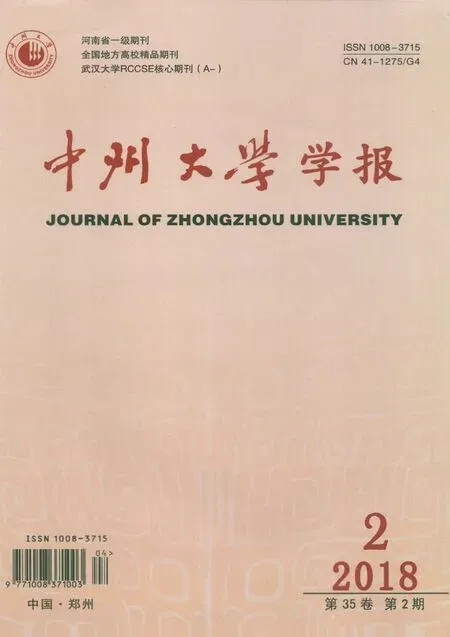万杉论坛:生态文明与佛教研讨会综述
2018-01-14刘海燕
刘海燕
(中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郑州 450044)
一、生态文明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佛教思想中的生态文明
胡振鹏(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原副省长,江西生态文明促进会会长,庐山庆云文化社名誉社长):人类必须以更前瞻的眼光,更高的责任感,转变传统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调整对待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控制自身的行为,不能把自然作为无限索取、任意支配的对象,从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员,尊重自然规律,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回馈自然,有目的地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系统,在最大程度上与自然和谐相处。
王先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依照对于人类在地球和宇宙中的地位的看法,可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类的生命是珍贵的,其他一切生物生命的价值要用它们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来衡量,所以,就有益虫和害虫、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和植物等种种名目,它们的认定,就是人类利益的标准,倘若人的认知变了,害虫也可以变成益虫。而在生态中心主义看来,一切动物的生命都有其价值,这价值与人类对它们的认知无涉,所有动物以及植物的生命应该得到与人类的生命同等的尊重与保护。
佛家的基本信念是众生平等。众生平等的核心是生命权的平等,每种生命都需要尊重。因此,佛教戒杀生,把杀害牲畜等一切有情之生命看作是十恶业之一。这里也潜藏了一个悖论,素食吃的是植物,植物也有生命,难道吃植物就不是杀生吗?人类要生存,不进食就会失去生命,绝对的戒杀办不到。地球上的生物链是亿万年形成的事实。这个事实使生态中心主义、使佛家的学说难以圆满自洽。弘一大师和丰子恺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是自觉的身体力行的生态主义者,他们主张保护一切生物的生命权。他们共同创作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以诗文。他们在画集中说,可以用扇子驱赶苍蝇蚊子,但不能扑杀……他们也承认地球上生物链的无法打破,承认人不可能完全避免侵害其他生物的生命,客观上提出了寻求众生平等的更加缜密的理路。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也是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所遇到的困难。生态学家、伦理学者一直在寻找化解这一悖论的途径。
我觉得,佛家的著述言论里,有不少相应的思想资料,值得我们重视。首先,对于“杀生”,佛教的典籍常常并不局限于从一时一事去看待,而是把大千世界作为整体,放在流转中来看。不杀生,并不是无分别地徒劳地阻止一切生物个体的死亡,而应该理解为维护地球良好生态,遏制地球生态的恶化,使得地球环境良性地流转发展。人类作为高等的创造了文明的动物,应主动协调人群之间、当代与和后代之间、人类与各种生物之间的利益;必要时放弃个体的、部分族类、部分人群的利益,维护地球长久的生态利益。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正是以众生的快乐为快乐,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
释庆道(湖北武汉古河禅寺住持):佛教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佛国净土世界是理想的生态王国,众生平等是佛教生命伦理的思想核心,慈悲护生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和谐相生是生态文明的内涵所在,心灵环保是生态文明的至高境界。
释仁静(庐山万杉寺监院,庐山庆云文化社副社长):佛教是重视自然生态保育的宗教。佛教里的杀戒、因缘观、正报依报思想,对自然生态起着保护作用;历代僧人建寺,高僧护持林木的情怀,“一花一草无不是禅”,其众生平等的意识和慈悲心,维持并保护着生物的多样性。
青青(《河南日报》三门峡记者站站长,作家):《访寺记》一书是我多年来走访寺院的结果。我走访了100多座寺院,这些寺院大多数都在山里。在访寺的过程中,深感佛教是重视自然生态的宗教,佛教寺院与自然环境之相融相生。
自古以来,寺院建筑常与山林融合,不破坏森林环境,寺院环境保护了自然生态,而自然生态又使寺院格外清幽出尘;僧人修行力求淡泊简朴,不侵犯自然资源,都是与万物同体共生的表现;历代的高僧大德,植树造林、整治河川、珍惜资源,倡导戒杀素食、放生护生,更是自然生态的具体实践者。
在访寺的过程中,我发现佛教徒们不仅用心维护寺院及周边的环境,而且广泛参与植树造林活动;很多寺院已经开始倡导文明进香,禁止烧有污染的香,以减少污染;提倡用鲜花供佛,不使用塑料假花,以解决假花难分解的难题;提倡资源回收,节水节电的细节随处可见;许多僧人的衲衣补了又补,居室里一床一桌一凳,简朴至极;他们信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寺院周围空地里种菜,种粮食,把劳动作为修行的一部分。他们这些生态环保的作为和意识,应在全民中推广。
二、佛教美好生活愿景勾勒·农禅的生态释义
张嘉如(黄河科技学院兼职教授,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副教授,宗教生态学学者):在现实生活里,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人类的幸福、动物福祉与环境净化是一体的。佛教作为一种实证的宗教,有着以慈悲为主导的关怀论述和长久的僧团传统,可以为我们当今思考社区建设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点,也可以作为我们衔接社区行动与学术界生态论述的一个平台。
“美好的生活”与精神安全感:美好生活的愿景是建立在精神安全感上。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缺乏精神安全感的根源为无名,就是迷、对生命根本错误的理解。一个缺乏生命安全感的人,无法过一种全然美好快乐的生活。在生命表现上多半呈现出来的就是贪生怕死,希望在一生中得到更多的财力、名利和权力。在集体层面上,一个没有精神安全感的社会,容易出现拜物拜金的风气,耽溺物欲。当前物质文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物质安全感取代了精神安全感。佛教的缘起观、修行和解脱,可以作为当今讨论精神生态的参考。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学者墨顿教授(Mimothy Morton)认为,生态不仅关乎全球变暖,也不仅关乎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关系,真正的生态精神更关乎爱、绝望与慈悲。
佛教美好生活观与僧团的重要性:佛教更接近生态哲学,因为它的美好生活或幸福观是“不二”的,它与外境是一体的。在当今世俗化的社会,许多现代科学对幸福、快乐的论述也多半放在个人主义的视角里。而亚里斯多德提出的美好生活基本上基于社会社区,人的福祉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此限制影响到个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条件与想象。在对美好生活观的理解和实践上,佛教与亚里斯多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与亚里斯多德一样,佛陀相信人的善与恶皆出于人性。亚里斯多德认为理性可以作为道德指导方针,而佛教不以理性取径,因为理性为思想的产物,属于六识的部分,佛教承认的只有慈悲心,也是“无我”精神境界的显露。佛教的利他主义与西方的道德论述不同,它并非出于对集体的道德责任义务,而是出于无我观及其体现出来的慈悲心。其次,与亚里斯多德一样,佛陀也重视训练和教育,但与亚氏不同,他把道德、修行与实证后所得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并创造僧伽制度,提供一个社区空间让大众能够共同生活、共同修行。从入世利他的心行之中,达成无我的自在解脱境界。由此可以看出,以利益众生为主的僧团建构和护生传统,可以作为当今生态社区建构的理论参考。
宋丽丽(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深层生态学认为,如果不从人自身的发展观念与生存方式上改变,而仅仅依靠技术的力量,人类只能在邪恶的怪圈里打转,其结果是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因此,深层生态学对人自身的改变提出了自我实现、生态智慧以及共生平等的发展观念。在深层生态学的带动下,近几年出现了倡导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回归土地,能动地走出危机,维护与有机及无机自然环境互相依存的关系。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生态智慧以及共生平等的发展观念,与农禅的融禅于农、以农悟道的禅修行为产生了交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禅是深层生态学的现实维。
农禅始于隋唐时代的道信,在黄梅双峰山率500信徒定居,改变了僧侣们依靠自己乞食和施主布施的修行方式,立足一方土地生产食物,开启把农事劳动生产纳入禅修之中。百丈怀海是农禅的确立者,他确立了农禅成为农业粮食生产与禅修并一的制度,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劳动在禅修中的地位被确定下来,并身体力行,实践众生平等。农禅的历史发展过程折射着两个层面的生态智慧:其一是精神上的自我实现,或戒定慧需要最大限度地守护一方土地,繁荣一方万物;其二,劳作对于生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是心性自在不变的媒介。
劳动、守护一方土地以及土地生命共同体的美丽与稳定,正是工业化之后急需张扬的生态智慧。随着农业化、化学化农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杀虫剂、化肥、除草剂的滥用,极大地破坏了土地生命共同体的健康。工业化的农业把人与自然隔离,让人类远离劳动、远离一方土地,同时也远离了人生存的根本。农禅的自我实现、自给自足以及劳动修行的生态内涵具有带领人们回归自然的定力。湖南的药山寺、江西的曹山宝积寺以及北京的龙泉寺,重新兴起的农禅,赋予了有机农业深层生态学的意义。
三、先哲诗人的生态思想及生活方式对当今时代的意义
傅修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校长,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陶渊明《归田园居》中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等,令躬耕田陇焕发出动人的诗意光辉。陶渊明在诗歌美学史上开拓出的劳动之美,与田园之美一起构成了桃花源想象的魅力所在。这一想象使桃花源之类的山间盆地摆脱了平庸,让人看到那是一个灵魂与肢体都能获得安顿的所在。在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当下,我们回头再看陶渊明,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桃花源想象中,还是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这位伟大的先行者都在倡导一种“资源节约型”加“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模式。我们应从中汲取教益,让这种文化基因代代相传,这也许是当前陶渊明研究的最大意义所在。
王晓华(深圳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万衫寺所在的庐山是中国生态群落中的标志性存在。无数动植物在这里繁荣生长,众多文化名人在这里诗意地栖居。陶渊明就是生长于此的田园诗人。他因退隐乡野而成为亘古的传奇,因淡泊明志而演绎了简单生活的古典范本。1500多年过去了,但他的故事依然引发无限的遐思。对他感兴趣的不仅是传统的隐士,更有我们这些生态主义者。我们从他淡泊的生活态度中发现了拯救性力量,看到了再造桃花源的希望,开始了这次朝圣之旅。此次会议在他的故乡召开,实际上是向其致敬的一种方式。
胡迎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赣鄱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陶诗中对村庄庭院、附近树木、远处岭陆、湖水洲渚都有生动的描写,以悠然之心看自然之物,心物交融,物我无间,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他写心态有乐:知足乐,饮酒之乐,与邻为友之乐,尚友古人之乐,读书之乐;心态有悲:以饮酒与赏菊为消忧解愁之方式。陶渊明影响大的原因:自身气节高,辞官不做,甘贫乐道;客观上社会意义大,历代士人失意,多以陶渊明来安慰自己,以恬淡之心看待得失。
刘晗(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苏轼一生与佛教结缘颇深,对不二法门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有着戒杀生的慈悲心、尚素朴的生活方式、与天同一的虚空心境,其浓郁的佛教情怀蕴含着万物平等、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是北宋文人服膺的“居士”。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漂泊不定,每到一处,无论如何困窘,总是买田筑屋,遍植林木,再植以瓜果蔬菜,努力营造一方富有诗意的居住场所。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一生德及草木、恩施动物。
苏轼一生多穷困潦倒,即使身处富贵之境,也始终抱持素朴勤俭的生存理念,过一种简单、素朴的日子。他视“甘脆肥浓”之物为养生大忌,提倡亲近自然、朴素简淡的饮食方式。在苏轼的诗文中,随处可见许多有关素食养生的内容,如枸杞、菊花、蔓菁、荠菜、桃花等,均为诗人所喜爱。
四、生态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日常生活应有佛学和生态文明的维度
王茜(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谈论生态批评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必然要包含与中西古今的对话精神。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谓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不是传统固有的,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现代和传统对话的视域中生成的。如生态批评在使用某些传统的概念话语时,应当首先将他们还原到它所在的具体生活世界中去,查看它们在其所在的历史时空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明确其当时所在的具体生活世界与我们所在世界的差异性,然后才能就其对当代世界的价值和适用性做出判断,而不是直接将其从历史语境中抽取出来,直接应用于当代问题的阐释与回答。
纪华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创造性吸收和发展的过程。佛教中国化的前提是中国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佛教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中国化,还与佛教中自身建立在缘起理论基础上的圆融平等、慈悲利他、中道智慧与净心行善等内容是分不开的。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的,没有独立自存和永恒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的,所以人与人、人与自然都处在互相依赖、互相联系之中。同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共存于这个世界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的缘起理论及其圆融平等、慈悲利他等思想,对于增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缓解因宗教间的不宽容而带来的冲突和暴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僧团组织制度方面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形成独具特色的农禅并重的传统。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道安大师的尼僧规范,后来百丈怀海禅师创始的禅林清规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性制度,形成了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
刘海燕(《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我们的日常生活应有佛学和生态文明的维度。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义务教育中的生态环境教育,已经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复杂的问题,教育效果也不仅仅是课堂教育所能完成的,教师、学校管理方、社会生活环境等,都影响着教育的效果。首要问题是,学生所接受的课堂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得不到印证,造成了认识和生活的疏离,随着环境的改变,功利性认知很快就会取代生态性认知。怎样让生态性认知在一个人的心中扎下根,让人心回转?
1.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日常生活中应有佛学和生态文明的维度,潜移默化,而不是灌输生态教条。践行高于知识。2.社会各界,如餐饮、服饰、各种消费、娱乐界等,倡导简约、绿色为美学生活的标志。3.研习佛法,深悟世间原初之道,和世间万物美好相处,自我的佛法修炼亦是生态践行训练,惠及自我也惠及万物。4.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自我心智的高度,就是教育的高度。自我对成功、生命、文化等,都应有超越时潮的理解和坚持。
总之,让简洁、天然、绿色理念和仁爱之心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让我们的心变得安宁美好一些,从有益于地球和宇宙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立场,来思考和做事。
张云江(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物欲和信息的膨胀等,使现代人越来越焦虑,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在改善个体心灵生态方面,佛教禅修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方法之一是坐禅,心理习惯的改善;方法之二是观念的调适。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及提议,以万杉寺和庐山区域为例
项镜泉(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庐山生态文明建设应按庐山市全境域统筹规划,起点应高;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作为总体布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方针,摒弃片面追求GDP快速增长的思想和行为。生态文明建设绝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文化的传承和自然条件变化规律等紧密结合起来综合协调进行。
贺伟(江西省庐山管理局作家协会主席):几千年来,人类在庐山所进行的宗教、教育等方面的活动以及近代涌现出的别墅山城,都十分注重与自然山水的融合,所建的寺庙道观、亭台路桥、书院学堂、民居别墅都与自然山水交融辉映,促进了庐山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完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得到了体现。
李勤合(江西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庐山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尤其是以杏林为代表的道家生态文化、以桃源为代表的儒家生态文化(陶渊明不仅贡献给中国文化悠然自得的田园诗,更贡献给中国文化一个以桃源为代表的儒家生态文明理想)、以万衫为代表的释家生态文化、以牯岭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生态文化,具有典型的生态文化意义。探求庐山文化中有关生态文化的线索,对建设当代的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昭希(黄河科技学院生态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馆员):就生态文明建设来说,首先需要转变自身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摆正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真正深刻认识到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才有可能从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进行改善和调整,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释能行(庐山庆云文化社社长,庐山万杉寺住持,江西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万杉寺为庐山五大丛林之一,历来属于禅宗寺院,因生态而得名,宋代高僧太超禅师种植杉树万株,受到宋仁宗皇帝敕封寺额“万杉寺”。
万杉寺的历史和生态实践,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以下参考:1.传承千年的生态文化。苏辙赋诗:“万本青杉一寺栽,满堂金气自天来。”朱熹造访万杉寺得诗句:“门前杉径深,屋后衫色奇。”2.充满灵性的生态环境。万杉寺坐落于名山名湖之间,背靠庐山庆云峰,南邻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万杉寺的生态之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之美,而更在于它的灵性之美。它的灵性之美,首先体现在建筑上,深山藏古寺,万杉寺的殿阁楼台、飞檐翘角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宛如画境。3.自净其意的生态精神。指通过断恶行善的修持来净化自己的思想意念,从而达到净化内心、身心清净、回归到物我一体、澄明空寂的本有自性,这是佛法修行的核心。4.和合共济的生态文明。万杉寺千年的生态实践,体现的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和合共济,心灵与环境的和合共济,精神与物质的和合共济。
作者补记:庐山市原名星子县,即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故乡,会议在此召开,也表达了对这位简约而诗意地生活的生态先贤的敬意。由会议发起者鲁枢元教授提议,此次会议餐均为素食,也体现了生态学者的践行理念。在大会及小组发言中,庐山籍及庐山本地的学者,对庐山区域的生态现状充满忧患意识,他们的历史记忆和强烈呼吁令听者动容,正如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