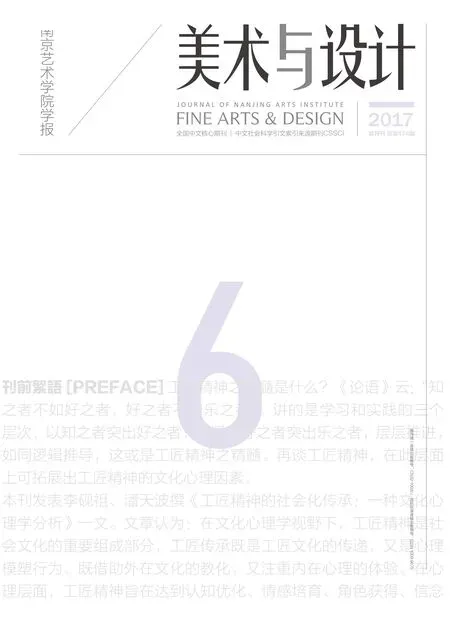版刻楷书横画末端三角形的出现时间
——兼论国图藏《龙龛手鉴》等宋刻本非“南宋早期刻本”①
2018-01-09刘元堂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刘元堂(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版刻楷书横画末端三角形的出现时间
——兼论国图藏《龙龛手鉴》等宋刻本非“南宋早期刻本”①
刘元堂(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在本文通过对存世南宋浙刻本版刻楷书的爬梳与对比,寻绎出其横画末端三角形的变化脉络:南宋早期直角三角形罕见,中期直角三角形量少且形小,晚期则大量出现。并以此为根据,结合刻工等因素,论证了被专家定为“南宋早期”的国图藏本《龙龛手鉴》,应是宋末元初或者更晚的刻本。
版刻楷书;三角形;宋刻本《龙龛手鉴》
“版刻书法”是指通过写稿、上版、镌刻及刷印等工序使书迹得以保存的书法样式。②较早提出“版刻书法”概念的是祁小春先生。见祁小春.中国古籍版刻书法例说.立命馆文学.1997年第549号。
版刻书法的主要书体是楷书。自唐到北宋,以浙刻本为代表的版刻楷书,基本忠实地再现了颜、欧等唐楷面貌。但至明中叶,版刻楷书演变成僵化的“宋体字”或“仿宋体”。横画末端的三角形是宋体字的典型特征,但这种特征最早起于何时呢?
版刻楷书是书手与刻工共同合作的结果。刻工的刀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版刻楷书的发展进程。本文通过对存世南宋浙刻本版刻楷书的爬梳与对比,寻绎出由刀法所导致的横画末端三角形变化轨迹,这不仅使文字发展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对版本鉴定也会起到细化作用。
一、版刻楷书横画末端三角形在宋刻本中的演变
(一)南宋早期——横画末端直角三角形罕见
南宋前期的版刻楷书书法风格,继承了北宋的特征:即以模仿欧、颜、柳等唐楷名家书迹为能事,与唐楷区别不大。刀法上,也基本上按照唐楷的形状进行镌刻。刻工遵循写手的底稿字样,丝毫不爽,圆润细腻,尽力忠于原作施刀。下面以《事类赋》(图1)一书为例加以说明。

图1 宋绍兴十六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事类赋》
宋绍兴十六年(1146)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事类赋》(国图藏),匡高22.2厘米,宽15.9厘米。半页八行,行十六至二十字不等。小字双行,行二十五至二十七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钤印: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赵礼用观、项元汴印、子京父印等。刻工孙勉、陈锡、徐高、丁珪、毛谅、弘茂、王珍等都是南宋初期杭州良工,又刻过《广韵》、《乐府诗集》、《水经注》、《毛诗正义》等书。是书字体取法欧阳率更,字口清晰,无断裂痕迹,系新硎之物。笔者通过对比,发现该书卷一页一的字体具有典型意义,基本可以代表南宋早期两浙刻本的刀法特征。
《事类赋》卷一页,一共有大字五十个,小字五十六个。大字横画末端形状基本可以分为a、b、c、d、e五种类型(图2)。其中大部分大字及全部小字属于a型,横画末端形状较为圆润,与欧阳询《九成宫》《皇甫诞碑》等相似。属于b型者占少数,一般是短横的特征。c、d、e三种类型都各有一例,属于偶有出现。其中c型末端呈细小的、近于等边的三角形,应引起关注。翻阅该书的其它页,情况与卷一页一基本相似:a、b两种类型最为常见,c、d、e三种类型极为少见。偶尔会有其它的奇特形状,也是昙花一现。

图2 《事类赋》横画末端形状类型表

图3 《事类赋》横折形状对比
该页横折的刀法,可分为 a、b 两种类型(图 3)。a型横折上方并不凸出,b型则在横、折交替处做了断笔处理,原本两三刀即可完成的衔接,变为多刀。该页乃至全书的横折,除了极少数的b行外,几乎全是a型。
就笔者所见的六十余本南宋早期浙刻本来看,情况和《事类赋》较为一致。横画末端大多较为圆润,基本上按照唐楷的笔画特征加以镌刻。横画末端偶尔出现凸出的三角形,形制也较小。横折也如唐楷之法,极少作夸张的耸肩形状。

图4 方坚所刻《通鉴纪事本末》卷十页三十三横画末端特征
(二)南宋中期——横画末端直角三角形量少形小
南宋中期浙本的刀法基本延续了初期的特征,变化不是非常明显。只是刻工通过刀法改造笔法的意识越来越重,比如嘉定十三年(1220),陆子遹刻本《渭南文集》,字体的竖画开始变得笔直,缺少韵律。表现在横画末端形状上,大多刻本依然延续初期a型和b型两种形态,只是渐趋方硬和浅薄,古意渐失。
值得特别注意的,在中期个别刻工的刀下,横画末端开始出现了小批量的直角三角形。以南宋中叶杭州名工方坚为例,①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修订本)》将方坚定为南宋绍兴间杭州地区刻字工人,不妥。请参见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修订本):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111。他参加过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本《春秋左传正义》(国图藏)的初刻工作,还参加过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易注疏》《周礼疏》等书的镌刻工作。在其所刻宋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刻本《通鉴纪事本末》(国图藏)②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二书中,对宋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刻本《通鉴纪事本末》做过严密的分析和考证,证明该书为孝宗初刊本无疑。请参看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27-135及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 .2009:228-229。卷十页三十三中,横画末端开始凸出三角形,甚至是陡峭的直角三角形,用刀锋利。(图4)该页是笔者所见宋刻浙本较早出现大量三角形的版页。但该书其他刻工刀法却一如南宋早期,极少见到直角三角形。在方坚所刻宋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本《春秋左传正义》③宋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刊刻时间、地点可靠,参看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图版八十的说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1。卷一页八里,只有大字“书”及小字“云”两字略带直角三角形状,并不明显,形制较小。是书其他南宋刀工如李侃、金滋、张明、方至等也是如此。说明在南宋中叶,横画末端直角三角形并没有广泛出现。
(三)南宋晚期——横画末端直角三角形量多形大

图5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

图6 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卷十二页一 局部
南宋晚期的版刻楷书,其欧体特征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异。以书棚体为代表的版刻楷书,更加僵化板结,整齐划一,状如算子。与其相呼应,此时期楷书的刀法特征极为明显,刻工的刀法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对各种笔画的刊刻几乎可以无视笔法的存在,千画一面,自成体系。在部分刻本里,横画末端的直角三角形已经大批量出现,且三角形的高度超过横画高度的两倍以上,成为南宋晚期浙本刀法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明中叶成熟的仿宋字的主要特征之一。字迹横折处呈现夸张的耸肩状,可以作为此期特点的辅助佐证。以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南图藏)(图5)为例,该书框高26.5厘米,宽19.1厘米。④《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解题部分将该书高、宽数据颠倒,误。见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5。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左右双边。钤有“八千卷楼珍藏善本”“八千卷楼藏书印”“钱塘丁丙藏书”“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等印。字体横平竖直,刀锋方锐,横画末端直角三角形量多且形大(图6)。横折处也大都作夸张的凸出状。在宋刻本《春秋经传》(国图藏)、宋咸淳七年(1271)吴安朝等刻公文纸印本《忠文王纪事实录》(国图藏)、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国图藏)①该书只存卷四至六,卷一至三钞配。此书有明翻本,目录后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一行。黄丕烈因此在书后跋语称:“此即所谓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也,且余所藏南宋书棚本,如许丁卯、罗昭谏唐人诸集,字画方板,皆如是。”傅增湘在《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中持相同意见。参看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 2009:621-622(图7)、宋咸淳九年(1273)刻本《无文印》(辽图藏)②该书为罗振玉获自日本,盖宋元时倭僧携归之书。属宋咸淳间浙刻本无疑。参看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9:1267。(图8)、宋临安府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刻本《宾退录》等书籍中,大都呈现此种特征。

图7 宋书棚刻本《图画见闻志》卷六页十三 局部

图8 宋咸淳九年刻本《无文印》卷一页一 (局部)

图9 越州本《周易注疏》刀法对比

图10 越州本《周礼疏》刀法对比
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周易注疏》(国图藏)和《周礼疏》(国图藏),即世称的越州本或八行注疏本。二书在南宋初年初刻后,又分别在南宋中叶和元初做过补刻工作。以《周礼疏》为例,第一期徐亮、朱明、陈锡、王珍、毛昌、陈高、徐茂等为南宋初期杭州名工。第二期方至、王恭、方坚、宋琚等为南宋中期补版工人。第三期郑埜、徐囦、陈天锡、徐友山、李德瑛等为元初补版工人。其中元初刻工大部分来自南宋晚期,因此刀法特征和南宋晚期没有太大区别。三期刀法共存一书,各期刀法特征分明,向我们展示了南宋至元初的刀法演变史。其中横画末端形状及横折形状与上文总结的南宋早、中、晚三期刀法特征完全一致。(见图9、10)

图11 南宋早、晚期典型横画对比图
综上所述,南宋早期两浙地区延续了北宋的刀法特征,仿照欧体为代表的唐楷笔画形状,刀法圆润,横画末端极少出现凸出的三角形,横折处也极少出现耸肩状。中期属于过渡阶段,横画末端开始有少量直角三角形出现。晚期则刀法犀利,出现大量三角形甚至陡峭的直角三角形,横折处也出现夸张的耸肩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在明中叶成为宋体字的重要特征之一。
南宋年祚毕竟只有一百五十余年,前、中期两浙地区刀法特征无法作截然的区分。由于部分中期刻工在前期也参加过书籍的镌刻工作,或者他们的师傅或父辈都是前期刻工,在技法上不免有师徒相承的惯性。因此前、中两期的区分不十分明显。但是,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已经相距百年之久,一位刻工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六十年,所以南宋前期与后期刻工风格差别还是极其明显的。两期横画末端迥然不同的形状便是最好的例证(见图11)。这为我们对南宋版本鉴定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
二、国图藏《龙龛手鉴》等宋刻本“非南宋早期刻本”
《龙龛手鉴》,原名《龙龛手镜》。为避宋翼祖讳而改“镜”为“鉴”。辽僧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撰。内容为解释佛教经论中的文字,是研究佛经尤其是六朝至唐代写本的重要参考书。该书取偏旁分部、各部首及各部之字,依平、上、去、入四声排列,每字下详列正体、俗体、古体、今字以及或体,详细说明各字之古今字形、反切、字义等,并注释其音义。书成于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计收录26430余字,注163170余字。

图12 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本《龙龛手鉴》序及其局部刀法特征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二”载:“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辩。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记录了《龙龛手镜》由辽传宋,并由蒲宗孟在浙西覆刻。查宋史,蒲氏是在神宗或哲宗时徙知杭州。故宋代最早的覆刻本当在此时,覆刻时改名《龙龛手鉴》。惜蒲本已亡佚。现存高丽《大藏经》中收有辽刻《龙龛手镜》,存一、三、四卷。1985年,中华书局曾对此本做过影印,缺失部分以涵芬楼藏本补齐。
被当作宋刻本的《龙龛手鉴》,现存以下几个版本:
一是涵芬楼藏宋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匡高26.4厘米,宽18.1厘米。半页十行,行无定字。白口,左右双边。仅存卷二上声一册。刻工有朱祥、沈绍、朱礼、胡杏、陈乙、王固、何全、张由、胡山、徐文、王成、王因等二十余人,其中朱祥、沈绍、朱礼、胡杏,南宋初年又刻《乐府文集》《资治通鉴》《徐铉文集》《昭明文选》等书,故此书当为南宋初年杭州地区重刻蒲宗孟本。此为传世宋刻中最古的一本[1]。张元济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中,作跋称是书乃由辽入宋时最初覆刻本,为北宋剞劂,有误。下称涵芬楼本。
二是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图12)。匡高26厘米,高18.7厘米。半页十行,行无定字,小字双行,大字一约小字四。白口,左右双边。版心单鱼尾,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卷数及页次,最下记刻工。刻工有范子荣(序言)、实新(或新实)、实、囻宝、范(以上卷一)、澄、张良、张、良、何、郑林(以上在卷二,卷二为补抄)、李生、林、虞、林盛、徐永、徐等(以上卷三,卷三包含了卷四)。卷内钤有“子晋”“汲古阁”“毛晋私印”“汲古主人”“阆源真赏” “汪士钟印”“铁琴铜剑楼”“瞿氏秉清”“绶珊经眼”、 “祁阳陈澄中藏书记”等印。是书初为明末毛晋汲古阁插架之物,后归黄丕烈士礼居,又归汪士钟艺芸书舍、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澄中等,最后归国家图书馆。其中卷二缺,系毛晋影宋钞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即是依此本影印。下称汲古阁本。

图13 台湾故宫博物院天禄琳琅本《龙龛手鉴》及其局部刀法特征
三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图13)。据《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著录,四卷全,版式与汲古阁本大致相同,但非一刻。刻工除了囻宝写作“国宝”、郑林写作“郑材”外,其余刻工与汲古阁相同。序文二页、卷三首页之前半页及卷四末页为补抄。钤有“吴城”、“吴城字敦复”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据《读书敏求记校证》引陈鳣说,是书系吴氏得之鲍氏知不足斋,后为清宫天禄琳琅藏本。下称天禄琳琅本。
四是傅增湘双鉴楼藏宋刻本。行款版式、版心记字数及刊工人名与汲古阁本《龙龛手鉴》大致相同,但非一刻。有明徐 跋及武林高瑞南藏印。[2]《四部丛刊续编》以其卷一平声、卷三去声、卷四入声及涵芬楼所藏卷二上声为底本影印。下称双鉴楼本。
以上四本《龙龛手鉴》,涵芬楼本字体取法欧阳率更,线条敦厚,刀法圆润,气息古朴,横画末端极少有凸出的三角形,为典型的南宋早期浙刻本风格。《中国版刻图录》将其定为南宋初年杭州地区刻本是正确的。后三者因为卷前有辽统和十五年(北宋太宗三年,997年)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序,所以分别被明徐跋(在双鉴楼本《龙龛手鉴》卷首)、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等错认作辽刻本,后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及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因避讳将“镜”改“鉴”等根据,遂将三者定为宋刻本。我们把三者字体、刀法与涵芬楼本进行对比,笔意既殊,镌法并异,有着明显的差别,说明不是同一版本。并且后三者字体刀法风格虽然接近,但仔细对比,也不是同一版本。那么后三者又是何时所刻呢?

图14 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本《龙龛手鉴》卷三页一及其局部刀法特征
汲古阁本《龙龛手鉴》,李致忠先生在《宋版书叙录》一书中,通过字体、刀法、刻工等将其定为“南宋初期浙江刻本”。[3]李先生大概没有仔细翻阅原书,本来缺失而由影宋抄本补齐者是卷二,却被说成卷三。并错将涵芬楼本的刻工“陈乙、王因、胡杏、朱礼、王成”等加到该本刻工之中。由此推断的逻辑必是混乱的,得出的结果更是不可信。比如文中称刻工王成又参加过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本《文粹》,刻工林盛又参加过《切韵指掌图》的镌刻工作。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了这部《切韵指掌图》,卷末有跋语称:“绍定三年(1230)庚寅三月朔四世从孙敬书于卷末。”从南宋绍兴九年(1139)到绍定三年(1230),已是近九十余年,王成与林盛显然是不能合刻《龙龛手鉴》的。我们细审该书,除了钞补的卷二外,序言与其它几卷书法风格如一,当为同时所刻。字体用笔皆有欧字特征,又呈明显的横细竖粗状,应是南宋晚期才出现的浙本风格。再看刀法,方楞板结,已无南宋早期之圆润灵活。横画末端大都呈现凸出、锐利的三角形,其中多有直角三角形,且三角形的高度超过横画的两倍以上。横折大都有凸出的耸肩状。刀锋峭立,方板硬朗。为典型的南宋晚期浙本刀法特征(图14)。因此,从字体刀法上,我们判断该书应是南宋晚期浙刻本,而绝不会是南宋早期刻本。
天禄琳琅本《龙龛手鉴》,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有相关解题并刊有两张书影。解题曰:“按日本翻刻明嘉靖高德山归真寺刊本,知原书中载有殷、让、恒、树、慎诸字,此刻悉刊削不载,盖避讳故。由此推考之,则此刻避宋讳止于孝宗,又查刻工张良见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光宗浙刊本《武经七书》,则是书之刊刻,应在孝宗时。复就此本字体觇之,甚类浙刻,其刻工徐、虞均见于明州刊本《文选》,明州为浙江宁波,则是本为浙江雕印,殆无可疑。”避讳不能作为鉴定版本的绝对标准,关于文中称避讳至孝宗的问题下文再谈。书中所言张良所刻《武经七书》,共有刻工二十一人,[4]仅仅张良一人重见,很难证明二者为同一人。仅以徐、虞两个单姓见于宋明州本《文选》,便断定是相同的二人,更是牵强。因此,刻于孝宗朝的结论也不可靠。从《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所刊登的两页书影来看,虽然字体步武欧阳率更,但刀法方楞,很多横画末端出现了凸起的直角三角形。前文已述,在南宋早期的浙本中不会出现此种特征。
双鉴楼本《龙龛手鉴》,傅增湘云:“详绎二本,瞿氏刻(按:汲古阁本)似在前,而余本或是覆本。以刊工证之,是南宋刊本,藏家侈为辽本或蒲传正刊本均误。”[2]傅氏只言是南宋刻本,并未指明是南宋的哪一时期。从《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来看,该书字体刀法也是南宋晚期风格。
总之,三本《龙龛手鉴》都不是南宋早期的刊本。从字体刀法风格上看,应是南宋晚期的产物。南宋晚期与元初浙本版刻书法风格基本一致,所以我们暂定为宋末元初刊本。仅以字体刀法特征得出的结论不能使人完全信服,我们来看避讳和刻工。
宋代理宗以前避讳严格,可以作为刻本断代的可靠依据。但大约自南宋理宗后半期起,国运颓败,版图日削,避讳开始不甚讲究。元代帝名多译音,很少避讳。宋末元初覆刻前代刊本时,多依原样镌刻,不作改动。所以上文提到的天禄琳琅本虽然避南宋孝宗朝讳,但不能就此确定是南宋早期刻本,也可能是宋末元初覆刻本。
再来看刻工,三本《龙龛手鉴》的刻工基本相同。除去单字的姓氏,还有范子荣、实新(或新实)、囻宝(国宝)(以上卷一)、张良、郑林(以上卷三)、李生、林盛、徐永(以上卷三、卷四)等八人。《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一书曾将《普宁藏》六百五十六位刻工全部刊登。[5]经查对,《龙龛手鉴》的八名刻工只有实新(或新实)、囻宝(国宝)二人不见外,其余六人均在其中。六人互见应不是偶然,说明《龙龛手鉴》的六名刻工也参加过《普宁藏》的镌刻工作。①又查《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卷一的范子荣、实新(或新实)、囻宝(国宝)三人不见外,余下三卷的五位刻工解释如下:张良:1. 南宋淳熙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武经七书》(半页10 行,行19 字),《龙龛手鉴》(10 行无定字)。2. 元前至元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中阿含经》、《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均《普宁藏》本)(页439)郑林:元前至元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普宁藏》本)。大德间参加刻过《胜思维梵天所问经》、《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佛说华手经》《佛本行集经》、《杂阿含经》、《摩诃僧祗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柰耶》、《根本说一切有部苾萏尼毗柰耶》(以上均《碛砂藏》本)。参加刻过补版《龙龛手鉴》。(页577-578)李生:1. 南宋淳熙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龙龛手鉴》(半页10 行,大字一约小字四,注双行,行30 字),《西汉会要》(11 行20 字),《方泉先生诗集》(陈道人书籍铺本),《记纂渊海》(13 行22 字),《东都事略》(五峰阁本)。2. 元前至元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四分律》(《普宁藏》本)。(页314)林盛:1. 南宋淳熙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龙龛手鉴》(半页10 行,行字不等)。2. 南宋绍定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切韵指掌图》(读书堂本)。又参加刻过《佛说大三摩惹经》(《碛砂藏》本)。元初参加刻过《根本说一切有部苾萏尼毗柰耶》、《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立世阿毗昙论》、《开元释教论》、《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以上均《普宁藏》本)。(页512)徐永:1.南宋绍兴间浙西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龙龛手鉴》(半页10行,行无定字),《广韵》(10行20字,注双行,行27字),《经典释文》(11行17字),《文选注》(明州本,10行20—22字)。2.元前至元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鞞婆沙论》、《出曜经》、《坐禅三昧法门经》、《经律异相》、《法苑珠林》、《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以上均《普宁藏》本),《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均《碛砂藏》本)。大德间参加刻过《礼仪集说》(半页12行,行18字)。至正三年(1343)参加刻过《宋史》(杭州路儒学本10行22字),《金史》(版本行款同上)。参加刻过补版:《宋书》、《魏书》、《新唐书》。(页706)以上词条中,张良、李生、林盛、徐永五名刻工在宋绍兴间、淳熙间刊刻过《龙龛手鉴》及郑林在元初参加过《龙龛手鉴》补版之说,显然来自以往有关书籍对《龙龛手鉴》版本的错误断代。而五人都在元初参加过《普宁藏》的镌刻工作,不可能是一种巧合。普宁藏始刻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77,南宋端宗景炎二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完成。因此,从刻工上可以证明《龙龛手鉴》刻于宋末元初。
综上所述,通过对书法风格和刻工两个方面进行推断论证,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天禄琳琅本及傅增湘双鉴楼藏本等三本《龙龛手鉴》,基本可以确定为宋末元初刻本,其中某一本的刊刻年代很有可能再晚一些。至于三者的前后覆刻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1]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M].1977:40-42.
[2](清)莫友芝.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M].傅增湘,订补.北京:中华书局.2009:182.
[3]李致忠.宋版书叙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292-293.
[4]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54.
[5]李富华,何梅.汉文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34-337.
J29
A
1008-9675(2017)06-0104-06
2017-10-03
刘元堂(1972-),山东乳山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古文献博士后。研究方向:书法创作理论研究。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宋元版刻书法研究”(项目编号:2020SJB76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