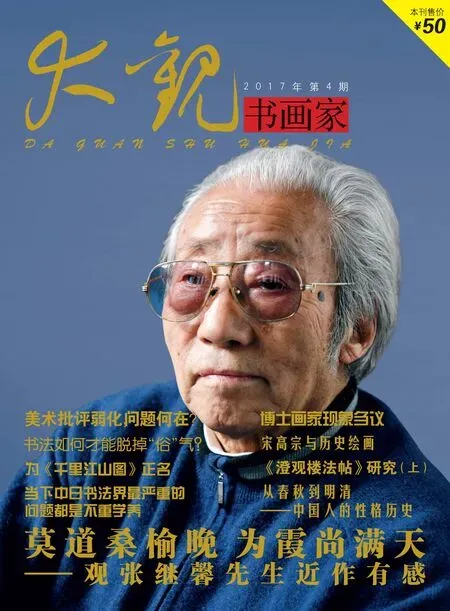“印外求印”之拓展—20世纪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对现当代篆刻艺术创新的推进
2018-01-05陈道义
陈道义
“印外求印”之拓展—20世纪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对现当代篆刻艺术创新的推进
陈道义
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对现当代篆刻艺术创新作用不言而喻。
20世纪新发掘与整理的古文字资料日益丰富,对现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无疑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些创新主要表现在下列六大方面。
一、甲骨文印风
20世纪甲骨文的发掘与整理,不仅从数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在古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上补充了一个新阶段。甲骨文字的形体与契刻技巧,及其章法布局乃至甲骨文字拓片的自然构成之美,激发了篆刻家的浓厚兴趣,为篆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有人取甲骨文字入印,著名的有丁辅之、王雪民、杨仲子、易大庵、简经伦、秦士蔚、谈月色等,其中以简氏作品为多且成就为高。当代探索甲骨文印创新者渐多,尤以刘江老先生最为执着,其甲骨印风安详稳重,厚实沉着,深含韵律与生命;西蜀徐无闻也常刻甲骨文印,而且时用于印款中,章法自然,气息渊雅;金陵苏金海先生是甲骨文印创作的中坚,其刀法猛利劲健,布局寓巧于拙,印风平中见奋;吴门林尔亦以甲骨文印为专攻,用刀干净灵巧,布局以印面契合文字,曾获“全国六届篆刻展”提名奖。其他零星刻制甲骨文印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西泠印社第四届篆刻作品评展”征稿中还特别要求参评者必刻甲骨文印一方,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印风的发展。甲骨文在结字和章法上较后世文字有更大的灵活性,除了少数简单的字以外,绝大多数的字都有几种乃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其笔画的多少、形体的长短、结构的安置都相当随意。章法上字距与行距都不严格相等,左行右行也无定式,这些可变性特点为甲骨文印布局取势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也拓展了甲骨文篆刻的创新空间。从而为篆刻艺术在古玺文字、金文、缪篆、小篆之后又添加一种字体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楚简文印风
楚简文字是中国最早的书法墨迹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起,楚简不断出土问世。在已发掘的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为丰富的。50年代开始,整理楚简文字的著录和研究、考释等文章不断问世,罗福颐、史树青、饶宗颐、陈直等文章荜路蓝缕;70年代以后,楚简发表更多,代表的有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也在此期间出版,广大书法篆刻爱好者能一睹这地下沉睡二千多年的文字之奇妙风采。楚简古文字,一开始就与西周金文拉开了距离,其结构造型以直绕和弧线纵横排叠,环环相扣,极具美术装饰意味。它吸收了中原文字的精华,又自成体系,与后来成为篆书主流的秦系文字有着较大的区别。其诡谲浪漫而又极尽变化的美感引发了篆刻家的极大兴趣,于是部分作者产生了以此文字入印的创作激情。据笔者所知,1980年“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马国权先生以集楚简文字的形式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其后,以楚简文字入印风气渐浓。据王庆忠、孙玉华统计,楚简文印在“第八届全国展”中约占全部篆刻作品入展的5%,在“首届青年展”中占6%,在“全国第五届篆刻展”和“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评展”中分别有九位和十位印人刻楚简文印入展。在近几年中国书协或西泠印社主办的篆刻展中,楚简文印也屡见不鲜,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代篆刻家中,李刚田先生是较早尝试楚简文字入印的代表,他将楚简文的洒脱浪漫糅合汉凿印的方劲沉着之中;徐畅先生也经常刻楚简文印,意欲保持楚简文字峻峭妍雅的本色。中青年篆刻家以楚简文印主创且成就突出的有许雄志、高庆春、张炜羽等。许印构图新颖,刀笔情趣爽快;高印以金文融化楚简,浑穆又不乏浪漫气息;张印注重吸收楚简文的奇诡多姿,风格精致而灵动,还常以楚简刻边款。青年印人中也有不少追随楚简印风的。当然,孙慰祖、赵山亭、刘洪洋、周斌等资深篆刻家或试刀楚简文印,或借鉴楚简古文字之意,都有精彩作品面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局部)

《毛公鼎》拓本
以上是在20世纪两宗最大考古发现的全新古文字材料的刺激下而产生的篆刻艺术创作的崭新面目。与此同时,在晚清民国篆刻家探索的前提下,由于20世纪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数量和质量都大胜于前,以及印人认识的不断提高,因此,现当代篆刻艺术创新又兴四大印风流行,可见历史性的定位。
三、古玺印风
古玺,即秦统一以前的官私玺印。识别古玺虽在清代中叶,但广泛认识古玺并对出土(或传世)的古玺进行整理研究,以及把古玺风格作为篆刻创新的追求,乃是近百年的事。沙孟海先生在一篇序文中说:“赵之谦、黄士陵印谱中,还都错认它(古玺)是‘秦印’。……不久,吴式芬《双虞壶斋印谱》和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出来,崭然列古玺于卷首。后来商务印书馆影印陈书,大量发行,从此天下皆知道这类遗物是古玺。”①其后,古玺及古玺文字整理与研究大为进步,至20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到八十年代,古玺研究进入了高潮时期,大量的研究论文和有关专著,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②。其中字书编纂代表作有罗福颐的《古玺文字征》(1930)和《古玺文编》(1981),至于古玺创作,则民国初岭南李尹桑开风气之先。马国权先生曾说:“古玺之艺失传近二千年,至牧甫始发其秘,尹桑更光而大之。……尝自负其章法篆法均消息于玺文。”③现当代篆刻古玺印创作渐多。据南京童迅先生统计,全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篆刻展中,古玺印式分别占27%、24%、21%和28%,“全国第五届篆刻展”中获一等奖的吴砚君、二等奖的陈靖、三等奖的鲁大东等均以古玺式作品取胜。“第六届篆刻展”中古玺印式所占比例也不小,可谓成一时风气。
古玺风格向以多样变化而著称于印史,主要缘于战国古文字的地域特点,其章法布局也是后来的秦汉印所无法比拟的,文人流派篆刻家对汉印风格挖掘较为深入,而于古玺风格却认识粗浅。现当代篆刻古玺印风的创新,得益于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印外功夫”,也与今人讲个性、重表现的审美选择相契合,这类印风既有印章之古意,又合视觉之新变,实为时代呼之而出。
四、金文印风
金文的狭义是指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宋代学者对金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清代古文字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但以金文印广泛示人则是近百年来有之,尤以现当代篆刻界为盛。一是因为青铜器铭文材料新出土的量大超于以前,如河南、陕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有多批发掘;二是因为全面整理金文有时代新科技的便利条件,如容庚先生分别于1925年、1939年、1959年三次出版修订《金文编》,1985年又出版了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金文编》;又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册,1994年完成出版,之后又有补充性的著录,可谓字书与拓片图版相得益彰,这当然使当代篆刻家大开眼界。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易大庵、冯康侯、童大年、寿石工、简琴斋、杨仲子、乔大壮等涉足金文印,其中简、乔二位成就最为突出。此外,部分古文字学者、考古专家如罗振玉、经亨颐、容庚、商承祚等,亦先后介入过金文印的创作实践。现当代印坛老一辈篆刻家如朱复戡、沙孟海、曾绍杰、蒋维崧等绝大多数都曾刻过金文印,尤以朱、蒋二老为多为最。朱氏金文印作商末周初之体,凝练浑穆,气势雄劲;蒋氏金文印在《蒋维崧印存》中约占80%,章法精妙脱俗,运刀洗练流畅,于平和中见姿态,影响了邹振亚、徐云叔、刘绍刚、傅舟等一大批印人。当代其他金文印作者还有王北岳、王壮为、熊伯齐、傅嘉仪、祝遂之、陈茗屋、陆康、魏杰、燕守谷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另外,不难看出,每次篆刻展览中金文印风都占相当的比例。
五、鸟虫篆印风
鸟虫篆印最早见于春秋而隆兴于两汉,篆刻艺术成熟后至明清有少数印人偶尔刻之,但有人斥为“几于谬矣”。现当代篆刻界鸟虫篆印大兴并形成一种风气,与20世纪发掘和整理研究的古鸟虫篆印及春秋战国铜器上鸟虫篆铭文是分不开的。从3O年代到8O年代,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出土了不少带有鸟虫篆铭文的剑、戈、钟、鼎等铜器;同时,容庚等前贤作《鸟书考》等研究;1987年,韩天衡先生编订《秦汉鸟虫篆印选》;其后,徐谷甫编《鸟虫篆大鉴》,曹锦炎作《鸟虫书通考》,侯福昌作《鸟虫书汇编》等,为广大印人进一步认识鸟虫篆之美,以及识读鸟虫篆并为篆刻创作服务大开方便之门。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其笔画蜿蜒盘曲,灵动莫测,时附鸟虫之形,极富装饰意味,用于印章,易于变化,独见特色。其华丽面貌和金石气息深深吸引着众多篆刻家跃跃欲试。方介堪先生便是20世纪鸟虫篆印大家,独创了印文纹饰语言的个人风格,“妙在亦书亦画之间”(马国权评语),且能做到朱、白文印的统一。其后,印坛涌现出一大批鸟虫篆印作者,驰名的有侯福昌、韩天衡、吴子建、陈身道、徐谷甫、吴承斌等。成就最高的韩先生所作气势恢宏,个性鲜明;吴子建先生还将青铜器、玉器等纹饰融入鸟虫篆印的创作中,高古雅致。近二三十年来鸟虫篆印创作一片繁荣,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六、中山王器铭文印风
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室出土好几件带有铭文的器物,如铜鼎、方壶、圆壶等。1979年,《文物》第一期发表了这一墓室的发掘报告和相关的研究文章,并附印了部分铭文拓片,当时在学界引起了轰动,不仅考古学家赞叹那些器物的精美,而目古文字学家也十分关注其文字形义的特殊性。1981年,在河北省博物馆工作多年、擅长摹写古器物铭文的张守中先生,撰集出版了《中山王 器文字编》,使更多的学人有机会研习器铭文。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篆刻家徐无闻先生却十分欣赏这些铭文的书法艺术之美,并身体力行,援笔临写。几年后,他创作的“中山王”体书法对联亮相于全国书法展中,引起了广泛的赞叹,不同凡响。同时,徐先生又思考如何以此系文字入印,曾几次写成墨稿,只因时间关系而未曾刻就。笔者于先生门下受教三年,先生耳提面命,使我获益良多。自1995年始,笔者探索中山王器铭文印风,极力表现其抽象装饰意味,作品参加了西泠印社、中国书协主办的部分展览。1997年在《书法报》发表了《试以中山王器铭文字入印》一文并刊载此类篆刻作品数方以求同道专家批评。之后,重庆的青年印人李健锐意进取,器铭文入印,创作了不少好作品。另外,广东、香港、台湾、黑龙江、上海、浙江等地都有人以中山王器铭文入印来创作篆刻作品,致使这一印风初成。
上述六大印风是在20世纪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刺激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势力较强的现当代篆刻创新的突出群体表现,其他以古文字为契机而促使篆刻创新的还有王镛、崔志强的陶文、砖瓦文印式,黄惇的瓷押篆印式,朱培尔的石刻篆文印式,潘敏钟的铜镜铭文印式,张弓者的碑额志盖篆印式,赵熊的古币文印式,葛冰华的道教符录印式,以及《天玺纪功碑》印式等等,只是涉足面不大,尚未形成一股风气。
总之,现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离不开新发现的古文字数据的滋养,篆刻家必须要正确利用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20世纪发掘与整理的古文字资料是篆刻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且,不久的将来,地不爱宝,还会有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必将为篆刻艺术创新带来新的契机。当然,应用新发现的古文字入印,必须经过“印化”的字法处理、神化的结构布局,才能保持篆刻艺术的特质。可见,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对现当代篆刻艺术创新的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④
注释:
①沙孟海《〈古玺通论〉序》,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③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
④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