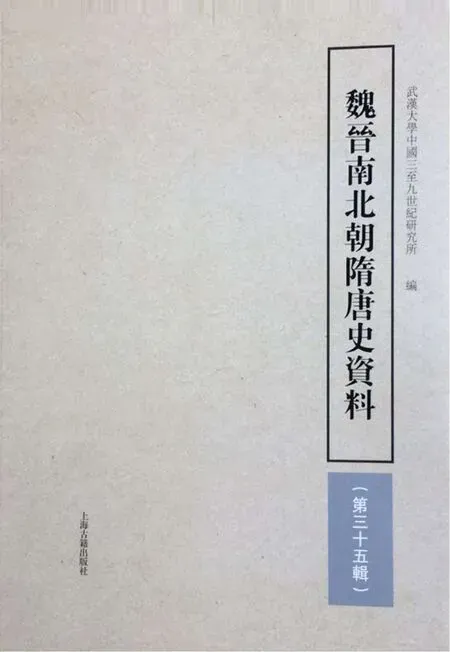因宦徙居: 唐代墓誌所見潞州人口遷入情況的個案考察
2018-01-02張葳
張 葳
因宦徙居:唐代墓誌所見潞州人口遷入情況的個案考察
張 葳
近年來,對墓誌等出土文獻的研究已成爲唐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大大拓展了我們對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墓誌材料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出土地域的分佈不太均衡,導致相關研究較爲零散。*在長安、洛陽之外,根據墓誌進行區域研究的,就筆者所見,有孫繼民主編: 《河北新發現石刻題記與隋唐史研究》,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馮金忠: 《唐代河北藩鎮研究》,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2年等。我們在翻檢唐代墓誌的過程中,注意到有一個地區較爲集中,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和研究,即唐潞州出土的墓誌。潞州,屬唐河東道,大致在今山西東南部和河北西南部,包括山西長治、壺關、長子、屯留、潞城、黎城、沁縣、榆社、武鄉和河北涉縣一帶。這一地區出土的隋唐時期墓誌,根據我的粗略統計,大約有470多方,*本文的統計資料主要來自於周紹良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以下簡稱《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周紹良、趙超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以下簡稱《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吴鋼主編: 《全唐文補遺》(第1—9輯)、《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以下簡稱《千唐誌齋新藏》),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常福江主編: 《長治金石萃編》(上下),太原: 山西春秋電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趙君平、趙文成主編: 《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齊運通主編: 《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 中華書局,2012年;胡戟、榮新江主編: 《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趙力光主編: 《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以下簡稱《碑林》),北京: 綫裝書局,2007年;趙力光主編: 《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以下簡稱《碑林續編》),西安: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趙文成、趙君平主編: 《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以及已發表於刊物的經過整理的零散墓誌。尤以唐上黨分佈最多,有將近300方,其餘則屬唐屯留、潞城、壺關等地。這些墓誌涉及的社會階層大多並非士族,但亦多屬地方社會的中上層。有一些有官職,但職位都不高,平民也有不少。對這批墓誌的研究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多地認識唐代地方社會、普通民衆的生活。
張正田先生是對唐代澤潞地區墓誌較早加以關注的學者,其《“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一書,*臺北: 稻鄉出版社,2007年。便利用此一地區的墓誌,釐清了不少傳世文獻未能明晰的問題,是我們寫作本文的重要參考。但他寫作時可供參考的墓誌還比較有限,近年來,隨着《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等墓誌彙編陸續出版,大量新的有關潞州地區的墓誌得以刊布,專題研究論文也不斷涌現。*這方面的論文就筆者所見有陳忠凱: 《墓誌瑣談——讀〈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碑林集刊》第14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12—423頁;陳忠凱、張婷: 《西安碑林新藏唐—宋墓誌蓋上的挽歌》,《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2—302頁;胡可先: 《墓誌新輯唐代挽歌考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第175—183頁;郭桂豪: 《〈唐車營十將安士和墓誌銘〉考釋》,《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9年第4期,第105—111頁;梁海燕: 《唐人墓誌蓋題詩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4期,第8—16頁;王慶衛: 《從新見墓誌挽歌看唐五代澤潞地區民間的生死觀念》,《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111—117頁;王慶衛、王煊: 《生死之間: 唐代墓誌中新見挽歌研究》,《碑林集刊》第16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82—107頁;王慶衛、韓釗、傅清音: 《唐代墓誌誌蓋鋪首紋飾之文化藴意探析——以碑林新藏墓誌爲例》,《文博》2012年第5期,第28—32頁;景亞鸝、楊婉萍、劉寧: 《唐代墓誌所見相墓習俗——以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爲例》,《碑林集刊》第17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62—177頁;劉天琪: 《墓誌“讖語”現象及誌蓋地域風格——以西安碑林新入藏隋唐潞州地區墓誌爲例》,《榮寶齋》2013年第6期,第118—131頁。這些圍繞新出墓誌展開的研究,除了對具體墓誌内容進行討論外,還涉及唐代潞州地區宗教信仰、喪葬習俗、民衆觀念、地域文化等問題,顯示了新出材料對推動研究的價值。
潞州位於今山西省東南部、黄土高原東南角,與今河北、河南省相接。其地勢東枕太行、南臨中原、西視河東、北接太原,周邊爲太行、太嶽、中條三大山脉所圍繞,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潞州之名因春秋時的潞子之國而得,三家分晉後其地爲韓、趙、魏所分割,秦漢時爲上黨郡,植被豐茂,“邑帶山林,茂松生焉”。*《後漢書·郡國五》襄垣條下注引《上黨記》,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3522頁。地方豪强勢力强大,號爲“難治”。《漢書·地理志下》記:
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1656頁。
魏晉以後,隨着羯、氐、鮮卑等族相繼進入這一地區,多民族混居,形勢更顯複雜。北周武帝時置潞州,隋改爲上黨郡,中廢而復置。唐又改爲潞州,後期此地成爲重要的藩鎮昭義鎮的治所。本文選取潞州作爲研究對象,既是考慮到這一地區唐代墓誌出土較爲集中,適合進行微觀個案的考察,同時也是因爲潞州所屬的昭義鎮在中晚唐的北方藩鎮格局中是重要的一環,有其獨特性。我們希望通過對這些墓誌内容的探討,進一步了解唐代潞州地區政治、社會變化的一些情況,也期望對中晚唐藩鎮,尤其是對藩鎮内部和基層的情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鄙陋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一、 爲何徙居主要“因宦”?
《舊唐書·地理志二》記載了唐前期潞州大都督府建制的情況:
潞州大都督府 隋上黨郡。武德元年,改爲潞州。領上黨、長子、屯留、潞城四縣。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四年,分上黨置壺關縣。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府。十年,又改爲都督府。貞觀十七年,廢韓州,以所管襄垣等五縣屬潞州。開元十七年,以玄宗歷職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天寶元年,改爲上黨郡。乾元元年,依舊爲潞州大都督府。*《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1476頁。這段記載中,説到開元十七年時設置潞州大都督府,所管爲慈、儀、石、沁州,其中還應包括潞州。之所以未提可能是舊史記載的習慣所致。參陳翔《唐代澤潞鎮建置及擴建考》,《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第109—116頁。
可知,安史之亂以前此地的行政設置屢有變化,潞州曾陸續設爲總管府、都督府、大都督府。安史之亂爆發後,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唐廷開始在潞州設置藩鎮。《新唐書》記:“至德元載(756),置澤潞沁節度使,治潞州。”*《新唐書》卷六六《方鎮三》,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1838頁。自大曆十二年(777)至建中三年(782),爲了防禦和制衡河北强藩,澤潞鎮跨越太行山脉,兼領邢、洺、磁三州,與昭義軍合并。此後多以昭義稱之,直至唐末。*關於安史亂後澤潞地區藩鎮的設置和變動情況,可參賴青壽: 《唐後期方鎮建置沿革研究》,復旦大學1999年博士學位論文;成一農: 《唐代地緣政治結構》,收於李孝聰主編: 《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王韻: 《論唐、五代的昭義鎮》,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旅遊學院2003年碩士論文;郎潔: 《唐中晚期昭義鎮研究》,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2007年碩士論文;陳翔: 《唐代後期澤潞鎮軍事地位的變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3期,第86—91頁;陳翔: 《唐代澤潞鎮建置及擴建考》,《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第109—116頁。此段論述對以上諸文均有參考,可以注意到澤潞鎮(昭義軍)的轄區在安史之亂後一段時間内變更情況較多,對此論者有不同的意見,關於澤潞(昭義)應如何準確稱呼,論者似乎也不太一致。這類問題因並非本文討論主旨,故在此略而不論,後文僅以昭義鎮統而稱之。
儘管潞州總管府、大都督府、都督府、澤潞鎮及昭義軍節度使的轄區在唐代不同時期屢經變化,但就潞州一地而言,其所統縣的數量主要還是在唐初有幾次變動。初領上黨、長子、屯留、潞城四縣,武德四年(621)從上黨分出壺關縣,貞觀十七年(643)韓州廢除後,舊所管五縣襄垣、黎城、涉、銅鞮、武鄉歸於潞州,*李吉甫撰,賀次君注解: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第420—423頁。此後,其轄境一直比較穩定,没有太大改變。
我們現在所見潞州出土墓誌主要分佈在唐代的上黨(今山西長治市)、屯留(今山西屯留)、壺關(今山西壺關)、長子(今山西長子)、襄垣(今山西襄垣)、黎城(今山西黎城縣西北古縣)、銅鞮(今山西沁縣西南故城)等地,即今山西東南部一帶,幾乎涵蓋了唐潞州全境。雖然墓誌出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上黨出土的墓誌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已顯示出它作爲府城在潞州的核心地位。唐代製作墓誌、撰寫墓誌銘、購買家族墓地都需要相當的財力支撑,張正田先生判斷,墓主“以當地小姓以上之中上階層居多。”*張正田: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第114頁。這些中上階層,從墓誌内容來看,有一小部分是父祖三代或四代中曾擔任過中央官員、節度使軍職的家庭,也有父祖三代或四代中擔任過州級或縣級官員的家庭,還有則是家族成員擔任過試官、勛官、低級文武散官、版授官等,也存在父祖三代或四代皆爲處士或從事商業的情況。總的來看,他們政治地位較低,對中央政治事務的參與度不高,但根基於本地屬於潞州地方社會的中堅力量。這或許與潞州本地的政治、文化特點相關。唐代這一地區能躋身中央的士人家族不多,比較知名的僅有苗晉卿家族。所以,看上去在潞州社會發揮作用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家族,如《王休泰墓誌》記其子嘉運“爲仁之領袖,鄉黨悌焉;作君子之模,宗族述其孝矣”。*《彙編》大曆023《唐故王府君(休泰)墓誌之銘》,第1774—1775頁。《蕭知義墓誌》記其“祖玄、父金,並高蹈不仕,淑德遐聞,代推領袖,家傳禮樂”。*《碑林》一五五,第392頁。郝四“恂恂於鄉人,平揖於府縣”。*《碑林》一八三,第461頁。郭延壽妻房氏“時蝗爲災,人阻艱弊。井税之外,請納金三百萬,粟十秉,以供軍用。”*《碑林》二一九,第558頁。這些人中蕭知義版授肅州刺史,房氏夫郭延壽爲試太子左贊善大夫,王嘉運祖父惠爲版授潞郡博士,郝四父科爲陪戎副尉,其家族隱約都有一些“官”的背景。可見像試官、勛官、低級文武散官、版授官這類官職,在地方上可能仍被視爲一種政治資源。特别是在具有中央背景的地方大族缺席的情況下,這類官員有可能成爲地方社會日常事務與活動的積極參與者,而官方史書很難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從這一角度來看,科舉制度的實行不僅逐漸消弭了世家大族的力量,或許也導致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有機政治聯繫被削弱和割裂,使地方社會從官方視野中淡出。
潞州墓誌分佈的情況還顯示,其治下的各縣里,中上層人士分佈的情況並不均衡。其中以上黨最爲集中,而隨着與上黨空間距離的增加,其密集程度逐漸減弱,如屯留、長子、壺關都有30方以上,稍周邊的潞城24方,襄垣18方,更邊緣的銅鞮、黎城則都没有超過10方,呈現出以上黨爲中心,屯留、長子、壺關爲内環,襄垣、銅鞮、潞城、黎城爲外環的輻射狀分佈,表明上黨集中了潞州主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對周邊地區具有絶對的主導地位,其向背可以直接影響潞州的政治選擇,也對澤潞地區的政治走向有決定性作用。潞城、襄垣、銅鞮、黎城在潞州所處的邊緣性地位,既與空間地理距離有關,也説明了其地人才資源的匱乏。貞觀十七年(643)韓州的廢除或有這一考慮,不過并入潞州似乎對其地的政治、文化並没有太大的影響和改變。
下面我們先從移民角度出發,對潞州墓誌中記録的漢唐時期人口移徙的情況進行一些探究。
翻讀潞州墓誌,述及墓主的籍貫和先世時,往往以“本望他貫,後徙居潞州,今爲潞州××人”這樣的敍述結構出現。徙居的原因包括因宦,宗支流散,避地,有别業等。其中,“因宦移居”或“食采於邑”是最爲普遍的説法。如:
《李石墓誌》:“君諱石,字黄石。隴西成紀人也。食倸無歸,流萍遂實,故爲襄垣縣人焉。”*郎保利: 《山西襄垣唐代李石夫婦合葬墓》,《文物》2004年第10期,第49—54、60頁。
《劉節墓誌》:“河間人也。遠祖因官上黨,子孫家焉,故今爲潞州上黨人。”*《續集》開元041《大唐故騎都尉劉君(節)墓誌銘并序》,第481頁。
《王貞墓誌》:“太原人也。遠祖鐘,晉朝上黨太守,子孫因而家焉。”*《彙編》天寶104《唐故上騎都尉王君(貞)之誌銘并序》,第1604頁。
這類説法不僅見於潞州,在隋唐墓誌中也非常普遍,像是遵循某一模式的套話,很容易被視作墓誌的固定程式而受到忽略。然而,爲什麽這種關於望貫變化的敍述在隋唐墓誌中如此盛行?在其模式化語言的背後能否發掘出一些歷史信息呢?
如所周知,望貫不一致是唐代士族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岑仲勉先生曾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貫,是一非二。歷世稍遠……而望與貫漸分,然人仍多自稱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從出也。延及六朝,門户益重。……此風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猶河北,或世居東魯而人曰隴西,於後世極糅錯之奇,在當時本通行之習。”*岑仲勉: 《唐史餘瀋》卷四《雜述·唐史中之望與貫》,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第229頁。郭鋒先生認爲中古時期郡望與籍貫的不一致,主要源於士族家庭的遷徙。*郭鋒: 《晉唐士族的郡望與士族等級的判定標準——以吴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郡望之形成爲例》,《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45—264頁。楊向奎先生也注意到唐墓誌題書中郡望的增加與開天後士族遷徙情況的增多有密切關聯。*楊向奎: 《唐墓誌題書郡望的增多及其原因探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111—115頁。總之,望、貫分離是唐代士族家庭現實生活的常態,與他們的中央化、官僚化有關。然而潞州的情況有所不同,在這些墓誌中,墓主身份能够稱得上士族的寥寥無幾,*郭鋒先生在《晉唐士族的郡望與士族等級的判定標準——以吴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郡望之形成爲例》(《唐研究》第2卷)一文中將是否列入郡望作爲判定某家族進入士族等級與否的標誌之一,本文也依照這一標準對唐代士族進行認定,即以敦煌文書所存唐代氏族譜殘卷中所列郡望爲依據,具體可參姜士彬著,范兆飛、秦伊譯,仇鹿鳴校: 《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附録五《唐代郡望表所見氏族索引》,上海: 中西書局,2016年,第227—256頁。另外潞州地區出土的墓誌中雖然墓主多稱自己的郡望爲太原王氏、太原郭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等,但大多爲無據可考者,對這類情況本文皆以非士族看待。誌文中雖然也敍及地望,但卻可視爲唐代郡望觀念普及乃至僞濫的結果。那麽,這些對望、貫不一致的敍述,是單純的攀附郡望?還是也與遷徙有關?擬或另有原因?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墓誌在書寫模式上深受士族文化影響。如潞州人暴賢的墓誌是一方頗爲普通、常見的平民墓誌,其文曰:
君諱賢,字洪相。元出清州。暴也,周文王之孫叔懷是也。乃德俠弘遠,燮首成龍,乃致太平,神基夐遠。迢迢麗筆,列封諸侯;迹迹巧詞,遂封叔懷於暴城侯,因宦任官,子孫遂居潞部。曾祖諱歲,齊任并州郡守……*《彙編》顯慶084,第281頁。按誌題失墓主姓氏,根據墓誌内容推測墓主應姓暴。
將他的墓誌與同時期的士族墓誌比較,不難發現他們在撰寫模式上的相類之處。如出自南朝梁宗室、蘭陵蕭氏之後的《蕭令懲墓誌》是這樣記述的:
君諱令懲,字令懲,蘭陵人,帝嚳之遠裔也。昔微子以殷王之嫡嗣,建國於前;丞相以漢帝之功□,封□於後。自兹以降,弈葉彌隆。七代祖順之,梁文皇帝。六代祖衍,梁武皇帝。五代祖統,梁昭明皇帝。高祖詧,梁宣皇帝。曾祖岑,梁吴王。祖瑾,梁侍中,永脩侯。父澤,廬州司馬。*《續集》顯慶026《唐故梁□□□孫蕭君(令懲)墓誌記》,第101頁。
從結構上來説,墓誌開章都追溯姓氏源流至黄帝、西周時代,後敍父祖姓名官爵,大體相似。高祖自北魏已開始任官、家族政治地位從北朝至唐一直很高的《唐儉墓誌》也不例外:
公諱儉,字茂約,太原晉陽人也。其先出自帝嚳,是生放勛,綿瓞克昌,濬源長發。夏御、周杜,皆分若木之華;楚勒、鄖羌,各挺詞林之秀。伯高飭行,位極文昌。儒宗創謀,竟淩天塹。焕前王之典册,光列代之油緗。事可征於博聞,此無得而稱矣。高祖岳,後魏肆州刺史;曾祖靈芝,齊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祖邕,侍中、中書監、左右僕射、尚書令、録尚書事、晉昌王……父鑒,齊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隋武賁郎將、戎順二州刺史、晉昌郡公,皇朝贈太常卿、上柱國。*《續集》顯慶006《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户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君(儉)墓誌》,第88頁。案此段“夏御、周杜”、“楚勒、鄖羌”,原文作“夏御周、杜”、“楚勒鄖、羌”,我認爲斷句標點有誤,詳見下文考證。
雖然從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些關於姓氏的追溯都玄遠而難以證實,但在隋唐墓誌中這已成爲約定俗成的書寫習慣。其風氣應始於北魏末年以降,尤其是東西對峙之後,一些胡漢士人出於攀附心態,將祖先遠溯秦漢乃至上古,*范兆飛: 《中古郡望的成立與崩潰》,《厦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第28—38頁。我們甚至還可以將這一風氣的源頭追溯至魏晉以來“引譜入誌”的傳統,*參陳爽: 《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上海: 學林出版社,2015年,第98頁,第111頁。至唐代已成爲墓誌書寫的標準格式,官僚、士族至平民皆如此。不過在敍述内容上,三誌的差别十分明顯。《蕭令懲墓誌》中關於蕭氏姓氏源流的説法與《元和姓纂》所記基本一致,以蕭爲微子之後。*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記:“蕭,宋微子之後,支孫封於蕭,蕭叔大心子孫有功,因邑命氏焉。”(北京: 中華書局,1994年,第556頁。)《唐儉墓誌》雖在源流敍述上從略,但引用了大量典故來書寫唐氏歷史人物,如“夏御、周杜”乃指陶唐氏的後裔劉累曾爲夏後御龍,賜姓御龍氏,在周爲唐杜氏,*《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第662頁。“楚勒”則指戰國時楚國的辭賦家唐勒,*《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第2491頁。“鄖羌”爲東漢桂陽郡臨武縣令唐羌,*《資治通鑑》卷四八《漢紀四十·和帝永元十五年(103)》,北京: 中華書局,1956年,第1559頁。“伯高”指西漢的清名之士沛郡唐尊,*《漢書》卷七二《鮑宣傳》,第3095頁。“儒宗”指西晉平吴將領唐彬,*《晉書》卷四二《唐彬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217—1220頁。這些精緻的用典顯然與墓誌撰者許敬宗南朝文學世家的出身有關。相比之下,《(暴)賢墓誌》中關於暴氏姓氏淵源的描述雖然篇幅不少,卻甚爲粗疏,與《元和姓纂》所記暴氏姓氏淵源並不相符,*《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九記:“暴公,周卿士,見《毛詩》。應劭《風俗通》云:‘暴辛,周諸侯也。’”第1311頁。而翻遍史籍,也難覓得“暴城侯(暴成侯)”蹤迹,*在《(暴)廉墓誌》中,作“暴成侯”,參見《彙編》咸亨079,第567頁。這個“暴城侯”或是爲了符合士族墓誌的敍述習慣,“依葫蘆畫瓢”的隨意編造。
我們當然不是苛責暴賢墓誌所犯的知識性錯誤,只想由此指出在唐代非士族墓誌中,這類關於世系源流書寫不知何據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隨手即可拈出數例。如《封深墓誌》:“君諱深,字泰澄,渤海人。若乃殷人受氏,乃興微子之封;梁運膺符,□□延陵之國。”*《續集》顯慶020《大唐故封府君(深)墓誌銘并序》,第97頁。將封氏與微子、延陵聯繫在一起,似乎離題甚遠。*《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一記:“姜姓,炎帝之後,封鉅爲黄帝師,胙土命氏。”第50頁。又《陽城縣丞王君夫人陰氏墓誌》中稱:“夫人諱容,晉陽汾陰人。其先晉大夫陰飴甥之後。”*《彙編》顯慶003《唐故黄州總管府陽城縣丞王君夫人陰氏(容)墓誌》,第231頁。陰飴甥其人雖然史書有記,但岑仲勉先生已指出此方墓誌對姓氏淵源的敍述“與林氏所舉兩説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第749頁。還有些墓誌乾脆以非常籠統、模糊的方式來敍述祖先淵源,如《杜旻墓誌》就稱他是“神龍之苗,襲帝嚳之裔”。*《碑林》二七三,第704頁。雖不確切,卻也不至大錯。這些説法雖不能説是完全隨意的編造,但顯然也不是出於熟稔典故的士人之手,撰寫者所具備的歷史知識與士人有較大差异,似足以説明非士族墓誌主要是從形式上接近和模仿士族墓誌。
這類形式上的模仿還表現在,一些非士族墓誌中關於父祖姓名、官爵的敍述常常會有所闕略。魏晉以來士族重門閥,因之父祖的世系、官爵在墓誌中歷來是敍述的重點。這一傳統也延續至唐代墓誌中,大部分墓誌在敍述祖先淵源後會對父祖三代以上的情況有所交待。*就筆者所見,大部分唐代墓誌都采用這種行文格式,比較例外的是亡宫墓誌,對此將另文專論。但父祖名諱、官職闕略的情況卻不少見,如《(暴)賢墓誌》僅記其曾祖姓名、官職。又如《孫欽墓誌》:“曾祖遇,隨朝任河東録事參軍。祖貞。”*《碑林》一九三,第488頁。父親的情況未記。《王貞墓誌》:“曾祖德,梁國子祭酒;父弼,輕車都尉。夫人李氏。”*《彙編》天寶104《唐故上騎都尉王君(貞)之誌銘并序》,第1604頁。祖父的情況未記。《李公素妻王氏墓誌》:“祖諱不載緒,父諱衛。”*《碑林》三三四,第873頁。明確説到祖父的情況已不詳。又或是父祖名諱、官職一律不見,如《張四胡墓誌》:“曾祖、祖、父並明慎令德,謹□謙柔。”*《碑林》一〇七,第499頁。以上所舉墓誌皆出於潞州,誌文的闕略之處各不相同,原因應也多樣,有些父祖的官職不書,也許是因爲未出仕;有些父祖的名諱不書,可能是缺乏記載;也有些只書任官的父祖情況,可能出於對官爵的崇重。不管爲何,内容的闕略在一定程度上説明現實的情形與士族墓誌中已固定化的父祖姓名、官爵敍述模式並不完全相契。在潞州墓誌中,這種闕略是普遍存在的,説明父祖姓名、官爵的闕略在非士族墓誌中比較常見,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不能否認在士族墓誌中也存在闕略的情況,只是並未如此普遍而已。
從以上角度來思考潞州墓誌中的“因宦徙居”解釋模式,我們認爲很有可能是由於士族墓誌中對郡望的强調,導致、影響了士族以外的群體對這種書寫模式的模仿和套用。只是士族墓誌中往往只提郡望,少言現居地。而對非士族來説,郡望本爲牽附,現居地纔是其家鄉所在,從情感、現實利益方面都無法割捨,因此在墓誌中,他們往往會更强調籍貫(現居地),以“因宦”作爲望貫分離的堂皇借口,其實反而欲蓋彌彰。正如上舉三誌中,《蕭令懲墓誌》與《唐儉墓誌》中都只强調郡望而不及其他,僅《(暴)賢墓誌》特别提及其家因宦徙居潞州。
不過,我們認爲從蕭、唐類型墓誌到暴賢類型的墓誌,中間還應存在過渡階段。雖然墓主出身確認爲士族的墓誌中幾乎很少提及現居地,但在一些僞冒郡望的官僚家族墓誌中,這卻是比較常見的情形,*以上只是一個大略的説法,並不排除在一些士族墓誌中也會提到現居地或籍貫,而非士族墓誌中也可能不會提到郡望。但從普遍的情況來看,山東五姓士族墓誌中提到現居地或籍貫的情況比較少見,他們往往還是强調郡望。如《鄭仲連墓誌》:“公諱仲連,族鄭氏,其先肇自宗周,宣王母弟友封之於鄭,是爲桓公子孫,因氏焉。……今爲滎陽人也。”(《彙編》寶曆019,第2093頁)從墓誌記載來看,鄭仲連自高祖以下世代爲官,其家族在唐中後期還居住在滎陽的可能性很小,但墓誌中稱其今爲滎陽人,是注重郡望的表現。非士族群體更傾向於强調現居地或籍貫,如《秦進舉墓誌》:“貫居上黨縣,鄉號雄山,湖泑之里,西火村。土居莊東,鶢鳴嶺下。”(《碑林》三六三,第949頁)因此望貫並舉最初可能較多出現在一些僞冒郡望的官僚家族墓誌中,如唐初的李弘節家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參見張葳《唐代李弘節家族略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4期,第122—125、146頁。因而我們推測,最初在墓誌中同時敍述郡望與籍貫的,可能就是這樣一些政治地位提高後,試圖擠入士族圈的官僚家族。他們希望通過僞冒郡望改頭换面,提升社會地位,但又不能不提及其真正的家鄉,遂以“因宦徙居”一語帶過。而隨着社會中下層郡望僞濫情況的增多,這種説法也被很方便地借用並成爲固定的書寫樣板。當然並不是所有墓誌都以“宦”作爲徙居的解釋,但“本望他貫,後徙居×州,今爲×州××人”的敍述結構,來自於模仿一些類似於李弘節家族這樣的——試圖通過僞冒郡望提升社會地位的官僚家族,這點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其濫觴並不在唐,北魏已出現。如《張整墓誌》記:“君諱整,字菩提,并州上黨郡刈陵縣東路鄉吉遷里人。源出荆州南陽郡白水縣。五世祖充,晉末爲路川戍主,因宦遂居上黨焉。”*《魏故中常侍大長秋卿平北將軍并州刺史雲陽男張君(整)墓誌銘》,收於趙超主編: 《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頁。此張整,學者已明其乃出身稽胡白氏,並不姓張,其郡望更爲僞託。*參見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02頁;何德章: 《僞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朝人墓誌爲中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37—143頁。近來,還有論者注意到“因官徙居”的敍事模式在唐代胡姓家族的族源敍事中也很常見,*尚永亮、龍成松: 《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敍事與民族認同》,《文史哲》2016年第4期,第123—138頁。這無疑也是漢族士族文化被效仿的結果。
由此可見,北魏至唐以來,在墓誌中頻繁出現的“因宦徙居”敍述模式源於社會上對士族郡望的崇尚及攀附心態的流行,體現了非士族階層的心理特點。唐代墓誌中這一敍述模式的普遍化反映了唐代社會仍然深受魏晉以來士族文化的影響,同時又對士族文化進行着改寫和發揮。
二、 隋唐以前徙居潞州的情況
“因宦”或許是一種方便的借用,“徙居”卻未必全是虚造。在潞州墓誌中看似通篇一律的描述中,仍有一些不盡相同之處,其中透露的歷史上潞州人口遷入的情況,耐人尋味。比如關於徙居的時間,就比較鮮明地分爲幾個階段。有自西晉時已徙居至潞州的,如:
《陳亮墓誌》:“九世祖鐘,晉上黨郡守。因官就封,遂爲上黨人也。”*《碑林》一六三,第411頁。
《王貞墓誌》:“遠祖鐘,晉朝上黨太守,子孫因而家焉。”*《彙編》天寶104《唐故上騎都尉王君之誌銘并序》,第1604頁。
《崔日進墓誌》:“列祖公侯以至十八代祖暉,晉太尉、上黨太守、開國公,封屯留侯,子孫因居上黨矣。”*《碑林》二七一,第699頁。
《韓鄭墓誌》:“祖韓温,晉鎮東大將軍、兗州刺史、上黨太守、長子侯。祖禰襲封,因即家於兹矣。”*《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二五三《唐韓鄭墓誌》,第311頁。
《牛征墓誌》:“隴西狄道人。五代祖金,晉永嘉爲上黨太守。”*《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四〇三《唐牛征墓誌并蓋》,第512頁。
《王讓墓誌》:“潞州壺關人也……我先祖往爲晉懷帝徵上黨太守。”*《碑林》〇四〇,第118頁。
以上幾方墓主的祖先有着驚人相似的經歷,其説法值得懷疑。首先,宣稱祖先曾擔任上黨太守(郡守),或許與兩晉南北朝時期地方官職多用於贈官有關。張小穩先生指出:“兩晉南朝,地方官職的主要贈與對象爲死難將士、地方官員和其他官員;作爲贈官的地方官職以都督、刺史、太守爲主……五品以下的低級官僚或無官職而死王事者獲贈太守。”“北朝前期,以贈刺史、太守爲主,五品以上的官員死後獲贈刺史,五品以下的官員死後獲贈太守……北朝後期,贈地方官職轉以都督、行臺、總管爲主,太守僅用於對地位極低或無官位者的追贈。”*張小穩: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官職的品位化》,《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第245—253頁。可見,兩晉南北朝,給予低級官僚或無官職而死於王事者的贈官往往是太守。墓誌中所稱的太守或即這一類贈官,在諛墓風氣的影響下,相沿而統稱官職不高或未有官職的祖先。
其次,上列墓誌中,陳亮和王貞的先祖都恰巧名“鐘”。遠祖名鐘在潞州不僅見此兩例,但大部分都出於王氏,王鐘似乎被相當一部分自太原遷居潞州的王氏視爲共同祖先,如《王能墓誌》中提到其遠祖鐘,授使持節冀州諸軍事、上黨太守、侯封潞縣,*《碑林》〇二五,第83頁。雖未提及時代,但冀州諸軍事是西晉的官職,所以其“遠祖鐘”與《王貞墓誌》中的“遠祖鐘”應該處於同一時代,很可能即同一人。又《王美墓誌》:“并州太原人也。……上黨太守王鐘之胤緒。”*《碑林》〇四一,第121頁。《賈紹墓誌》:“夫人王氏,即王鐘九代孫也。”*《碑林》〇七七,第207頁。《王里奴墓誌》:“其先太原人。……王鐘之後。”*《碑林》〇八二,第220頁。等等。雖然這些王氏彼此之間的血緣關係無法探明,但將西晉時的王鐘視爲徙居上黨的祖先,大概是存在於潞州王氏中的一種普遍認識。在《晉書》中我們僅找到一條有關王鐘的記載,“(姚)弼至姑臧,屯於西苑。州人王鐘、宋鐘、王娥等秘爲内應,候人執其使送之。”*《晉書》卷一二六《載記二十六·秃髮傉檀傳》,第3152頁。此王鐘是否爲彼王鐘,殊難確定。*根據筆者的考察,潞州的移民有一部分來自於北魏初期的平涼户,即有可能來自於河西。而《晉書》所記的王鐘亦爲河西人,這是否只是歷史的巧合,目前無法確定。參張葳《隋唐時期潞州的申屠氏溯源》,待刊。但潞州王氏的先祖王鐘顯然不是史傳中具有名望的某個太原王氏人物。上述墓誌中提到的陳鐘、牛金、崔暉等可能也是類似的情況,這就很值得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以西晉爲先祖徙居潞州的時間,應該不完全是隨意僞託。我們知道,魏晉以來,上黨是胡族特别是羯胡内遷的主要地區,*《魏書》卷九五《羯胡石勒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2047頁。永嘉之亂前後更是這一地區人口頻繁流動的時期,匈奴、羯等諸胡都曾在并州一帶起兵、活動。*參《晉書》卷四《惠帝紀》,第92頁;《晉書》卷一〇一《劉元海載記》,第2644—2652頁;《晉書》卷一〇四、一〇五《石勒載記上、下》,第2707—2756頁;《晉書》卷一一九《姚泓載記》,第3009頁。這些必然會引起上黨人口劇烈的變動,尤其是以匈奴爲主的胡人大量遷徙,因此墓誌中提到徙居發生在這一時期合乎常理。然而從姓氏上來看,陳、王、崔、韓等都是傳統的漢姓。根據我們的了解,漢人並不屬於這一階段移民的主體,對他們來説,這一時期上黨地區反而是要逃離和避開的。那麽墓誌中爲何卻特别强調其祖先的移徙發生在這一時期,並且有幾例還特别强調是在晉懷帝、永嘉之時?稽之史實,這種説法恐怕很難成立,但如果考慮到西晉是隋唐以前統治這一區域的最後一個典型的漢族政權,則聲稱西晉時遷居上黨也許可視爲帶有標明、强調漢族身份的意圖。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聲稱祖先在北魏時徙居潞州的説法。如:
《蕭知義墓誌》:“後魏因官遂居潞州大都督府上黨縣焉。”*《碑林》一五五,第392頁。

《翟德墓誌》:“七代祖□,後魏上黨郡守,子孫居壺關也。”*《碑林》一四五,第367頁。
《郝四墓誌》:“君諱四,名科,太原人也。周武王之錫姓,因封太原公郝子期之後。……後(魏)上黨太守赫那之孫胤也。”*《碑林》一八三,第461頁。
這四方墓誌的墓主姓氏,蕭、崔可歸爲傳統漢姓,翟、郝則未必。翟氏是魏晉北朝丁零中的著姓。據考,魏晉時期,大量丁零部落從漠北遷入中原,主要分佈於定州的常山、中山、趙郡和并州的上黨郡,*段連勤: 《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2—155頁。其中上黨郡壺關縣是翟氏丁零的主要聚居區之一,正與《翟德墓誌》中述祖先定居於壺關的説法吻合。另外誌文稱翟德原爲馮翊下邽人,*《碑林》一四五,第367頁。同出潞州的另一翟氏翟洪景也稱祖先爲馮翼(翊)人,*《碑林》二〇〇《翟洪景墓誌》,第507頁。但馮翊下邽並非唐人所熟知的翟氏郡望。*據《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翟氏郡望有鄧州南陽、澤州高平、江州潯陽。參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集校注》,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3—363頁。史傳中關於下邽翟氏的記載,僅見於《史記·汲黯傳》中太史公曰:“下邽翟公有言”,*《史記》卷一二《汲鄭列傳第六十》,第3113頁。《元和姓纂》據此記“漢文帝廷尉翟公,下邳人。”*岑仲勉先生校“下邳”作“下邽”。參《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582頁。翟德、翟洪景墓誌大概是牽附於此。只是既爲牽附,爲何不選擇《氏族譜》所記地處鄰近的澤州高平,卻選擇不太爲人所知的下邽爲其郡望呢?在目前出土的隋唐墓誌中,聲稱爲下邽(邳)翟氏的除潞州外亦有數例,他們與粟特、小月氏等胡族通婚較多,*參《續集》開元080《大唐故右威衛將軍武威安公故妻新息郡夫人下邳翟氏(六娘)墓誌銘并序》,第508頁;《彙編》永徽020《隋豫州保城縣丞支君(彦)墓誌銘》,第143頁;《彙編》貞觀138《大唐故萬年縣尉孔府君(長寧)墓誌銘》,第95頁。爲胡族後裔的可能性較大。因此儘管翟德的父祖名諱及其家文化傳統呈現出漢文化特徵,但仍不能排除翟德爲翟氏丁零後裔的可能性。潞州墓誌中還記有崔禮弟妹嫁與翟郎爲婦,*《彙編》建中009《貝州青河郡崔府君諱禮弟進葬誌銘》,第1827頁。他們可能都是魏晉以來的丁零部落遷入中原後留下的後裔,此時顯然已完全融入當地社會。
另郝四,據其墓誌的説法,他是東漢末興起的太原士族郝氏的後裔,似乎可確證爲漢族後裔。*范兆飛《中古太原士族群體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14年,第25—43頁。然墓誌中提到的郝氏祖先郝子期、郝那在史書上都無記載,不太像出自太原著姓。據姚薇元先生的考證,太原郝氏也可能是烏丸大人郝且後代。他們在東漢以後漸居塞内,魏晉以後成爲邊境諸胡中的大姓。隨着烏丸與諸胡的融合,匈奴、盧水胡、稽胡及支胡中,皆有以郝爲姓者。*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未見魏書官氏志諸胡姓·第一東胡諸姓》,第173頁。因此,郝四更可能是烏丸或諸胡後裔。從郝四名“科”與父名“科”相同的情況來看,他也不太可能出於士族。其妻索氏,稱京兆扶風人,而非敦煌著姓索氏,是否可能也出於胡族呢?*按漢魏以來,索氏爲敦煌著姓,多爲漢姓。但郝四墓誌中有兩處都强調其妻索氏出自京兆扶風,或許有可能與唐武周時的酷吏索元禮一樣爲胡人。
以上所述雖大多爲推測,但唐代潞州居住着一些胡族後裔應該是可信的。*張正田的考察也傾向於認爲潞州的民族結構是比較複雜的。參張正田: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第117—138頁。除翟、郝外,墓誌中還能看到匈奴姓氏中比較常見的董氏、*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第197頁。董氏在潞州頗爲普遍,在此僅舉數例,如《碑林》一五一《董禮墓誌》,第383頁;《碑林》一五八《董亮墓誌》,第400頁等。靳氏、*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第195頁;《碑林》〇三〇《靳稽墓誌》,第97頁;《碑林》二七七《靳進墓誌》,第714頁。呼延氏,*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第198頁;《碑林》一四九《和善墓誌》,第375頁。鮮卑的慕容氏,*趙君平、趙文成主編: 《秦晉豫新出土墓誌蒐佚》七六四《唐慕容華墓誌》,第983頁。羌的庫狄氏等等。*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第126—128頁;《續集》儀鳳016《唐處士杜君(美)墓誌銘》,第239頁。其中有些聚落也以這些姓氏命名,如董村、*《碑林》一五一《董禮墓誌》,第383頁。北董村、*《碑林》一五八《董亮墓誌》,第400頁。郝村等,*《秦晉豫新出土墓誌蒐佚》一二六《唐郝世義墓誌》,第165頁。他們可能是集體遷徙而來,當然也有可能是經過長期繁衍而形成。
我們知道,大約自東漢末,匈奴等各族就已開始内遷,與漢人雜居。*唐長孺: 《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122—184頁。西晉時,上黨已成爲羯胡的聚居地,十六國時期翟氏丁零已在中原的政治舞臺嶄露頭角。但爲什麽,這些有可能是胡族後裔的人卻宣稱其先祖晚至北魏時纔定居上黨呢?我們一個不成熟的看法是,或許北魏時期有許多胡族部落已趨於解體,其成員逐漸融入漢族,甚至編户入籍,成爲定居居民。唐長孺先生在《魏晉雜胡考》中談及魏晉時期入居塞内的幾個胡族時説“五胡的割據與拓跋氏的占領北中國造成的後果之一是漢族與邊境各族的融合,但是在過程中間還貫串着鮮卑、氐、羌各族間相互影響與分解、融合的問題……大體上當北魏時期雜胡之中除了稽胡之外就有鮮卑化與漢化的兩大支。”*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429頁。可見北魏是一個胡族融入漢族,轉向定居農耕生活的重要時期。而北魏太和年間實行三長制,整頓户籍則更加速了這一進程。雖然此點在墓誌中並未明確透露,但在較晚一些的唐代墓誌中,隱約提到了定居與編户入籍的關係。如《栗簡墓誌》:“遠祖因官述職,遂編潞州黎城人也。”*《唐故栗府君(簡)墓誌銘記并序》,收於常福江主編: 《長治金石萃編》(上),第169頁。此“編”應爲編户之編。又《王素墓誌》:“則有府君者,并州太原郡人。……遂爲因官逐任,分散他州,置潞府襄垣縣長樂鄉禮教坊人也。”*《唐故王府君(素)墓誌銘記并序》,《全唐文補遺》第七輯,第436頁;另收於常福江主編: 《長治金石萃編》(上),第200頁。此“置”也應與户籍有關。《牛敬福墓誌》説得更清楚:“憲高祖上望,本出隴西,因任此居停留編附壺關爲貫。鄉屬洪山,關壁莊園,永就恒措。”*《碑林》二〇五,第519頁。《任素妻李氏墓誌》的敍述最爲詳盡,其祖“後因官隨任,登涉潞州,寄客居於府城西北廿里壁子村。三代墳塋列在村東而首,本望在於墳州西河,□致别業於上黨,故爲此地人焉。”*《碑林》三一七,第827頁。有别業,有家族墓地,纔算是真正的定居。雖然栗簡等人祖先定居潞州的時間並非北魏,但誌文清楚表明編户入籍被視爲定居的標誌之一,這也可以解釋那些聲稱先祖在北魏時定居潞州的,除了翟氏、郝氏等可能爲胡族後裔的姓氏外,也還有蕭氏、崔氏這樣的傳統漢姓。也許他們的祖先遷居上黨的時間未必皆在北魏,但在其唐代後裔的眼中,卻很容易將定居時間歸到户籍被大量整頓的北魏時期。
此外,根據我們的考察,北魏平北涼後,一部分平涼户被徙至代京,安置於雁門一帶,其中有些逐漸擴散到潞州,他們定居潞州的時期大約也在北魏至隋這段時間。*張葳: 《隋唐時期潞州的申屠氏溯源》,待刊。這些人大部分爲漢族,那些聲稱祖先在北魏以後移居潞州的,也有可能是平涼户的後裔。
以上分析説明,在潞州墓誌中,聲稱其祖先徙居的時間,無論是在西晉還是在北魏,都有值得懷疑之處。其中既包含了某些真實的歷史情況,也有社會歷史記憶綜合影響的結果。而對西晉或北魏的不同選擇,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他們在唐代的子孫出於自身立場而做出的不同選擇。對於一部分漢族而言,他們更願意把西晉視爲其家族徙居的開端,作爲其漢族身份的一種表達;而對胡族而言,他們對祖先的記憶則更多地與北魏聯繫在一起,也許從融入漢文化的那一刻開始,定居纔真正發生。儘管到唐代,無論是漢族還是胡族後裔在文化上已相互融合,都宣稱自己是黄帝的後代,習慣於追溯自西周以來姓氏的演變,但兩者之間的差异仍然滲透在有關家族徙居的歷史記憶中,而這,也許是胡漢移民雜居區域的重要文化特徵。
比之稍晚,還有聲稱北齊時徙居潞州的家族,我們將相關内容列表如下。

表1 北齊徙居潞州者墓誌一覽表
這五方墓誌的撰寫年代基本都在唐開天以前,雖然《李楚墓誌》中並没有提到其家遷居於祖父李纂時,但屯留侯是唐人聲稱其先祖遷居潞州時常用的説法,由此或可推定其家的遷居也發生在北齊。
與之前聲稱祖先在西晉或北魏時移居潞州的墓誌敍述有所不同,這幾方墓誌中先祖的官職不再僅僅是“上黨太守(郡守)”,而有了一些别的職任,如儀同三司、伏波將軍、韓州司户參軍、長平郡守等。從時間上來看,墓主與其北齊曾祖、祖父僅隔兩、三代,記憶應該還比較準確,但細察這些官職,卻不免令人生疑。如儀同三司在北齊位二品,誌題中卻書其僅爲騎都尉;伏波將軍在南北朝頗爲常見,爲第五品上階,*《魏書·官氏志》記北魏時伏波將軍爲第五品上階,北齊官制多循魏制,亦應爲第五品上階。參見《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2984頁。按照北朝後期的贈官制度,其贈官不應該僅爲太守,而應爲更高的都督、行臺、總管之類,這裏仍稱上黨太守,也許是遵循“因宦徙居”的書寫模式;至於韓州司户參軍,由於北周建德六年(578)纔在襄垣設置韓州,*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第423頁。這一職任也不太可信;長平郡守同樣存在這一問題,長平郡在北齊初已廢,隋大業初纔復置,*施和金: 《北齊地理志》卷二《河北地區下》,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第250—251頁。因此北齊不太可能有長平郡守。如此看來,這些關於北齊先祖的官職大都不準確,或許徙居發生的時間更晚,在北周或隋,但在後人模糊的記憶中被遥想成北齊。
三、 隋唐時期徙居潞州的情況
上述分析表明,潞州墓誌追述其祖先在隋唐以前徙居情況時,比較模式化,存在不少想像和粉飾的成分。相對而言,對其祖先在唐以後徙居的敍述則更具個性,也相對更爲真實、可信。如隋末戰亂引發的動蕩導致一些人徙入潞州。陳領的祖父仁“有隋之日,爰命征遼,於時山東諸州,並未賓款,往討德州,遭陷城没落,子孫奔投上黨,遂乃家焉”。*《續集》018《大唐故處仕陳君(領)墓誌銘并序》,第96頁。莫休“但以遠騎從征,近入關於此地。……因楚郡號名,置光身於韓部。”*《碑林》〇九八《莫休墓誌》,第256頁。唐代,自外地徙居潞州的情況可以比較鮮明地分爲兩個階段,唐前期主要是正常情況下的人口流動,如宋元逸“祖降,秀才擢第,任潞州録事參軍,秩滿,因家此焉”。*《碑林》一二五《宋元逸墓誌》,第320頁。而安史之亂前後,遷入的情況則以避亂與從事藩鎮爲主。鑒於安史之亂前後遷入者的情況有其特殊性,並對當地社會産生顯著影響,以下擬對此作詳細探討。
作爲唐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安史之亂影響深遠,自不待言。其所引發的全國範圍内的人口流動規模巨大,特别是這一時期北人南遷的人數和影響直可與永嘉亂後的南遷相提並論。然而長距離的南遷需要耗費大量的財力和物力,還要承擔巨大的未知風險,並非是最佳選擇。*如著名的崔祐甫家族在安史亂中的南遷旅程就充滿了艱辛和死亡,遑論其他。參伊佩霞著,范兆飛譯: 《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2—123頁。相較而言,就近避亂,遷居至北方戰火尚未延燒到的地區或比較偏僻的山區不失爲更好的選擇。*參葛劍雄主編,吴松弟撰: 《中國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時代》,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8頁。上黨居於群山圍繞的高地之上,*此爲“上黨”得名之由來,參東漢劉熙《釋名》,唐李泰《括地志》等所論。杜佑《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稱:“澤、潞兩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狹,積谷全無。”*杜牧: 《樊川文集》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7頁。《大清一統志》亦稱其擁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據天下肩脊,當河朔咽喉,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太行瞰其面,并門負其背。”*仁宗敕纂撰: 《大清一統志》(嘉慶重修)第8册,卷一四二《潞安府一》,四庫叢刊續編史部,上海書店,1984年。不僅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同時環境較爲封閉,自成一體,非常適合避亂。安史之亂前後徙居至此的家庭主要來自於鄰近的并州、洺州一帶。如:
秦承恩,“其先天水郡人……遠祖因官於太原,子孫相承,分枝流派,遂爲太原祁縣人焉。……公因避地移家,久居上黨,經五十餘年矣。”*《碑林》二四〇《秦承恩墓誌》,第615頁。
田意真家,“本松栢并州人也,遷居潞□龍潛處,向四紀焉”。*《彙編》大和082《唐北平故田府君(萬昇)墓誌銘并序》,第2155頁。案此與後條都是出於田意真家族的墓誌,後條“狂胡逋梗,俶擾中華”應該指的是安史之亂。此條稱遷居上黨,“向已四紀矣”,根據墓誌撰寫時間大和八年(834),四紀應該是四十八年,將近五十年的時間,向前推應該是公元786年,安史之亂以後。綜合兩條墓誌内容,可以推斷田意真家是在安史之亂後遷居上黨的。“洎狂胡逋梗,俶擾中華,人無懷土之心,匪唯流於上黨。”*《彙編》元和114《唐故田府君(意真)墓誌銘并序》,第2029頁。
馬考顔,“封家扶風……因官廣平。……時也,頻經凶寇,士馬交横,黎庶流離,人失其業,因居潞焉。”*《碑林》二五一《馬考顔墓誌》,第641頁。
稍遠有來自華州的,如李士温,“本隴西人也。……公士九世祖任華州長史……子孫因先□封食官邑,遂爲華陰人。……頃因離亂(下闕)潞人焉。”*《碑林》二七〇《李士温墓誌》,第696頁。
可見由於戰亂,潞州接收了不少周邊地區的流民。這些流民中像秦承恩、田意真等並未在安史亂平後返回故里,而是就此在潞州定居。張正田先生對安史亂後澤潞地區州縣增廢情況曾進行過考察,指出澤潞地區在這一時期没有增廢州縣,説明這一地區的政治與社會結構較爲穩定,人口流動不大。*張正田: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第73頁。澤州在此不做討論,就潞州而言,它在整體上呈現出的結構穩定,或許是因爲這一時期遷入的人口多少補充了因戰亂而損失的人口。遷入者還有助於本地兵將的補充,如父輩遷入潞州的郭元貴在昭義軍中擔任衙前散將,*《碑林》三四六《郭元貴墓誌》,第902頁。安史亂中遷入的張朝清擔任中軍副將,其子□岩擔任左金吾衛大將軍、百人將,*《碑林》二四五《張朝清墓誌》,第628頁。安史亂後遷入的田意真的四個兒子也都在河東軍或昭義軍中任職。*《彙編》元和114《唐故田府君(意真)墓誌銘并序》,第2029頁。他們都不是從原籍應兵募徵發而來,而是在遷居潞州後纔加入軍隊。
據《舊唐書》記載,澤潞最早的鎮帥程千里曾經於安史之亂爆發後在河東地區招募了十萬人的部隊,駐扎於上黨。*《舊唐書》卷一八七《忠義下·程千里傳》,第4903—4904頁。這十萬人中的大部分應是來自於河東道其他地區,也有出自潞州本地,如:
郝茂光,“望在太原,數世居潞。即平時業善府正員折衝,因安史騷亂,爲國討寇而不迴”。*《碑林》二五五《郝茂光及妻孫氏墓誌》,第653頁。
王守廉,“太原之雅望也。遠祖從宦,因居上黨焉,相襲自遠,迄于盛唐。……頃有叛臣構亂,蟻聚憑陵,屢乃畢力輸忠,志誠□命,恩效左領軍豐州府折衝。”*《彙編》元和133《唐故左領軍衛太原豐州府折衝都尉員外王府君(守廉)墓誌銘并序》,第2043頁。
王駕,“太原人也。因官遷播,奕葉居焉。……豈謂囑逢時難,爲國盡忠,討逆殊功,制賜高勛柱國。官授方州仁里府折衝都尉,賜緋魚袋。”*《碑林》二二九《王駕墓誌》,第588頁。
吕崇一,“遠祖從官,因居上黨焉。……中原叛换,爲國忠良,斬將搴旗,功勛授賞。”*《碑林》二二七《吕崇一墓誌》,第581頁。
田進,“宗本雁門,因官上黨,子孫在此,是爲居人。……頃屬亂離,久從戎幕。……醜徒彌迹,寰海清波。返步鄉園,退就田里。”*《碑林》二五六《田進墓誌》,第655頁。
耐人尋味的是,葬於潞州的以本地士兵爲主,來自其他地區的士兵則大部分未葬於本地,或者他們没有能力製作墓誌。考慮到這支部隊在安史亂中常被調動外出作戰,並未在上黨停留較長時間,出現這種情況也是可能的。此外,外地士兵被徵募時,並非携家眷而來,很多人在亂後大概也都與田進一樣,回到了各自的家鄉。總之,程千里爲鎮帥時期招募的河東士兵留居潞州的應該不太多,而此後昭義軍的組成中本地人也占有主要的分量。*《舊唐書》卷一三二《李抱真傳》:“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沖,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户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傜,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覆命之如初。”第3647頁。

這些自外而來的士人、軍將不僅任職於昭義,也有不少即定居於此,其中又以擔任武職者居多。這能否説明昭義鎮的藩鎮僚佐中,外來的武職僚佐多於文職僚佐呢?*本文對藩鎮文職僚佐、武職僚佐的認定依據嚴耕望: 《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於氏著: 《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6—452頁),張國剛: 《唐代藩鎮軍將職級考略》(收於氏著: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57—174頁)。
按照一般的情況,藩鎮以軍事爲要義,設置的武職多於文職並不奇怪。儘管如此,潞州墓誌中所見外來文職僚佐稀少的情況仍然值得注意。戴偉華先生曾對唐各藩鎮文職僚佐的情況進行整理,*戴偉華: 《唐方鎮文職僚佐考》(修訂本),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就昭義鎮而言,從至德二載(752)王思禮擔任鎮帥到天祐四年(907)李嗣昭擔任昭義軍節度使爲止,大致可確認有68人左右曾任職昭義。*按據戴著統計人數應爲69,但其中所舉《唐代墓誌彙編》貞元040《張石墓誌》與《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山西卷《張石墓誌》實爲同一方墓誌,誌記張石父張茂實曾在安史亂中擔任昭義節度副使,張石爲汝州梁川府折衝都尉,戴書誤以爲張石也曾任昭義節度副使一職,因删。新出史料可進一步將此人數增加到91人。*陳長征: 《〈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增補》(載於《唐都學刊》2010年第5期,第32—36頁)增補2例,但其中1例李仲昌在李抱真手下僅擔任過洺州司倉參軍,今不録;郭茂育: 《〈唐方鎮文職僚佐考〉新補》(載於《圖書館雜誌》2012年第5期,第86—90、96頁)增補1例;石雲濤: 《唐方鎮及文職僚佐考補正》(載於《人文叢刊》第九輯,北京: 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264—285頁)增補1例。另本人在墓誌中新檢20例,參見文末附表。這91人,大部分並非潞州人,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包括節度副使、掌書記、行軍司馬、營田副使、判官、參謀、孔目官、要籍、觀察支使、觀察推官等,説明昭義與其他藩鎮一樣有着數量衆多、職類完備的文職僚佐,但這些文職僚佐中留居、葬於潞州的卻寥寥無幾,大約21例,占23%左右。*這一統計不够精確,昭義軍統轄範圍包括澤、潞、邢、銘、磁等五州,因此有些文職僚佐可能並未居住或葬在潞州,而是居於或葬於其他四州。但考慮到澤、邢、洺、磁州資料很少,而潞州作爲昭義軍治所,其政治地位在諸州中最爲突出,如果外地文職僚佐留居昭義,葬於潞州的數量應該是最多的,從這個角度來説,這一統計仍具有參考價值。我們不妨對此推測一二。
首先應與唐代充任藩鎮文武僚佐人選的身份差异和取向不同有關。據渡邊孝先生對浙西、淮南兩方鎮文職僚佐的考察,二鎮中文職僚佐出身於貴族階層者,占全部人數的2/3,出身不明者占20%,庶姓出身者僅有百分之十幾。*(日) 渡邊孝《唐後半期の藩鎮辟召制につぃての再檢討》,《東洋史研究》60-1,2001,第46、53頁。他所説的貴族,即士族。文職僚佐以士族出身居多,不僅限於浙西、淮南兩方鎮中,而是中晚唐藩鎮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論者指出,中晚唐時期,大量士族後裔涌入藩鎮任幕職是普遍現象。*李翔: 《中晚唐五代藩鎮文職幕僚研究》,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2014年博士論文,第137頁。雖然其具體情況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但無可争辯的是,中晚唐時期,科舉出身的明經、進士多有入幕者,以至文宗、武宗時還對進士出身者入幕進行了限制,*石雲濤: 《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256—257頁。但是效果並不佳。這些人中出自士族的比例較高,*毛漢光: 《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收於氏著: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書店,2002年,第334—364頁。他們在政治、文化上大都以中央爲歸屬,死後也往往歸葬兩京。而武職僚佐呈現的面貌則不同,根據劉琴麗先生的統計,藩鎮武職僚佐中士族階層所占比例較小,庶姓類占了3/4多,具有職業化、世襲化的特點,往往爲軍將子弟所把控。*劉琴麗: 《唐代武官選任制度初探》,第176—177頁。文職與武職僚佐由於社會構成的差别導致他們對藩鎮的感情不同。
説到底,這還是與藩鎮文武僚佐在藩鎮外遷轉之途的差异相關。石雲濤先生在對唐代幕府的研究中指出,“唐代幕制與官制在性質上雖有區别,幕府辟署和中央銓選在程式和方式上也不同,但兩者並未脱節”。使府參佐離開幕府後,“除了一部分由於種種原因不能或不願爲宦者外,大多數則重新進入中央任官銓選的軌道,到朝廷或州縣任官”。*石雲濤: 《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290頁。這主要指的是文職僚佐。戴偉華先生也説:“事實上唐代中後期的文士很多應使幕之聘以作進身之階的,發展到宋代進士必先任幕職。”*戴偉華: 《唐代幕府與文學》,北京: 現代出版社,1990年,第19頁。中晚唐時期,擔任藩鎮的文職僚佐,常常是爲了解決一時的經濟問題和快速進入中央官僚系統,這種過渡性很難令他們選擇長期定居於藩鎮,一些卸任幕職後不再任官的士人,往往也回到家鄉度過餘生。比如中唐時期的詩人熊孺登曾經爲西川從事,也曾在湖南觀察使府擔任判官,在罷職後選擇回到故鄉鍾陵;*傅璇琮主編: 《唐才子傳校箋》第3册,卷六,北京: 中華書局,1990年,第78—80頁。又如李戎,雖然在磁邢居住了大半輩子,最後仍然歸葬洛陽祖塋。*《唐故太常寺協律郎趙郡李公(戎)墓誌銘并序》,《千唐誌齋新藏》,第291頁。
藩鎮武職僚佐的情況則不同。他們在藩鎮外的遷轉之途主要有二,一是入朝爲官,一是隨藩帥移鎮。*劉琴麗: 《唐代武官選任制度初探》,第172—175頁。入朝爲官有人數和級别限制,根據馮金忠先生的統計,唐後期昭義鎮中入朝爲官的僅有朱忠亮一例。*馮金忠: 《唐代河北藩鎮武職僚佐的遷轉流動(一)——以與中央朝官間的流動爲中心》,收於氏著: 《唐代河北藩鎮研究》,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1頁。這在順地藩鎮中實屬罕見。而隨藩帥移鎮的方式,實際上只是隨節度使更换到另一個藩鎮,從嚴格意義上説仍没有進入中央官僚系統。雖然由武職升爲文職僚佐情況會有所不同,但一般都發生於高級武職僚佐中。因此藩鎮武職僚佐進入中央官僚系統並不容易,中下層武職僚佐更缺乏晉升孔道。此外,由於昭義作爲藩鎮的功能主要在於防禦控遏,除劉悟祖孫掌權時期以外,唐廷一直比較有力地掌控着昭義軍節度使的任命權。憲宗時即開始有意識地選擇文人擔任節度使,武宗討平澤潞後,更注意縮短節度使任期,以防節度使與地方發展出錯綜複雜的關係。*張正田: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第191—207頁。凡此種種,都强化了昭義軍武職僚佐的在地化、土著化。因此,無論就制度規定而言,還是從現實發展的情況而論,藩鎮文、武職僚佐與中央官僚系統的親疏之别是導致外來武職僚佐更容易留居潞州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儘管昭義軍的外來文、武職僚佐都有不少,但武職僚佐更容易實現在地化、土著化,這也使得昭義鎮的藩鎮性格更偏於武質化。外來武職僚佐的不斷加入與昭義鎮武質化的藩鎮性格形成相互作用。
潞州的墓誌材料同時顯示,墓主或其親屬擔任昭義鎮武職僚佐的數量也大大超過文職,文職僚佐中以擔任驅使官、要籍這類與節度使關係親密的職務較多,而掌書記、判官等對文學修養要求較高的職務則未見本地人出任。*粗略統計,潞州墓誌中提到墓主或其家人擔任昭義鎮文職僚佐的情況有23例,職務有節度副使,驅使官,要籍等。擔任武職僚佐的情況有64例,職務有兵馬使、十將、散將、押衙、都虞侯等。文職僚佐中,擔任驅使官的比例很高,有9例,要籍4例。這説明不僅外來文職僚佐難以留居潞州,本地人出仕文職或進入中央官僚系統的意願也相對淡漠,他們的文學素質可能也不太高。對此張正田先生早已指出,唐前期澤潞區(包括澤、潞兩州)相對於邢洺區(包括邢、洺、磁三州)遷葬兩京的情況較少,大都遵循“從舊貫葬”的舊習。這其中既有受限於本區地理因素的緣故,也體現出本地地域性格較爲保守的特點。張先生同時指出,澤潞區“不仕”或“歷代皆不仕”頗多,到唐後期更甚,本地没有大士族産生,而新興的莊園主又没有積極地結合官僚體系以取得功名。*張正田: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第94—117頁。這也可以得到正史記載的部分印證,唐中晚期基本上没有出自這一地區的士人載於正史,而新舊《五代史》中所記出於澤潞的人物如安崇阮、李建崇、武漢球等幾乎清一色皆爲武將。*《舊五代史》卷九十《安崇阮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第1186頁;《舊五代史》卷一二九《李建崇傳》,第1701—1702頁;《舊五代史》卷一〇六《武漢球傳》,第1394頁。
儘管如此,傳世文獻和碑誌記載仍顯示,一直以來本地的儒家文化傳統並未斷絶。開天前後,士族遷往兩京的高潮過後,留居於此的仍有儒學修養深厚者。如田佐時,“偉容儀,涉獵經史,好大言時務。……隱居於潞州,懷道高尚。觀察使李抱真,數薦之。自拾遺至諫議,皆不起。”*參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 《册府元龜》卷七七九《總録部·高尚第二》,南京: 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9028—9029頁。又《新唐書》卷一五二《張鎰傳》亦記:“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第4830頁。安士和“考諱良素,儒林洪業,學富九經。寔德長材,聞一知十。不趨名利,靡謁王侯。公禄不窺,安閑樂道,時人號三教通玄先生。”*《碑林》三二一《安士和墓誌》,第833頁。郝四“曾祖將,祖璧,並高結養志,塞門不仕。恣情琴酒,嘯傲林泉,賞風雲,玩書史。……(郝四)丱歲聰敏,弱冠成人。經籍大猷,莫不窮覽。固天多縱,出言有章。恂恂於鄉人,平揖於府縣。”*《碑林》一八三《郝四墓誌》,第461頁。自稱滎陽鄭氏之後的鄭朝尚“樂道自怡,高尚不仕。皆以洪儒碩學,博雅君子。幼而讀書,長而學釰。文武雙美,忠孝兩全。丘園隱迹,里閈哲賢。”朝尚子叔倫“九流諸子,非不□求,三史五經,披尋博攬。”*《碑林》二四二《鄭朝尚及妻栗氏墓誌》,第620頁。
在一些遷入的士人家庭中,也可看到詩書傳統的繼承。李勍“曾祖□,弱冠勤學,明經及弟。調授漢州參軍,遷潞府士曹,因家上黨。祖業,臨漳府折衝都尉、賞緋魚袋。父殊,將仕郎、吏部常選。府君幼習經明,早從鄉薦……以經史□資身之本,以仁義爲一族之源……嗣子□,恭守家風,雅多才藝。專勤禮教,頗擅□名。抱器懷能,才諧仕進。次□,遊學於外,□即榮途。幼□,□□鄉貢明經。”*《碑林》三五五《李勍墓誌》,第925頁。
但上述描述也顯示,像田佐時、安良素等本地士人往往秉持清高不仕的態度。還有一些士人,雖曾有仕進企圖,卻遭遇種種不利,未能如願。如房某“姓(性)本英賢,儒門立仕,年未弱冠,經史並通。功業既成,早蒙鄉貢。纔登省閣,丁妣之憂,乃歸私第,守其禮制,永不求於名利,達其大道者也。”*《大唐西市博物館墓誌》四六二《房府君墓誌》,第997頁。因母喪放弃了大好前程。王玘“好玩墳典,德達儒章,鄉閭薦舉,省門得疾,庠於京□。春秋廿有八,卒於私第。”*《碑林》二二九《王駕墓誌》,第588頁。早逝令他走進長安的步伐戛然而止。也有由文職轉向武職的,如廉汶,“曾門諱元裕,文林郎、守果州朗池縣主簿,後任承務郎,東宫□監丞。皇祖諱均,前鄉貢明經。”到廉汶這一代,則“不墜門地,歷事旌旄”。廉汶的兩個兒子“禮樂立躬,書劍標美。……軍府推景行君子。”*《碑林》二七四《廉汶及妻孫氏墓誌》,第707頁。儘管一些遷入的士人家庭如李勍家族,還能保持儒業的傳續,也更積極於中央官僚系統的仕進,但由於數量較少,使本地不仕的保守態度更占據上風,造成潞州文士匱乏的印象。不仕傾向對中晚唐潞州士人在科舉中的表現也造成影響。以相似的幽州爲例,據統計,中晚唐時期出自幽州的舉子可考的有38人,*劉琴麗: 《中晚唐河北舉子研究》,《史學集刊》2009年第4期,第39—42頁。而我們在唐中後期潞州墓誌中卻只見到數例鄉貢明經,1例鄉貢進士。*《碑林》二七四《廉汶及妻孫氏墓誌》,第707頁;《碑林》三五五《李勍墓誌》,第925頁;《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六七九《唐王傑墓誌》,第875頁。也許這一對比不够精確,但唐末澤潞成爲李克用、朱温集團争奪的重要地區,兩個集團中,河北士人都更爲活躍,也從一個側面説明了這一問題。*陸揚: 《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唐研究》第19卷,第287—329頁。

以上我們對唐中後期昭義鎮文武僚佐遷入的狀況以及潞州本地人出仕文武僚佐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討論。僅想由此説明,或許由於藩鎮文武僚佐的社會構成、政治取向及朝廷對藩鎮文武僚佐不同的政策,導致了昭義鎮外來武職僚佐更多留居潞州,但昭義鎮本地人出仕的情況也表明,他們更傾向於出任武職僚佐。充任文職僚佐的本地資源有限,外來文職僚佐又少有留居潞州,造成人才匱乏,加重了昭義鎮對中央資源的需求和倚賴。
平心而論,潞州從北朝以來就不是一個具有深厚文化資源的地區,不像鄰近的幽薊地區,曾經産生過如范陽盧氏、祖氏等世家大族,比之同區的邢洺也有所不如。可能源於這一地區一直以來屬於兵家必争之地,不斷有移民進入,不能形成本地有影響力的大族,也導致潞州在政治、文化資源上需要更多借助外來力量。中晚唐時期,昭義與唐廷總體緊密的關係使它可以更多地利用中央的政治、文化資源,而不必强求於本地,這或許導致了本地文化基礎的進一步弱化。同時,河朔藩鎮的壓力迫使朝廷要更加確保對澤潞的掌控,特别是武宗平澤潞後,爲了更好地控制昭義軍,唐廷頻繁調任節度使,使得節度使的任期過短,少則數月,多僅三年,與本鎮不足以形成緊密聯繫,不利於他們對本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經營,軍事與軍人成爲這一藩鎮顯著的特色。
四、 結 語
作爲墓誌敍述中的常見用法,“因宦徙居”很容易被視爲模式化的描述,受到忽略。我們選擇以潞州爲研究的出發點,一方面從整體上探討了“因宦徙居”這種敍述模式在唐代墓誌中的普遍化問題,另一方面則以潞州爲具體的個案研究對象,嘗試探討唐代墓誌中所展現的這一地區自晉至唐的人口遷入情況及相關問題。
我們認爲,“因宦徙居”敍述模式在唐代墓誌中的大量出現,並非完全是套話。其敍述内容既存在“虚”的套話的一面,即反映了這一時期非士族墓誌在形式上對士族墓誌的接近和模仿,是這一時期社會上存在的崇尚和攀附士族郡望的體現,它與唐代士族望貫分離現象關係並不大,只是巧妙地爲攀附郡望者所利用,成爲掩飾的借口,又隨着郡望僞濫而演化成墓誌中常見的敍述語式,形成套路化和形式化的措辭。*相關研究還可參見柳立言《宋代墓誌銘的虚與實及其反映的歷史變化——蘇軾乳母任採蓮墓誌銘探微》,北京論壇(2005)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全球化視野中亞洲的機遇與發展:“歷史變化: 實際的、被表現的和想像的”歷史分論壇論文或摘要集(上),第262—283頁。同時,“因宦徙居”敍述模式也存在“實”的一面,我們可以根據墓誌中關於“徙居”的一些具體描述來考察潞州自西晉以來人口遷入的情況。發現,徙居發生時間距離唐代愈遠,則相關的描述愈加呈現一致化,比較突出地表現在徙居的祖先往往擔任的都是上黨太守(郡守)、屯留侯一類的官爵。這説明,對於唐代的子孫而言,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其祖先具體的徙居過程已不重要,但何時徙居仍然被視爲一個重要問題,因此對於徙居時間的描述,出現了西晉、北魏、北齊等不同説法。其中聲稱西晉末永嘉之亂時遷徙的漢姓比較多,我們認爲這並不符合史實,推測可能帶有標明、强調漢族身份的意圖;聲稱北魏時期徙居的人群中則既有漢姓也有胡姓,這或許與北魏時期户籍的大量整頓有關,也可能是遷徙至代京、雁門的北魏平涼户擴散到了潞州。不管怎樣,我們認爲一部分胡姓以北魏作爲其祖先徙居潞州的起點,可能是一種刻意的選擇,與其胡族身份有關。從中似乎可以窺見,儘管到唐代,漢族和胡族後裔在生活、文化上已經互相融合,但他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定仍能通過家族徙居的歷史記憶顯露出來;聲稱祖先徙居發生在北齊的幾則墓誌,在關於先祖官職的敍述上更多元化,但具體考之,則大多不符合史實,這可能與缺乏族譜等系統記録家族歷史的文字資料有關。
相對來説,隋唐時期,關於徙居情況的描述漸趨具體和個性化,其内容也更趨於真實的歷史描述,這讓我們大致可以了解隋唐以後潞州地區的人口遷入情況。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安史之亂前後,遷入潞州的人口明顯增多,有些是爲了避亂從鄰近地區遷入,有些則是亂後爲了謀取更多的政治發展機會而從事藩鎮,此時潞州對外來移民的吸引力與其作爲昭義鎮的軍政中心有一定關係。我們發現,因避亂而定居潞州的家庭,其後代中有一些成爲昭義軍的士兵和軍將,而因從事藩鎮,最終定居潞州的僚佐,也以武職居多,似乎武職是他們更傾向的選擇,這可能與唐廷對藩鎮文武僚佐實行的不同政策有關,也與昭義鎮在唐帝國中所處的地位有關。可以説,唐中晚期潞州遷入人口的特點既是昭義鎮作爲控禦防遏型藩鎮導向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昭義鎮進一步武質化,兩者互爲因果,共同塑造了中晚唐的昭義鎮,使其呈現出以軍事與軍人爲顯著特徵的藩鎮性格。*需要指出的是,這裏僅重點討論了潞州一地的情況,中晚唐昭義鎮治下的其他地區情況可能有所差异,但潞州作爲昭義鎮的治所,應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唐末潞州墓誌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敍述傾向,即記述墓主貫屬,詳至某鄉某村或某鄉某坊,五代至宋,這種情況更爲普遍,並不僅限於潞州,考其墓主多非士人。對墓主籍貫的詳盡敍述在北朝墓誌中也出現過,如《韋彧墓誌》:“京兆杜人也,今分山北縣洪固鄉疇貴里。”*羅新、葉煒: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五四,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128頁。《高殷妻李難勝墓誌》:“趙郡柏仁永寧鄉陰灌里人也。”*羅新、葉煒: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七八,第194頁。但這些籍貫其實是墓主郡望,並非其實際居住地。而潞州墓誌中所述貫屬、貫居則表明此地爲其目前所居地,且如果誌主因故不居於此,誌文中也會有所説明,如《苗存墓誌》:“本當府屯留縣蒲汭鄉穀西村人。……早因家户寄迹戎門,遂流居府内。”*趙文成、趙君平主編: 《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九七九《宋苗存墓誌并蓋》,第1358頁。《牛安墓誌》:“牛府君本貫壺關縣崇賢村,見在府城市東街□□王宅矮槐園内住。”*趙文成、趙君平主編: 《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九八七《宋牛安墓誌》,第1366頁。爲何從唐末開始,非士人的墓誌中會出現這樣的傾向,我們推測或許是他們和本地之間的聯繫加强,亦或是基層户口制度更趨完善?總之,墓誌記敍的重點有了變化。在隋唐五代買地券中,也常會詳述墓主生前居住鄉里貫屬的情況,而買地券在晚唐五代也呈現出逐漸增多的趨勢,*魯西奇: 《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第三章《隋唐五代買地券叢考》,厦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76—259頁。這種敍述是否對同期墓誌的書寫産生影響?還是兩者受到共同的政治、文化因素影響?或俟有識者進一步研究。

附表: 新出史料所見昭義鎮文職僚佐

續表

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