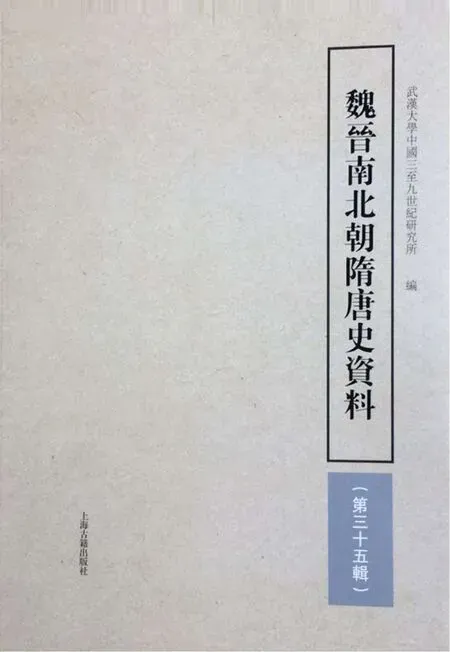武英殿本與四庫本《唐會要》非同本考
2018-01-02劉安志
劉安志
武英殿本與四庫本《唐會要》非同本考
劉安志
一、 序 言
北宋王溥所撰《唐會要》一百卷,是研究唐代歷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史籍。惜宋刻本不存,僅以鈔本傳世,故脱誤頗多。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開館,館臣對徵集來的《唐會要》鈔本進行加工整理,修成武英殿聚珍本(以下簡稱殿本)和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兩種《唐會要》本子,流傳至今,其中尤以殿本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工完善的江蘇書局本(以下統稱殿本),影響最爲深遠。今天通用的中華書局本(以下簡稱中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以下簡稱上古本)、陝西三秦出版社本(以下簡稱三秦本)等,即屬此類。*《唐會要》,北京: 中華書局,195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006年新1版(本文據新1版);牛繼清: 《唐會要校證》,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2年。按中華本乃用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原紙重印,源自殿本,並做了一定的校勘。上古本則以江蘇書局本爲底本,校以殿本、上海圖書館所藏四種《唐會要》鈔本,以及《舊唐書》、《册府元龜》、《通典》等書,被認爲是整理精良的本子。三秦本同樣以江蘇書局本爲底本,校以殿本、四庫本,及兩《唐書》、《通典》、《資治通鑑》、《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等文獻。
隨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數字化與電子化,四庫本《唐會要》的原貌及其與殿本之間的差异,已逐漸爲學人所熟知。然殿本與四庫本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同爲一書,二本爲何差异頗大?這種差异反映了什麽問題?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探討和解明的問題。同時,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也有助於準確認識殿本與四庫本的原貌及其相關史料價值,爲今後《唐會要》的整理與研究提供某些參考和借鑒。
學界一般認爲,殿本與四庫本《唐會要》所據底本,同屬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如日本學者島田正郎先生、周殿傑先生及上古本《唐會要·前言》等皆持此説。*(日) 島田正郎: 《在台北·国立中央圖書館藏鈔本·唐會要について》,《律令制の諸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84年,第669—689頁。羅亮譯、劉安志校漢譯文,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周殿傑: 《關於〈唐會要〉的流傳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上古本《唐會要·前言》,第11頁。吴楓、黄永年等先生雖未明言出自汪啓淑家藏本,但都指出武英殿本據《四庫》本排印。*吴楓: 《隋唐歷史文獻集釋》,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5頁。黄永年: 《唐史史料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70頁。當然,也有個别學者持折衷説法,如牛繼清先生即認爲,後來收入四庫全書史部的《唐會要》,就是汪氏家藏本,而武英殿本則是四庫館臣并四庫本與“又一别本”而成的本子。*牛繼清: 《唐會要校證·前言》,第6頁。
四庫本與殿本如果是同本,爲何會在内容上出現差异?董興豔博士認爲這是後人校改的原因。*董興豔: 《〈唐會要〉研究》,厦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19—120頁。顧成瑞先生通過考察殿本與四庫本及國家圖書館藏鈔本卷五七《翰林院》“中書待詔”與“書待詔”之异同,指出殿本“中”係衍字,認爲四庫本修成在先,殿本後來刊行時,並未使用館臣校勘的成果,殿本非盡善之本,四庫本則經館臣整理,具有很高的校勘價值。*顧成瑞: 《〈唐會要〉版本獻疑——從標點本〈唐會要〉一條材料説起》,《書品》2012年第6期。黄正建先生在細緻比較四庫本與殿本《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與《議刑輕重》之後,指出四庫本可能更接近《唐會要》原貌,*黄正建: 《〈唐會要〉校證獻疑: 以卷三九爲例》,《東方早報》2015年5月17日,第010版。但未論證二本何以出現這種差异的原因。
日本學者古畑徹先生在認真比較四庫本、殿本、臺北圖書館所藏《唐會要》兩鈔本、日本静嘉堂所藏《唐會要》鈔本五個版本基礎上,首次指出,殿本與四庫本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二本源自不同的底本,認爲四庫本所據底本爲浙江汪啓淑家藏本,而殿本所據底本則爲清初存在的某個“刻本”之節本。*按古畑徹氏在《〈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東方學》第七十八輯,1989年,第82—95頁)一文中,最先提出清初存在某種《唐會要》刻本的觀點。其後,又在1998年發表的《〈唐會要〉の流傳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史研究》五十七—一,第96—124頁)一文中,進一步修正、完善其既有觀點,認爲殿本所依據的底本,是流傳至清初的某種宋刻本之節本。
古畑徹先生從其所掌握的三種《唐會要》鈔本入手,通過比較其與殿本、四庫本之异同,進而對《唐會要》版本流傳問題提出新解。這一研究極具啓發性。雖然他有關殿本與四庫本所據不同底本的相關判斷和認識,尚存扞格難通之處,但首次指出二本爲不同版本的觀點,卻是值得充分重視的。本文擬在古畑徹先生及前人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參據目前所掌握的數種《唐會要》鈔本及相關文獻,對殿本與四庫本所據底本問題續作探討,以期對四庫本《唐會要》有更爲深入的認識,進而爲今後《唐會要》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二、 《唐會要》鈔本存在不同的傳抄系統
迄今所知國内外所藏《唐會要》鈔本,總有十六種之多,其中國家圖書館藏三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二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種,上海圖書館藏四種,浙江圖書館藏一種,江蘇鎮江圖書館藏一種,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一種,臺北圖書館藏二種,日本東京静嘉堂文庫藏一種。古畑徹先生在比較臺北、東京所藏三鈔本與四庫本、殿本之异同後,指出清初《唐會要》鈔本應該有一個以上的版本傳寫,所言甚是。*(日) 古畑徹: 《〈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七種《唐會要》鈔本,*七種鈔本情況大致如下: 國家圖書館藏有三種《唐會要》鈔本,已全部上網。其中編號10521爲明鈔本(以下簡稱國圖A鈔本),03873號(以下簡稱國圖B鈔本)、04216號(以下簡稱國圖C鈔本)兩種爲清鈔本。鄭明《〈唐會要〉初探》(中國唐史學會編: 《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167—182頁)一文,曾對此三種鈔本有過介紹。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唐會要》鈔本一種(以下簡稱廣圖本),亦屬清鈔本,已於2015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卷》第二十四、二十五册。臺北圖書館藏有《唐會要》康熙舊鈔本(以下簡稱臺北A鈔本)、舊鈔本(以下簡稱臺北B鈔本)兩種,日本學者島田正郎、古畑徹在前揭文中對兩種鈔本都有過介紹和考釋。尤其是臺北A鈔本,業已確認即浙江汪啓淑家藏本。筆者曾蒙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朱振宏教授慷慨相助,獲得此兩種鈔本的複印本。日本東京静嘉堂文庫藏有《唐會要》鈔本(以下簡稱静嘉堂鈔本)一種,平岡武夫先生早年有過介紹,認爲是明鈔本(《唐代の行政地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5年,第19頁),古畑徹先生則考證認爲是康熙年間鈔本(氏著《〈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筆者已通過購買方式獲得静嘉堂鈔本的複印件。可以證明這些鈔本其實存在着不同的傳抄系統。最爲明顯的例子,就是這些鈔本中卷九二至九四的三卷文字的殘闕與否。按臺北A、B兩鈔本與静嘉堂鈔本,經古畑徹先生考證,認爲皆屬康熙或康熙以前寫本。*(日) 古畑徹: 《〈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這三種鈔本中,卷九二《内外官料錢下》皆僅存長慶二年至會昌二年諸條内容,其後《内外官職田》、《諸司諸色本錢上》及卷九三、九四皆闕。國圖A鈔本乃明鈔本,僅存四○卷,其卷八五以後皆闕;國圖B、C兩種鈔本皆爲清鈔本,然B鈔本卷九二殘闕情況同臺北A、B兩鈔本與静嘉堂鈔本,卷九三與其他各卷書法不同,似爲後人所補,因此卷子目分爲《諸司諸色本錢上》、《諸司諸色本錢下》,且内容也與殿本《唐會要》卷九三同,故極有可能乃後人據殿本所補。該鈔本卷九四書法與卷九三有异,子目與内容雖與殿本相近,但差异至爲明顯,如多次使用“嗣聖”年號紀年,以致達“十八年”者,而殿本只使用“嗣聖三年”、“嗣聖四年”兩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卷抄有“玄”、“弘”、“暦”諸字,完全不避康熙、乾隆皇帝諱,可見其抄寫時間當在康熙以前。國圖C鈔本、廣圖本卷九二至九四這三卷與殿本同,已避“弘”、“暦”二字諱,當爲後人據殿本所補。
上述情況足以證明,清初的《唐會要》鈔本,實際存在着不同的傳抄系統。值得一提的是,與國圖B鈔本卷九四相比,四庫本《唐會要》卷九三、九四除把《北突厥》分爲上下外,其餘文字内容皆與國圖B鈔本同,尤其是“嗣聖”紀年的使用上,二本完全一樣,這説明國圖B鈔本與四庫本所據底本之間,當存在着某種密切的淵源關係。殿本則與二本有所不同。據黄麗婧、吴玉貴二位先生考證,四庫本卷九三、九四與殿本卷九四,乃後人據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所補。*黄麗婧: 《〈唐會要〉闕卷後人僞撰考》,《江淮論壇》2012年第4期。吴玉貴: 《〈唐會要〉突厥、吐谷渾卷補撰考》,《文史》2015年第2輯。從國圖B鈔本不避“玄”、“弘”、“暦”諸字諱看,這一補撰工作早在康熙以前就已完成了。以此言之,四庫本卷九三、九四文字内容,並非四庫館臣所補撰,應該是可以肯定的。而殿本卷九四内容,與國圖B鈔本、四庫本已有若干差异,三種版本之間究竟是何種關係,就值得考慮了。不管如何,乾隆以前的《唐會要》鈔本存在着不同的傳抄系統,則是可以肯定的,這對考察四庫本與殿本是否同本問題極有助益。
三、 殿本與四庫本《唐會要》之差异
古畑徹、黄正建、董興豔諸先生都在其前揭相關論著中,指出了殿本與四庫本《唐會要》存在的種種差异,本節擬從二本目録與子目差异、内容是否完整、文字有否异同等方面展開進一步論證,確認二本非同一版本。
1. 目録與子目差异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殿本《唐會要》有完整的目録,而現存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諸四庫本皆無,*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會要》外,筆者在朋友和學生幫助下,對現存文津閣本、文溯閣本、文瀾閣本《唐會要》進行了調查,確認諸本皆無目録,且文淵、文津、文瀾三閣卷七至十各子目下亦無殿本“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之類的雙行小字標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圖書館所藏文瀾閣本《唐會要》,雖無目録,但卷七至十、卷九二至九四子目與其他閣本有异,而與殿本同,推測原本有可能毁於1861年太平軍攻占杭州時,後人乃以殿本補抄而成,已非四庫全書本了。浙圖所藏文瀾閣本《唐會要》的調查,承蒙該館曹海花博士的熱心幫助,謹致謝忱!另外,文溯閣《唐會要》的情況有些特殊,承蘭州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易雪梅副館長見告,卷七、十有“補”字,卷八、九無“補”字。文溯閣爲何與其他三閣不同,尚待進一步求證。爲何如此?劉遠遊先生曾對此有過探討,認爲文淵閣本《唐會要》、《春秋經解》、《元史》、《元豐九域志》四種原本應該是有目録的,後來因爲底本和《提要》出現撤换,導致目録遺失。*劉遠遊: 《〈四庫全書〉卷首提要的原文撤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僅就《唐會要》而言,劉氏這一看法,或許對認識和理解殿本與四庫本《提要》相同這一特點有所助益(詳後),但没法解釋文津、文溯、文瀾三閣本爲何目録也同樣缺失這一問題。從現存種種迹象看,筆者推測,四庫本所據底本可能原來就没有目録。比較後人增補的卷七至十、卷九三至九四子目,與殿本和國内外所藏諸鈔本目録和子目之异同,即可看出此點。
筆者曾考證指出,四庫本《唐會要》卷七至十内容,乃清人沈叔埏據秦蕙田《五禮通考》所補。*劉安志: 《〈唐會要〉“補亡四卷”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殿本明言此數卷文字據四庫本録入,但各卷子目並未從四庫本。爲便於説明問題,兹列表分析如下。

四庫本、殿本《唐會要》卷七至十子目异同表
③按“齋戒”等條,實乃補撰者照抄秦蕙田《五禮通考》而不加細查。其實,這些條目屬“皇帝冬日至祀圓丘儀”中的文字,作爲本卷的子目實在有些不倫不類,這也反映了補撰者工作的粗疏。
據上表,殿本與四庫本《唐會要》卷七至十的子目名稱,明顯存在着差异。筆者掌握的七種《唐會要》鈔本中,除臺北B鈔本無目録外,其餘六種鈔本目録均爲: 卷七《封禪》(按: 國圖A鈔本缺卷七目録),卷八《郊議上》,卷九《雜郊議下》,卷十《親拜郊》、《雜録》、《親迎氣》、《后土》、《藉田》、《藉田東郊儀》、《九宫壇》、《皇后親蠶》。這應即《唐會要》原本目録。殿本雖據四庫本抄録,但目録和子目基本依據原目,僅把卷八改爲《郊議》、卷九《雜郊議》分上下兩卷、卷十《雜録》移至《親迎氣》之後。而四庫本子目則與原目存在較大差异。這種差异説明四庫本整理者並未按照《唐會要》原目進行增補,其原因或在於四庫本所據底本目録原已佚失。
除卷七至十外,四庫本卷九三至九四的分卷與子目,同樣也與殿本有异。四庫本卷九三子目爲《北突厥上》,卷九四爲《北突厥下》、《西突厥》、《西陀突厥》、《吐谷渾》,而殿本卷九三爲《諸司諸色本錢上》、《諸司諸色本錢下》,卷九四爲《北突厥》、《西突厥》、《沙陀突厥》、《吐谷渾》,與四庫本明顯有异。再看諸鈔本的目録,國圖B、C鈔本及廣圖本、臺北A鈔本、静嘉堂鈔本皆爲: 卷九三《諸司諸色本錢下》,卷九四《北突厥》、《西突厥》、《沙陀突厥》、《吐谷渾》,這同樣也是《唐會要》原目。殿本只是把卷九二的《諸司諸色本錢上》下移至卷九三,做了適度的調整,而四庫本則與原卷目次完全不合。這樣把原屬九四卷的《北突厥》,强行拆分爲《北突厥上》與《北突厥下》,並爲《北突厥上》單列一卷,置於卷九三,致使原卷九三《諸司諸色本錢下》消失不存,而原目卷九二《諸司諸色本錢上》也因此失去前後依託。四庫本所據底本抄寫者或補撰者爲何進行如此分卷安排?感覺有些不可理喻。個中原因,或與原本目録缺失有關,否則不會率意如此。
綜上所述,再結合目前所見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諸四庫本皆無目録這一特點,筆者推斷,四庫本《唐會要》所據底本,極有可能原本目録缺失。類似情況,在現存諸鈔本中也有存在,如臺北B鈔本即是如此。
另外,四庫本與殿本在子目方面存在的差异,也有若干,如四庫本卷五七《左右僕射》“建中元年三月”條乃錯簡,其後子目爲《左右司員外郎》,同樣也是錯簡,殿本則無此問題。諸鈔本中,國圖B鈔本、臺北A鈔本、静嘉堂鈔本同樣出現錯簡,而國圖C鈔本、臺北B鈔本則無錯簡,這説明當時的諸鈔本之間其實存在着不同的傳抄系統。
又如,四庫本卷六六《北京軍器庫》,殿本作《西京軍器庫》;四庫本卷七五《附科甲》,殿本作《附甲》;四庫本卷九八《霫國》,殿本作《霫國》;四庫本卷九九《朱俱婆國》,殿本作《朱俱波國》;四庫本卷一○○《大辭彌國》、《舍利毗迦國》、《波羅舍利國》,殿本分别作《火辭彌國》、《金利毗迦國》、《哥羅舍分國》。等等。
四庫本與殿本不僅在子目名稱上存在差异,而且殿本中有些子目,如卷九六《渤海》、卷九九《南平蠻》、卷一○○《多福國》等,均不見於四庫本,也反映了二本之間存在明顯差异。
總之,四庫本與殿本在目録、卷次及子目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少差异。這些差异表明二本極有可能屬於不同的版本。
2. 内容是否完整
在内容是否完整方面,相較而言,殿本《唐會要》除卷三《内職》末尾標有雙行夾注“此條原本有闕”六字外,其餘皆完整無缺。四庫本則不一樣,多處標“闕”,如卷三八《葬》、卷四三《五星臨犯》、卷五○《觀》、卷五三《雜録》、卷六○《御史臺》、卷六九《州府及縣加減員》、卷七○《州縣改置上·關内道》、卷七五《東都選》等;也有少數幾處標“原闕”,如卷三一《裘冕》、卷九二《内外官職田》等。“闕”與“原闕”皆表明這些地方原本是殘缺不全的。從目前所見《唐會要》諸鈔本情況看,普遍存在殘缺不全的情況,《四庫全書總目》稱“今僅傳鈔本,脱誤頗多”,*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唐會要·提要》,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確屬實情。很明顯,殿本之相對完整,乃是四庫館臣進行增補、修訂和完善之故。此點日本學者島田正郎、古畑徹均在前揭文中早已指出。問題是,這些增補和修訂,是否符合《唐會要》原貌,恐怕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唐會要》各鈔本之間也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差异,如國圖B鈔本卷三一《裘冕》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條“又云悉與”後空闕十數行,其後接抄“禮惟從俗”云云。而其餘六種鈔本“又云悉與”後皆不闕,接抄“宰相二十三人”云云,内容與上文絶不相干,這裏明顯出現了錯簡。臺北A鈔本該頁上有粗筆眉批:“‘宰相’以下至‘謚曰聖穆景文’止,應改入《帝號》,以補懿宗、僖宗並昭宗前半之缺。此處係傳鈔之誤。”此後第3頁又有眉批:“‘禮惟從俗’以下,仍接前《裘冕》事。中間疑有闕誤。”這一眉批是否爲四庫館臣所爲,尚待求證。然四種鈔本均出現同樣的錯簡,表明它們當源自同一鈔本系統。有趣的是,四庫本《唐會要》卷三一《裘冕》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條“又云”後同樣空闕十數行,其後接抄“天下禮惟從俗”云云。這種殘闕情況和抄寫格式,與國圖B鈔本相同,而上文所言四庫本與國圖B鈔本卷五七《左右僕射》、《左右司員外郎》同樣出現錯簡,四庫本與國圖B鈔本之密切關係至爲明顯,二本有可能源自同一鈔本系統。上文對二本卷九三至九四兩卷内容之分析,也已表明此點。
殿本卷三一《裘冕》前後内容完整,明顯乃四庫館臣所增補。*國圖A鈔本即明鈔本,同樣出現錯簡,有可能是後來鈔本之源頭,但相關内容錯入卷二《帝號下》宣宗條後。殿本所記内容與之不合,可證爲清人增補。認真考察殿本所記文字,實據《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所補。此涉及《唐會要》佚文問題,容另文探討。殿本所據底本原貌爲何尚不清楚,然其卷九二《内外官職田》與四庫本之間存在的明顯差异,足可證明二者並非源自同一鈔本系統。按殿本卷九二《内外官職田》總存二十餘條記事,内容前後完整。而四庫本卷九二《内外官職田》下標“原闕”,中空2行半後再接抄“五品以上田”等内容,總存四條記事,其中有二條並不見於殿本記載,另外二條文字也與殿本不盡相同。古畑徹先生曾考證指出,殿本此處乃後人據《册府元龜》等書增補,並非《唐會要》原文,而四庫本所殘存的四條記事,則是《唐會要》原文。*(日) 古畑徹: 《〈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這種差异表明殿本與四庫本不可能出自同一底本。如果二者同出一個底本,殿本只需在原有四條記事基礎上進行增補完善,而不會無緣無故删除原本所記條文内容了。
另外,殿本有些内容並不見於四庫本,如卷四一《酷吏》載初元年九月條“十曰求破家”之後,殿本尚有雙行夾注:“王宏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中華本,第740頁。上古本,第866頁。三秦本,第634頁。“宏”,上古本與三秦本皆作“弘”。國圖B、C鈔本、廣圖本與臺北A、B鈔本皆同殿本,然四庫本並無此注。值得注意的是,静嘉堂鈔本卷四一《酷吏》“十曰求”後闕1行,亦無雙行夾注,情形與四庫本略同。*古畑徹先生已最先指出此點,參見氏著: 《〈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這説明四庫本卷四一《酷吏》下闕雙行夾注這一情況,早在康熙年間的《唐會要》鈔本中就已出現,其並非個案或孤例,是顯而易見的。諸鈔本之間存在不同的傳抄系統,於此又添新證。雙行夾注的有無,也可證明殿本與四庫本並非出自同一個版本。
3. 文字异同
有證據表明,殿本與四庫本的整理者並非同班人員。如《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貞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條,除國圖C鈔本外,其餘六種鈔本皆空闕二字:
正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減(闕二字)入徒者七十一條。
按國圖C鈔本亦空闕二字格,但有後人補入的“軍流”二字,四庫本與殿本對此則有不同的增補:
貞觀十一年……分爲十二卷,減死罪入徒者七十一條。(四庫本)*《唐會要》,四庫本,第520頁。
貞觀十一年……分爲十二卷,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殿本)*《唐會要》,中華本,第701頁。
四庫本補入“死罪”二字,雖不知其所據爲何,但所補内容與鈔本殘闕二字情況正相吻合。而殿本據《舊唐書·刑法志》補入“大辟者九十二條”、“流”等八字,*《舊唐書》卷五○《刑法志》載:“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2138頁。與四庫本明顯有异。此種情況的出現,當與二本分屬不同人員整理有關。同卷《議刑輕重》會昌三年十二月條,可進一步證明此點。
與《定格令》一樣,除國圖C鈔本外,其餘六種鈔本卷三九《議刑輕重》“刑部郎中”後皆空闕二字:
(會昌)三年十二月,澤潞劉稹平,欲定其母裴氏罪,令百寮議之。刑部郎中(闕二字)議曰(後略)。
國圖C鈔本亦闕二字,後人補一“等”字,四庫本與殿本所補同樣不同:
(會昌)三年十二月……刑部大理等議曰(後略)。(四庫本)*《唐會要》,四庫本,第531頁。
(會昌)三年十二月……刑部郎中陳商議曰(後略)。(殿本)*《唐會要》,中華本,第715頁。
殿本於“刑部郎中”後補“陳商”二字,正與前揭鈔本殘闕情況相吻合。而四庫本作“刑部大理等議”,與殿本和諸鈔本皆不合,其原因或在於所據底本不同,或是整理者隨意增補、删改所致。不管如何,四庫本與殿本的這一差异,可進一步説明二本整理者並非同班人員。
類似諸鈔本殘闕而四庫本與殿本所補文字並不一致的例子,尚有不少。當然,如上文所述,四庫本並非對原底本所有殘闕之處都進行了增補,故書中多處標記“闕”、“原闕”字樣,從而大致保留了所據底本的若干原貌。殿本則不然,對原底本進行了全面增補,然所補内容是否皆《唐會要》原文,就很難説了。因此,在利用殿本《唐會要》所記相關史實時,有必要對四庫本和諸鈔本《唐會要》予以充分關注。
四庫本與殿本文字上的差异,不僅表明二本整理者不同,而且所據底本也有不同。兹再舉一例,以證此點。據《唐會要》卷一○○《日本國》載,武周長安三年(703),日本遣其大臣朝臣真人來朝事,四庫本與殿本所記略有不同:
長安三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來朝……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温雅。則天宴之,授司膳卿而還。(四庫本)*《唐會要》,四庫本,第433頁。
長安三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來朝……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閑雅可人。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而還。(殿本)*《唐會要》,中華本,第1792頁。
相較殿本而言,四庫本多了“則天”二字,但又無“可人”、“麟德殿”五字。這種文字上的差异,導致文義也出現了不同。如果二本所據爲同一底本,如何理解這種差异?對此,《唐會要》諸鈔本又是如何記載的呢?經核查,諸鈔本皆無“麟德殿”三字。“可人”,國圖B鈔本同殿本,*據日本學者榎本淳一先生對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盛鐸舊藏《唐會要》鈔本的調查,其卷一○○《日本國》亦作“容止閑雅可人”,無“麟德殿”三字。參(日) 榎本淳一: 《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舊藏〈唐會要〉の倭國·日本國條について》,《工學院大學共通課程研究論叢》39-2,2002年。又收入氏著: 《唐王朝と古代日本》附論二,東京: 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188頁。臺北A鈔本、静嘉堂鈔本作“則人”,國圖C鈔本、廣圖本、臺北B鈔本作“則天”。可見,諸鈔本存在“則天”、“則人”、“可人”三種不同的記載,四庫本與殿本所記,皆淵源有自,各有所本。據《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日本國傳》、《太平御覽》卷七八二《四夷部三·日本國》引《唐書》,皆云“(朝臣真人)容止温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舊唐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5340—5341頁。《太平御覽》,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第3466頁。可證《唐會要》原本作“則天”。由此不難看出,“則人”實乃“則天”傳抄之誤,“可人”則是“則人”傳抄之誤。諸鈔本之間各自不同的傳抄關係,於此可見一斑。至於殿本中出現的“麟德殿”三字,推測整理者感覺“宴之”二字有些不詞,遂據《舊唐書》進行增補。從諸鈔本所記情況看,《唐會要》原本並無此三字。
總之,上述四庫本與殿本“則天”、“可人”之不同記載,均能在諸鈔本中找到其源頭,説明二本各有所據,其並非出自同一版本,足可肯定。那麽,四庫本與殿本各自所據底本爲何?《四庫全書總目·〈唐會要〉提要》中,曾提及“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又一别本”兩個《唐會要》鈔本,這兩個鈔本與其後成書的四庫本和殿本是何關係?如何理解四庫本與殿本《唐會要·提要》内容相同這一問題呢?下節擬對此展開探討。
四、 《四庫全書總目·〈唐會要〉提要》辨析
關於《唐會要·提要》,存在《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本、殿本等多個版本。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明確記載《唐會要》出自“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乃《四庫全書總目》的删節版,四庫本《唐會要》書前提要記有“恭校上”時間和總纂官、總校官姓名。*四庫本《唐會要》書前提要,也存在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瀾閣之别。文淵閣“恭校上”時間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文溯閣則爲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參見《金毓黻手定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 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第358—359頁。本文所論《唐會要》,主要依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除此之外,在具體介紹《唐會要》作者、成書過程及其版本流傳等方面,諸本《提要》大體一致,並無什麽明顯差异。那麽,如果認定四庫本與殿本源自不同底本的話,又將如何認識和理解二本《提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呢?故而有必要結合四庫本與殿本的實際情況,重新對《提要》所記内容展開分析與考辨,確認其與四庫本和殿本之關係。
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唐會要·提要》載:*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第694頁。
《唐會要》一百卷(浙江江啓淑家藏本)
宋王溥撰。(中略)今僅傳鈔本,脱誤頗多。八卷題曰《郊儀》,而所載乃南唐事;九卷題曰《雜郊儀》,而所載乃唐初奏疏,皆與目録不相應;七卷、十卷亦多錯入他文。蓋原書殘闕,而後人妄摭竄入,以盈卷帙。又一别本,所闕四卷亦同,而有補亡四卷,採摭諸書,所載唐事依原目編類,雖未必合溥之舊本,而宏綱細目,約略粗具,猶可以見其大凡。今據以録入,仍各注補字於標目之下,以示區别焉。
上揭《提要》所記,尤可注意者,有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今僅傳鈔本,脱誤頗多”,説明當時四庫館臣所見《唐會要》版本,皆爲鈔本,這與明末清初大儒朱彝尊所言可以相互印證。按朱氏《曝書亭集》卷四五《唐會要跋》有如下記載:*朱彝尊: 《曝書亭集》,上海: 世界書局,1937年,第545頁。
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常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缺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按朱彝尊生於1629年,卒於1709年,其購之四十年而不得“雕本”,此事當發生在清初時期。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本《唐會要》修成進上,四庫館臣仍稱“今僅傳鈔本”,説明當時所見《唐會要》,皆爲鈔本。不僅如此,參與《四庫全書》編纂工作並擔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的彭元瑞(1731—1803),也在其手校鈔本《唐會要》書前題有“是書傳鈔都無善本”之識語。*《唐會要·前言》,上古本,第7頁。即使到嘉慶初年刊刻武英殿本《唐會要》,其書前提要仍説“今僅傳鈔本”,未提及此前有任何刻本發現之事。清末周星詒述及常熟錢氏鈔本時,亦明言“此書舊無刊本”。*邵懿辰撰,邵章續録: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八《史部十三·政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334頁。因此,古畑徹先生推測當時存在某個《唐會要》刻本之節本,並認爲是殿本所據之底本,其説頗感理據不足。另外,古畑氏據《國朝宫史續編》卷九四《書籍二十·校刊》所記“御定重刻唐會要一部。宋王溥撰,凡一百卷。奉敕校刊”,*慶桂等編纂,左步清校點: 《國朝宫史續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18頁。指出《御定重刻唐會要》即指武英殿聚珍版《唐會要》,既稱“重刻”,説明殿本以前尚有刻本,並可能是殿本的底本。*(日) 古畑徹: 《〈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按《國朝宫史續編》卷九四所記,除“御定重刻唐會要一部”外,尚有“御定重刻論語集解義疏一部”、“御定重刻補後漢書年表”、“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詩一部”等,*慶桂等編纂,左步清校點: 《國朝宫史續編》,第917—918頁。皆明記“奉敕校刊”。然除《唐會要》外,其餘三書皆不在目前所確認的一三八種《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參見張升: 《四庫全書館研究》附録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纂校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90—404頁。另外,《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爲宋代熊方所撰,後收入《四庫全書》,所據底本爲編修汪如藻家藏本,而此前于敏中等於乾隆四十年(1775)撰成的《欽定天禄琳琅書目》中,亦明確記載“宜其此書刋行流傳絶尠,是不能不有賴於影鈔矣”。*于敏中等撰: 《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卷四《影宋鈔史部·集補後漢書年表(一函四册)》,收入《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二四二册,臺北: 世界書局,1990年,第594頁。若按古畑氏之推斷,《補後漢書年表》與《唐會要》一樣,此前都已有刻本的話,那如何理解如上清人的相關記載呢?其實,所謂“重刻”,乃指重新刻印圖書,並非在原刻本基礎上重新刊刻,古畑氏的理解似有偏差,其推斷恐難成立。
其二,“又一别本,所闕四卷亦同,而有補亡四卷,採摭諸書,所載唐事依原目編類,雖未必合溥之舊本,而宏綱細目,約略粗具,猶可以見其大凡”,表明當時四庫館臣所掌握的《唐會要》鈔本,除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外,尚有另一“别本”,當然也可能還有其他鈔本。此“别本”具體情況如何,並不清楚,然其卷七至十殘闕情況亦同汪啓淑家藏本,並有後人采摭諸書予以增補的“補亡四卷”。换言之,此本卷七至十文字,已屬後人增補的“補亡四卷”。有趣的是,如上文所指出的,四庫本《唐會要》卷七至十内容,乃清人沈叔埏據秦蕙田《五禮通考》所補,殿本《唐會要》卷七至十又據四庫本增補。很明顯,就卷七至十内容皆爲後人所補這一相同特點看,“别本”與四庫本當存在某種關聯。
其三,“今據以録入,仍各注補字於標目之下,以示區别焉”。所謂“今據以録入”,即指據“别本”中“補亡四卷”録入書中。然其後“仍各注補字於標目之下”一語,頗值注意。觀四庫本與殿本卷七至卷十標目之下是否有“補”字,即可知道《提要》所述究竟是指何書了。
殿本目録中,卷七、卷八、卷九上、卷九下、卷十上、卷十下皆注“補”字;正文中,子目“唐會要卷七”、“唐會要卷八”、“唐會要卷九上”、“唐會要卷九下”、“唐會要卷十上”、“唐會要卷十下”下,皆有雙行夾注“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十一字。其後同治年間刊印的江蘇書局本,亦復如此。可見,殿本《唐會要》明確標記“補”字注文,是確鑿無疑的。反觀四庫本《唐會要》,文淵閣、文津閣、文瀾閣諸本,皆闕目録,且正文卷七至十子目下並無殿本“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之類的注文,也無“補”之類的字樣。*承蘭州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易雪梅副館長調查見告,文溯閣《唐會要》卷七、卷十有“補”字,卷八、卷九無“補”字。文溯閣《唐會要》的這一標記,與文淵閣、文津閣、文瀾閣《唐會要》不同,原因爲何,尚待進一步求證。可見,四庫本與殿本在是否標注“補”字這一點上,差异至爲明顯。
》所言“今據以録入”,與殿本夾行標注“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二者正相吻合,昭昭顯示汪啓淑家藏本與殿本之密切關係。再聯繫現存四庫本《唐會要》皆無“補”字這一特徵,則《提要》所述,是指殿本而非四庫本,至爲明顯。
關於四庫本與殿本是否標注“補”字,鄭明先生較早注意到這一差异,然不解其緣故。*鄭明: 《〈唐會要〉初探》,中國唐史學會編: 《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178頁。結合上節所述四庫本與殿本存在之種種差异,以及《提要》所言與二本是否吻合之情況,筆者認爲,其原因即在於《提要》所述,其實是對殿本之介紹,而與四庫本無關。這可進一步證明上述四庫本與殿本實爲不同版本之觀點。
那麽,如何理解四庫本《唐會要》書前提要除“恭校上”時間、總纂官與總校官名外,其餘主體内容與殿本書前提要完全一致呢?前揭劉遠遊先生在《〈四庫全書〉卷首提要的原文撤换》一文中,*劉遠遊: 《〈四庫全書〉卷首提要的原文撤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曾論及文淵閣本《唐會要》、《春秋經解》、《元史》、《元豐九域志》等書,因底本撤换而導致書前提要出現不同的問題。另外,在《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一書“影印前言”中,亦舉出若干例證,指出《四庫全書》因版本更换而導致提要出現差异的問題。*金毓黻輯: 《金毓黻手定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 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第4—6頁。可見,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因底本或版本發生更换而導致相關問題的出現,並非個别現象。上文業已論證,四庫本與殿本《唐會要》並非同一版本或底本,這種提要相同而版本不同的現象,有無可能也是因爲底本或版本發生更换而導致的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按《四庫全書總目》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編修,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稿完成,四十七年(1782)七月修改定稿。*參見崔富章: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文史》2004年第2輯。而汪啓淑家藏本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就已進呈四庫全書館(詳下),四庫館臣當據汪本初擬《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標注《唐會要》出自“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可明此點。然後來基於某種考慮,四庫館臣用某一别本替换汪啓淑家藏本收入《四庫全書》,又未及撰寫新本《提要》,繼續沿用汪本《提要》,故而導致版本不同而《提要》相同的問題。限於史料,這當然僅是筆者的一種大膽推測,尚有待進一步證實。不過,北宋孫覺所撰《春秋經解》一書,同樣分别編入《四庫全書》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亦存在底本有异而《提要》基本相同的情形,*參見葛焕禮: 《孫覺〈春秋經解〉四庫本訛誤考析》,載《史學月刊》2005年第7期。這説明《唐會要》並非個案或孤例。
五、 殿本與四庫本各有所本考
上節結合殿本與四庫本實際情況,對《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唐會要·提要》進行了若干考辨,確認《提要》乃是對殿本的介紹,而與四庫本無關,這與二本之間存在的種種差异也頗相契合。《提要》明記出自“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可知殿本所據底本即汪啓淑家藏本。據日本學者島田正郎先生調查,臺北圖書館所藏《唐會要》康熙舊鈔本(即臺北A鈔本),實即浙江汪啓淑家藏本。該鈔本第一册裱紙中央上部押有6.3×9.9cm的朱印,上書: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
撫三寶送到汪啓淑家藏
唐 會 要 壹 部
計書貳拾肆 本*“本”,島田正郎先生原文作“部”,今據原鈔本影本改。參見前揭島田氏文。
其中下劃綫部分係朱筆所書。同册卷首中央上部押有10.2cm的方印,上面刻有滿漢兩種文字的“翰林院印”。這件鈔本寬17.3cm,長26.5cm,半頁12行,每行25字。第七卷到第十卷散佚,後人用他書補充而成。島田先生還指出,該鈔本卷九二第二條(内外官職田)以下及卷九三、九四皆闕失,其與朱彝尊在借抄常熟錢氏本跋中的記載完全一致。兩者應該來自同一個足本。鈔本是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開館時浙江汪啓淑進獻的家藏本,四庫館抄録後退回汪家。*參見前揭島田氏文。經核查原鈔本複印本,島田先生所言,除朱印位於裱紙中央上部(應爲下部)有誤外,其餘皆屬實。
如前所述,古畑徹先生認爲四庫本《唐會要》所據底本爲汪啓淑家藏本,然在比較汪本與四庫本之异同後,感覺此説尚存若干疑問,尤其在目録、分卷及子目關係問題上,二本彼此無法相互對應。首先,汪本一百卷目録完整無闕,而四庫本闕目録,且不僅文淵閣本如此,其餘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諸本亦復如此,這恐怕不是因爲個别閣本抄漏的問題,也不是因爲底本撤换所導致的問題,而是四庫本所據底本原本就没有目録。其次,就二本的分卷與子目情況看,汪本(即臺北A鈔本)卷七至十目録與子目皆同其他鈔本,依次爲卷七《封禪》、卷八《郊議上》、卷九《雜郊議下》、卷十《親拜郊》等;而四庫本無目録,其子目及分卷與汪本頗有不同,《封禪》分上、下卷,卷九上爲《郊祭》,卷九下則出現《齋戒》等引文條目,並非子目名稱,卷十上爲《親拜郊(正月祈穀)》、《親迎氣》、《后土(方丘)》、《后土(社稷)》,卷十下爲《籍田》、《九宫壇》、《皇后親蠶》,二本差异至爲明顯。值得一提的是,如上文所述,殿本雖據四庫本抄録,然子目並不從四庫本。殿本除改《郊議上》爲《郊議》、《雜郊議》分上下兩卷、卷十分上下兩卷外,其餘皆同汪本。此外,上文還指出,四庫本卷九三、九四子目也與殿本和其他諸鈔本不同。汪本卷九三、九四目録同其他諸鈔本,卷九三爲《諸司諸色本錢下》,卷九四爲《北突厥》、《西突厥》、《沙陀突厥》、《吐谷渾》,惜兩卷子目和具體内容完全闕失;而四庫本卷九二《内外官料錢下》、《内外官職田》後闕,卷九三子目爲《北突厥上》,卷九四爲《北突厥下》、《西突厥》、《西陀突厥》、《吐谷渾》,與汪本目録完全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庫本卷九三、九四,乃後人據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所補,然其相關内容已見於國圖B鈔本,只是分卷不同而已。國圖B鈔本卷九四不避“玄”、“弘”、“暦”諸字諱,表明後人對突厥等卷的補撰工作,早在康熙之前就已完成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清人沈叔埏奉魚門太史程晉芳之命校《唐會要》,亦稱該本(即江淮馬裕家藏本,詳下)卷九二、九三、九四三卷尚存,同樣可以證明突厥等卷在此前已被補撰。再比較四庫本與汪本卷九二的相關記載,不難發現,汪本卷九二首頁存《内外官料錢下》、《内外官職田》、《諸司諸色本錢上》三條子目,然正文僅存《内外官料錢下》諸條,其後闕;而四庫本卷九二《内外官料錢下》後,尚存《内外官職田》四條,明顯也與汪本不合。綜上所述,四庫本與汪本不少方面均存在着明顯的差异,尤其是二本卷九三、九四兩卷内容的有無,可證四庫本不可能以汪啓淑家藏本爲底本。當然,汪本與殿本之間也存在着種種不同,殿本如何在汪本基礎上進行增補、修訂和完善,仍有待另文探討。
既然確認殿本與四庫本並不同本,且殿本所據底本爲浙江汪啓淑家藏本,那四庫本所據底本爲何呢?前揭《唐會要·提要》所言“又一别本”,與四庫本有無關係?清人沈叔埏《頣彩堂文集》卷八《書自補〈唐會要〉手稿後》的一段記載,或有助於這一問題的解答:*沈叔埏: 《頤彩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第一四五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9頁。
乾隆戊戌(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魚門太史屬余校《唐會要》百卷,内第七卷至九卷,竹垞跋所謂失去雜以他書者也。余因鈔新舊《唐書》及《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册府元龜》諸書補之,且以七卷之《封禪》分作二卷,八卷之《郊議》、九卷之《雜郊議》并爲一卷,則十卷之《親拜郊》以《雜録》并入,繼以《親迎氣》,《后土》則分《方丘》、《社稷》,《藉田》則以《藉田東郊儀》并入,《九宫壇》則專抄《禮儀志》,終以《皇后親蠶》,四卷遂成完書。至竹垞所闕之九十二三四三卷,此本尚存。蓋館書之進,自邗上馬氏嶰穀、涉江兄弟所藏者,勝虞山錢氏本多矣。昔褚少孫補《史記》……諸人皆以補史著稱,而余以抄撮成此,於少孫輩特札吏比耳,豈可同年語耶!
沈氏的這一記載,對重新認識《唐會要》版本流傳,以及四庫館臣如何纂修《唐會要》諸問題,均極富研究價值。“魚門太史”,即時任四庫館總目協勘官的程晉芳。乾隆四十三年九月,程晉芳令沈叔埏校《唐會要》時,已距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汪啓淑家藏本進館近五年時間,這説明四庫館臣當時至少掌握了兩種《唐會要》鈔本,而且有關《唐會要》的整理工作,至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仍未完成。據沈氏所記,其所整理的《唐會要》一百卷,“自邗上馬氏嶰穀、涉江兄弟所藏者”,即江淮馬裕家藏本。由此不難推知,當時對《唐會要》的整理,是由不同的人員進行的,這與本文第一節所揭殿本與四庫本分由不同人員整理的情況,可以相互印證。沈氏自言“余因鈔新舊《唐書》及《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册府元龜》諸書補之”,雖非事實,但所述“以七卷之《封禪》分作二卷,八卷之《郊議》、九卷之《雜郊議》並爲一卷,則十卷之《親拜郊》以《雜録》并入,繼以《親迎氣》,《后土》則分《方丘》、《社稷》,《藉田》則以《藉田東郊儀》并入,《九宫壇》則專抄《禮儀志》,終以《皇后親蠶》,四卷遂成完書”,則與四庫本《唐會要》卷七至十子目完全相符。牛繼清先生曾指出:“沈氏所云與《四庫》本《唐會要》分卷目次恰同,而其時程晉芳(字魚門)在四庫館任總目協勘官,據此則《唐會要提要》所言‘又一别本’抑即沈氏所補本歟?倘如此,《提要》撰寫者又何不直言爲沈氏所輯補呢?姑存疑待考。”*牛繼清: 《唐會要校證·前言》,第6頁。牛氏所疑不無道理。據《唐會要·提要》:“又一别本,所闕四卷亦同,而有補亡四卷。”此“别本”已有“補亡四卷”,與沈氏所言“四卷遂成完書”,也頗相契合。因此,沈叔埏所補《唐會要》,極有可能就是《唐會要·提要》中的“又一别本”,即馬裕家藏本。
又據沈叔埏所記,他整理的《唐會要》卷九二、九三、九四三卷内容尚存,而臺北A鈔本(即汪啓淑家藏本)卷九二第二面後闕,卷九三、九四兩卷全闕,殘闕情形與朱彝尊所見常熟錢氏鈔本同。現已確知,《唐會要》卷九三、九四兩卷乃後人增補,而沈氏所補本此二卷尚存,説明此事並非四庫館臣所爲。而且,如上文所言,國圖B鈔本卷九四不避“弘”、“暦”二字諱,表明後人對此突厥等卷的補撰,早在乾隆之前即已完成。四庫本卷九二《内外官職田》後雖有殘闕,但其卷九三、九四是完整的,且其内容除避“玄”、“弘”、“暦”諸字諱外,其餘皆與國圖B鈔本卷九四相同,表明四庫本卷九三、九四並非四庫館臣所補撰,其内容應早已存在於所據底本中。這一情形與沈叔埏所補本也頗相契合,再結合沈氏所補卷七至卷十的分卷目次及目録名稱,皆與四庫本完全一致情況看,沈氏所補《唐會要》,應該可以判定就是四庫本所據底本了。换言之,四庫本的底本實爲江淮鹽商馬裕家藏本,而非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汪啓淑家藏本就已入獻四庫館,而沈叔埏奉程晉芳之命校馬裕家藏本《唐會要》,已遲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此相距文淵閣四庫本“恭校上”時間“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僅三年多時間。要在短期内完成《唐會要》卷七至十的增補任務,並非易事,故沈叔埏雖據秦蕙田《五禮通考》完成了“補亡四卷”這一工作,但疏誤、失查之處仍有不少,*參見拙文《〈唐會要〉“補亡四卷”考》,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當時增補工作的緊迫性。沈氏何時完成這一增補工作,未見其明言,但四庫館臣最終確定沈氏所校馬裕家藏本,取代汪啓淑家藏本入選《四庫全書》,只能發生在沈氏增補工作完成之後,其後還有抄寫、校訂等一系列工作。沈氏從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開始接手《唐會要》整理工作,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四庫本成書定稿,其間時間至爲緊迫。而殿本“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的相關標記,表明當時四庫館臣對汪啓淑家藏本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在此情況下,相較汪本而言,經沈叔埏整理的馬裕家藏本,既有“補亡四卷”,又卷九二至卷九四三卷尚存,全書除目録殘缺外,整體尚較完整,故最終被四庫館臣選定,取代汪本編入《四庫全書》。或許因爲時間緊迫之故,倉促之間未及對四庫新本撰寫《提要》,僅在原擬汪本《提要》基礎上進行加工完善,然後直接附於四庫本《唐會要》書前,從而導致版本不同而《提要》相同的問題。儘管如此,四庫本殘闕之處仍有不少,書中“闕”、“原闕”標注時有所見,難稱完本。因此,在《四庫全書》編纂工作完成後,四庫館臣繼續對汪啓淑家藏本進行加工整理,並參據相關史料和記載,大致補足所有殘缺之處(僅卷三《内職》一處未補),使之在體系和内容上更趨完備,直到嘉慶初年纔正式刊刻問世,形成在後世影響極大並廣爲流傳的武英殿本《唐會要》。
六、 結 語
以上對四庫本和殿本《唐會要》的底本問題進行了若干粗淺探討,初步認爲,四庫本所據底本爲江淮馬裕家藏本,而殿本所據底本則爲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四庫全書總目》之《唐會要·提要》,其實是對殿本的介紹,而與四庫本無關。至於四庫本與殿本《提要》之所以相同,其原因有可能是底本發生替换所致。
正因爲四庫本與殿本所據底本各自不同,故二本在子目和具體内容上都存在不少差异。這兩個版本分别都經過了四庫館臣的整理,相對而言,四庫本對原鈔本的加工整理不是太大,其原因或許受時間所限,但因此保留了原鈔本的不少面貌,故書中多次標記“闕”、“原闕”等字樣。而殿本則對原鈔本進行了大量加工、修補和完善,雖在體系和内容上更趨完整和齊備,但不少内容已非《唐會要》原貌,觀其與四庫本和諸鈔本之間存在的種種差异,即可明白此點。因此,在使用殿本及相關整理本時,實有必要認真參考四庫本及諸鈔本的相關記載。從這一意義上講,今後《唐會要》的整理與研究,依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