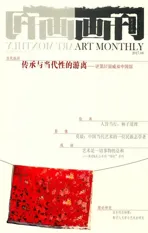人皆当行,衲子道理
2017-12-14寒碧
寒 碧
人皆当行,衲子道理
寒 碧

《常是我来新雨后》 衲子 纸本水墨 45cm×34cm 2016年
我与衲子先生本不相识,昔曾读过他的画,觉得品格比较高,宽闲未掩恣意,道气不毁情灵。但都属吉光片羽,并不曾大量经眼。
他日前办了个展览,规模并不是很大,却每一幅都有可观之处,这令我非常惊讶。
我和衲子的另一重因缘,是同与周汝昌先生有过交往。不过我是向周先生问学,应比他早一些时日,只是后来一度南走,从此就再无见面的机缘。彼时他已真盲聋,鳞鸿往返亦未便。我们曾有约定,我给他写信,他不用回复,可那时我亦忙迫,因此有头无尾,也就断了联系。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之前,好多年我没都有敢去打扰,自然,也就无从与衲子先生有所交集。
衲子的一本画集,扉页即周先生的题诗,流连前辈手泽,不禁感激动容,也难免为之怅触。我最早的一卷旧体诗集即由周先生删存题序,算来将近30年了。今先生墓草无人,而我亦青丝换雪,天命不常,风尘倦眼,徒咨嗟耳。
但是这个座谈,却是我的主张。全由公器作用,不关任何私谊。
京生[1]命了题目,要谈“衲子现象”。依照今日常言习见,“现象”就是某种效应,或者就是某种显在,着眼于影响范围,小可在圈内,大可及社会;又据更为普遍的理解,“现象”乃与“本质”相对,惟其凝视现象,易于无视本质。但胡塞尔不赞同这个说法,而以为现象最关本质,其“意向”照耀本质,本质就在其中,现象将之显现。
胡塞尔将“现象”命为“显现者”,他的解释来自希腊文,此处且不考镜源流,因与讨论关系不大。唯一有关的是“显现”和“现象”的中文翻译,我要回到动词理解:“现”之于“象”,是个动宾结构。

《露气》 衲子 纸本水墨 34.5cm×69cm 2016年
所以可以说,“衲子现象”就有两个言说角度:一是衲子究为何种“现象”?二是衲子所“现”究为何“象”?我想简略地就后者申说,用以贡献对前者的支持。
衲子的画,主要指花鸟画,我个人粗浅的看法,洵可推当世独步,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无人与之比伦。这不是对赏定论,我本人无此资格;也不是吹嘘上天,我与他并无深交。
但是,即使未觉这个评价俗气,也要小心是否标置过高,所以就应该花些心思,提供依据。这依据何所来哉?无疑是笔墨语言,或者讲得复杂一点,就是我的发言题目:“衲子的笔墨道理。”
衲子的画,有很强的笔墨意识和从容生发能力,心手乘除,自成结构,两笔不作三笔,尽量约言丰义。我说他品格高,可按其朴素性,不虚张,无矫饰,旨归在平淡冲和,有安舒自得的宽和理致,而不失韵秀虚灵的情趣机锋,兼得稳重大方,自有一种风度。按说他的题材并不新鲜,整体的才调格局,包括逗露的法律布置,均波澜于明清以来的文人画风潮。这个风潮近现代以来(“五四”期间、“四九”之后)曾有以阻遏,却没有堵死,陈师曾、吴昌硕、齐白石,实践外加理论,可以观为巨澜。直到李苦禅,仍绮丽为余波。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新文人画”的开展,其成果虽稍嫌平弱,但一直能自成格局,与主流的“毛笔加速写”、“改造中国画”相对应,乃至成对反,有一种非主流的不服气,尽管其遭逢不如意。
因为在历史文脉上有所依据,所以其不大可能断港随流,这个依据的宽泛解释,就是由儒释道传统共同作用的“写心随意”之学,更职是之故,就未及挖掘或不屑展开西方统绪下的“造型”理论。不但不去“造型”,甚至不去求“型”。居然“型”与“形”两不重,至少从宋元已肇端,并且很快形成主要共识。虽在此之前,晋唐讲“形神兼备”,但“气韵”必也为主,宋元尚“意气”、“道理”(在画家为生意、为画理),到明清就都归笔墨语言了。恽南田倡言“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可以肯定他这样想:在“笔墨”和“气韵”面前,“型”之“造”或“形”之“求”,不过是“见与儿童邻”的“描头画角”,既不关“画理”,更不知“化理”。而所谓“老成人”之“典型”,要关注的就是“造化”,戴熙的名言“吾心自有造化”,就开明了这个命脉问题。
这种思想支撑或价值依据,按照童中焘教授的说法,就是所谓“笔墨天地”、“笔墨实体”。我和他比较熟悉,常就此研索开谈。他是接续传统的一位,得一种文儒式的思考,又曾亲炙潘天寿先生光仪,所以对中国画(不限于文人画,更强调士人画)的理解较深,能明眼看到画之学问与人之品格的深刻关系。所谓“天地”、“实体”,最终是讲“人道”,古人也称“文道”,“人文”赞化“天地”,所以比于“三才”。这早在刘勰的时代,已统称为“自然之道”。

衲子作品
我前面讲到衲子画中的“道”气,最好不要局于道流或者禅趣解会,还是宏通为最:“周道如砥”之道、“道不远人”之道、“朝闻夕死”之道……这是我想说的关键问题,也就还要回到或重复前言:按说衲子的作品,所涉题材并不丰富,笔墨形式也无多新造,画同类题材的人很多,用同样画法的也不少,他怎么就独步称奇了呢?其差异性或辨识度如何确认呢?这个不能回避的一点,就关系于“笔墨道理”了。
“笔墨道理”是我临时措词,概念是否准确,大家可以商量。我只想强调,它不是“笔墨”,也不是“画理”。这是个特殊问题,先贤早有所体察,钟繇就认识到了“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或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显然是一种笼罩性的彻上彻下,命脉在“全体此心”的感知存养。理学家常言“入道静守”,伊川说“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所以古来士学文心,常言“顶天立地”,此意深蕴文脉,并非虚饰标榜。

《荷》 衲子 纸本水墨 104cm×70cm
黄大痴讲“石分三面”的时候,说“理”字最要紧,他讲的是“画理”。王原祁崇拜大痴,却从来不重这种画理,而只说“画石欲活忌板,用笔飞舞不滞”。林木写过一本《明清文人画》,我虽不尽赞同他的观点,却特别赞赏其敏锐对比。他说黄公望讲的理是自然生成规律,属于造化之理;王石谷则以笔墨为中心,只追求抽象形式的处理。而我的看法是:假如把境界推得更大,应该不是生成规律、抽象形式的关系了,而要联及石涛的“画从心者障自远”,这就是“写心随意”的“参赞化”,或可称顺受其理的“真造化”。
“画理”和“化理”,有高下、有宽窄,都是“道”之所当行。“理”者,“条理道路”,或称“经纬脉络”,这一点,清儒王双池讲得既辨且辩,他写过一本《读〈读书录〉》,既析言“道”与“理”之别,复酌议“道”与“义”之殊:
“义是人去行那路如此处。往京师向北行,往福建向南走,故义者,宜也。路皆是路,行之则随事各有其宜……”

《甲子大雪夜灯》 衲子 纸本水墨 68cm×68cm
我想就此评论衲子,他的笔墨意识,也包括所画题材,不过就是“人皆可行之路”,或“人皆当行之道”,重要的是那个“随事各宜”的“义”或“理”,他是深深悟到了。因此他的生命感受和生活思考,就不隔于“画理”以致“化理”,自然调畅于心手关系,安然呈现为作品气息,显然关联着人品格调,平淡、安详、沉稳、言简意赅、单刀直入,这究竟是讲画呢,还是在讲人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惟有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画。人外无画,画外无人,人以画见,画以人传,笔墨是他自己,面目是他自己,内心是他自己,所以不同于他人,又不与他人对立,我称为“和而不同的差异性”,或“周而不比”的辨认度。温和极了,含蓄极了。
所以衲子这个人,最为重情理。我这样一种评断,是读画读出来的:他不会强调反叛或反抗,不会龂龂于“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说辞,而时不时回头向后看,会安步当车往前走,以水到渠成得修证。故其师从王慎生、王雪涛,一直崇仰不忘情,却与他们不一样。我也看到李苦禅的影响,但避免了过于熟练的挥洒。我也感到他对齐白石的崇拜与心解,却也没有尾随齐白石的热烈和洋溢。而只从个人的才情和心性的 养成出发,呈现为亲切的生活感受和安分的人间情怀(当然包括深刻的笔墨理解),而平淡了许多、松弛了许多、安详了很多。

衲子作品
如果让我指出某种不足,或提供一些建议,我个人的粗浅感觉,就是他的格局还没有全部撑开,气象还不够阔大,这当然是更高的期望?也许是无理的要求。
我还想讲一讲“花鸟画”与“宋明理学”的内在联络问题,所谓“乐意相关禽对话,生香不断树交花”,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思才智和生命理解,但是感到发言太冗长了,如果不即刻停止,无疑会导致对各位的冒犯。
2017年7月24日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注释:
[1]朱京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
编者注:本文为衲子绘画座谈会发言稿。经作者本人裁定。原标题为《衲子的笔墨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