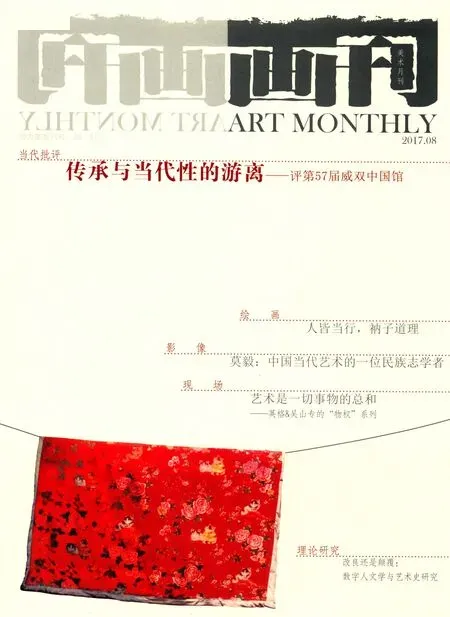余晖犹在
2017-12-14郁俊
郁 俊
余晖犹在
郁 俊
写在前面:《画刊》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本特别有影响的杂志。30多年前,也就是我刚开始启蒙的时候,《江苏画刊》就给出了当时很难得的资料呈现和审美标准,精美得都有一些异样。记得当时我死盯着梅清、萧云从和王原祁的山水画,目光贪婪得都不愿意挪开。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江苏画刊》的创刊号和第2期。第一次啊,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精美的印刷品。当时这些图像的惊艳程度,不是今天看惯了真假二玄、眼高于顶的美院学生可以体会的。
风水轮流转,纸媒风光不再。我揣摩,靳卫红主编和她的团队,也经历了一些辛苦,才能够让这本杂志保持了一贯水准和格调。南京,是令我百感交集的美丽古城,也是让我的职业生涯开始步入正轨的福地。不仅仅大丰先师,几乎所有一线的南京前辈,都或多或少对我本人产生过影响。本文已是我的专栏第12期了,给大家交一份年终小结。如果这个专栏能够为此地诞生的艺术杂志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实在也是很荣幸的事。
我暂居的地方,距离本焕祖庭弘法寺,很近。南北窗都可看山。深圳这几天又多雨,早上起来,看到山被云彩笼着,山上一堆一堆,满布葱绿的树。
写了一年的专栏,这次是最后一篇。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精辟、特别新鲜的话题再来交代,无非是就着这么好的雨云笼罩的山色,来写一点对当今绘画的遗憾和期待。
虽然我一直不太认可中国画这个提法,但是为了理解起见,就这么来约定俗成地说说看。中国画几百年来,最大也最令人遗憾的问题,就是色彩。
如果粗略划分的话,国画的基本元素是线条,就像油画的基本元素是色彩,在照相无限普及的今天,造型准确与否,已经慢慢让位于其他的绘画问题,所以线条和色彩,是现在从事绘画这一行业的人,理应比较注意的课题。但是国画,如果没有对色彩,甚至是写生色彩关注的话,其实也是不可能发展和走到今天的。
上海博物馆有一张特别引人入胜的画,谈不上镇馆之宝,不过这幅画和董其昌的《秋兴八景》,一直是上海博物馆绘画收藏方面非常非常难得的杰作。这张画就是《吴兴清远》手卷,原为赵孟頫所作,上博收藏的是赵孟頫外孙崔彦辅所临的摹本。
历来都把赵孟頫定位成一个复古的书画家。他对身边的遭遇、元人统治,可能不太满意,他对南宋,当然也不会太满意,甚至对北宋也不太满意,所以他老人家要穿越,回到唐朝去。这张《吴兴清远》,一般人也认为是对唐朝山水画的模拟之作。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幅画在色彩上特别微妙、特别写生的一些运用。
那幅画是所谓的平远山水。在视平线的尽头,山的轮廓线和天空交界的地方,赵孟頫非常细心地用赭石染出了一片很漂亮、很瑰丽的晚霞,使得前面大青绿画的山水衬托得有一点点苍白。整幅画的天和水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和反复渲染,这种处理技术,包括对色彩的敏感程度,根本不输给印象派主义大师。
百年来,很多有抱负的艺术家都在考虑,如何把中国画和西画做一些良性的组合和嫁接,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色彩问题。因为站在中国画的角度上,艺术家首先解决的问题,必然是线条,把色彩慢慢地忽略掉了。反而是晚清,岭南居家兄弟和任伯年,还带着一点有意思的追求。民国这一块弱了,用的色彩都非常简单僵化。
当时的浮世绘呢,色彩精妙、敏感,对实景写生的尊重,甚至情绪的表达,都已经优于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家。印象派宣称对浮世绘的借鉴,并不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画的好处,而实在是一个从美术史上来讲,特别顺理成章的选择。
最近的一些中国画家,也会谈到色彩的问题;但是主要考虑什么是矿物颜色纯正性之类,还是在所谓复古命题上纠缠。而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色彩的耐久程度,其实和是不是矿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主要还是看原料厂商的良心。这种单纯的材料问题,并不应该成为一个值得艺术家去关注,甚至可以自我炫耀的点。

《吴兴清远图》[元]崔彦辅摹赵孟頫 绢本设色
虽然本世纪已经不是一个架上绘画作为主流表达的艺术时代了,可是西方绘画界,依然有尤恩·厄格罗(Euan Uglow,1932-2000年)这样的大师,在色彩上、在造型上,取得了空前的突破,依然不停地有色彩大师涌现出来。
国画的材料,因为水性,毛笔的尖锐、敏感和流畅程度,都是西方油画不太能够企及的。放弃这样的优势,放弃千百年来我们的色彩教养,去做一些程式化的东西,太令人痛心了。这也和当代的国画美术教育有关,和当代的国画色彩观落后陈腐有关。
说穿了,还是这句老话,所有问题,都是基本功问题;解决好基本功,你什么都有了。可惜了,我们这个时代都比较着急,想到基本功问题的人并不多。唉,色彩,不是最起码、最基本的绘画课题吗?
好了,诸君保重,有空再喝茶聊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