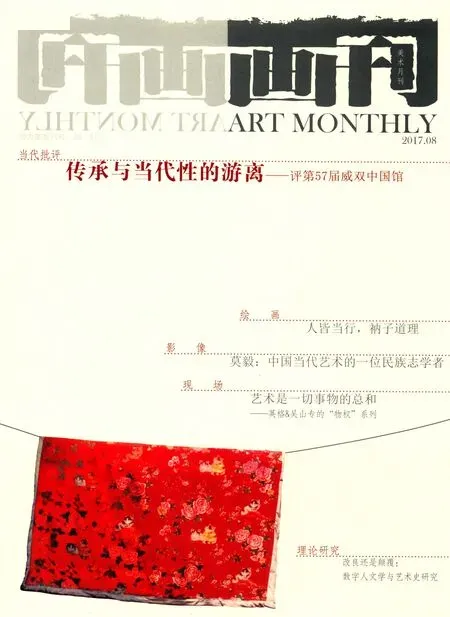艺术是一切事物的总和
——英格amp;吴山专的“物权”系列
2017-12-14高士明
高士明
艺术是一切事物的总和
——英格amp;吴山专的“物权”系列
高士明

“起因和从中投射出来的例如物”展览现场
20世纪90年代初,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Inga Svala Thorsdottir)出现在吴山专的生命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之于吴山专,不只是合作者,而且是对话者。吴的极端复杂、英格的极端纯粹,构成了一种思想上相生相克的关系。如同张颂仁所说:英格对吴,或吴对英格,是一种相对的“镜化”关系,镜里反映的“问号”是各自的“反向面”。1992年后吴山专名下的大多数作品都出自二人的“合谋”,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结合。这些作品汇聚了国内和海外两个体制、两种情境“之间”的生活经验,呈现出从这种相异的经验出发对于世界的不同解读。
我猜想英格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吴山专,并直接造成了吴山专作品的气质性转变。
首先是“彩虹美学”[1]。吴山专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以两张A4纸上的红色为标志的,其一是1985年的《75%红,20%黑,5%白》,其二是1990年的《怎样从超市中偷一千种红》。前者是“意识形态的红”,按照色彩成分被分解开,从1至100填满整张表格;后者则是从超市的各种商品中搜集到的不同的红,裁剪成小方块贴满从1至100的表格。这超市中的红是商品的红,同中有异的红,是红之家族谱系中绽放出的一道彩虹。这是吴山专和英格的工作中出现的第一道彩虹,从此之后,“彩虹美学”以及它所滋养的肉身和性的华丽慢慢地取代了红色意识形态的喧嚣与沉重,《单性》(Monosex)、《天堂们》(Paradises)、《二手水》(The Second Hand Water)、《蔬果乐》(Vege-pleasure)、《国际汤》(An International Soup)等作品随之涌现出来。

《玻璃水瓶》 吴山专 amp; 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 1997年
其次是面向“物”的姿态,这一点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山专与英格的创作中最核心的部分应属“物权”[Thing’s Right(s)]。而这个系列的一个重要源头应是英格的“粉化”(Pulverization)行动。1992年,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创办了“雷神女儿粉化服务”(Thorsdottir’s Pulverization Service)[2],坚持不懈地把各种事物磨成粉末,装入玻璃瓶中,瓶上的标签注明了粉化的方式和盛载的原物。“粉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清除笼罩在艺术作品之上的视觉美学,英格认为“瓶上的标签能更有效地彰显粉化前对象的特性、粉化所需工时和物品的物理价值”。通过“粉化”,英格不仅用一以贯之的极端态度消灭了“物”的现成身份,而且以一种寂灭的方式达成了与世间万象的和解。
“粉化”的核心是“以同一种态度对待所有事物”,而这正是“物权”的前提。这一“齐万物”的姿态使“物之为物”的实存与虚幻被同时凸显了出来。
英格的“粉化”只是“物权”的一个源头,而它的另一个源头,是“欣赏”。
1991年,吴山专与英格对杜尚的雪铲进行了一次“欣赏”,这不是在博物馆中的观赏或膜拜,而是在北欧的冰天雪地中用雪铲来铲雪。当然,此雪铲只是一把普通的器具,然而博物馆中的那把除了杜尚的加持之外,作为“物”难道有任何特异之处吗?吴与英格用来铲雪的工具是“符号的它”,也是“实际的它”。这个复杂的悖论是对杜尚遥远的回应。一年之后,这种回应变得更加令人震惊。1992年10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吴山专在杜尚的《泉》中小便,把小便池本来的功能重新归还给这个“物”。这一行为的标题仍然是“一个欣赏”。
如果T.S.艾略特是对的,每件伟大作品的问世都会加入一个历史性的意义序列,并且重新建构这个传统中所有作品的意义,那么,杜尚的《泉》却把艺术的传统、把这个历史序列切成两段——杜尚之前的时代和之后的时代,从此,一种新的意义机制确立了起来,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在艺术史家们带着伤痛和几丝受虐的兴奋的叙述中,问题的核心似乎集中在杜尚对现成品的使用上,而现成品之所以会出现在艺术史中,却是因为杜尚的“点金术”。
杜尚的小便池只是成千上万的小便池中的一个,它是“适逢其会的物”(thing in the case),而非物本身,当然也就不是康德所谓的“物自体”(thing in itself)。在吴山专看来,“点金术”是一种“罪”,通过点金术,这个小便池被命名、被签名,成为一次罪行的“物证”。对艺术史而言,这一罪证意义重大,因为它揭发了追求“自治”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对世界的霸权,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机制所定制的皇帝的新衣。1992年3月,在第一则题为《物权》的笔记中,吴山专写道:“在本世纪初,艺术家们选择了对物的沙文主义。在本世纪末,我选择把物放回原处。”

《学者和他的妻子-学者和她的丈夫》 吴山专 amp; 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 1994年
吴山专对博物馆中的那个小便池的使用,只是把它放回了原处。三年后,在《造句练习》(Making Sentence)中,吴山专以“罪”的名义进行了自我忏悔:“杜尚用‘点金术’把‘小便池’变为无用之物。为自己,他杀死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对那个时代,他把一种罪具体化了。我们时代的艺术世界正在再现这种罪。对‘点金术’来说,吴也犯了一种罪。”
杜尚在小便池上签了Mutt先生的名字,这一签名撕裂了作品与生产的界限。因为Mutt先生的生产/作品是无限量的(此处与本雅明所谓的技术复制无关),而小便池们的所有权也是开放的。吴山专1992年所设想的一系列“清除原作的方式”就是从这里出发。1的无限等于100的无限,无限是使物变得平等且自由的一种方式——Objects at large,物因而超越尺度并逍遥法外。吴山专想到了“乘零法”。“乘零法”不是要回到原点式的“归零”(Ground Zero),而是对原点的清除,对原作观念的消除。这是针对艺术品的“原作病”的一种治疗术,因为事物成为“现成品”,继而成为艺术品,不只是因为它去离原位而适逢其会,而且因为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本源”意义,它似乎因此变得独一无二了,它成了“原作”。“原作”的观念封闭了物之为物的可能性,使它成为艺术系统中的一个意指符号。杜尚自己并没有把雪铲和小便池定义为作品,是艺术系统、艺术史通过自我协商把它们接纳并论证为作品,把它们从无数把雪铲、无数个小便池中孤立出来,指认为“原作”。实际上,“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只是艺术的一个例如物”[3],正如所有的“作品”都是且只能是“原作”。杜尚在这个艺术史的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中间人。而吴山专的工作是把这件已成定论的“作品”——这件“艺术史的现成品”重新定义为器具,并把功能重新归还给这个“物”。但是,这仍然只是做了一半,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物的有用性(dieblichkeit)、器具之器具性(小便池的功能)也是对物的一种统治,其基础是以人为中心的对于物的占有,这依然是对物之为物(dingsein)的一种扰乱。对于这一点的意识,使吴山专注定要与杜尚分道扬镳。
就《物权》而言,与杜尚有关的只是故事的前半段,虽然这前半段已经走得足够远:“艺术是迄今为止吴所知道的一切事物的总和。”[4]
“当吴称那物为现实中的艺术例如物时,他是这物的艺术家,而不是所有物的艺术家。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成为艺术家。”[5]
通过对原作观念的清除,吴山专与艺术史终于做了了断,他的创作从此只能被称作“吴的物”(Wu’s Thing)。在故事的后半段,吴山专的工作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那是艺术史无法笼罩之处,那是“物的吴”的故事。
然而,吴山专并没有走向对于物之“自立”(selbdtstand)、“自持”(insichruhen)的追问,也没有沿着海德格尔的道路去沉思“物之物化”(dingen des dinges)。在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中,去除形而上学神学的代价是向着某种深沉晦涩的存在神学的回归。吴山专着力之处,是对于人与物之间的权力结构的破除,在此,“物自身”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必要的假设。换句话说,在人与物的因缘关系中,他关心的并不是自然(吴山专说:“自然是一辆出租车”),而是自由。
正是在自由的意义上,吴山专提出了“物有九用”。凡物必有其用,这句颇具神学设计感[6]的话提醒我们,一切事物都被它的有用性所定义,物的有用性似乎成为了它的本质,使用价值替代了存在价值,即使无实用性的艺术品,也依然为艺术收藏和流通系统所“用”。而物的有用性又被禁锢在其日常功能之中,日常的物是不自由的,因为“日常”也终究是一座堡垒、一种意识形态[7]。要想获得物之自由,必须把它从日常的“用”中解放出来,把可能性归还给它,于是“物有九用”。“九”是虚指,“物有九用”,即是物尽其用。

左·《物权版画2013 第一条》 吴山专 amp; 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 纸上丝网、平板印刷 73cm×55.5cm 2013年右·《圆振荡》 吴山专 amp; 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 布面油画 56cm×76 cm 2016年
当被问到他们的工作领域时,吴山专画了一张图。这张图显示了两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透视与投射。自文艺复兴以来所确立的透视法的世界观确立了我们的日常姿态,即主体-客体之间的目的论式的认知模型,该模型往往从日常上升到政治,最后到神学结束,其终点-灭点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点,那是上帝的居所,最终的原因、理由和目的,其视野是一个封闭的锥形;而吴山专与英格的工作却是投射式的,从这个“原点”出发,穿越政治,最后抵达日常[8],这是一个朝向无限开放的反锥形,那是吴与英格用“完美的括号”所标识的领域,是最初和最终的at large[9]。
当被问及他的小说的命运时,他说:“《今天下午停水》还没有被扔掉,是因为我们的未来还没有结束,今天还可以使明天成为现实,今天还可以把昨天做得更好。”
注释:
[1]“彩虹美学”由孙田博士提出,在此表示感谢。
[2]根据一项古老的传统,英格采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她的组织。她说:借此可以向我父亲和他钟情的北欧神话致意,我觉得雷神托尔(Thor)手执铁锤的形象充分体现了这种艺术实践,“雷神女儿粉化服务”因此得名。
[3]引自吴山专《字母格言,example》,1995年。
[4]引自吴山专《字母格言,art》,1995年。
[5]引自吴山专《字母格言,artist》,1995年。
[6]在思想史上,“设计”有非常崇高的神学-形而上学血统。在16世纪中后期,瓦萨里将disegno界定为对心灵中形成的concetto(内在观念)的一种视觉表达。而祖卡里(Federico Zuccari)更是将disegno interno(内在设计)阐释为人与上帝之相似性的一种词源学象征——disegno=segno di dio in noi(即上帝与人同在)。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在物与器具、创造与设计、用与自由之间捕捉到物权所牵连着的一条意味深长的思想史线索。
[7]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哲学话语之中,“日常生活”被界定得过于明确,在诸如“日常生活的政治”的论述中,“日常”已经成为一座堡垒、一种意识形态。对吴山专来说,日常生活只是一切艺术和“主义”逍遥法外(at large)之所。
[8]然而此日常并非作为经验之出发点的最初的日常,这是日常的“开放域”。这与其说是一种反向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穿越形而上学原点的旅行。[9]这是一种本质的政治学差异——其一是以透视为模型的“目的政治”,而后者则预示了一种以投射为模型的“关切政治”的差异。此处涉及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论述的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向“物的政治”(Dingpolitik)的转换。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高士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结构——吴山专、托斯朵蒂尔的物权及其他》,部分图片由长征空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