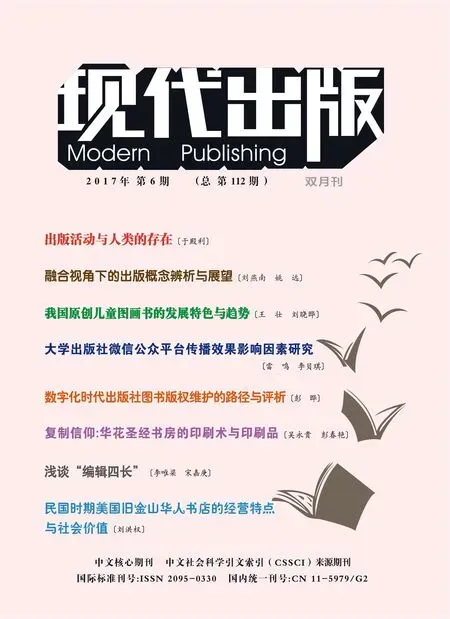金陵书局刻印书籍考论
2017-12-04朱宝元
◎ 朱宝元
金陵书局刻印书籍考论
◎ 朱宝元
金陵书局是晚清设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官书局,亦是晚清官刻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的重要代表。鉴于金陵书局以往研究考史实者多,研刻本者少,而刻本保留了丰富的原始信息,对金陵书局的深入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为此,本文以代表性的公藏、发行和推荐书目为基础,结合查考刻本和已有研究,论述金陵书局的兴盛衰落、编校活动以及与晚清社会在刻印和传播方面的互动。
金陵书局;编校活动;刻书活动;传播活动

金陵书局是晚清设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官书局,亦是晚清官刻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的重要代表。金陵书局之设,为“当事诸公,因时立制,以经济一时之变者”,虽是官办但又不在朝廷官制之列,故原始档案文献大多散佚,除当事者的文集、书信、日记等一手文献外,存世最多的只有刻印之书。百余年来,有关金陵书局的论述,考史实者多,研刻本者少。为此,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以《中国古籍总目》《中国丛书综录》等公藏书目、《官书局书目汇编》等发行书目以及《书目答问补订》等推荐书目的著录为基础,梳理出题金陵书局和江南书局牌记的书112种、3046卷(重刻重印者不计)。本文将以此为基础,论述金陵书局的兴盛衰落、编校活动以及与晚清社会在刻印和传播方面的互动。
一、金陵书局的兴盛衰落
金陵书局从同治四年七月成立到民国三年归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存世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从书籍刻印看,金陵书局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同治四年至同治十三年,集中刻印经史,突出经世意识,共刻印书籍61种。同治四年七月,李鸿章设立金陵书局,刊刻的都是五经、四书等童蒙书。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抵达金陵后,开始谋划长远,与书局人员共同商定刻书计划,继续刊刻《十三经》和前四史,还刊刻了《文选》《渔洋山人古诗选》《五七言今体诗钞》《五种遗规》。同治八年任直隶总督后,又命张文虎校刻《读书杂志》。曾国藩主张“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兼而取之,但强调根柢义理之学而求经世,读书不在多而在“慎择”,因此所选的书都是各门学问的经典。虽然同治八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与浙江书局、湖北崇文书局、江苏书局公议合刻《二十四史》(后淮南书局加入),金陵书局承担了“十四史”的校刻,但这只是刻书范围的延伸。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曾氏去世后,均以校刻“十四史”为主,并于同治十二年刊刻了《曾文正公奏疏文钞合刊》,以纪念曾国藩。
第二阶段是光绪元年至光绪十六年,以刊刻史地和钦定义疏为主,新刻印书籍26种,重刻同治间金陵书局本经部书籍10种。这一时期,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先后任两江总督。光绪初年的刻书,主要是由提调洪汝奎组织,基本延续同治间刻印经史的计划,新刻印的多是史部书籍,如光绪四年刻仿汲古阁本《史记》,光绪六年至八年刻成《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元和郡县补志》《元丰九域志》《元和姓纂》等史地和传记类书籍。曾国荃于光绪十年至十六年任两江总督时,共刻印了《御纂七经》《古文苑》《近思录集注》《王船山年谱》《湘军记》等17种,是书局刻书的一个小高潮。但相比同治年间,此期已明显后继乏力。
第三阶段是光绪十七年至宣统元年,刻印书籍涉及史、子、集三部,新刻印20种,重刻同治金陵书局本经部书籍11种。光绪十七年曾国荃去世,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后又与张之洞交替任两江总督。在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四年刻印了《徐骑省集》《劝学篇》等书,其中《李氏五种》为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出资刻印,光绪十八年又题金陵书局牌记印行;重刻了同治间金陵书局的易、诗、礼、小学等6种。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后,刘坤一命裁撤书局人员、停止拨款,金陵书局只能靠卖书周转,只刻印了《酿斋训蒙杂编》《异闻益智丛录》《续古文类纂》。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主译西书,金陵书局和淮南书局都归入。直至清朝覆亡,金陵书局只刻印了《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权言》两种书。
第四阶段是宣统元年以后至民国十四年。这一时期书局没有再刻书,只售卖同光年间刻印的书籍。
金陵书局有多个名称,如江宁书局、江南书局、江南官书局等。查考刻本,用于牌记者有“金陵书局”“江南书局”和“金陵官书局”三个。其中,“金陵官书局”只见于《圣门名字纂诂》1种。江南书局牌记最早出现在同治十一年刻印的《毛诗诂训传》。从牌记使用看,题金陵书局刻印者95种,其中重刻者6种;题江南书局刻印者33种,其中新刻印者23种,重刻金陵书局本者10种。江宁书局、江南官书局只是俗称。
二、金陵书局的编校活动
在晚清地方官书局中,金陵书局名士云集,刻印书籍以校勘精审而著称。这主要是就同治年间而言。
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编校人员,大多是曾国藩幕府中的宿学之士。这些人或如汪士铎精通史地之学,或如张文虎精于天文算学,或如刘毓崧、刘寿曾精治《左传》,或如刘恭冕精治《论语》,或如戴望精治今文经学和《管子》,或如唐仁寿精通音韵等。尤其是,他们大多不愿或不能仕进,专意学问。编校人员的学有专长、校刻经验丰富和心无旁骛,是金陵书局编校质量保持高水平的保障,晚清其他地方官书局可以说无出其右。而曾国藩去世后,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这些人或他出,或去世。这在刻印数量上得到体现。金陵书局在同治年间共刻印书籍61种,光绪年间新刻印50种,宣统年间只刻印1种。
金陵书局刻印书籍中,翻刻本共有71种,占刻印总数的63%;其中,同治年间翻刻本共有45种,占翻刻数的63%。因为多是翻刻,所以校勘尤为重要。在人员保障的同时,金陵书局还有一整套编校流程。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命周学濬、张文虎草拟章程,四月亲自改定。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曾国藩于同治七年正月廿一日“三更后核定刻字法式四条、书局章程八条,约改三百余字”。这就是《金陵书局章程》。虽然这个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通过《张文虎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到金陵书局编校刻印的基本流程包括:选择底本和参校本、初校、发抄、复校、刻排、校样、挖改修版、校样、刷印装订。
在校勘过程中,编校人员往往广搜博取,如张文虎在校《尔雅》时,就先后参考《艺文类聚》《玉篇》。一些大部头的书,还设有总校和分校,并订立校勘条例。如同治六年十一月,曾国藩计划用聚珍版印顾炎武《肇域志》,底本是朱兰提供的顾炎武手稿本,并由汪士铎拟订了“校编条例”,张文虎、成蓉镜、刘恭冕、刘寿曾参与校勘。其中,张文虎校勘了贵州卷并发抄。同治七年三月,薛福成也看到过刘恭冕所校的部分。《汪梅村先生文集》中也收有《<肇域志>跋附校刻<肇域志>商例》。可见该书总校为汪士铎,其他几人为分校,并已部分发抄,但不知为何最终没有印成。一般的书大多是一位编校人员始终其事。重要的书,会由不同的人员一起初校,或一人初校、另一人校样。曾国藩平生最重礼学,就亲自校勘了《仪礼》的样本。此外,书局编校人员相互之间还就个人专长,请同仁代为校勘某书的部分篇章。如唐仁寿在校勘汲古阁本《汉书》《晋书》时,就请精于天文的张文虎校勘《汉书》的《律历志》《地理志》等,以及《晋书》的《律历志》。张文虎所校《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和撰写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校刊札记》更成为书局的经典之作。
三、金陵书局的刻印活动
金陵书局在两江总督的领导下,与官府、私刻和学人有很多交流,体现了书局刻书与晚清社会的多重互动。
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收购或受赠了一些私刻版片,可考的有9种书版。同治四年七月,张溥斋听说李鸿章要开设书局刊刻五经,就跟莫友芝说,欲出售家刻《周礼》郑玄注、《尔雅》郭璞注版片,以为进京盘缠。同治六年十二月,曾国藩购买了两书的版片。同治七年五月,曾国藩复信朱兰说:“《周礼》《尔雅》补缺板均已补刻。”《五种遗规》是承自道光三十年歙县洪氏版片,同治七年重修。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春秋公羊传解诂》为道光四年扬州汪氏问礼堂刻,同治二年魏源的侄子魏彦在上海购得版片,并增补《晋本校勘记》一卷刊行。之后,金陵书局题“同治五年七月金陵书局开雕”牌记印行,纳入《十三经读本》。此外,《五七言今体诗钞》也是继承嘉庆十三年版片,于同治五年八月重修。
在曾氏出资刊刻《船山遗书》的影响下,也有多人捐资在书局刻书,并由书局藏版印行。同治五年刻《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是朱兰请刘恭冕校勘,李鸿章捐俸在书局刊刻:“适延宝应刘叔俛茂才在幕,茂才以经学世其家,余属为校刊,经始于今年春,十月蒇事,爬梳抉摘,条分件系,始灿然可读。时李少荃宫保方开书局于金陵,因将是书暨其夫妇诗集,节俸锓诸板,俾少石终其事焉。”《浪语集》牌记题“同治辛未二月金陵书局开雕”。据孙衣言所撰序言,此书也是由李鸿章捐俸在书局刊刻,版归孙衣言。还有《近思录集注》,光绪元年由何璟出资刊刻,光绪十五年又由金陵书局印行。《圣门名字纂诂》则是由时在书局任编校的朱孔彰出资,在书局刊刻藏版。
光绪年间,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时,户部出资,在金陵书局公刊了《御纂七经》,以及《周易传义音训》《书集传音释》《诗集传音释》等11种书籍。这既有曾国荃的个人影响,也体现了朝廷对金陵书局的重视。同时,《御纂七经》不在《官书局书目汇编》所收的江南书局发行书目中,则版片可能归户部了。而该书目中还列有《中兴将帅别传》《吴学士文集》《临阵心法》等书,但牌记都题“江宁藩署”。这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这些书的版片在金陵书局,由书局印刷发行;其次,结合其他未题牌记的情况,可以推论,金陵书局的牌记使用相对严格,本局出资、本局刻印、本局收版三具其二者,方才题书局牌记。
此外,还有两种特殊的情况:一是书局出资为私人刊刻书籍。如同治十一年刊刻的丁晏撰《曹集铨评》。书局提调洪汝奎坚持“私家著述,弗应及”,意思就是不能公款为私人刻书,但曾国藩敬重丁晏,还是坚持由书局刊刻。二是个人集资请金陵书局刻工刊刻书籍。同治五年,杨仁山时在江宁工程局办差,集资刊刻了魏源撰的《净土四经》,书末有“金陵书局甘国有镌板”字样,被视为金陵刻经处首刊之书。光绪间又请刻工甘国有刊刻了《大乘起信论裂纲》《大乘起信论疏解汇集八种》。《总目》将《净土四经》《大乘起信论裂纲》都著录为金陵书局刻本,是不对的。
四、金陵书局的传播活动
金陵书局刻印的书籍通行半个多世纪,与其他地方官书局共同成为传统典籍、学术文化播扬的场域。
赠书是一件雅事。曾国藩在同治六年先后将《五经》《四书》《春秋公羊传解诂》等各二十部,分送幕中诸友。尤其是任直隶总督期间,曾国藩多次向书局索要前四史,赠给了很多枢庭要员和友人。同治八年,李善兰收到曾国藩所赠的《汉书》《后汉书》后,复信说:“承惠大本两《汉书》,照眼光明,汲古阁初印本殆不能及,感甚喜甚!虽千镒之赐,不是过矣。”莫友芝在同治八年四月致信曾纪泽,言及曾国藩曾答应分赠诸友《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泾棉纸初印本,请其印好后给他和李鸿裔各一部。这些赠送的书一般都为初印或前几批的刷印本,除了莫友芝提到的用纸不同外,曾国藩也针对赠送对象,就《史记》《三国志》两书提出不同的装订和版式要求:“《文选》一部其天地之长,两边钉处之阔,大约如此,仆因告缦云、子密,云‘两汉’当仿此刷之。然偶刷数部则可,太多则不相宜。不知目下已刷若干部,寄枢府之五部系用二十一串者乎?用十四串者乎?其余赠送人书均以十一串者为适用。”(同治八年九月初七日《复洪汝奎》)这些赠予对象,集中在官员和学人,不仅联络了感情,也宣传了书局,是同治年间金陵书局迅速扩大影响的口碑基础。
同治六年五月,朝廷奏准江苏学政鲍源深请各省刊书籍疏,颁发学校,培育人才。这是晚清地方官书局的主要功能。同治十年,时任江宁盐法道的孙衣言请曾国藩在惜阴书院设“劝学官书局”,送存了金陵书局、湖北崇文书局、浙江书局、苏州书局刻印书籍,备寒士阅读。其他书院收藏官书局刻印者,有的上奏请求赠送,有的则直接购买。如光绪五年(1879)顺天金台书院成立时,顺天府尹上奏朝廷,请拨金陵书局等官书局书籍;黄彭年在光绪年间任莲池书院山长时,建万卷楼藏书,请李鸿章拨专款购买各地官书局的藏书,《万卷楼藏书总目》中有很多金陵书局刻印书籍。
晚清地方官书局的经费来源都是盐务等闲款,所以经费随地方财政的富余程度,及当政者的支持力度,时多时少,没有定数。同治六年,曾国藩就意识到书局发展会遇到经费问题。他要求周学濬在精刻精印的同时,“至卖价不妨略昂,取其赢余,以为续刻它书之资”。薛福成在同治八年的日记中,记下了金陵书局不同印本的书价:“前、后《汉书》三十二本,重皮宣纸印者,本洋十八元;大料宣纸者,十三元;宣料半纸者十元;色纸者七元。《史记》廿本,价十一元、六元至四元二角止。《三国志》自四元五角至二元八角、二元止。《文选》自五元二角、三元二角至二元四角止。”这一定价长期变化不大。光绪七年《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中,记载的《汉书》《后汉书》四种用纸印本售价,分别只高出五钱、四钱、二钱、九钱。1931年《官书局书目汇编》收录的售书目中,两书的杭连纸印本售洋十七元,赛连纸印本售洋十八元八角六分。不同的用纸和定价反映出金陵书局对个性化需求的考虑。但金陵书局与众多地方官书局一样,都缺乏利润观念,自始至终也没有实现自负盈亏。
综上所述,金陵书局存世半个世纪,刻印书籍主要以传统典籍为主,尤其是同治年间,在曾国藩的领导下,金陵书局汇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名士,他们之间相互商讨,精审校勘,为晚清书院教育和士子学人提供了一批佳本,奠定了金陵书局的声誉。金陵书局与官方和民间、官员和士人有着广泛的刻书与传播互动,与其他地方官书局一起,共同为传统典籍和学术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时代贡献。
注释:
① [清]蒋启勋,[清]赵佑宸,修,[清]汪士铎,等纂.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六年刻本,1991:49.
②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四[M]. 长沙:岳麓书社,2011:13.
③ 陈大康,整理. 张文虎日记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13-130.
④ [清]薛福成日记(上册)[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7.
⑤ [清]汪士铎. 汪梅村先生文集[M]. 清代诗文集汇编六一二册影印光绪七年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1-533.
⑥ [清]顾炎武,撰,谭其骧,等点校. 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8.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6:349.
⑧ 陈大康,整理. 张文虎日记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72.
⑨ 张剑,张燕婴,整理. 莫友芝全集·郘亭日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7:263.
⑩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M]. 长沙:岳麓书社,2011:415.
⑪ [清]李贻德. 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M]. 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刻本.
⑫ [清]张文虎.舒艺室杂著甲编[M].清代诗文集汇编六三〇册影印光绪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35.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M]. 长沙:岳麓书社,1985:367.
⑭ 张剑,张燕婴,整理.郘亭书札[M].北京:中华书局,2017:708.
⑮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M].长沙:岳麓书社,2011:4.
⑯ [清]莫祥芝,[清]甘绍盤,修;[清]汪士铎,等纂. 同治上江两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同治十三年刊本,1991:206.
⑰ 赵连稳,韩修允.顺天府尹在金台书院文化传播中的作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40.
⑱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M]. 长沙:岳麓书社,2011:309.
⑲ 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上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53.
(朱宝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