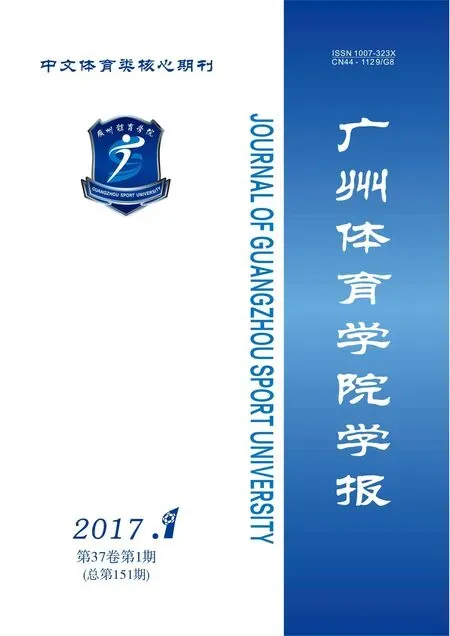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的法学透视
2017-11-27黄华
黄 华
(广东医学院体育教学部,广东 湛江 524023)
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的法学透视
黄 华
(广东医学院体育教学部,广东 湛江 524023)
我国足球事业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以广州恒大为代表的职业队伍在国际赛场上不断取得喜人的成绩,由此也带动了职业足球转会制度的改革。基于中国足协2015年12月30日正式下发新版《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这一重大事件节点,从法学角度解析了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的发展与变化。新规对自由转会制度以及随之配套的转会费、转会名额限制、青训补偿、联合机制补偿等一系列相关措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足球转会的自由度明显得到提升,显现出了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从“包办”到“有序自由”的发展脉络,而足协干预与市场自治之间的边界也在逐步厘清,与足球转会密切相关的培训利益分享机制亦是当前足球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职业足球;转会制度;法学透视
足球运动在我国的体育事业中处于较为特殊的地位,一直具有较高的公众关注度,而逐步完善的足球市场,又使得足球运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我国职业足球正是在这种潮流中经历着从“举国体制”到“产业化”的发展进程,若具体到转会制度层面,则表现为从“包办”到“自由”的转变。所谓“包办”指的是过去我国足球球员转会方面呈现出较强的行政干预特色,转会相关方的自由意志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而“自由”则是足球机构与人员的市场化配置特征更加明显,转会交易中更注重球员和俱乐部的意思自治。“包办”到“自由”的转变,展示出我国职业足球正在逐渐融入国际足球的规则体系,尤其是2015年12月30日中国足协下发的《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转会规定》)更是以里程碑式的姿态彰显了我国足球改革之近况,职业球员转会的自由度明显增强,转会交易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更加平衡。在此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解析足球转会新规,把握未来足球转会制度的发展脉络,其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1 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的发展历程回顾
1.1 彰显意思自治的“无序自由”时期
我国职业足球正式开始于1994年,著名球员马明宇成为中国足球转会第一人。当年在成都召开的金牛会议上,中国足协与业界人士商讨编制完成了职业足球联赛初创阶段的转会细则,“在这个中国足球转会条例的原始版本中规定,球员转会市场全面放开,只要收购一方愿意支付转会费,而球员又愿意,原俱乐部不得阻挠”[1]。
此时的足球转会制度奉行了绝对自由市场的立场,意思自治成为了决定转会诸多事宜的唯一关键因素,拟转入球员的新俱乐部和球员只要达成合意,即可产生排斥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绝对自由市场的弊端在其他经济业态中早就暴露出了不合理性,而我国职业足球初创时期之所以奉行这样一种明显存在风险的制度模式,与当时意在彻底打破足球运动举国体制的决心不无关系。之后的事实也印证了绝对自由市场的缺陷,虽然职业联赛初尝阶段的球员转会较为自由,转会成功率高,但是实际上的转会却并未有想象中的那样透明,由于经济利益的诱导,单纯依靠意思自治的转会只能使球员和新俱乐部的利益最大化,原俱乐部对球员的培养付出无法得到实质性保障,并且转会过程还产生了一系列不道德行为,诸如球员索要高额签字费,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签订阴阳合同,新俱乐部突袭买人损害原俱乐部联赛利益等等。
整个职业足球市场充斥着一派自由而又无序的状态,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从法律角度看,市场交易过程中过度强调意思自治的神圣性,并不能真正提高交易的公正和效率,当自由交易损害了市场整体秩序时,绝对自由的市场必然走向末路,因此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和干预成为了下一阶段足球转会规则的重点。
1.2 强调干预的“包办”时期
“包办”常常被用于形容家庭长辈对子女婚姻的严重干预,但本文使用“包办”描述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经历初尝阶段之后的全面严控和规制,可谓用词恰当。在意思自治导致的转会乱象冲击着职业联赛秩序的背景下,中国足协对球员转会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于1998年正式结束了过去绝对自由的转会市场,并代之以“摘挂牌制度”。此项制度的核心在于,转会必须由拟转出球员的原俱乐部启动,将拟转出球员挂牌至榜单并附明转会条件,拟转入球员的俱乐部则通过摘牌的方式与原俱乐部达成合意,交易完成后,球员必须转入新俱乐部,以此杜绝球员索要签字费、私下交易、突袭买人等现象。
为了进一步利用摘挂牌制度构建职业足球联赛的公平竞争态势,中国足协又分别尝试了“顺摘牌”和“逆摘牌”机制。所谓“顺摘牌”是指按照联赛上赛季的排名,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摘牌,联赛排名较高的俱乐部享有优先摘牌权,最终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之后又实行了“逆摘牌”,效仿NBA选秀制度,按上赛季联赛排名由低到高决定摘牌顺序,但又降低了高水平俱乐部加大投入的积极性;最终改为“双轨制”,将摘挂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由摘牌,俱乐部可在转会榜单上自由选择一名球员;在第一阶段未能成功摘牌的球员进入第二阶段——逆摘牌。
摘挂牌制度以及双轨制的产生,体现出了法学视域下的效率与安全这一永恒矛盾。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市场行为,其价值在于优胜劣汰,实现高效率;对意思自治的干预,则是为了避免过高效率而损害市场安全。1998年以来的足球转会摘挂牌制度即秉持了维护市场安全与秩序的逻辑,足协为转会交易预设了十分严格的流程,从而规避意思自治的个人本位所产生的外部性。但摘挂牌制度以及双轨制本身却存在重大缺陷,转会交易的启动权全部交给拟转出球员的俱乐部,新俱乐部只能被动摘牌,球员更是完全丧失了自由选择俱乐部的就业权利。因此,摘挂牌制度不仅规制了交易过程中的意思自治,还损害了交易各方主体的平等性,整个转会市场沦为卖方市场,挂牌的球员缺乏吸引力,新俱乐部选择空间有限,被挂牌球员更是可能转入不希望加入的俱乐部,这一切均导致转会成功率大大降低,2004年的挂牌榜单中只有11%的球员成功转会;同时球员的主体地位也遭到剥夺,沦为了转会交易的客体,这又产生了一些球员无故拒绝赴新俱乐部报到的现象,如“申思事件”[2]等。
1.3 初步放宽的“自由摘牌”时期
摘挂牌制度或双轨制被证明是失败的尝试,这种不符合足球市场规律的转会机制完全是对NBA选秀制度的拙劣模仿,从根本上破坏了意思自治、平等协商等交易成功的必要基础,也不符合成熟球员特别是明星球员转会的实践需要,受到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诟病,最终于2005年寿终正寝。之后中国足协以“自由摘牌”的形式意图恢复之前的自由转会制度,同时足协对自由摘牌制又进行了强烈的限制和干预:限定每家俱乐部每年只能自由转入5名球员;赋予俱乐部针对25岁以上球员的强制续约权;对转会费设定较低上限等。此种(以自由摘牌为形式的)自由转会制度可谓徒有其表,转会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拟转出球员的俱乐部手中,实际上与原先的双轨制无本质区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还发生了中国足球联赛扩军的事件,为此中超联赛暂停降级,可见当时足协对联赛的干预意愿十分强烈,完全不局限于转会层面,而是实施了一种系统性、全盘性的干预。由于联赛停止降级,联赛的竞争性大打折扣,各俱乐部在转会方面的需求大幅降低,以致于不少球员一旦被列入转会名单即意味着失业。总的来说,自由摘牌制度过多地维护了拟转出球员的俱乐部利益,让“球员利益受到俱乐部限制,这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中劳资双方公平自愿合作的精神相悖”[3]。
若以转会球员的视角来看,自摘挂牌制度开始施行,中国足球的转会制度本质上就完全脱离了自由转会的本质,球员在转会交易中的自由意志根本得不到尊重,彻底沦为交易客体。这种局面的形成,说明当时足协对转会市场的干预力度远远超出了合理范畴。因此,寻找足协干预与足球转会市场之间的平衡点,即聚焦在了转会交易中的球员主体地位问题上,这也成为了近几年以来学界及足球业界经常探讨的问题。
1.4 球员主体地位回归的“有序自由”时期
2009年起,中国足协下发了《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09版《转会规定》”),并于2015年12月再次修改了该规定。《转会规定》的核心在于彻底废除摘挂牌转会制度:(1)恢复自由转会的基本模式,只要进入转会名单的球员,其他俱乐部均可通过自由交易的方式进行转会谈判;(2)针对过去挂牌权完全由拟转出球员俱乐部掌握的问题,新《转会规定》将转会决定权部分赋予给了符合特殊情形的球员(如自由球员、正当理由终止合同),防止俱乐部以“冷藏”、“低价续约”等方式胁迫球员续约或强迫球员转入其不希望加入的俱乐部;(3)平衡转会各方主体的利益冲突,《转会规定》借鉴了FIFA规则及欧洲足球联赛的有益经验,引入青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从经济利益的层面杜绝了俱乐部因付出培训成本而不甘心本队球员低价转会、阻挠球员转会的情况;(4)在足协监管机制方面,新《转会规定》取消了足协的一部分权力,如不再收取转会管理费、取消转会费上限管制等,放松了足协对转会市场的干预,试图构建一种适度干预下的有序市场。
总之,从历史纵向上来看,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在市场效率和市场安全之间曾经有过迷失,既有试图以意思自治打破举国体制的壮志雄心,又有矫枉过正、过分干预而损害交易主体平等性的错误决策,特别是在球员主体地位问题上,一度还出现过球员沦为转会交易客体的境况。但就整体发展历史看,我国转会制度的运行轨迹仍然是以恢复球员在转会交易中的主体地位为线索,球员的自由意志,及其在转会交易中的意思表示正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保护;而在转会市场方面,我国亦正在逐步规范足协干预力度,力求在法律关系的结构上维持转会相关各方的平等性,恢复意思自治,增进足球市场的自由度与活力,但同时也保留了转会名额方面限制,避免马太效应损害职业联赛的竞争性。
虽然新规定的实际效果还有待检验,但我国的足球转会制度毋庸置疑已站上新的起点,自由转会市场正在逐步回归,而且当下的自由转会与初创之际的绝对自由转会完全不同,是一种基于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在有序规范的框架内的,力求把握足球发展规律的自由转会机制。
2 我国职业球员转会制度的新变化
2.1 球员工作合同法律性质的初步界定
2.1.1 劳动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之争
职业足球是一个市场化的产业体系,足球转会表现为球员在不同俱乐部之间的流动,其本质是职业足球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过去我国将足球人力资源视为转会交易的客体,是对这种交易的扭曲,压制了球员在转会交易中的自由意志。但球员在转会交易中主体地位究竟应当如何界定,牵涉到了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签订的工作合同的法律性质,若将其认定为劳动合同,则转会交易实际上属于对劳动合同关系的变更并建立新的劳动关系,球员在转会交易(即转会合同的谈判、签订等环节)中自然应受劳动法保护,享有自主择业的自由。若将球员工作合同认定为一般的民事合同,则对工作合同的变更应按《合同法》处理,那么俱乐部根据中国足协下发的《转会规定》在工作合同中设定相应的转会限制条款即完全具备法律依据,此种情形下,由于摘挂牌时代足协制定的转会规则中赋予了原俱乐部强大的转会控制权限,球员在转会交易中的实际地位即近似于无自由意志的交易客体。
虽然学界观点普遍认为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工作合同为“劳动合同”[4],且09版的足协《转会规定》中已在字面上使用了“劳动合同”的称谓[5](新《转会规定》现已修改为“工作合同”),但原《转会规定》却并未向《劳动法》那样保护球员自由择业权,即便是结束了摘挂牌制度的09版《转会规定》,亦有不少根本违背《劳动法》之处:如针对工作合同期满的球员,未使用国际通行的“自由球员”概念(工作合同期满后即可自由转会),而是创制了所谓的“自由人”(工作合同期满后30个月未能续约的方能自由转会);又如球员被俱乐部拖欠薪金3个月以上方可单方终止工作合同等。可见,“劳动合同说”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实际上,若以劳动法的标准衡量我国转会制度或国际通行的转会规则,均可得出“违反劳动法”的结论,因足球运动毕竟不同于一般劳动,如“俱乐部引援时既受制于转会市场,还要受制于运动员的意愿”[6], 足球行业内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普通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完全不同,二者本质上属于不同的社会关系,采用同一种法律制度调解两种不同社会关系,当然会在实践中产生矛盾与冲突:如国际、国内球员工作合同中常见的“租借条款(俱乐部有权将球员租借至其他球队工作)”、“解除合同违约金(远超出劳动法标准)”、“限制转会下家(俱乐部可禁止球员未来转会至敌对球队)”、“特殊争议解决机制(体育仲裁)”等条款,在实践中均具备法律效力,但这些条款实质上已脱离劳动法的范畴,而进入了劳动法所不能涵盖的领域;但球员工作合同中的工作时长、工作薪酬等制度又必须劳动合同完全一致,方可在法理上具备正当性,否则若任由俱乐部与球员自行约定工时、薪酬等事宜又必定造成谈判地位不平等等问题,有损实质公平。
因此,劳动法与一般民事合同之争,体现出了现有法学理论在体育法领域内的局限性,民事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均不能完全解决足球工作合同或其他体育项目工作合同中的特殊问题。由此也就导致了裁判机构在处理转会合同法律纠纷时的两难境地,无论适用劳动法还是一般合同法律均不能对球员工作合同中的条款有效性作出合理认定,进而使得针对转会行为的有效性裁判难以获得法理上的逻辑自洽。
2.1.2 转会新规构建的特殊雇佣合同制度
为此,15版的《转会规定》之法理价值即在于对球员工作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行了合理解释,摆脱了“劳动合同还是一般民事合同”的概念之争:(1)15版《转会规定》将09版中的“劳动合同”全部修改为“工作合同”,在形式上脱离了劳动法的框架;(2)同时在实质层面赋予了球员一系列贴近于劳动法的权利,取消了欠薪3个月方能解除合同的限制,增加了球员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如上场时间未达到10%),放宽了新工作合同的洽谈期限(从3个月增加为6个月)等。这样就从根本上将球员的工作合同界定为了一种特殊的雇佣合同,既不冠以劳动合同之名义,实质上又扩充了球员在工作合同中的权利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未来我国在《体育法》修改方面的立场,即更加关注体育产业的特殊性,不再单纯按照民事法律或一般合同制度来处理体育产业内的工作合同问题。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职业足球转会新规的出台必将进一步推动《体育法》的立法进程。
球员工作合同的法律性质在15版《转会规定》中得以确定,这对球员转会过程中的一系列法律适用亦有所帮助,工作合同的特殊性即决定了俱乐部之间签订的转会合同既不因为与劳动法不符而失去法律效力,又不因为形式上满足了足协转会规则中的某些规定而获得一般合同法上的法律基础,最终使得球员转会交易中可以更多考虑球员本身的意愿,并且得以根据足球运动的特殊性在《转会规定》中设定一些更为公平的终止工作合同,保障球员和俱乐部利益的特殊机制;裁判机构在处理转会纠纷时,亦不再纠结于球员与原俱乐部签订的工作合同应当适用劳动法还是合同法来处理,可直接根据《转会规定》中特殊的足球行业规则来解决纠纷。这些都将有益促进转会行为的公平和效率。
2.2 足协对转会干预的逐步规范化
2.2.1 原有转会规定中的严格干预
转会行为是足球市场运行过程中最核心的交易行为,体现了足球市场最大份额的经济利益,所以对转会行为的规制,就是对足球市场最有力的干预。自摘挂牌制度施行以来,足协对转会行为的立场一直秉持的是干预主义,希望以严格的限制来实现足球市场的有序发展:(1)限制转会名额,俱乐部引入内援与外援须受到名额限制,避免优秀球员过度集中于某只队伍,“若一支足球队集中了所有优秀运动员,导致比赛结果缺乏悬念,那么这支球队也难以获取更大利益。简而言之,是比赛本身的质量而不是某个俱乐部的竞技水平决定了俱乐部的利益”[7],欧洲等域外先进足球国家对引援名额也有不同形式的限制,比如限制上场外援数,限制本土球员的最低人数等;(2)限制转会费,直至09版的《转会规定》,我国一直都设置了转会费的上限,无论是最初的一定数额(如500万封顶)还是到一定计算标准(球员转会费=上一年度的收入乘以价值系数),职业足球转会的经济规模一直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这种管理模式是对足球市场泡沫的担忧,而国外先进足球国家早已取消了此类限制;(3)赋予足协收取转会管理费的权利,按照转会费的5%收取管理费,体现了足协增加俱乐部引援成本的立场,实际上也是对俱乐部引援行为的规制,不鼓励俱乐部单纯通过引援的形式提高本队竞技水平,希望将转会的规模缩小以减小不同财力俱乐部的差距,实现联赛竞争的均衡性。
上述干预措施直接限制了我国职业联赛的经济规模,但是在国际足球发展的大潮流中,这种干预虽然让职业联赛整体呈现出了高度的秩序化状态,却最终因为排斥了资本的充分流动而使得各个俱乐部实际投入的积极性下降,因转会的市场规模有限,俱乐部无法从球员转会运作中获得较大利益,就必然影响了俱乐部的资金投入额度,俱乐部无法通过青训、梯队建设培训高价球员而谋取经济利益,也无法引入强力外援而与其他国家的球队开展有力竞争,因此资本的缺失使得我国职业足球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
2.2.2 放宽干预,回归市场
15版的《转会规定》最终确立了回归市场的根本立场,在各个层面均放宽了足协对足球市场的干预:(1)针对转会名额限制问题,新规仍然没有改变1994年来沿用至今的“5+3”模式(每年限定转入5名无限制年龄的内援,及3名21岁以下球员),但又进行了科学的区分,考虑到了国内球员“留洋”后又转会国内的情况,此类球员非特殊情形下不再占用“内援”名额;另外,租借球员亦不占用转会名额。(2)不再设置转会费上限,交由市场调解,最大限度上排除了资本进入的障碍,以致我国职业联赛最近一次转会窗口中出现了大量“标王”,数千万人民币的转会比比皆是,而转会名额的限制又进一步减少了优质球员的供应量,在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结构影响下,进一步推动我国转会费用不断创下记录;(3)取消转会管理费,俱乐部的引援成本进一步降低,但15版的《转会规定》只明确取消了中国足协转会管理费,对于地方足协是否有权收取管理费的问题并未提及,在转会费数额不断高涨的背景下,还须进一步理顺地方足协与俱乐部之间的转会利益分配关系。
虽然资本的大量流入是否会造成新的问题或法律困境还有待实践检验,但金元足球的产生的确从客观上促进了各个俱乐部的发展,高水平外援和教练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使得我国足球俱乐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以广州恒大为代表的中超球队屡次在亚冠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让中国职业足球联赛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联赛知名度和关注度与日俱増,又刺激更多企业不断扩大投资和赞助力度。
可见,15版的《转会规定》在法律干预层面上有所调整,主要是优化了足协对足球市场的干预力度,市场规模因此得以扩大,而在转会名额方面继续沿用1994年的规定则说明了我国希望通过法律干预来避免俱乐部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实现各地足球运动的均衡发展。这不得不说是对未来我国进一步修改《体育法》的一种探索和试验,构建体育产业的市场化和体育运动的普及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2.3 构建球员培训问题的利益平衡机制
“利益平衡”是制定法律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思维,任何法律制度都是旨在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达到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如上文所述,转会制度的价值就是在于对足球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经济利益得到公平的安排,俱乐部才可能加大资金引入球员、运作球队,并随之提高球员培训和梯队建设水平,球员也才可能尽力参加训练和比赛以期创造价值,获得更高经济回报。
而在足球运动项目中,经济利益并不简单局限于球员、转出俱乐部和转入俱乐部三者之间,由于足球运动普遍存在低龄化的特点,球员的职业黄金期集中于25~30岁之间,因此球员水平的培育期更早,21岁以下的竞技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球员的职业生涯发展,故足球运动的良性发展必然以青训工作为根本。但青训工作往往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为联赛竞争因素的影响,俱乐部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会单纯引入已经成熟的明星球员,而通常还会通过自己的梯队建设和青训培养优秀的本土球员,一些情况下还可能引入其他球队具有潜质的青训球员,保证未来的长远发展。这就体现出了期待利益在足球运动,特别是转会交易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青训工作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的俱乐部必然希望通过公平的转会交易获取充分的经济回报,而尚未成熟的潜力球员在转会市场上往往又不能直接以高价转出。因此转会交易的定价机制必须考虑到此种期待利益,方能真正保证青训俱乐部的利益;职业初期的合理定价,以及职业成熟期的合理利益分配,亦是对青年球员的保护,只有青训俱乐部能够获取足够利益,引援俱乐部能够获得期待利益,方能刺激俱乐部在青训工作上的投入,以及鼓励俱乐部转出青年球员,让青年球员获得更多的参赛机会。
国际足球市场上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是青训补偿金制度以及联合机制补偿制度:青训补偿金制度是指青训球员转会后,原俱乐部可以根据该笔交易的转会费获得一定比例的青训补偿金;联合机制补偿则是指任何年龄的球员转会后,曾经培训过该球员的所有机构和俱乐部均可按照转会费获得一定数额的补偿金。
我国09版《转会规定》引入了青训补偿金制度,但并未引入联合机制补偿,而且09版规则对青训补偿金的标准设置过低,根本无法弥补青训机构为培训青年球员所付出的资金代价。为此,15版《转会规定》首先将青训补偿金的标准翻倍,“国内转会时,中国足协管理的俱乐部划分为以下类别:中超俱乐部为第一类别;中甲俱乐部为第二类别;中乙俱乐部为第三类别。培训费用标准为:第一类别俱乐部:10万元人民币/年;第二类别俱乐部:6万元人民币/年;第三类别俱乐部:2万元人民币/年”[8],从当前的实践经验看,以山东鲁能为代表的青训工作较为出色的俱乐部,其对高水平青年球员的训练投入平均为10万元/年,新版《转会规定》设立的青训补偿标准已较为贴近俱乐部的实际付出;其次,15版《转会规定》正式引入了联合机制补偿,与国际制度实现了充分接轨,在青训补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确保了青训期之后参与球员培训的俱乐部的利益。
青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制度的确立,说明了体育领域内的立法在利益平衡机制上必须考虑体育项目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应当着重解决青训与职业体育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不是简单处理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经济利益问题。足球《转会规定》对此问题的制度建设对未来《体育法》的修改亦可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3 结论与展望
经过20余年的风风雨雨,我国职业足球再次迎来了发展的契机,2015年《转会规定》的出台试图厘清行政干预与市场自治的边界,这不得不说是一次谋划深远的改革。在转会新规的作用下,未来足球运动的发展可能呈现出资本不断扩充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态势,而球员和俱乐部在足球市场的交易行为中将享有更为宽广的意思自治空间,尤其是对球员主体地位的恢复,体现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人本主义的复苏,这些都是公众和舆论愿意见到的有益尝试。总之,转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必须构建在坚实的法理基础之上,而体育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又需要我们基于更为广泛的视角来探索和把握体育发展的规律,更加公平地平衡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未来我国还将对《体育法》进行重大修改,如何从号称第一运动的足球产业发展历程中寻找科学的立法思维,将成为体育法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
[1] 细数转会制度变革三阶段规则日益失衡致弊端丛生[EB/OL].新浪体育, http://sports.sina.com.cn,2007-01-24
[2] 效力中远每分钟2万 申思因钱与俱乐部不欢而散.[N/OL].中华网,http://sports.china.com/zh_cn/football/na/other/11062529/20101018/16193130.html
[3] 肖赧.中超新赛季赛程初定 摘牌制彻底被废身价上限500万[N/OL]. 新浪网. http://sports.sina.com.cn/j/2009-12-09/13454736799.shtml
[4] 孙逊. 法律视角下中国足球转会制度问题浅析[J]. 现代经济信息,2010(13):161
[5] 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Z].足球字[2009]536号
[6] 朱文英. 职业足球运动员转会的法律适用[J]. 体育科学,2014(34):44
[7] 李章龙.博弈论自我国竞赛表演业中的应用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5
[8] 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Z].足球字[2015]649号
Legal Perspective on Transfer System of Professional Soccer in China
HUANG Hua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23,China)
Chinese football industry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now, especially the football teams have mad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onstantly in the leading of Guangzhou Hengda, which also promote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transfer system. Based on this important event that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formally issued the new version of transfer rules which names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players Identity and transfer regulations’ in December 30, 2015", this article res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transfer 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legal respective. The new regulations carried out drastic reforms to a series of mechanisms of football transfer, including free transfer system, the limits to transfer fee and player number, the youth compensation, join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ose measures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freedom of transfer market, show tracks of that our countries` football transfer is developed fro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o ‘organized freedom’, and the new transfer rules gradually clarif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and market autonomy, then the benefit-sharing related mechanisms for players training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focal point of current football reform.
Professional Football; Transferring System; Law Perspective
2016-11-18
黄华(1976-),男,讲师,硕士
G80
A
1007-323X(2017)01-0016-05
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