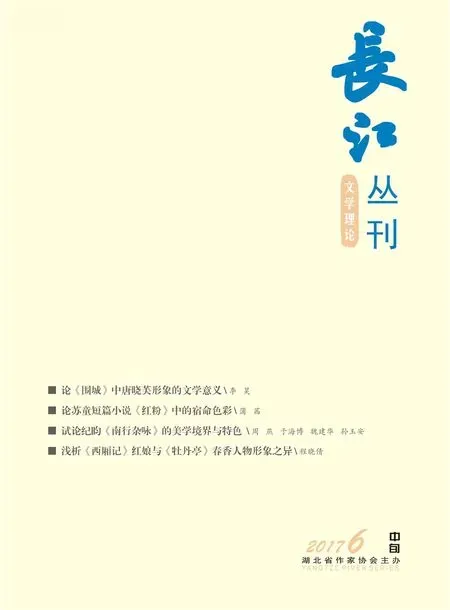翻译诗学观操控下的诗歌翻译形式
——以《哀希腊》汉译为例
2017-11-25任宋莎
任宋莎
翻译诗学观操控下的诗歌翻译形式
——以《哀希腊》汉译为例
任宋莎
根据安德烈+勒费维尔的操纵论,翻译作为改写的一种形式,主要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以及诗学观因素的影响。本文从操纵论的视角,分析了诗学观对于晚清民初《哀希腊》汉译的影响,得出了主流诗学观决定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的结论。
诗学操控 《哀希腊》 汉译
一、《哀希腊》简介
晚清民初时期,不少文人学士都受到充满反叛个性和革命精神拜伦作品的影响,对拜伦诗歌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翻译高潮,《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的翻译为最典型的一例。《哀》诗所属《唐璜》第三篇章,共16节,每节6行,韵律为ababcc。
二、主流诗学观与翻译形式的选择
翻译是最易辨、最具影响力的改写,翻译中的改写过程主要受到3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包括文学批评家和评论家,他们的点评将影响一个作品的接受程度;其次是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包括特定历史时期影响力和权力大的个人,出版商、媒体或政党等团体,以及掌控文学分布的机构;最后是“主流诗学”,包括文学修辞手法和文学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 (同上)。其中主流诗学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解决具体翻译问题的方法。那么,“诗学”由2个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类型、主题等文学要素;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起什么作用的观念 (Lefevere, 2004)。简言之,它包括要素部分和功能部分,后者是由文学系统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势力所生成的 (同上)。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受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所制约,其翻译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被“操控”的改写。
译入语文化的主流诗学与译作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外来文本通常都要经历被改写这样一个过程,使其以便与反应当地政治文化价值的主流的文学文体和主题相协调 (Venuti, 1995)。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用更简洁的话语阐释了它们的关系,即主流诗学必定制约着文学系统的动态过程 (Lefevere, 2004)。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认为诗歌是“翻译中失去”的观点突出了诗歌翻译之难,这个难处主要在于要考虑到所有涉及到的因素,还要用目标语文化和传统所能接受的语言和形式去传达原作的所有特征。从审美形式层面来看,诗歌的韵律、节奏和排版都应是译者必须传递的原作特质,然而这些特质是因语言而异,难以传达的,这对译者来说是莫大的挑战。从语义层面来讲,一首诗的内容是有关现实世界和其作者感受的,这也是译作必须重现的内容。然而,一首诗的内容通常是微妙含蓄的,这将会引起人们有关它的诸多种的阐释,正如阅读一首诗歌的方法不只一种,一首诗歌的译本也不只一种。许多译作实际上是译者对原作的改写本,于是译作的“忠实度”和“合法性”令人质疑。从语用层面来看,一首诗的译者们通常被要求生产出功能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下同样是“诗”的文本,具有内在的诗学价值,能够激发人们的感情,制造出类似的情感效果。这些使得诗歌翻译难上加难,诗歌翻译的困境在于如何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两个方面之间取得平衡,充分性主要考虑的是关于原作的典型特征,可接受性是朝向译入语的读者们。根据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看法,“创造性移位”(creative transposition),而不是“翻译”,更适合处理如此费力的工作。创造性移位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要受到主流诗学的限制。诗学反映出文学系统中占主流的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法和“功能观”(Lefevere, 2004)。
《哀》诗受到诸多文人的翻译,如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都对《哀》诗进行了翻译,这4位文人兼译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翻译,或改写《哀》一诗,并选择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翻译此诗,如梁译采用了元曲,马译是七言古诗体,苏译是五言古诗体,胡译采用了骚体,举例如下:
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①
希腊之民不可遇, 希腊之国在何处? 但余海岸似当年, 海岸沉沉亦无语。②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亹,荼辐思灵保。③
往烈兮难追;故国兮,汝魂何之?④
这 4位译者都采用古汉语和古体诗来译《哀》一诗,晚清民初时期的译者们他们本身首先便是文人学者。在诗歌翻译中,主流诗学决定了译者对译本文学形式的选择,因为译者们必须考虑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五四运动发生前的晚清时期,用古文所著的文学作品仍然占主流地位,诗歌创作严格受语言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制约,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诗歌是语言艺术,便是指受指修辞造句、音韵格律一整套规矩的制约,那么诗歌翻译也就必须是语言艺术 (辜正坤, 2015)。这一整套规矩隶属于主流诗学之下的,那么诗歌翻译也要受到相应译入语主流诗学的制约,而进行翻译诗歌活动的主体,即译者,更是如此。这些文人兼译者无一不是受过良好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他们无疑会从用符合当时主流诗学的文学形式来翻译诗歌。梁译采用了元曲,马译是七言古诗体,苏译是五言古诗体,胡译采用了骚体,他们各自的翻译都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形式。
三、结语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他们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使其译本符合当时的文学规范,亦即符合了主流诗学。4位译者对原作主题的选择呼应着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对译作形式的选择保证了其译作在本土文化中的接受。诗歌
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或全部是不可译的,特别是涉及到2种异质文化间不同语言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选择对原作进行改写,使译作符合接受文化的诗学,并使其接受语文学系统内继续它作为诗的功能,期望其译作在目标语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大致如原作产生在源语读者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化在当时相对弱势,而且处在关键的转折点,翻译在这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于是为了使这样的一个异国形象融入到中国本土文化,并产生相应的政治文化效应,遂在译作中对其形式进行改写。
注释:
①梁译文均来自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全集·饮冰室专集之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36:45~46(此处原文为繁体字).
②马译文均来自莫世祥编.马君武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438~445.
③苏译文均来自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一)[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79~84.
④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93~101.此文所引胡对于《哀》的译文均来自此书.
[1]辜正坤.世纪性诗歌翻译误区探讨与对策——兼论严复先生的翻译[J].中国翻译, 2015(03):75~81.
[2]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 raryFame[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 ss,2004.
[3]Venuti,L.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任宋莎(1989-),女,四川阆中人,硕士,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