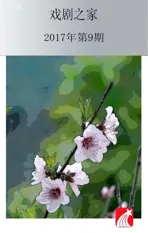电影《宠儿》中边缘世界的狂欢
2017-11-16朱晓丽
朱晓丽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电影《宠儿》中边缘世界的狂欢
朱晓丽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电影《宠儿》充溢着狂欢化色彩,洋溢着狂欢精神。它用狂欢式的电影镜头和语言唤醒黑人的集体失忆,实现了以狂欢精神消解、颠覆美国主流文化及重构非裔美国人完整身份的功能。其狂欢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非裔历史狂欢式的重构;黑人文化狂欢式的突围;女性狂欢式的姐妹情谊建构。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解读电影《宠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黑人们通过边缘世界的狂欢获得了从边缘来到广场中心的希望。
狂欢化;《宠儿》;边缘;中心
1998版的电影《宠儿》是美国滚石电影公司根据诺贝尔奖得主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为了致敬这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黑人巨著,好莱坞名导乔纳森·戴蒙担任导演,美国脱口秀巨星欧普拉·温芙蕾担纲饰演小说主人公塞丝一角。影片怪异、妖灵的哥特式基调使该片蒙上了狂欢化色彩,充溢着狂欢精神。
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解读电影《宠儿》的狂欢化特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三要素密切相关,组成了狂欢理论的核心范畴。狂欢节型的庆典上,不同肤色身份地位的人们暂时超越等级和禁令,在狂欢广场上戏谑地给庆祝仪式上的临时国王加冕和脱冕,具有全民参与、乌托邦式和颠覆性的特点。狂欢式是狂欢节活动中的礼仪、形式等的总和的体现,传达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1]。旨在讽刺和颠覆等级制度。将狂欢节上的仪式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转化成文学或电影语言,这就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电影《宠儿》中主人公疯狂的举止和狂欢的语言生动地再现了黑人族群在美国边缘世界的狂欢,狂欢化视角下的电影《宠儿》探析有助于处于边缘世界的黑人来到狂欢节广场中央,体验跨过禁锢他们身心种族界限的狂欢,重构完整的非裔美国人身份。
一、非裔历史狂欢式的重构
对于黑人的历史,莫里森曾说“小说人物不愿意回忆,我不愿意回忆,黑人不愿意回忆,白人不愿意回忆。”[2]电影《宠儿》就是这样一部逆流而上的片子,它无情地再次撕裂黑人的伤疤,以镜头闪回的方式重温过去。影片并不是用温和的叙事手段把充满耻辱伤痛的黑人历史搬上银幕,而是用狂欢式的电影镜头和语言唤醒黑人的集体失忆,允许黑人们在幽暗杂乱的房子和狭窄的棚屋里以发疯、大笑哭泣,甚至杀戮的颠覆方式狂欢,引导黑人在狂欢中正视并重构那段“难以言说”的非裔历史。只有承认耻辱创伤,黑人才能在共同回忆中治愈创伤并走向明天。
影片一开始,挽歌声中镜头从镌刻着“Beloved”墓碑拉近到塞丝一家居住的124号,屋内鬼魂在肆意狂欢,镜子一照就碎,蛋糕里出现手印,狗被狠狠抛到墙上,血淋淋的眼珠掉了出来。塞丝的两个儿子提起包袱狂奔而逃。小女儿丹芙吓得蜷缩在奶奶怀里。而塞丝早已习以为常也无法逃避,鬼魂的疯狂作乱一次次强化了塞丝努力要忘却的痛苦记忆,因为鬼魂正是她18年前为了避免自己孩子再次沦为奴隶而杀死的大女儿宠儿,代表着历史的伤痛。宠儿鬼魂的疯狂纠缠表明奴隶制废除后的黑人们依旧与历史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影片前部,当奴隶种植园“甜蜜之家”的最后一个男人保罗·D来到124号时,奴隶制下的创伤记忆也随之席卷而来。作为奴隶悲惨生活的见证人,塞丝和保罗·D不敢直面痛得无法言说的过去,他们有意避开过多的言语交谈,试图以肉体的狂欢形式来忘记过去。然而狂欢过程中,塞丝背上神似樱桃树的伤痕镜头特写进一步强化了保罗·D记忆中塞丝被奴隶主凌辱和鞭笞的场景,也让塞丝麻木的身体重新感受到后背被鞭打,奶水被抢的锥心之痛。肉体的狂欢也让保罗·D胸前紧锁并发锈的“烟草罐”里耻辱苦痛的记忆倾巢而出。记忆的反复闪回瓦解了他们自我封闭的防线。塞丝意识到作为黑人母亲的主体性,保罗·D选择正视历史、打开心结,成为塞丝重建自我的精神盟友。
影片后部,保罗·D拿着18年前有关塞丝弑婴的旧报纸回来质问塞丝,镜头闪回到18年前的124号房屋,奴隶主在逼近,绝望的塞丝抓起两个女儿,带着两个儿子冲向棚屋。电影对血腥的画面采用了迂回的表现形式,画面里奴隶主走向棚屋,耳边是塞丝疯狂的喊叫和孩子尖锐刺耳的哭声,一片混乱。当一片血腥呈现在奴隶主面前时,塞丝正发疯地把小女儿往墙上摔打,怀里大女儿的头颅已被锯下,血淋淋的,两个儿子倒在地上血流不止。狂欢式的弑婴行为颠覆了传统的黑人母亲形象,但却是塞丝浓厚的母爱的体现,是对非人道的奴隶制的抗争,向奴隶主宣告了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的主权和自我意识。
整部电影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揭开了黑人的痛苦伤疤,在回忆中让全体观影者明白黑人是有主权的平等人,并不是白人奴隶主口中只具有动物属性的牲畜,旨在让黑人牢记创伤,重构起被白人歪曲的非裔历史,重构起黑人作为独立人的身份。
二、黑人文化狂欢式的突围
黑人们难以言说的记忆和传统实质就是非洲黑人文化,“是美国黑人在为生存繁衍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和自然、族群及白人之间关系的象征和实质性的表达。这种文化植根于南方腹地,植根于非洲文风、欧洲特性和土著美国文化交汇相融的沃土里,植根于性别阶级和种族差别的动态变化之中。”[3]然而,白人文化的霸权地位注定了非主流的黑人文化沦为了边缘文化。丧失了文化之根就会被白人文化同化,失去自我。为了重构黑人文化身份,长期压抑的黑人需要一场颠覆的文化狂欢来突破强权文化壁垒的障碍,发出强有力的呐喊,弘扬黑人文化。
电影《宠儿》以黑人的视角直观地展现了一场由黑人平等参与的边缘世界的文化狂欢。黑人的文化遗产中包含着古老的信仰和传说、语言和舞蹈等,其中的核心就是音乐。电影的主旋律淋漓尽致地运用了黑人音乐作为背景音乐,从挽歌、福音音乐、节奏布鲁斯到灵歌。整部影片的狂欢场景中都离不开背景音乐、歌唱和舞蹈。
保罗·D赶走屋里的鬼魂后尝试着与塞丝母女开始新的生活,主动邀请她们去参加星期四的城里狂欢节。狂欢节上舞台上表演者都是白人,上演着各种荒诞搞笑的节目,观众全是黑人,在狂欢广场上,一直被压迫的黑人可以无拘无束地观看嘲笑白人了。黑白身份地位颠倒,白人被临时“脱冕”,黑人被临时“加冕”,而黑人的前黑奴身份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注定了他们狂欢节一结束就会面临“脱冕”的境地。黑人的笑声里也充溢着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上,白人像小丑一样表演节目来娱乐黑人,接受黑人的讥笑,黑人四处闲逛,在优美的非洲背景音乐声中用黑人的语言自由交谈跳舞唱歌,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文化狂欢世界。以前孤立塞丝一家的黑人群体也接纳了塞丝。塞丝、丹芙和保罗·D欢快地笑着,获得了新生,然而,走出了狂欢节广场,三人就迎来了鬼魂宠儿的再次纠缠,生活重新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下。
为了应答黑人们回归传统文化的诉求,达到深化主题的艺术效果,影片三次以镜头闪回的方式再现了塞丝婆母贝比·萨格斯在“林中布道”时带领黑人们狂欢的场景。“林间空地”是树林深处的一块宽阔的空地,是黑人们尽情狂欢的广场。黑人们长期受奴隶制迫害,失去了珍爱自我的勇气。作为精神领袖,萨格斯布道时所用的广场语言自由放松,颠覆了黑人内心对自我的错误定位,她大声鼓励黑人们热爱身体的每一部分并深信身体所具有的更新的力量,强调自爱是黑人们从被“脱冕”到获得“加冕”的唯一途径。在欢快的节奏布鲁斯背景音乐声中,寻回文化之根的黑人们大声欢笑和尽情跳家乡舞。在萨格斯的带领下,黑人们一边共同坚定地说出爱、尊重和团结,一边围着萨格斯快速旋转跳舞,情景交融的狂欢化气氛消解了白人文化的霸权地位,凸显了黑人传统文化在边缘世界的重要地位。
三、女性狂欢式的姐妹情谊建构
超越种族肤色差异性的姐妹情谊体现在社会中“每一个女性都会本能地去保护她们的大家族,因为这个大家族可以包容每一个成员,无论她与其她成员有任何异同,都不会被孤立其外”。[4]姐妹情谊的实质就是狂欢中的姐妹救赎。不同肤色的姐妹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撑,共享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从而缔造了强大的情感纽带。姐妹情谊的有效建构赋予了全体女性一种全新的力量,成功的自我定位。
电影《宠儿》里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女性,可以说是一部女性影片,凸显了姐妹情谊的可贵价值。影片中丹芙因为母亲18年前的弑婴暴行而被黑人社区疏离,变成悬空的空心人,内心几近崩溃。当满载历史的宠儿还魂归来时,丹芙一下找到归属感。两个姑娘欢笑着在厨房里、草坪上和树屋里跳非洲舞唱黑人歌,狂欢的过程中,丹芙找到了文化之根,宠儿也了解了塞丝更多的过去,弥补了内心母爱的缺失。
影片借丹芙之口讲述了母亲塞丝当年怀着身孕逃跑的经历,节奏鲜明的非洲鼓乐声中,塞丝在昏暗的树林里独自狂奔逃跑,由于受伤严重,塞丝体力不支倒在草丛里,绝望无助地哭泣,此时,镜头里出现了一位白人姑娘爱弥,她发现塞丝的糟糕情况后没有弃之不顾,而是表现出了同情和怜爱,耐心地帮塞丝治疗皮开肉绽的后背和按摩肿痛的双脚。当爱弥协助塞丝在破船上生孩子的时候,破船临时成了两个不同肤色的女性狂欢的广场,气氛达到了高潮:空灵激荡的背景音乐里,塞丝躺在破船舱里大口喘气喊叫,用尽全力生孩子,爱弥一边尖叫咒骂耶稣,一边大声鼓励塞丝用力,孩子被拽出时,两个女人齐声大笑。视觉听觉的冲击力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了她们狂欢的喜悦。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白人社会中,穷苦的白人姑娘也属于被压迫的阶层,毫无价值,而通过帮助黑人塞丝,她实现了自我价值。塞丝在得到爱弥的帮助后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生命个体,自我意识进一步苏醒。一种跨越了种族、肤色和等级的姐妹之情的建立更有现实意义,承载着黑白女性种族融合的强烈愿望。
影片接近结尾处,保罗·D离开了124号,塞丝翻出家里全部积蓄买回五颜六色的布料、彩带和蛋糕,和宠儿、丹芙一起布置彩带,制作衣服和品尝蛋糕。她们欢呼跳舞,大笑着互相欣赏评价衣服,气氛热烈,传递了狂欢精神,形成了一个属于母女三人的亲密无间的狂欢化世界。在这样的女性狂欢空间里,塞丝不再因为内疚而低三下四,宠儿不再怪异疯狂,丹芙不再自闭痛苦。塞丝暂时弥补了亏欠宠儿的母爱,丹芙临时感受到了久违的尊严和关注,宠儿也短暂地得到了缺失的母爱和姊妹之情。然而这种排外的狂欢过后,生活更加艰难,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的宠儿再次发狂,进而加倍折磨塞丝。丹芙为救母只得外出求助,黑人社区的三十个女性与塞丝共同的遭遇让她们深切感受到塞丝的困境,当即怀揣着非洲传统的护身符,用黑人女性的凝聚力去解救塞丝。她们挥舞着十字架和圣经等物品,把塞丝家门口的空地作为黑人女性狂欢的广场,齐声呐喊并高唱非洲灵歌,黑人姐妹们的团结和集体力量成功地驱逐了宠儿的鬼魂,也让丧失自我的塞丝得到了非洲传统的洗礼,获得了新生的可能。宠儿的消失与塞丝的新生恰恰体现了狂欢精神的实质:交替与变更的精神。
电影《宠儿》通过再现宠儿鬼魂疯狂纠缠的狂欢、塞丝“弑婴”颠覆式的狂欢、加冕与脱冕的全民参与的狂欢节、“林间空地”的黑人狂欢以及超越种族肤色的女性狂欢,凸显了小说里无处不在的狂欢化特征,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美国主流社会歪曲了黑人的非裔历史,禁锢了黑人的传统文化,边缘化了社会底层的黑人女性,黑人群体被迫处于主流社会外的边缘世界。为了获得完整的非裔美国人身份,黑人群体只有通过颠覆式的狂欢才能从边缘来到广场中央,认同自我。
注释:
①(前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63.
②Taylor Guthrie,Danille ed.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i,1994:257.
③刘捷.美国黑人的文学传统[J].译林,1999,(1):43-46.
④Michie,Helena.Sororophobia:Differences among Woma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M].New York:Oxford UP,1992:3.
[1]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5).
[3]托尼·莫里森.宠儿[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4]朱小琳.镜头中的魅影:《宠儿》从小说到电影的二次构建[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2).
J905
A
1007-0125(2017)09-0110-03
朱晓丽(1979-),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盐城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托尼·莫里森小说的狂欢化风格研究”(2016SJB75003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