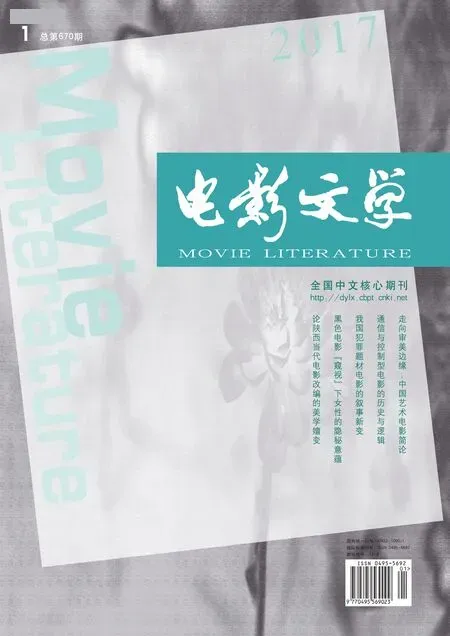《路边野餐》:乡村美学中的跨时空漫游
2017-11-15曾薇薇
曾薇薇
(武汉东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路边野餐》是苏联科幻小说家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在197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后来被塔可夫斯基改编成了其名作《潜行者》。青年导演毕赣对于自己电影《路边野餐》的命名是对塔可夫斯基的致敬,他在访谈中坦言,《潜行者》是自己电影创作的启蒙之作。
一、后城市化的转向
电影学者和导演们在21世纪初开始便以“城市一代”作为框架,探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批年轻导演和他们的作品,期间也不断挖掘和再度解读90年代的电影。在经历了第五代电影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后,这群新锐导演将焦点瞄准中国向都市化转型过程中的转型阵痛和冲突,以写实的基调、多变的风格叙事、冷酷的色调和黑色幽默,更生动地来记录社会结构的剧变、都市风情和人物关系的大规模破坏与重构。
手拿摇摇晃晃的DV摄像机,试图真实地还原与记录生活,这些导演们深入民间,试图像媒介一样生成行动主义和现场美学。直到最近,这20年来标榜都市写实的电影传统似乎又有了新动向,比如一批80后导演,有些不再聚焦于城市,落脚在遗世独立的小镇、农村或者少数民族部落,讲述出奇特或者荒诞的故事。
这不得不提到近期广受评论、“文艺”气息浓厚的院线电影《路边野餐》。如此一部无任何“明星”出演、低成本制作的电影能在院线上映实属不易,独立极端的影片基调更是广受观众和行业人士的好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电影《路边野餐》英文名:Kaili Blues(凯里布鲁斯)——电影名字听起来直接并且显露出浓烈的诗意和浪漫色彩。凯里就是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也是导演毕赣的家乡。布鲁斯就是蓝调音乐的音译,蓝色代表忧郁,蓝调音乐起源于黑人音乐,是特别感性的情绪重于情节的音乐。名字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气质。
凯里是电影的背景,也是苗族青年导演毕赣的家乡。毕赣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创作者具有一种胆怯的本质,而家乡可以给予一种安全感。另一个安全感的可能来源,是电影中的主角演员陈永忠,同时他也是毕赣的小叔父。据毕赣描述:“他庞杂的生命经验,尴尬的肢体语言,都与我心里 ‘蹩脚诗人’的形象相吻合。”这也就不难理解影片名字的来由了。让本土电影获得诗意不容易,这是巨大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代际式的——对中国电影史而言。之前内地的艺术片导演,第某代,拍的是“伤痕电影”;第某代,则基本是拍现实主义,或者说是批判现实主义。但不管怎样,骨子里都是农业文明的作者,《路边野餐》拍乡下,虽然远离都市和城市化进程,但不是农业文明,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也不再聚焦于城乡结合部的“小镇青年”这一角色,而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讲述失意者的故事。
二、漫不经心的时间骗局
电影里展示的贵州的凯里、镇远的风景和人物的生活以及音乐,都很美,也有几分宁静致远的意境。这种美不是指风景如画、民风淳朴,而是投射出东方文化中的一种幽暗、含蓄和散淡之美,是普通人像泥土一样生活,不加PS和滤镜的自然原始之美。相信这的确是导演26年来心中的肿胀。他不是要讲述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也不是去寻求乡愁,只是单纯地让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小镇,讲述平凡小人物的失落与寻回。小镇生活的人都漫不经心,年轻人大都趿拉着拖鞋、叼着烟,打牌、打台球、喝酒、K歌,却又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关联,每一位观者都融入了电影本身。
电影讲述了出狱后,与老医生一同在母亲遗留的房产里开小诊所的诗人陈升,在得知他关心的侄子卫卫,疑似被同母异父的弟弟老歪卖给之前混过黑道的“花和尚”后,决定前往镇远寻找卫卫,并帮老医生将信物交给同在镇远的过往“爱人”。途中,陈升沿途路过一个叫荡麦的小镇。他遇见了一名疑似亡妻的洗头店女子以及一名疑似长大后的卫卫的同名男子。
不同于贾樟柯粗粝画面中的生活质感,区别于娄烨摇晃镜头下的晦涩意象,《路边野餐》在绿色蜿蜒的夏日美景中完成了一次时空漫游。梦里列车,镜中虚像,光天下的腐锈,昏暗中的荧光,旧楼小屋滴雨潮湿,细碎诗词与流动影像相融,虚实之间穿梭流畅。在场景转换中,《路边野餐》找到了一种残酷的美丽。随着陈升回望自己曾经参与、曾经错过的时间记忆,《路边野餐》带着观众一起经历他面对失落的人、事和空间的一场追寻。这一段梦幻般的40分钟长镜头,晃晃悠悠让人晕眩,甚至有几分“无聊”,也成为此片最受注目的亮点。
远离都市生活,在乡土场景中却又处处弥漫着强烈的工业气息,主人公沿途穿越的美景,加上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舞厅、台球桌、迪斯科球这些意象,其间夹杂着这位蹩脚诗人的诗歌。《路边野餐》混淆了时空的界限,只是纯粹地跟随主人公的意识,在记忆隧道中穿梭漫游,编织了一场时间骗局。 正如影片中老陈从凯里前往镇远时,路过荡麦这个虚无之境。在真正进入荡麦前,有一段几分钟的空镜长镜头,似乎是老陈与开车司机的几段看似无意义的交谈。那时老陈坐在列车上,因此那些对话或者说是自言自语,就仿佛是在梦中又套置的一个梦,也有时间回到过去的体现。对话结束,镜头回到列车上的老陈,梦境抵达最深处——荡麦。途中偶遇在手上画着表的摩的司机卫卫,唱流行歌曲的青年乐队,将要去凯里当导游的洋洋,理发店的女老板……镜头依靠这些人物的视线转换、推进以及延续,这些情节和对话又像套嵌的梦境和呓语。由一人到一人,搭建起完整的、虚幻的路边荡麦。洋洋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老陈用手电筒照着理发店老板的手指,虚拟出看到海豚的样子,更像是梦,也是向往。
三、一种“布鲁斯”般的即兴
布鲁斯是黑人的音乐,相对于音乐风格,它更是一种状态。这种沟通方式最终成为一种灵魂的交流,延续至今并演化成一种音乐风格和状态。虽说《路边野餐》情绪、氛围重于情节,但并不是没有情节,只是少了通常电影里惯常的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局的套路和强烈的戏剧冲突,换了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而已,这是一种布鲁斯般的即兴。这种不同段落的歌词和旋律都不断地反复,重复表达一种感觉,这一点又像我们的诗歌。从这种角度来说,它和《路边野餐》的叙事手法是呼应的。同时,作为一种情绪和色彩,它营造了一种神秘和忧伤的气氛,表达了主人公回溯过往失落伤感的心情。
影片中在荡麦发生的场景把这种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老陈在途中偶遇在手上画着表的摩的司机卫卫,唱流行歌曲的青年乐队,将要去凯里当导游的洋洋,理发店的女老板……镜头依靠这些人物的视线转换、推进以及延续,这些情节和对话又像套嵌的梦境和呓语。由一人到一人,搭建起完整的、虚幻的路边荡麦。洋洋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老陈用手电筒照着理发店老板手指,虚拟出看到海豚的样子。之后老陈穿上花衬衫,唱完《小茉莉》,把那盘“告别”的磁带送给理发店为他洗头的女老板。电影的形式关于现实与梦境,剧情上则表达记忆与告别。梦境戛然而止是导演要将故事停留在最好、最沉醉的地方。就像我们做梦,常被突然打断或惊醒,总是没有后续,而那段完整流淌的印象又总是回味无穷。
在影片一开始导演就已经用几组镜头开始了他的“布鲁斯”之旅,奠定一种幽暗、悲伤的气质。比如小男孩卫卫童年时住的破旧屋子旁边就是一个瀑布,屋子中间悬着个歌舞厅里才会有的那种很大的球形射灯,非常突兀。在后来男主人公向女理发师以第三人称讲述自己和妻子的故事时,才明白那个突兀的灯的由来:原来他们在歌舞厅认识,平时因为住在瀑布旁边,讲话都听不见,不如跳舞。而那栋破房子以及过去9年发生的事,又体现了兄弟间的厌恶和隔膜。
除了长镜头以外,《路边野餐》的第二大争议在于“诗”。但电影里的诗不仅仅是毕赣的诗,很多人忽略了主角陈升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其实在电影一开始就已经介绍到“诗人陈升著有诗集《路边野餐》”。正如前文所说,布鲁斯和诗歌是相通的,它们反复、有韵律,在回环之间释放出原始的情绪。因此影片中不断出现的旁白之诗,也是陈升的念白和自语,符合当下语境,符合人物特点,比如坐牢九年的老陈,在诗的表达上就是那句“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这些不断出现的诗歌意象以及期间穿插的音乐《小茉莉》、卡拉OK厅里的《世界第一等》,这些载体本身都是导演私有化的直观写意,也是自身与灵感的结合。
四、雕刻时光及台湾电影美学
毕赣讲故事的方式不依赖于剧本,也不依靠台词,所有的引申和延续都通过镜头影像来完成。虽然相对晦涩难懂,却成就了他“有时令人费解,有时令人着迷”的作品。在不同的访谈中,毕赣不断提及两位重要的电影作者——侯孝贤和塔可夫斯基。1973年,苏联科幻小说家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创作了《路边野餐》,这部小说后来被塔可夫斯基改编成了其名作《潜行者》。塔可夫斯基曾一度被评论家们称为“电影诗人”,他的作品对电影与诗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对隐喻、象征、节奏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探索和融合,无疑从精神本源上深化了苏联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诗电影创作。
在毕赣导演的电影观念中,诗歌是从来都不曾缺席的存在。按他的话说:“电影是一种肤浅的幻觉体验,我想用更高级的语言带领它,这之间有种落差,非常过瘾。”《路边野餐》以诗歌念白贯穿始终,融入了导演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及对贵州凯里的幻梦乡愁,文本与镜头形成的光影互文,令人印象至深。那句摘录在《路边野餐》海报上的诗句,则使我们相信,只有诗歌才能揭秘镜头语言的本质:“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重逢就是一间暗室。”毕赣的这句诗,正好呼应了塔可夫斯基曾经提出的关于“雕刻时光”的创作理念:人们到电影院看什么?什么理由使他们走进一间暗室?为了时间,为了已经流逝、消耗,或者尚未拥有的时间。
而对于更多熟悉侯孝贤电影的观众来说,初看《路边野餐》一定觉得有一种亲近感,因为他们会在《路边野餐》中发现侯孝贤早年的印记:黑道、台球室、火车、花衬衣。不难看出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1996)带给《路边野餐》的启发:那种迷幻的当代感。《南国》以火车、汽车、机车这些意象巧妙转换传达不同世代的台湾情愫,《路边野餐》也利用这些交通工具来处理电影关于时间和漫游的主题。
除了侯孝贤的美学延续,电影也请到台湾音乐人林强配乐,再现了《南国》经典机车段落的变奏。毕赣曾说他从小听的多是台湾流行歌曲,因此电影里大量使用伍佰、邓丽君、任贤齐、包美圣、李泰祥的歌,年代足足横跨40年。歌曲的设计也花了很多心思,《告别》在电影中第一次出现是在老医生的诊所里,磁带是坏掉的,透过对话和磁带封面才大概知道了这首歌的意义;第二次,磁带已经修好了;第三次才在片尾听到完整的歌曲,有一个线性的过程。他更提到特別期待台湾观众能欣赏他的电影,因为家乡的民俗风情对台湾观众来说最为熟悉、容易亲近。
电影好看不在于它像谁,而在于它是谁,借助影像,导演们让自己或者帮助大众找到自我,提供一种认知世界的角度。无论是塔可夫斯基还是侯孝贤,没有导演是不看电影就能拍电影的,对于毕赣来说,先前任何电影中的素材或表现方式就像“潜行者”一样进入他的潜意识——但电影最终还是完全属于毕赣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