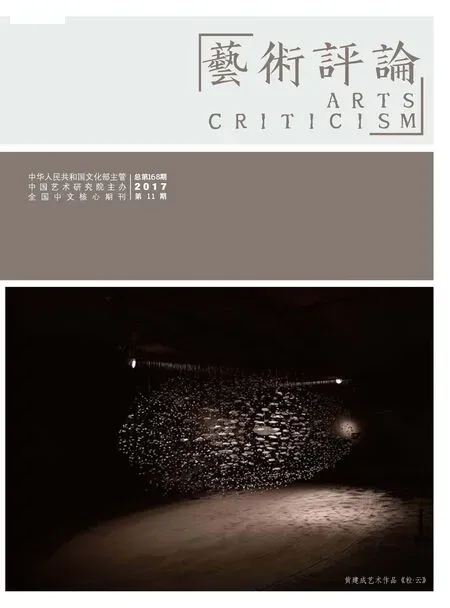从学院式探索到中国式改编
——关于易卜生“冷门”剧作在中国演出的思考
2017-11-14吴靖青
吴靖青
20世纪早年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对世界戏剧巨擘易卜生的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美学形态,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的易卜生就是在这样的传播路径中逐步树立于中国观众心中的。新时期以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有了加速度的发展,易卜生的隐藏在“社会问题剧”之后的多个“层面”被一一开掘,直至易卜生的“冷门”剧作也在中国找到了演出机会并有了转向“热门”的可能。从学院式探索到中国式改编,从戏剧工作室的主动发掘到中外文化交流机构的相关剧目引进,易卜生“冷门”剧作在中国演出时强调剧目的大胆拓展,呈现出立意风格的多样化的特点,为外国戏剧在中国的多样化、深层次传播添加了独特的一笔。
一、《布朗德》:新时期早期的学院式探索
新时期以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新时期之初《培尔·金特》的上演使中国观众对易卜生戏剧有了“写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之外的新的认识,为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现当代多样化舞台阐释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现代跨文化改编演出(例如吴晓江执导的《人民公敌》《玩偶之家》),标志着易卜生戏剧再度引起了中国的重视,为21世纪易卜生戏剧在中国走向繁荣作了铺垫;2006年前后易卜生逝世百年之际新老剧目集中、持续的上演,标志着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除此之外,易卜生的一些“冷门”剧作也在中国找到了演出机会。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冷门”主要是指在中国相对“冷门”的易卜生剧作。一方面,它们本身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不亚于那些热门的易卜生剧作;另一方面,它们的“冷门”境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在某个时间点被发掘出来并持续得到较大范围的关注的话,它们也就不“冷门”了。因此,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它们。
在新时期之初,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导演选中的《培尔·金特》剧本对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可谓相当“冷门”,但该剧的隆重上演,以及之后国内外多个不同版本在中国的演出,已使《培尔·金特》成为一部“热门”剧作。而与《培尔·金特》相比,同为民族浪漫主义思想哲理剧的《布朗德》目前在中国还只能算一个“冷门”剧目。20世纪90年代初,继徐晓钟的中国元素版《培尔·金特》之后,中央戏剧学院排演了《培尔·金特》的姊妹篇《布朗德》。鉴于《布朗德》剧本的思想深刻性以及它在中国演出的“稀缺性”,中央戏剧学院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选中该剧是有独到眼光的。
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鲍黔明执导“86综合班”的学生演出了该剧目。在排演之前,鲍黔明写下了详细的相关导演阐述(如作者当时在文中所说,这个事先写好的导演阐述是对这部即将排演的戏剧的演出构想,因此在实际排演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动),并在演出后发表了出来。事实上,《布朗德》比《培尔·金特》更难搬上舞台。因为同样是传奇式的思想剧,《培尔·金特》还具有猎奇性和幽默诙谐等特征供导演挖掘,而《布朗德》则更为艰涩深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精神价值(或曰“类宗教的精神价值”)似已“撑破”了它的故事结构。鲍黔明在1990年前后排演这样一部剧目,其勇气可与20世纪上半叶熊佛西排演《群鬼》相比。从《〈布朗德〉的导演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鲍黔明确实也是更看重该剧中的“全有或者全无”的精神价值。“希望每一个创作者首先在自己的心灵中”,把“各种各样的‘一点点’:一点点庸俗;一点点虚伪;一点点市侩;一点点……统统挖掘出来”,“面对坚守‘全有或者全无’的布朗德,向这些‘一点点’宣布决裂’”。1990年前后,多媒体技术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还比较罕见,但鲍黔明在导演构想阶段就为该剧的舞台演出设计了影像辅助手段。“《布朗德》是写意的同时又是写实的一部诗剧”,“未来的演出将不受任何所谓‘戏剧观’的打搅”,“要有时空的动感,戏剧舞台还可以尝试全景与特写相接(即电影)的艺术手段”。“在我朦胧的视像中,未来舞台上的布朗德站在高耸的冰川上迎着绚丽的北极光向我走来”。“不要失去希望,像布朗德一样勇敢地去追寻吧,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权利和使命!”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这部“冷门”剧目的演出虽然没有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但该剧目的排演过程不啻为导演和演员自身的心灵净化和修炼过程。
20世纪90年代初《布朗德》能够在中国进行排演(包括20世纪80年代徐晓钟导演的《培尔·金特》),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满足于搬演易卜生的几部耳熟能详的“社会问题剧”了。在戏剧类院校这个既专业化又更为开放、宽松的环境里,易卜生的“冷门”剧作被有识之士关注和发掘,找到了在中国登台亮相的机会。
二、《当我们死者醒来》:不同演出版的立意风格
21世纪以来,易卜生“冷门”剧作在中国的演出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有些原先的“冷门”剧目目今已经不在“冷门”行列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城市中的一些民营戏剧团体、戏剧独立制作人和戏剧工作室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包罗万象的竞争、整合与发展的环境下,一些优秀的民营戏剧机构和一批优秀的剧目脱颖而出,外国经典剧作也越来越多地被这些社团或工作室搬上舞台(例如林兆华戏剧工作室所搬演的《建筑大师》《人民公敌》),这反过来使得城市戏剧观众的鉴赏水平在“曲折中”不断提高。再进一步地说,易卜生的几部“冷门”剧作在中国的发掘和传播,也多有赖于一些目光深远、不忘艺术初心的城市民营戏剧团体的不懈努力。
到了2008年,802戏剧工作室复排《当我们死者醒来》,导演仍为刘恩平,但又根据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了新的改编。如果说,该剧的2001年版的导演原动力是“梅雅”的“走自己的路”,那么该剧的2008年版中的灵魂人物则是“艾琳”,“而艾琳,就是鲁贝克,也就是‘复活日’”。2008版与2001版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凸显鲁贝克与艾琳这一对人物形象在雕刻者与被塑造者、作者与作品对象、罪人与指控者这个位阶上的对比与对峙”,相反,鲁贝克与艾琳“其实是一体的,完全的,形二而神一”,并且他们二人已“指向符号和象征”。2008版的结局也有了较大的改变,“艾琳用随身潜藏良久的那把小刀——这也是鲁贝克所用雕刻刀的一个象征,舞台上并不以实体形象出现——‘自杀’了”,“艾琳在自杀时,鲁贝克的身体亦同时感受到这种‘戕动’”,“通过这一举动,两人同时完成了对自己的重新雕刻,也就是以生命完成并回归了对艺术、对信仰的重塑和复活”。剧中的人物“指向符号与象征”,尤其在最终结局的处理上,艾琳的“自戕”由鲁贝克、艾琳两人共同完成,“‘彼此’成全一个作品”,“是一个‘重塑’,也是一场‘雕塑舞’”,“艾琳的外在躯壳‘倒下’了,鲁贝克的内在灵魂‘挺立’着,走向‘高处’的世界”,接着是雪崩与漫天的“大小气泡”,尾声回转到开始,即“清晨的阳光照在鲁贝克和梅雅‘看报+刺绣’的画面上”。在2001版中,梅雅“走自己的路”,艾琳与鲁贝克分开,鲁贝克孤独而悲怆地面对灾难与死亡,这是导演挖掘出剧作中“独立自主”的思想精神并大加发挥的结果;而在2008版中,鲁贝克与艾琳彼此相连,合而为一,并以牺牲自己肉体生命的方式,勇敢地与过去的自己决裂,共同走向精神的胜利,这是导演撕开剧情中人物矛盾冲突的表象,进一步探求该剧的“类宗教”精神的结果。刘恩平能够对易卜生的同一部剧作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说明时隔七年,他对易卜生的原作有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他本人也在“重塑”《当我们死者醒来》的过程中得到了“重生”。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艺术节上,来自印度东北边境曼尼普尔邦首府英帕尔的合唱演出团(也称印度英帕尔合唱话剧团)出演了《当死人醒来时》。这个小城剧团“是见过大世面的,爱丁堡戏剧节、美国肯尼迪中心,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而剧团创始人、导演拉坦·提亚姆在印度戏剧界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人物,被认为是和铃木忠志、彼得·布鲁克、耶日·格洛托夫斯基齐名的戏剧家”。“拉坦的《当我们死人醒来时》创作于2008年,这部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富含象征主义意味,通过东方的假定性表演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合唱演剧团的剧本创作和表演“有着浓烈的曼尼普尔色彩和深邃的思想”。2015年,该版《当死人醒来时》又有机会到上海演出。该版演出后陆续收到了一些不同的观后感。比如,有观众认为“戏剧奥林匹克选戏的逻辑还是有迹可寻的,尤其是第三世界这几个,大概都有大师的影响”,这部易卜生剧作改编过来的印度戏“有点铃木忠志的路子,不同于日本美学,导演做了太多加法,现在来看当然会有哭笑不得的地方,但是换一种说法,就可以说那是民族性了”。更有观众直言“好些元素用得没看懂,不知道印度文化”,但随后又说“跪拜应该是向神跪拜”。看来,中国观众要想全面理解易卜生“冷门”剧作的异域哲理化改编还需假以时日。虽然比起一个世纪以前,中国观众对外国戏剧的兴趣度和鉴赏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面对一部经过第三个国家再度“异域哲理化改编”的相对“冷门”的西方剧作,面对异域文化的“多象折射”,目前的中国观众恐怕兴趣还不够大,或者说在理解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当我们死者醒来》(《当死人醒来时》)的这几个版本的演出,从对其中隐含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发掘,到“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探索,再到“异域哲理化改编”的引进,可谓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而观众对它们的接受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总体看来,《当我们死者醒来》这一剧作正处在由“冷门”向“热门”转变的过程中,这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戏剧独立制作人和戏剧工作室蓬勃发展、中外戏剧交流机制走向成熟的结果。
三、《小艾》与《爱的喜剧》:中国式改编下对“爱”的呼唤和思考
易卜生的《小艾友夫》在“五四”时期就已被介绍到中国,后来又有了完整的中译本,但由于一直以来在中国少有演出,因此也成了一部“冷门”戏剧。《当我们死者醒来》在中国上演之后,《小艾友夫》终于也引起了中国戏剧人的关注。2010年7月,802戏剧工作室在挪威驻沪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上演了根据《小艾友夫》改编的《爱你一辈子,小艾》(简称《小艾》),导演仍是刘恩平。围绕该剧的演出,802戏剧工作室和挪威驻沪总领事馆还面向读者与观众举办了一系列读书见面会、现场交流互动等活动,另外又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与交流功能,再次在网络发表相关的“导演阐述”,又一次为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深度传播作出了贡献。
在《小艾》中,“‘小艾友夫’改名为‘小艾’,男孩子的形象改为女孩子”,删去了艾斯达的追求者博杰姆这一人物,“将原剧本删减重构后,分为七场戏,全剧场次以动作及剧中人的关键性台词,逐一命名”。导演把该版《小艾》定位为“一部具有人类普遍思考价值和中国民族诗情、内蕴涵容而张力饱满的哲理化正剧”。该版演出中“小艾”手中的“小拐杖”和“大艾”(“小艾”的“姑妈”艾斯达)手中的“莲花”共同组成了全剧的“形象种子”——“莲花绽放中的拐杖舞”,在小艾的“‘瘸’与‘溺’,‘死’与‘生’”的命运转换中,“小拐杖”的“‘划船’般的肢体表现”,“在如‘莲花’绽放的‘水’中完成这个意向行为的设计”。一方面,“每个人都需要一根‘小拐杖’,为了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爱、责任和信念”,而另一方面,“小拐杖”被用来作为类似于“划船”动作的工具,则“象征着小艾的‘水手’心愿,象征着剧中所有人走出‘溺水’,撇弃‘拐杖’,自由‘游弋’的精神动力”。以上具体的删减与重构说明,《爱你一辈子,小艾》在西方的有关“爱、责任、信念”问题的社会批判性思想和象征中,已大量融入了佛教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种总体上的改编已经改变了原剧本所要探讨的具体社会问题,而使小艾的悲剧成为“爱的突围”的契机。该演出通过思想内容、结构形式和意象的全面改编,完成了从“对残缺之爱的哀怨与批判”向“对大爱的渴望与呼唤”转变的哲理化过程。20世纪早年作为“社会问题剧”介绍到中国的《小艾友夫》剧本,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中国舞台亮相时,已将重点移至中国本土化的“心灵救治”和“疗伤”中。
2015年9月至10月,“任明炀实验戏剧团”联手“易卜生国际”在北京的蓬蒿剧场上演了易卜生的《爱的喜剧》。该演出版“从易卜生的同名原著剧本出发,却不是一个精确复排或现代改编”,“它与原剧本共同呼吸,带着当代中国特有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在肢体表达的辅助作用下,用群体创作的方式给一百多年前的故事新的生命气息”。该版演出的导演为任明炀,他“将150年前的迷惘和抗争移置到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用当代语言表现“诗与远方还是买房结婚”“在世俗成功学之外,理想究竟是什么”“年轻人的困惑和失落到底有没有意义,答案在哪里”等“永恒的主题”。导演致力于让观众看到“从原剧本走出来的、鲜活的现代角色,也能看到信息时代的生活与易卜生故事的重叠”。该版演出中有大量肢体舞蹈动作,故邀请了金晓霖、汪圆清两位青年编舞家进行编舞。其中金晓霖“舞蹈风格简约、干净而又带有其特有的委婉,创作上有个人独特的审美视野”,汪圆清身兼舞蹈编导和平面设计师两项职责,“着力于多领域、跨平台的融合创作”,两位编舞家用肢体语言和舞蹈语汇进一步揭示剧中两对恋人及其周边人群的矛盾与困惑。《爱的喜剧》原本在中国也相对“冷门”,但任明炀导演的同名演出版能看到“信息时代的生活与易卜生故事的重叠”,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易卜生剧作超越时代的思想艺术魅力。
《小艾》与《爱的喜剧》的演出,是对易卜生原作进行不同戏剧类别的中国化改编。这类演出中,原著的思想内容结构是改编者撬动整个戏剧的支点,改编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所从事的戏剧类别工作,则成了架在支点上的“杠杆”。这两部改编剧不约而同地将易卜生原著中的冷峻与艰深变得慈悲与委婉,体现了当代中国式改编下对“爱”的呼唤和思考。
四、《博克曼》与《野鸭》:近年来易卜生“冷门”剧作的新拓展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易卜生逝世百年纪念活动以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形成了一定的“常态化”演出机制,呈现出中外官方与民间文化机构多方协作、中国剧院与外国剧院交流合作、国营演出制作单位与民营演出制作单位齐头并进、专业院团演出与学生演剧相得益彰、学术研究与演出实践参差前行、二度创作与一度创作紧密结合的局面。除《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群鬼》等中国观众熟悉的“社会问题剧”有了不同版本的演出外,《培尔·金特》《建筑大师》《海达·高布乐》《海上夫人》等易卜生的民族浪漫主义思想哲理剧、心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戏剧,通过多种渠道也在中国找到了演出机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引进剧目或改编剧目。与此同时,易卜生的一些“冷门”剧作引起了戏剧实践者的注意。除上文提到的《当我们死者醒来》《小艾友夫》《爱的喜剧》等剧以外,近一两年来,易卜生的《博克曼》与《野鸭》也得以登台亮相,这标志着其“冷门”剧作在中国又有了新的演出拓展。
在底物质量浓度2 mg/mL,酶添加量2×105U/mg,pH值12,酶解时间5 h条件下,考查酶解温度对玉米醇溶蛋白Zn2+螯合能力及酶解度的影响。
2016年6月至7月,“柏林戏剧节”组织者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精选剧目的展演,其中一台剧目是易卜生的《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简称《博克曼》)。这是易卜生晚年的一部心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戏剧,该剧作20世纪早年就被介绍到中国。新时期以来,该剧作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一定的关注,但却长期被中国舞台所“遗忘”。此次的《博克曼》由汉堡德意志剧院推出,德国新锐女导演卡琳·亨克尔为此做了大胆、先锋的实验和创新。《博克曼》原剧本诞生时虽然还远未出现荒诞剧,但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多年之际,该演出版本却早已将荒诞剧的元素融入全剧的各个角落。导演“让曾经存在于世的道德公义,用一种怪诞的方式瓦解殆尽”,“被折磨和被羞辱,只能靠去折磨和去羞辱来抚平”。在戏的一开始,“纵深的灰色台阶和高墙组成了幽黯封闭的舞台空间,在最深处的高平台上,一道闸门被打开,一束刺眼的白光将一张铺着纯白色床单的大床照亮,上面躺着酣睡的博克曼,他年老,肥胖,臃肿”,“就像躺在棺材里的一具死尸”。此后,这个由多个台阶组成的“纵深的灰色的台阶”以及左右两侧和背景的“高墙”少有变动,全剧“舞台空间”的真正变化主要是根据演员舞台行动的变化和灯光、音响的变化来实现的。“博克曼与妻子在八年里互不相见,但却彼此关注着,偷听着,憎恨着,折磨着”,“在楼上楼下相互敲击”。博克曼曾经的情人与现任的妻子原本是一对孪生姐妹,却为了争夺博克曼父子的“爱”势不两立。在此版演出中,为了抢夺已经成年的小博克曼,姐妹俩甚至各自死死扯住小博克曼的衣袖,把他的衣袖一左一右拉出了数丈之长,极富舞台荒诞效果。墙上的涂鸦既带有儿童的天真幼稚,又如变形的骷髅一般带着死亡的气息,暗示着剧中人在“爱”与“稚拙”的表象下日益增长的贪婪、嫉妒、报复心和控制欲。另外,剧中的音乐和音响效果带有神秘感和些许的“恐怖感”,也为演出增色不少。汉堡德意志剧院版的《博克曼》来到中国时就已经过全面改编,被赋予了浓重的先锋、实验、荒诞的色彩。该版演出在中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在演出结束后的互动过程中,观众针对该演出的表导演艺术、舞美效果,针对该演出版与原著的思想内容的区别,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另外,不少观众颇能领会该演出版中荒诞色彩的妙处。这说明新时期以来,经过数十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观众对西方现当代戏剧的鉴赏已经由原先的“粗略式”变得精准起来。
2016年8月至9月,北京燃烧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易卜生戏剧《野鸭》在北京和上海演出,导演朱希安是个“90后”。《野鸭》也是易卜生晚年的心理象征剧,该剧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余上沅的推崇,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逐渐被重视,有关该剧的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有逐年增多的趋势,但该剧2016年之前在中国的演出机会并不多(2010年中国举办的首届国际易卜生大学生戏剧节上,有脱胎于《野鸭》的学生演剧参赛)。朱希安版的《野鸭》“人物情感表现得十分饱满”,“将西方文明与社会现实完美地融入剧情当中,使故事穿越岁月、跨越国度而毫无违和感”。在总的导演风格上,“‘极简主义’贯穿到剧情的各个细节,用简单的道具来反衬剧情的多变、用淳朴的台风刻画演员心理的复杂多变”。该版演出展现了“现代人”与“野鸭”间的对应关系,揭示了他们“受一些挫折就一蹶不振”,然后“躲在小阁楼里”成为一只“受伤的野鸭”的苦闷心理与懦弱本质。对于剧本中台词的改编,导演明确了以下的原则,“尽量在让大家能懂的情况下,非常清晰了解过去的情况下,然后再把剧本做到最符合易卜生的”。此外,该版本的导演比较偏好结构化的“极简主义美学”,因此删去了像“房客”这一类角色,删去了瑞凌医生这个“清醒者”的“直露的揭示性话语”,也大量删去了威利与索比太太对婚姻关系的认识的戏,反而加重了威利女儿的戏,让她成为一个“叛逆的”“心理变态的”女孩,使人物关系“特别精要”。由于《野鸭》的剧本台词中提及“身边的事物就像泥沼”,剧中人恨不能“要藏到水底下”,野鸭的“头都是黑的”,所以舞台背景用的是“黑色的塑料垃圾袋一样的布景”,以便与“泥沼”一样的现实相呼应。另外,在排演过程中,导演比较善于培养演员的主观能动性,在“做一个最初的引导”并且“调子对了”之后,就让演员建立自信心,主动去创造角色。
上述《博克曼》和《野鸭》在中国的演出,或填补了易卜生某个剧作在中国演出的空白,或使易卜生的某部曾在中国“起大早”的剧作“郑重其事”地“赶上了晚集”,这种剧目的拓展建立在十多年前易卜生的一些剧作在中国的“常态化”演出之基础上,与易卜生在中国之影响力的长期积累密不可分。
五、余论
本文所涉及的易卜生的“冷门”剧作本身就带有诗意或象征主义色彩,另外,由于它们在中国上演的年代相对较晚,故在当代社会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它们大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戏剧演出。它们有的是带有明显的现代导演风格的演绎,有的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结合体,也有的是融戏剧、歌舞、音乐于一体的跨界演出。
话说回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还未达到完美的境地: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规模和场次需要继续扩大与增多;易卜生的民族浪漫主义戏剧、“社会问题剧”、心理象征主义戏剧之中,还有一些重要剧作只得暂且作为一次也未在中国上演的“冷门”剧作待在图书馆里。当然,这还有待于社会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包容和开放,有待于更多具有“咀嚼精神”的观众参与进来。目前看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正走向繁荣的路上”,需要全社会为之继续努力。
注释:
[1][2][3][4]鲍黔明.《布朗德》的导演阐述.中央戏剧学院(官网)>艺术研究>中戏教师论戏剧>中央戏剧学院教师论导演,2007-04-03.
[5][6][7][8][9][10]刘恩平.复活日——2008版话剧《当我们死者醒来》导演阐述.人静庐——刘恩平的博客之“恩平剧场(16)”.
[11][12][13]毛小雨.《当死人醒来时》:这一次我们谈谈印度戏.微博:北青艺评.
[14]57.《当死人醒来时》的短评,详见《〈当死人醒来时〉演出》,“豆瓣同城——上海”.2014-11-30.
[15]亲小于.《〈当死人醒来时〉的短评》,详见《〈当死人醒来时〉演出》,“豆瓣同城——上海”.2014-11-28.
[16][17][18][19]刘恩平.我们都是尘缘深重的人——话剧《爱你一辈子,小艾》导演阐述.人静庐——刘恩平的博客之“恩平剧场(17)”.
[20][21][22][23]9.30-10.4 易卜生《爱的喜剧》——任明炀实验剧团全新演绎.http://www.toutiao.com/a6199275053958267138.
[24]见“柏林戏剧节 大宁剧院五周年庆典巨献”演出单,第9页。
[25][26]彧孜孜.《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活死人的“死亡之舞”.中央戏剧学院吧“柏克曼演出”.http://tieba.baidu.com/p/4648352501.
[27][28][29][30][31]冯婧.中国首版《野鸭》致敬易卜生,94年导演展现“心灵解码”.http://culture.ifeng.com/a/20160902/49888150_0.shtml.201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