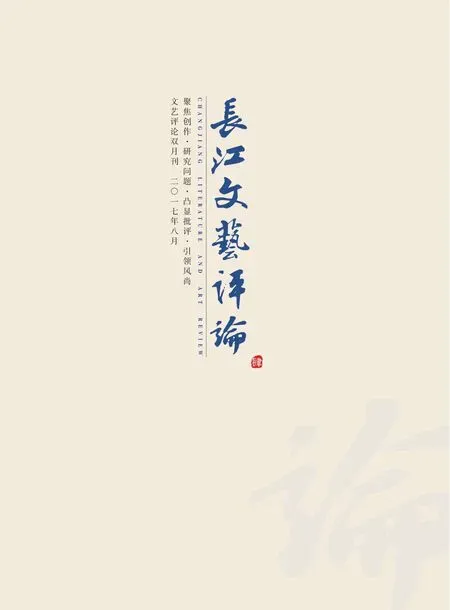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
2017-11-13◎房伟
◎ 房 伟
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
◎ 房 伟
历史在中国文化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词汇”。表面上看,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注重历史的话语权威了。史笔寄兴亡春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维护话语权的工具。一个历史定论,往往寄托了很多煌煌大义,一个历史概念的断代、内涵,往往引发现实的诸多麻烦和争议,甚至产生巨大的威胁——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历史研究更是这样,诸多禁区、雷区,让不少学者作家噤若寒蝉,躲避不及。历史在某些作家那里,甚至成了某种隐喻——借此展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其实,这种做法也并不新鲜。从儒家经典今古文之争,一直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或六经注我,都是厮杀激烈,触目惊心。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人又是最不尊重历史的。看看整天刷屏的“抗战神剧”,大家就能体会到,中国人对戏说历史、颠覆历史、玩笑历史,有着多大的热情了。裤裆藏雷,手撕鬼子,历史变成了封神演义,抗战变成了传奇魔幻,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又有着深深的悲哀。
其实,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当我们过于将其道德化与神秘化,都会产生怪异的反弹。这也是人类古怪的心理反应之一。更何况,这种反弹,又处于当下消费社会语境,就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究其原因,我们尚未在文学之中养成“平视”历史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说,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文学是可能发生的事。历史考究的是真实,文学体现的是虚构,但二者都服务于人类探索自我和世界关系的好奇心。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历史和文学,让我们充满了热情的想象与严肃的思考。金圣叹曾言,文学乃因文生事,历史却是以文运事。二者又常常交叉在一起,就有了所谓的历史小说。真正现代的历史小说,应该是想象力的虚构与对历史真实的寻找共存的精神诉求。文学既不是仰视历史,将之视为最高准则,也无需俯视,以肆意的怪诞夸张,以虚无的虚构,践踏历史真实的存在。在历史小说之中,文学和历史,应该是一种“平视”、“交流”的关系。但在实践之中,这些想法,往往无法落实。
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大多分传奇和演义两类,一种是借助一点背景,完全点染开来,另一种则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不过将之更为故事化。说到底,还是虚构大于真实,追求“好玩的历史”。但让人担忧的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又迫使历史与道德结盟,进而遮蔽了人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往往演变成忠奸善恶的巅峰对决,圣人君子与奸夫淫妇的PK。这种道德化与消费娱乐化结合的倾向,也就导致了抗战神剧的奇怪剧种。和这种道德化的意识形态企图共存的,还有借助民族国家叙事,将历史“铁血化”的倾向。这种做法,始于晚清小说,而大盛于网络小说之中。这类铁血争霸“强人历史剧”,如《大秦帝国》《大汉王朝》之类也很多,主角都是帝王将相,套路都是征伐四方,霸气侧漏,成就辉煌大业。这两类历史文艺作品,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历史威权意识过分扩张的产物,也依然有着道德化的影子。
文学对于历史而言,正是想象力与追求真实的遇合之处。文学并非为历史各类心机背书,而是要在波澜壮阔之中看到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参天大树之上发现褶皱之处的细微变化,捡拾那些遗憾与悔恨,体验崇高伟大与卑鄙阴谋,并将之以巨大想象力与好奇心表现出来。历史文学的真实,并非简单的史实再现,而是人类心灵真实的再现。文学给了历史想象的魔力,给了历史好奇心,也给了历史一颗人类心灵的种子。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展现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拿破仑的最后一分钟,令人心撼神摇;井上靖的《敦煌》,以儒生赵行德与异域公主的生死恋,再现了西夏的崛起与佛教的神秘氛围;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之中,以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会谈,铺展灿烂如星空般的虚构城市;库切的《等待野蛮人》,则干脆虚幻化历史背景,以一个类似罗马边陲城市的架空故事,探索了西方世界内部的殖民意识。
但阅读当下中国历史小说,往往是令人失望的。有的和意识形态靠得太近,以道德乏味的面孔为“庄严肃穆”,以拖沓冗长为“宏篇巨制”,浪费了大量的纸张,不过是讲了一个政治课本的常识。而新历史主义的写作倾向也是可疑的,那就是刻意塑造反体制的英雄形象,以解构与颠覆,替代理性的重建,以无底线的戏仿,将历史化为新的消费传奇。同时,一部历史小说,可以进行政治讽刺,但绝不能替代文学审美,更不能以文学替代现实政治,这无疑是走回了老路之上。文学必须有距离地实现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我至今认为,热闹荧屏的“裤裆藏雷”的抗战神剧,从根子上就是新历史主义惹的祸。我们有时候很羡慕西方的《权力的游戏——冰与火之歌》,同样是重写神话系列的作品,咱们的“重写神话”都在颠覆神话,讽刺现实上下功夫,而人家马丁却在完全虚构的架空故事里,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沧桑感的重建。说到底,所谓历史小说之中的主体历史感,就是一种文化主体力量的确认,在杀戮、阴谋或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之中,我们能在历史的坐标之中,窥见人性的反思和尊严。所谓历史理性,其实就是在历史之中树立文化进步坐标的勇气和能力。而如果仔细辨认我们那些所谓的后现代性的、新历史主义作品,所看到的,却无非是农民式的道德伦理,肆意夸张的传奇,还有浓重的历史虚无感。可以说,在历史小说领域,最能体现后发现代国家文化的边缘弱势地位,即永远无法正面言说自我,只能以碎片化的寓言方式存在。
尤瑟纳尔说:“历史是人类获得自由的学堂。”这种自由就是心灵的自由,能够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和场域,而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或者说表现历史。在无限接近历史的过程中,文学赋予了我们强大的热情、想象力与好奇心,都让我们和历史人物成为可以亲密交流的朋友,我们不但能看到他们心灵的真实,体验到历史悲壮、平庸,甚至是诡异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接近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加放松地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之下,我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我最初的创作冲动,并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对史料的兴趣。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我阅读了很多民国史料,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史料。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独自在历史的场域之中穿行,恍惚就回到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我突然发现,当我们的作家,整天将目光盯在都市男女那些鸡零狗碎之上的时候,我们竟然视这么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藏于不顾!
正是这点肤浅的自信,让我这个操持文学批评职业的家伙,懵懵懂懂地闯入了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去年至今,我一口气写了18个有关抗战的中短篇小说,包括《中国野人》《幽灵军》《去国》《杀胡》等。不敢说写得好,只是自己写得很高兴,就像一个无知的顽童,突然得到一件有趣的玩具,只是想如何最大限度地破解它的秘密。我写了蒋介石、汪精卫这样的大人物,希望写出他们在复杂历史语境之下的表现,我也写了一些战争的小人物,日本军队的同性恋军官,抑郁求死的中尉,深山遇鬼的日本军医,喜欢写小说的日本大佐,被砍掉手的汉奸,叛逃的参谋长,英勇杀敌的八路,凛然起义的将领,死守村寨的中国农民。我还写了很多普通人,毒死日寇的厨师,在北海道求生的中国劳工,痴痴等待爱情的女中学生,甚至是现实生活中设计抗战网游的宅男。我试图在每一篇小说之中,尝试一种新写法,新形式,新内容,写出不同的氛围、节奏和意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达到这个目标,我只知道,这些小说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关于历史的思考。我的创作还很肤浅,也不敢声称自己是个小说家,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认真地写下去。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