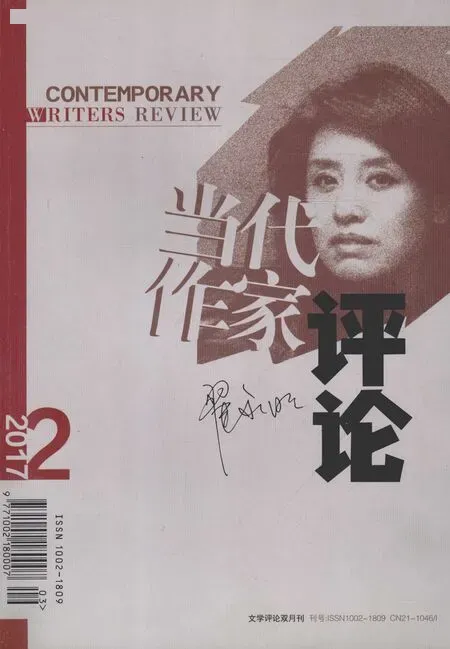乡土文学的非虚构和“非虚构”的乡土文学
2017-11-13邓晓雨
邓晓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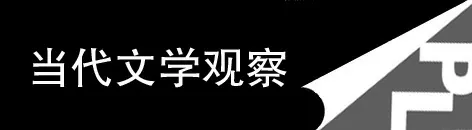
乡土文学的非虚构和“非虚构”的乡土文学
邓晓雨
20世纪以来,乡土文学一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作家的数量还是其作品所代表的艺术水平来看,乡土文学都不愧被称为“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从20世纪初到现在,鲁迅的《故乡》、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边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家杰作,早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颗颗最为璀璨的明星。
在这百年间,乡土文学从内容题材到艺术形式上,都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早期的传统乡土文学,如鲁迅、萧红、沈从文的作品,内容上大多包含着作者对故乡的“真实回忆”,再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其升华为“艺术真实”。90年代以来,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让乡土文学以更具现代性的方式呈现在众人面前,其作品也逐渐从“艺术真实”转而呈现出一种更为直接的“生活真实”。2010年,梁鸿《梁庄》的出现又让非虚构的乡土文学成为了一种新的可能。这些变化不仅仅体现着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更体现着百年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审美需要。而在种种需求之中,对真实的渴求,一直是百年乡土文学最突出的本质属性之一。
一、传统乡土文学中的“非虚构”
(一)记忆中的乡土与文学中的乡土
鲁迅在定义乡土文学时曾说过,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这层含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被重申,并最终形成了早期乡土小说的定义: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作者是用“靠回忆重组”来进行虚构小说的创作,这就使得乡土小说在其诞生之初,就带有一种对自身文体的解构意味。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带有着自己的“故土记忆”,也就自然使得最终呈现出的文本带有更多的“自传”意味,并且表现出极为真实的乡土风情。当然,所有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所有人类创作的艺术作品,都会受到其创作主体经历的直接影响。小说不管如何虚构,读者还是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作者自己人生的“影子”。而传统的乡土小说和这些更为纯粹的“虚构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的记忆和经历不仅仅是作为创作的土壤和灵感的源泉,更是直接的素材,甚至和作品的背景呈现出互为“镜像”的关系。“故乡”在这里通过某种艺术的“重组”和“加工”之后,用更为直接的方式呈现着中国真实的乡土风情。以鲁迅的乡土小说为例,在他的作品中,浓郁的浙东乡村风情几乎随处可见。《孔乙己》中对咸亨酒店的描写,以及其他众多篇目都提到的鲁镇的酒馆,显然与绍兴酒馆的文化格局是一致的。此外,《祝福》中的祭祀场景,《药》中的茶馆,《社戏》当中的故乡习俗,甚至是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如闰土),都能在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中找到原型。鲁迅自己也承认“所写的背景以绍兴居多”。不仅仅是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光,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小镇,贾平凹笔下的清风街,都几乎直接体现着作家本身的人生经历和童年生活。就像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所写的:“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可以看出,为故乡“立传”已经成了作者创作最主要的原发动力之一。
对于这些乡土文学的作家来说,他们几乎全部都来自中国乡村,又或者有着极为深刻的乡土记忆。这份属于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时尽管作家是有意识的用虚构的笔触进行创作,但这些虚构的文本却无可避免地带有大量“真实的影子”。例如萧红,她在粗犷的北方大地度过了寂寞的童年,北方荒凉严酷的环境,酷寒与饥饿都深深地烙在她所有的作品之中。这份“寒冷”我们在《边城》中是无法感受的。沈从文来自温暖、宁静的湘西净土,属于故乡的特质也让他的乡土小说有着纯净清秀的柔和之美。
总的来说,在这些乡土小说中,带有着更多的“非虚构”性质,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回忆除了虚构和想象之外,还包含着大量的对自身记忆的“重组”工作。作家真实的经历在文本中留下了如此明显的印记,这就让乡土文学呈现出更为独特的真实性。这份真实不仅源自于作者重要的生活经历,也来自作者对故土爱之深察之切的拳拳之心。它也正是乡土文学能够强烈地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生活的真实仍然需要通过艺术的加工,才能达成更具普遍性的意义和影响。鲁迅也说过,阿Q是不必非要说绍兴话的,这“不是怕得罪人,而是为了让力量更集中”。文学作品中的真实,不是“指名某处”的现实,而是经过加工和处理的艺术真实。如果说真实是乡土文学最重要的本质属性之一,那么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则是,我们到底要如何讲述这份真实?
(二)从艺术真实到生活真实——传统历史化叙事的解构
真实只有一个,但接近真实的途径却有无数种。在内容上,乡土文学由于其创作上的独特性,包含着更多创作者自身的直接经历和记忆,而显得尤为具有真实色彩。而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则一直呈现着多样化的风貌。我们不仅仅有《创业史》,《白鹿原》这样相对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有《边城》《大淖记事》等更为抒情诗意的呈现方式。但不管是哪一种,就作品呈现出的结构和形式来看,叙述大体上是整体连贯的。即便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和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主题也基本上是通过富有意味的事件发展得以呈现。在阅读中,读者仍然在期待着情节的展开和故事的结尾,一场想象中的乡村旅行,一个在“他乡”发生的故事。
进入新世纪,在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乡土文学作品在审美上呈现出了一种新的转变,在这些作品中,故事不再完整,乡村也无须完整。真实的乡土不再仅仅呈现为故事,还可以更直接地呈现出生活的原貌。这种转变在阿来的《空山》和贾平凹的《秦腔》中表现得尤为典型。2005年,阿来发表了《空山》的第一卷《随风飘散》,到2009年,六卷本的《空山》全部完成。这部讲述藏族村庄的作品无疑有着精巧而宏大的叙事,但我们同时看到了和《尘埃落定》截然不同的一种叙述方式,以《随风飘散》为例,作者用大量的笔触描写着格拉母子二人琐碎而绝望的日常,情节的发展不再是清晰的,甚至不再是必要的,一直到死亡来临,意义仍然没有降临,我们仿佛只能像接受现实一样无奈地接受这一结局。当然,在《天火》和《空山》后面的几卷里,阿来重新将意义赋予文本,从而保证了叙述的完整性。而到了贾平凹的《秦腔》中,这种完整性几乎被彻底摒弃。我们在作品中看到,大量的对话语言代替了叙述语言,情节背后也不再有紧绷的张力,清风街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仿佛是在说:这个故事可以有情节,但没有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日子都是这样过的,文学也可以这样做。就像贾平凹自己在《秦腔》后记中说的:
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续写……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我唯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
由此看来,贾平凹显然认为《秦腔》的“这种写法”不是主观的选择而是某种必然的结局,这一观点在陈晓明的《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和补充:“乡土中国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它是边缘的、被陌生化的、被反复篡改的、被颠覆的存在,它只有碎片,只有片断和场景,只有它的无法被虚构的生活。乡土中国的生活现实已经无法被虚构,像贾平凹这样的‘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也已经没有能力加以虚构,那就是乡土文学的终结,就是它的尽头了。”在他看来,这样的叙事方式就是真正的“乡土叙述”,也是乡土文学最终所能达到的完美形式。在作品中,“去现实化”的想象空间被最大程度地减少,真实感也就空前的鲜活起来。最终,对主题的表现让位给对状态的还原。读者得以无限地接近真实乡土的本貌,想象和虚构到达了终点,文学也因此到达了终点。
这样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些消极,声明任何的文学或是艺术到达了“尽头”或是呈现出某种“终结”显然是荒谬而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来说,乡土文学并不需要某种“答案”,更不会存在尽头。与其把《秦腔》看作乡土文学的终结,不如看作是一种新的尝试。单从形式上看,这种对“完整叙事”的反叛并非完全没有先例,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中就大多以淡淡的“散文的笔触”描述出一幅幅隽永的乡土画面,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也同样没有故事主干,没有中心人物。《秦腔》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这部作品终结了什么,而在于它开启了什么。这样的叙述方式并不是必然,它更不会成为某种“终极形式”。它是一次带有目的性和意味的尝试,而这一尝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是对真实乡土的一次极致的“贴近”。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了大量的呈现式描述,这些描述为我们再现着秦岭乡村的日常真实,破碎的叙述节奏也并非全然没有意味,而是在不断地尝试接近真实。文学永远不会“没有能力去虚构”,而只是选择用“非虚构”的话语,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以此呈现一种更“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在这份选择的背后,是乡土文学对于真实的渴望,更是整个社会对于“真实”的渴望。不管这份“原味”的真实是否真的高于艺术的真实,但它无疑让乡土文学在如何诉说真实的问题上,展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作为“非虚构”的新乡土文学
(一)作为真实生活呈现的乡土
2010年2月,《人民文学》在报告文学之外新开设了非虚构栏目,此外,像《中国作家》的“非虚构论坛”,《厦门文学》的“非虚构空间”,《钟山》开辟的“非虚构文本”都纷纷发表了一批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作者梁鸿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南穰县梁庄,用真实的笔触记录着故乡30年间的种种变迁。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新世纪乡土文学写作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即用非虚构的方式来书写、呈现真实乡土。在作品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鲁迅式的精神返乡。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作品中的故事是真真切切发生的,这也让《梁庄》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产生了全新的价值和意义。
用真实的笔触书写真实的乡村并非新鲜事,在报告文学当中乡村题材并不少见,但绝大部分的报告文学都把反映社会问题当作更为主要的目的。但这些作品大多将所创作的对象放在绝对的主体地位,而一定程度上弱化写作主体的“介入”,同时也忽视了在写作过程中创作者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们在读王宏甲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时,一定会对这个家庭百年来的历史及其映射出的百年中国乡土有很深刻的感受;在读管捷的《天地之间》时,则会看到张文山书记如何率领村民改变了香堂村落后的面貌。在这些阅读之中,读者会把视线都集中在作品讲述的事件任务和它们所具有的意义上,而忽视了另外一些显然也很重要的问题:作者是谁?他有着怎样的经历?他是如何选择这一题材创作的?他的风格在文章中优势如何得以体现?人们似乎总是只关注故事的真实,而并不在意这份真实的发现者和讲述者到底姓甚名谁。在这些作品中,创作主题和创作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的单向的,他们观察事件人物,讲述记录事件人物,表达观点或是抒发感情。但书写对象却并不和他们发生关系,这样的作品作为调查报告显然是合格的,但作为文学作品却显得有些“冰冷”。在一批优秀的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更为和谐的表现形式,作家勇于发现真实,但同时也不畏惧被真实所改变。他们试图在反映社会现实和进行文学创作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向外的探索和观察和向内的反思和感受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新的位置。
这种平衡在作品中,首先体现为一种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探索。在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的开头,作者对于自己的状态就进行了诚恳的剖白:
曾经,我善于在很小的事务上挖掘痛苦、寻找忧伤,喜欢在快乐的人群里出示沉思的表情,在光明的背面探测潮湿的阴影……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但不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我一直以为我在堕落,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走向心灵的衰退。
在这里,作者进行创作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观察和报告,而是通过“走出去”的方式来达成作者改变自身现状的诉求。作者不再仅仅作为“观察的眼睛”、“报告的声音”而存在,而是在作品中不断地被外界改变着,成长着,蜕变着。他们不仅热情地追求着外在世界的真实,更敢于在作品中体现其内心世界的真实。
除了对内心真实的勇敢表达,在“非虚构”乡土文学中,作者还表现出向外探求真实的巨大激情。作家们纷纷选择走出象牙塔,进行真实的“田野写作”。作为人民文学“行动者计划”(2011年,《人民文学》开启该计划,设立专门的基金,以此鼓励作家走进生活)的第一个签约作家,李娟在《羊道牧场》系列当中,和哈萨克族的牧民一起进入牧场,去经历自己从来不曾尝试过的生活,从而感受乡土的魅力。不同于梁鸿的返乡,刘娟的写作是一次更为单纯的“出发”。她并没有预设任何目的,而是主动地用亲身经历去介入真实,从而书写真实。
当然,关于非虚构到底可不可以称之为一种成熟的文体还存在着诸多争议,毕竟我们在报告文学中或是西方的新闻特写中并非完全没有看到过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梁庄》被刊登在非虚构作品栏中甚至只是一个偶然。但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本体论问题不谈(它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有意义),这些表现中国乡村的纪实文学作品,完全可以看作是乡土文学接近真实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在这些非虚构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者不仅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探求,还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亲自触摸真实,讲述真实。乡土文学从未距离真实如此之近,读者对真实的乡村感受从未如此之深。
(二)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仍需加强的艺术性
当下,非虚构乡土文学面临着一个较为迫切的问题:如何能在作品中呈现出更强的文学性。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所有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所共同面临的——即“如何能够呈现出更有意味的形式而不失真实”。在这方面,非虚构乡土文学也确实有了一些新的发展:首先,这些记述真实乡土的作者大多为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有着较为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他们在创作之初就十分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也在作品艺术风格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用富有个性风格的笔触对真实的乡土进行了细腻的表达。此外,一些作品在形式上也确实呈现出很多更为复杂的结构。例如获得了2013年《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作者阿来在用“小说”的方式讲述着真实的故事,在史料和大量事实的基础之上运用了合理的想象,呈现出历史某一时刻的“原貌”。同时,他在叙述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创作主体的声音也掺入其中,不断地尝试着和历史“隔空对话”。这些都让作品呈现出更为独特的文学特质。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类乡土文学所呈现出的形式确实较为单一,大体上仍然是游记式、散文式的叙述,其中夹带着新闻式的情节展开。这显然不是因为创作者们缺少某方面的能力,像孙惠芬、阿来、贾平凹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都具备着一流的“讲故事”的能力。然而,也正是这种“讲故事”的做法,被广泛地认为和“真实”相悖。人们普遍怀疑的问题是:这种被加工和处理过的真实,是否还是真实?退一步讲,对于真实的加工也许并不意味着远离真实,但如果这加工是依着叙述者的个人喜好,故事的真实客观性可就要大打折扣了。如此看来,文学创作所带有的虚构想象意味和非虚构所一直坚持的真实性似乎誓不两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读到的,都是一个想要努力保持客观,甚至为此不惜隐身的记录者。生怕这份真实被自己的主观意识情感所“污染”。于是,将真实当作最大的意义和价值的非虚构乡土文学,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份“真实之索”的束缚。
对待这一现象,或许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的问题是:乡土文学所追求的真实到底为何物?我们知道,即便是新闻和历史,也会因为叙述者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和视角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在文学中所追求的真实,更是本就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逻辑真实,而是独属于创作主体的真实。正像没有鲁迅的鲁镇便不再是鲁镇,而我们读到的梁庄,也本来就是属于梁鸿的梁庄。同样的,非虚构乡土文学所渴望和追求的真实也并不仅仅是冷静客观的新闻真实,而是在真实的乡土与真诚的讲述者二者之间发生的一种艺术关系。这份真诚绝不该成为创作的窠臼,而更多地应被看作是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写作态度。反之,如果创作者只是过分地拘泥于绝对客观,只会使文学陷入美学的低谷,从而失去了这份艺术的真实。归根结底,我们在文学中所能够得到的,绝不仅仅是生活的真实,更是艺术的真实。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非虚构乡土文学是否真的需要这种美学意义上的建构?传统的乡土小说,由于本质上是虚构类作品,因而逐渐在艺术形式上逐渐呈现出一种更加“无意味”的表现方式,以此来贴近真实的乡土生活。就如陈晓明所说,《秦腔》是乡土文学在美学想象上的解构和终结,言下之意,虚构的小说通过追求完全“自在”的形式,摒弃形式的意义,最终得以无限靠近真实的乡土。然而,非虚构的乡土文学与虚构的小说不同,在这里,“真实”不再需要努力呈现,而是创作的基线。因为讲述真实是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对待这样的作品,我们除了需要努力还原乡土的本真面貌,更需要的是在美学意义上对真实的事件进行重新建构。这并不是一种“掺假”,而是透过形式让真实展现出更大的力量,产生更大的影响。它让非虚构乡土文学能够超越社会报告和田野调查所具有的意义,散发出文学之美、艺术之真。
广袤的土地,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寻根之处。在乡土文学的世界里,我们共同关注着这片真实的大地,也共同书写着祖国发展乃至富强的图景。在这里,我们感受着来自故乡的冷漠和温情,憧憬着纯净秀美的世外桃源,也为土地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种种隔膜所困扰。但正是有了这一部部经典的乡土文学作品,才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这片土地最真实的灵魂。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怀着一颗热爱土地、渴求真实的心,才能写出激动人心的好作品。而不管乡土文学将来的道路如何,真实,也将永远是它不断渴求的品质之一。
(责任编辑 李桂玲)
邓晓雨,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