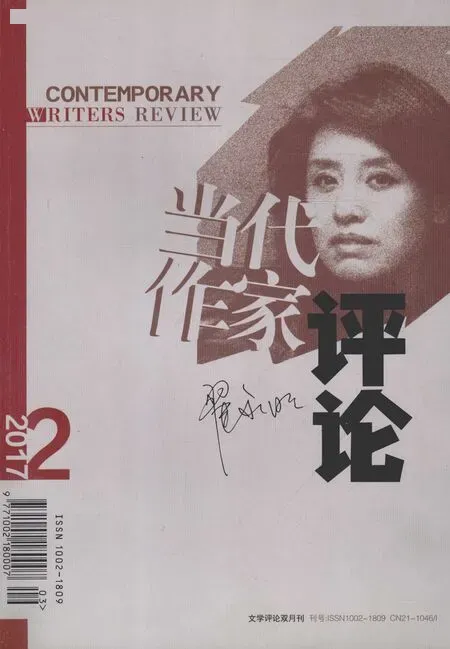法兰西语境下的莫言文学
2017-11-13刘海清
刘海清

法兰西语境下的莫言文学
刘海清
莫言是拥有海外译本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其中数量最多的并非英译本,而是法译本,译介莫言作品最多的法国为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莫言在获奖之前在法国已颇具知名度,2004年他荣获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莫言在法国的成功推广与中国的崛起密不可分,他享有颇为有利的国际接受环境,法国公众乃至国际社会都将目光聚焦于处于重大发展期的中国。本文将重点探讨法国主流媒体、学术界、出版界等不同受众群体对莫言创作的多层次解读与诠释,揭示其作品的世界性视域与民族性特质,从中折射出法兰西公众对中国作家的期待、认同或误解,从而修正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片面认识。
一、莫言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
莫言是最快融入西方文学市场机制的中国当代作家,他登陆法国时正值法国汉学界和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走向常规化的时期,法国出版社力图抓住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来进行有规划的市场推介和宣传。1990年法国南方文献出版社(Actes Sud)出版了《红高粱》的法译本,标志着莫言正式在法国亮相,1995年法国瑟伊出版社(Seuil)出版了莫言的《十三步》,与莫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之后瑟伊出版的《酒国》获得了法国劳尔·巴塔庸翻译奖,但真正铸就莫言巨大声誉的是瑟伊出版的《丰乳肥臀》,该作品被译为《美乳美臀》(Beaux seins belles fesses,2004),并在书封冠以“中国式《百年孤独》”的名号,令莫言被大众熟识。此后瑟伊的推介明显加快,近三年又出版了《变》《红高粱家族》《超越故乡》《幽默与趣味、金发婴儿》等作品的法译本。目前法国已出版20多部莫言译本,主要出现在瑟伊与毕基耶(Picquier)出版社的书目中,前者在几次收购后几乎垄断了莫言小说,后者对其短篇小说较有兴趣。翻译与出版之间的时差愈来愈短。莫言的成功得益于优秀的译者团队,其中有诺埃尔·杜特莱(No⊇l Dutrait)和尚德兰女士(Chantal Chen Andro)等知名汉学家,他们对莫言有深入的学术研究,中文功底和翻译水平堪称一流。2014年巴黎三大张寅德(Yinde Zhang)教授关于莫言的研究专著《莫言,虚构之地》(Mo Yan,le lieu de la fiction)由瑟伊正式发行,极大地拓展了莫言作品的跨文化生命力和艺术价值。
法国对莫言的译介与出版反映了灵活多样的传播模式。诸多的法译本将跨文化张力凝聚于副文本边缘,印刷在封面上的中国风格图像在跨文化的混合语境中更有利于表达作品的幻象色彩、忧思精神和东方民族智慧。最初的法译本封面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情调,中国古典艺术占据了主导:毕基耶出版社的《透明的红萝卜》(1993)封面画为宋朝的野兔绢画,南方文献出版社的《红高粱家族》(1990)封面取材于唐朝李寿墓碑上的壁画,画了一队骑马的猎人。近年来出版者更多借助中国当代艺术来设计封面,梅西多(Messidor)出版社的《天堂蒜薹之歌》(1990)封面为歌颂下乡知青的宣传画,与小说的乡村背景和农民生活构成呼应,而瑟伊的《天堂蒜薹之歌》(2008)采用的则是蒜瓣静物画,与小说蒜农闹事案件的情节线索形成意象的指涉。瑟伊《酒国》(2004)封面为一幅笑态可掬的胖娃娃画作,与小说中的红烧婴儿案件构成呼应。为吸引读者视线,出版社有时会选用前卫新潮的艺术封面,所以毕基耶的《藏宝图》(2004)与《欢乐》(2007)封面采用了当代画家郭伟的系列画作《室内蚊子与飞蛾》《蓝蚊子》,而近年出版的《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2011)则采用了画家兼摄影师崔岫闻《天使》影集系列的一张照片,大大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瑟伊的《美乳美臀》(2004)封面为当代画家魏东的一幅三折画局部,展示了一位水边梳妆的丰满女性的背部,与小说主题意象构成了生动呼应。瑟伊的《生死疲劳》(2010)封面为一个巨大的龙头准备将一只驴子吞入腹中,这是暗示历史浩劫的方式,既呼应了小说的生物学和物种学视角,也昭示着中国农民在土改、大跃进、“文革”等历史背景下的艰难生活,体现了荒诞、怪异和戏谑的文体风格。瑟伊的《蛙》(2012)封面画为几只两栖动物摇摇欲坠地悬在一个屋梁上,这个被动场景影射着女主人公内心的忐忑和信念的纠结,从接生婴儿的乡村医生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身份的变换令她无法逃脱极度的矛盾痛苦。借助于封面图画的影射,读者更能读懂《蛙》中心灵的震荡,反思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民生问题,接受灵魂和道义的洗礼。大量取自中国艺术的封面都与文本正文构成互补或衬托效果,可谓相得益彰,从而契合了瑞典文学院的评价:“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代融为一体。”
大部分莫言作品法译本没有序言,封底发挥着重要作用。瑟伊出版的莫言图书封底融合了作者简介、作品概述、译者名字、相关评论以及文本节选,全方位展现作品的独特性。瑟伊的书籍护封在作者评论方面可谓独具匠心:从“独特的天才”(《美乳美臀》2004),到“闻名于世、语言大气、文风遒劲的作家”(《檀香刑》2006),“今后全世界公认的作家”(《蛙》2011),诸多溢美之词彰显了莫言的世界性权威。如果说封面图像学体现了对异国情调的坚持,那么相反的是封底文字话语有淡化异国情调的倾向,有时向文化同化方向靠拢。出版商们在描述莫言风格时强调现实主义与魔幻主义的结合,粗犷与精致的结合,这种杂糅性介绍有利于加强西方读者的文化认同感。
近年来莫言在法国主流媒体上频频出现,各大出版传媒和学术团体都为传播莫言不遗余力,中法作家圆桌对话和学术研讨会也渐趋频繁。法国传统报刊媒体起着首要作用,2000年8月18日法国《世界报》发表题为《莫言:字里行间的中国》的访谈文章,勾勒了莫言的大致轮廓,2004年之后法国报刊媒体开始持续关注莫言,例如《解放报》《费加罗报》《新观察家》《快报》等报刊以及更专业的文学杂志等,会定期刊登关于莫言的资讯、访谈和评论。互联网也举足轻重,部分网站专门报道中国作家最新讯息,例如2009年以来网页报《参媒》(www.mediapart.fr)、《街头89》(www.rue89.com)数次将莫言作为头条报道。法国的《拉鲁斯百科全书》和《环球百科全书》都收录了莫言。即便如此,莫言目前尚未获得法国文学类的嘉奖,虽然《生死疲劳》入围2009年美第奇奖,最终还是遗憾落选。自1998年开始,莫言被列入巴黎三大张寅德教授开设的比较文学研究生课程,然而中国当代作家迟迟未被选入法国中等教育纲目,只有余华的《活着》被引入国际中文科目用来比较小说与其改编的电影。虽然莫言与余华、王小波等作家出现在法国中学教师学衔竞试中文科目的《现代文学》大纲中,但中国作家却持续缺席文科会考,这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教育体系中的接受程度还远远不够。
二、莫言在法国的接受与评论
翻译质量和出版策略对一个作家在异域的成功只能起到辅助的推动作用,关键还在于作品内容本身。莫言指出:“法国是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西方的艺术之都,他们注重艺术上的创新而创新是我个人的艺术追求,总的来说我的每部小说都不是特别注重讲故事,而是希望能够在艺术形式上有新的探索。这种变化可能符合了法国读者求新求变的艺术趣味,获得了相对广阔的读者群。”莫言的文学创作扎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和地域色彩,却善于利用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法展现中国社会现实,呈现出亦幻亦真的文学特色,这种经过加工的民族文化和奇特文笔深深吸引着海外的读者,法国不同领域的读者对莫言作品进行了丰富且多层次的解读与诠释。
莫言作品没有大规模对意识形态的探讨,而是着眼于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和生活,无形中契合了普通大众的心理需求,奇幻独特的故事情节和幽默讽刺的叙述基调恰恰是法国读者所钟爱的,他们能够在莫言作品中找到符合西方审美传统的共鸣元素。2004年4月1日法国《快报》“读书”专栏发表访谈《莫言,粗犷的介入》,指出莫言“为了摆脱中国文学中一些固有的束缚”,往往采用“拉伯雷的夸张写作手法,卡夫卡式的暗喻,君特·格拉斯对政府和家庭关系的描绘,马尔克斯史诗般的文字冲击”。法国《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2009年9月刊上收录了莫言的访谈,莫言承认拉伯雷的《巨人传》及其超现实主义风格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远影响,“是因为上世纪60到90年代,我们的社会很像拉伯雷笔下的世界。这种与世隔绝,这种癫狂,这样虚张声势而又夸张的生活,也存在于我的作品里”。莫言在2010年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演讲中也亲口承认受到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尤其他1984年后的作品吸收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认知社会、观察世界的方式,即从人类存在的本真意义出发去还原生活的状态,以变换性、想象性的艺术方式演绎人的荒谬感和现实感,从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精神的支持。
中西文学的熏陶帮助莫言打开了创作思路,糅合众家之长的他用最奇特的方式表现了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译者杜特莱曾打比方说:“莫言是个食魔,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西方叙事传统、中国传奇故事、大众戏剧、流行歌剧。”莫言身上浓烈的民间艺术气息、超现实的怪诞想象风格和游走于中西文学传统之间的游刃有余,让西方人看到了他们所期待的具有世界水准、与西方文学相通同时又具有中国性的文学。例如《酒国》《生死疲劳》与拉伯雷的《巨人传》一样充斥着大量奇异形象的描绘和荒唐离奇的故事情节,都力图通过审丑视角和天马行空的粗犷叙事来反思社会现实。《生死疲劳》既继承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传统,又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和野性想象的民间叙事小说,通过一个地主的多次投胎转世,追问了荒诞历史进程中人性的复杂和个体的悲剧。《酒国》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进行了无情揭露,尤其批判了官场的腐败堕落以及铺张到病态的“吃文化”和“酒文化”,这种融侦探小说、怪诞想象和讽刺寓言为一体的叙述风格体现了中西文学思潮和流派的杂糅,蕴含着对社会风尚问题的忧虑和反思。
当代中国和世界复杂多变的政治文化形势,使得法国各领域的读者群体对中国文学的关照不可能采用单一的或纯文学的视角。钱林森说过:“部分译者和批评者把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的‘晴雨表’,欣赏现当代文学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动向的政治、社会资料。”法国媒体对莫言的现实主义笔触及其作品反射的人类境遇、社会难题、历史悲剧与人性的沉沦等颇为关注,尤为看重他对社会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反思,正如皮埃尔·哈斯基(Pierre Haski)在网页报《街头89》中所言:“为了解今日之中国,大量阅读莫言作品颇有必要,中国经济腾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严苛制度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普通个体的苦痛遭遇。”许多评论聚焦莫言笔下的历史动荡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揭露,引发了诸多争议和思辨,例如法国学者维罗里克·布莱恩(Véronique Brient)在中国武汉大学主办的《法国研究》杂志2010年第2期发表论文《莫言,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苦涩批判》,安德烈·克拉威尔(André Clavel)于2011年8月26日法国《快报》发表文章《莫言:不卑不亢写中国》。这些文章评论着重于小说政治背景的参照,强调着莫言作品指涉的中国当下社会关系和官场腐败等问题,探讨着以矛盾性和问题性为特征的中国形象,诸如1950年到1960年间的饥荒灾害,强制性计划生育,或政府贪官间的贿赂等社会问题。
莫言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非常凌厉,常常直指普通中国人所面临的暴力、贫困和痛苦,他的作品曾涉及到中国制度下的官僚主义、强制性计划生育、土地改革运动等现象,这些敏感话题在法兰西的语境中有时被刻意放大,产生与作者本意有所偏差的误读。我们要批判地审视国外对中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凸显与遮蔽,某些评论会有意识地建构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学形象,片面地认为莫言以寓言、神话和想象等作为创作题材是为了避开官方审查、抵抗主流意识形态和抨击本国社会制度。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的身份、政治姿态甚至中国的自由民主,一度成为部分媒体从政治层面炒作的对象,例如《费加罗报》曾有文章偏执地评价莫言:“借助魔幻与隐喻的路径,作家抨击了官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流弊……譬如戏仿侦探小说的《酒国》,用完全拉伯雷式的手法虚构出出卖肉孩的非法交易,展现出如黑社会般党的干部的极致兴奋的丑态。”文化新闻的政治化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客观评价,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针对莫言的颁奖辞重点强调了落后愚昧的中国农村形象,缺乏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推崇,体现了西方人意欲塑造的中国形象。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西方人对新中国的发展崛起充满顾忌与担忧,往往用滞后和局限的眼光看待中国,这并不利于双向对等的跨文化交流,异质文化间的接受应以客观的认识和尊重为基础。
相较之下,译者杜特莱的评论更加客观:“莫言有敢于触及中国当代社会最尖锐问题的勇气。而他总是从人性角度来思考和写作这些问题。这就使他获得了一种独立身份:他既不是异议人士,也并非官方作家,而是一位深植于社会与人民中间的独立作家。”莫言也指出:“我承认,小说中涉及到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文革’‘改革开放’,我都是站在超越阶级的角度去写的……我想以具体的人为出发点去理解并解释历史。”莫言眼中的文学大于政治,他始终以超越地域、种族和阶级的立场去写人,重点关注个体的困难遭遇、不合理的现象习俗,而不是倡导或反对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过去的一百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政治革命和经济改革的世纪,作为文学平民的莫言认为:“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是人类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丧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历史对莫言而言,不过是虚构性的背景,他透过社会变迁关注的是人性和情感,正如《丰乳肥臀》并未从政治历史的视角去建构叙事,而是引入了基督教文化的罪恶、救赎、博爱、牺牲、救世等宗教意识来塑造人物,围绕母亲和儿女们的命运描写了一部心灵的受难史、堕落史和抗争史。莫言有意消解了旧历史主义小说中意识形态视角和政治话语写作的规范性和有限性,而是以新历史主义文学(多元文化视角、民间话语、中立性审美、相对化价值判断、变换性想象)的手法展开民间化的故事叙述,解构有悖人性的异己力量,展示出复杂历史进程中芸芸众生的坎坷命运和精神诉求。
三、莫言作品的世界性与榜样性
莫言写作与其成长经历紧密相关,其故事背景很少游离于出生地山东高密之外,故乡的历史事件、风物人情、民间传说、童年生活记忆等,均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法国学界普遍认为莫言与“寻根文学”颇有渊源,然而莫言绝非普通意义上的寻根作家或乡土作家。他博大宏阔的乡土情怀彰显了世界主流文明精神的人文情怀,其笔下的芸芸众生代表着伟大神圣却又不无邪恶丑陋的“人类”。弗格·特朗(Phung Tran)在《亚洲研究》(Études Asiatiques)杂志2011年第1期发表文章《莫言小说中的自然书写或文学中的乡村视角:〈透明的红萝卜〉作为乌托邦的象征》,指出浓墨重彩的民间语言、魔幻的自然意象和奇异的故事情境成就了莫言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大自然的美好情境和美丽事物成为饱受苦难的孩童内心深处向往的精神家园和自由乌托邦,也象征着“文革”浩劫下的中华民族对未来的希望。
面对敏感历史问题的莫言并未武断地采取赞成或反对立场,而是运用辩证思维将个体境遇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在对生命本体的追问中彰显出诗性的哲思品格和理性的诘问精神,体现了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张寅德先后在法国《神州展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期刊2010年第3期和2011年第4期发表文章《生命的虚构:莫言书中的人和动物》与《生物政治学小说:关于莫言小说〈蛙〉的思考》,探讨了《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关于人道、生存和生物伦理维度等悲悯性主题的表达,并指出“在莫言所有的小说中,人与动物之间都有一种共生和交流的关系”,呈现了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旨在引导国人从更宏大的人性道义和生物存在视角对社会政策、民生问题、个体责任等方面进行深刻的道德反思,从而矫正某些过激的、异化的社会现象。张寅德从生命政治学角度指出《蛙》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探讨了计划生育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用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出中华民族在新历史时期的困难和考验,在肯定计划生育的同时,又从生命伦理层面拷问一些有违人性的极端行为,引发大众在时代需求与伦理道德之间进行深度反思。
从总体上看来,法国学术界与汉学家的评论有别于媒体话语,他们能以更深入的方式揭示莫言在创作初衷、形式手法和文学价值方面的独特性,即重点从社会人文与人性剖析层面去解读莫言,甚至希望莫言作品能反哺法国文学,促进了法国读者对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的客观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片面认识。世界性作家的创作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其中必然包括对本民族历史的反思。一方面,“莫言作品是对中国农民之历史伟力的文学写真”,莫言向世界展示了富有血性、勇于叛逆又甘于奉献的中国农民形象。另一方面,莫言作品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兼具批判和反思精神的中国形象。
综上所述,当代文学作为构建国家形象的具象载体,在国际化语境中为消除各民族误解与偏见、促进相互认知与沟通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文学“走出去”必然面临中外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等态势的冲击与影响,当下创作者应以构建真实国家形象并提升其正面国际影响为己任,从而使中国文学更有尊严地迈向世界。莫言独特的中华民族本土经验写作和深邃的人文关怀意识契合了全人类最为关注的人文主题元素和伦理价值,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相异性与共融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既是中国文化国际影响的确认,也是全人类共识性价值的别样呈现。莫言的成功为那些在国际之路上踯躅前行的中国作家指出了方向,即文学在建构民族性的同时,也要具备宏大的世界性视域和终极关怀意识,才能在世界文学谱系中抒写出更精彩的中国文学篇章,进而促进中国梦的发扬光大。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572)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刘海清,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