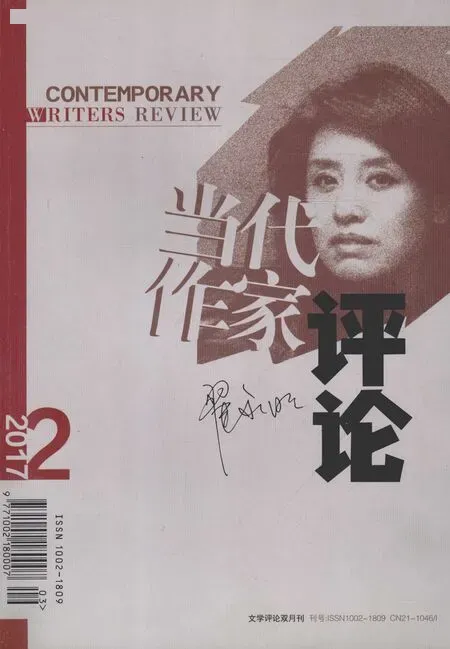后理想主义时代的困惑与求索
——甫跃辉小说论
2017-11-13陈林
陈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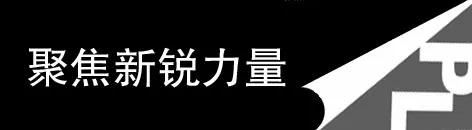
——甫跃辉小说论
陈 林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理想主义的终结”、“人的消失”、“人的死亡”、“人文精神的失落”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一判断背后的价值取向、文化立场、知识谱系、问题意识不无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李劼在回顾“人文精神”讨论时说明了当时存在的分歧,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的是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另一些则是“对商品经济冲击的故作惊恐”。差异背后的历史共识隐约可辨,理想主义的式微日益凸显。市场对公共领域、个人生活的腐蚀,政治与市场互相缠绕、互相嵌入及伴之而来的问题,80年代重建的人道主义和个人自由价值体系的人为中断等,无疑从不同方面侵蚀着理想主义大旗。
然而,“终结”、“消失”、“死亡”的内在因素不容忽略,我们对“这种理想和人文信念的最强有力的批判却来自知识分子的内部”,理想精神“消逝或死亡的征兆却是文化内部发出的”。换言之,我们谈论的精神危机、价值错位、理想失落,更是知识分子的意识特征,是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精神症候。从思想史的角度看,80年代后期兴起的反激进主义即开始清算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在一些反激进主义者看来,“五四”、“文革”,以及“文化热”构成一条激进主义线索,百年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盖因激进主义太强而导致不断革命的缘故。余英时指出:“中国百余年走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中国为了这一历程已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激化的起点就是转型时代出现的思想气氛或心态,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之后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讥讽,对“告别革命”的鼓吹,亦可在这一思想史脉络中加以理解。
作为社会躯体中的文化神经,文学及时而敏感地回应时代的震动。如陈晓明所说:“在8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大写的人’(人的理想)已经萎缩,‘先锋文学’已经无力创造出具有正面肯定价值的人物,即使反面价值的人物也未必能确定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水准。”旷新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9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登陆中国,‘先锋文学’以欲望和暴力的书写成为了‘人性恶的证明’,颠覆了新时期初期‘大写的人’及其有关人性的神话,宣告了‘理想主义的终结’和‘人之死’,使人从世界的中心退出,导致了‘人’的消散和人道主义潮流的衰竭。”除了他们所说的先锋文学外,“大写的人”在其他作品中同样“已经萎缩”。如果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还多少存有理想主义的流风余韵,人物作为独异个体而不是道德主义的集体人格确立其主体性存在,那么对大部分“新写实小说”而言,高蹈的理想主义已被现实的“一地鸡毛”所取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不复存在。而到王朔和王小波笔下,知识分子反复成为被揶揄、被反讽的对象,理想主义几乎成为伪崇高、假道学的代名词,避之唯恐不及。
“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像躲避瘟疫一样喊出了“躲避崇高”的口号。无论是“归来者”的一代还是知青一代,他们中许多人的创作从8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从“崇高”到“反讽”的转变,这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如下判断:“9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的重建在总体上显得疲乏无力。”韩少功的《归去来》中,黄先治疲惫不堪地喊出“我累了,妈妈”;贾平凹的《废都》中,庄之蝶终于心力憔悴地倒下;徐坤的《斯人》中,“诗人已经永远消失”;格非《沉默》中的知识分子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看着它终于成笑谈。”李洱呼应100年前尼采的“上帝死了”,无可奈何地喊出《导师死了》。尽管有张炜、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一批持之以恒地坚守理想主义高地、重视精神气质的作家,但理想主义整体的溃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里不妨用“后理想主义时代”指称8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至今的时段。
以上时代环境和思想文化、文学状况,既是甫跃辉的成长背景,又是他问题意识和艺术经验的重要来源。早在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中,就强调过文学艺术创作与种族、环境、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一位“纯文学”作家,甫跃辉的写作从个体经验出发,有意识地赓续庞大的写作传统。与前辈作家虽然存在代际差异,但同时面临诸多相似问题,在这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间,甫跃辉寻找着自我表达的途径。因此,我愿意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语境和文学传统中理解甫跃辉的小说创作。
一
当我们说甫跃辉的许多小说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时候,这并不是说那些小说里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事,而恰恰是,在那些个人气息、个体经验之外,可以看到“80后”一代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肖像。因此,尽管甫跃辉走在“纯文学”的道路上,并一再强调小说艺术的自足性,但文学批评仍不能轻易将“世界”拒之于“文本”的大门之外,而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如萨义德所说的那样,肯定“文本与人类生活、政治、社会和事件存在真实(existential actualities)之间的关联”。
甫跃辉的创作题材涉及乡村、小镇、城市,但他不愿意以此作为划分小说类型的依据,也不想为自己找一个写作的“根据地”——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而宁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的不少小说写到云南老家乡村世界的“日常传奇”,包括《散佚的族谱》《鱼王》两本小说集中收录的作品和长篇《刻舟记》等。尽管故乡并未形成上述意义的写作“根据地”,但我认为,甫跃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世界是他另一意义上的创作“根据地”——无论他的创作置于什么时空,他对世界的理解是基于故乡背景的理解,他在作品中寻找和求索的,未必是题材学或地理学的故乡,却无疑是精神的故乡。
甫跃辉们的成长是从告别故乡开始的,不管是顾零洲们负笈求学,还是李绳们外出打工,他们都努力挤进开往城市的列车,这点与他们的前辈并没有多少区别,如《人生》里的高加林,《黑骏马》里的白音宝力格,《塔铺》里的复习班学生,《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风景》里的“七哥”等。不同的是,对于80年代的路遥们来说,实现现代化是他们的集体想象和共同目标,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让他们相信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即便理想受挫,仍能像高加林一样重返故乡获得慰藉。而对顾零洲们而言,由于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的加剧,他们很难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所属的阶层,因此产生普遍的失败感和绝望感,甚至像方方笔下的涂自强一样过早夭折。既无法在城市获得立足之地,又回不了故乡,这是顾零洲们的真实处境。如果说高加林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那么顾零洲们这些“失败的青年”,几乎无法再维续或确立任何坚固的理想,他们置身的时代或可借《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来概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但关于理想的记忆、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并不能彻底根除,它就像《动物园》里弥散的气息一样不时地提醒、刺痛着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痛与在往往十分吊诡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顾零洲们与世俗化时代的犬儒主义者尚有所不同的地方,也是甫跃辉与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者的不同。甫跃辉通过描画顾零洲一代的精神肖像,捕捉人性内部微弱却弥足珍贵的光芒,以此重建和确立人的信念,同时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
从乡村一跃而进入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中间越过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史,与“50后”、“60后”作家相比,甫跃辉这一代人的成长是去历史化的,对宏大历史的建构与解构似乎与他们无关。甫跃辉基于自身经验的体认和反思,不是对某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反思,也不是对革命史的反思,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不可忽视的是,甫跃辉的反思既迥异于启蒙主义话语,又绕开了革命话语,同时并未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而是努力搭建具体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宇宙人生之间的有效通途。在《鱼王》自序里,甫跃辉征引鲁迅的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他解释道:“这里说的‘有关’,也就是关系,‘与我有关’的,不仅仅是‘无数的人们’,还有‘无尽的远方’。这‘无尽的远方’,以我的理解,就是天地万物。”这种意识的出发点是“我”,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我们”,落脚点却既不是“我”,也不是“我们”,而是浩渺无涯的天地万物。在个体与天地万物的互相往来中,甫跃辉创造了他的小说诗学。他从对日常生活的精耕细作入手,于习焉不察的事物中,令人惊讶地开启一片澄澈的境界;以细腻的写实手法,却出人意料地铺垫起勾连精神彼岸的通幽曲径。
二
在《理想国》第7卷中,柏拉图的太阳代表着“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这样的真理和理性,曾长期被认为是人类走出幻觉和影子,抵达“真正的存在”的唯一路径。在甫跃辉的小说《鱼王》中,关于太阳的隐喻系统被彻底改写了,它所代表的理智化世界不再是真、善、美的化身。这部小说可以理解为马克斯·韦伯“除魅”思想的一个注本。小说中,牧童与白水湖的关系象征着人类的童年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那是一个观念化、理智化之前的世界,在那里,世界是给养、庇护人类的寓居之所。社会的现代化是理智化的一个结果和组成部分,而用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则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刁氏父子收购白水湖开启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世界的对象化。象征理性的太阳烤干湖水,直到最终鱼王被捕,完成了对世界的祛魅。在甫跃辉笔下,理智化带来的结果不是柏拉图所要努力达到的真正的存在。祖祖辈辈关于鱼王的美丽传说像鱼王一样,被分解得支离破碎,代之以鱼王腐臭的气息。从此,我们不再有故事,世界于是变得日益枯竭、乏味。
甫跃辉不是将现代性置于历史主义的进步观念中加以理解,他所呈现的是现代性祛魅之后意义世界的萎缩和枯竭,李敬泽准确地指出这一点:“甫跃辉力图表现个人世界的枯竭——他使枯竭转化为意识,变成被我们想到、认识到的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重建世界的努力。”黄平进一步将这种枯竭归咎于现代资本交换系统的压抑:“面对城市的交换系统而无法交易,不断体验着空间的压迫感,一步步向角落里退缩,途中间或吞噬着比自己更弱小的以发泄,我们称之为‘人性’的存在,就在这过程中一步步枯竭下去了吧。”“无法交易”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资本交换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腐蚀,这甚至更关涉当代意义的危机。
在小说《巨象》中,生活在自然雨林中的巨象闯入梦境,成为一个文化寓言。作为外来者的李生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被转化为与一个女人的关系,而巨象的压迫感也被具体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压力。李生曾提出结婚,女友的回复是:“结婚住出租屋?神经病!”并最终导致分手。在现代文明的外衣下,潜意识里的巨象遵循着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李生欺辱比他更弱小的小彦,正如他的前女友欺辱他一样。这是现代文明阴暗面的表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反讽。《晚宴》可视为《巨象》的姊妹篇,顾零洲与徐靓的爱情同样败给了坚硬冰冷的现实世界。《苏州夜》《饲鼠》里的生活意义已经消失殆尽,只有交易系统的欲望永动机不舍昼夜地运转。甫跃辉这里的书写,让人想到西美尔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人们甚至太轻易地就相信,能够在货币价值的形式中找到这些对象确切的、完整的等价物”,导致“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狐疑的特征、不安与不满的深刻根源”。
资本交换系统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现代性规划,不同的主体奠定了现代性的根基,现代性批判必然要追溯主体性问题。在《鱼王》自序中,甫跃辉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把自己当作天地万物的主宰……人类创造世界,人类必然是世界的主宰多么理所当然!多么无可争辩!这是我们一直深藏心底的意识,以致我们能够无视两眼所见:我们不过是世界亿万存在中的一种。”这无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诘难。《鱼王》的某些细节处,不难看出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影响痕迹,不过它们的意指却完全不同。如果说《老人与海》是一曲关于“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英雄主义的赞歌,它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力量,那么《鱼王》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清算,前者是典型的现代性叙事,后者是对现代性叙事的质疑。
主体性的反思源于它自身的内在危机,甫跃辉的一系列小说都呈现出了这种危机。《秋天的喑哑》《秋天的声音》《秋天的告别》三部“秋天”系列是同一个故事题材不同视角的叙事。这几部小说更加内化了,它们完全搁置外在的政治经济学而直逼人的内部世界。李绳与曹英互相爱慕,但谁也没有勇气表白,彼此无法沟通,李绳每次拨通电话后都一言不发,于是所谓的电话实际上是曹英的独白。在现代社会,如马歇尔·伯曼所说:“由于主观性和内在性一下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和发达,更加孤独和身不由己,沟通与对话在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电话作为现代通讯工具拉近了人与人的空间距离,但人的心灵之间壁垒森严、坚不可摧。封闭的原子式的个人因缺少“沟通与对话”,缺少“主体间性”,而只能走向“堕落的无边泥沼”和“死亡的黑暗高地”。李绳最终必然要将手中的匕首刺向屠元犀,实现他沉默后的一次性爆发。这是主体性溃败的最后仪式。除“秋天”系列外,像《动物园》《坼裂》《丢失者》等作品,无一例外地写出了存在感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虚幻。
三
顾零洲们是一群无根的漂泊者,他们被称为“外省青年”或“异乡人”。他们的困顿和迷失与这种无根状态密切相关。无根乃是经验与时间断裂的结果。生命历时性的展开过程被同质化的空间所置换,时间的皱纹被拉平,甚至被割弃,一种平面化、浅表化、匀质化、空间化的生活成为个人生活史的终点,自我与意义的深刻危机由此产生。如张颐武所说:“历史与伦理所支撑的是一个‘人’的整体构想,历史的信念的存有支持着‘人’走向更为完美未来的可能,而伦理的信念的存在则支持着‘人’对自身完整性的确认。‘人’的理想只有在历史与伦理的基本架构之中才能得以实现。”历史主义许诺的一切并未如期而至,而由历史断裂导致的伦理和意义困境却日益严重,顾零洲们因此产生双重的失落。
顾零洲们的历史和记忆与故乡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乡土经验和个人记忆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就像《动物园》里的气息妨碍了顾零洲的爱情,《饲鼠》里的老鼠影响了顾零洲的邻里关系,《丢失者》里的女人扰乱了顾零洲的生活,《巨象》里的小彦成为顾零洲打进城市的累赘,《普通话》里的方言不但是沟通的障碍,甚至关乎存在的尊严。对顾零洲们来说,融入现代都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与故乡经验和记忆诀别的过程,由此产生的阵痛似乎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自我的确立又恰恰只能在记忆和时间的连续性上才成为可能,没有记忆,就没有自我。这是顾零洲们痛苦和分裂的深刻根源。
《丢失者》这部小说很好地讲述了存在的被遗忘、记忆的断裂与身份感的迷失。有多少海漂青年不是这个时代的“丢失者”呢?打电话向顾零洲求助的与其说是陌生人,毋宁说是他生命中非常紧要的存在,对她的遗忘,即顾零洲对自身历史的遗忘。因此,所谓的“丢失”不仅指女人迷路,顾零洲丢失手机后的短暂消失,更是指顾零洲因断裂、破碎的记忆而丢失自我。手机丢失几天而没有人联系,顾零洲意识到了生活的“裂缝”,“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生活,就是用彼此相似的今天去抵消明天。时间以惊人相似的面目,取消了彼此的差别”。甫跃辉说的是用“今天去抵消明天”,其实更抵消了“昨天”,因此顾零洲们所拥有的是一种没有时间的空间化的生活。在此意义上,顾零洲寻找的不是迷路的女人,而是他迷失的自我,或者说并不存在那个真实的女人,所谓的女人,不过是他分身出的遗忘已久的另一自我,是一种被压抑的潜意识。
《动物园》亦可作如是观。顾零洲和动物园的动物一样,深陷现代文明的“铁笼”之中,但动物园的气息还能唤起他儿时的记忆和梦想。这种气息对他的女友只是嗅觉意义上的,但对顾零洲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是最本己的“根性”的东西,所以他才会执拗到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动物的世界和外面的现代都市是“互为异乡”的存在,当顾零洲站在动物园里辨识自己的窗口时,却发现难以辨认出现代化大都市中那扇“我”的窗口,因为出租屋中的“我”已异化为“非我”,如卡夫卡笔下的格雷戈尔·萨姆沙已异化为甲虫。
陈思和注意到:“在甫跃辉的小说创作里,自我异化的元素一直在牵制着他的艺术感觉。这种元素对他来说,既是致命的又很独特。”不过,甫跃辉的一些小说让我们看到,他并不止于呈现一个异化的世界,更力图找寻某种治愈和拯救的可能。他找到的是一条老路,那就是回归,或者也可以说是寻根,就像《动物园》里顾零洲最后独自回到动物园,《丢失者》里顾零洲毅然走向郊区,《普通话》里顾零洲虽离家多年,但乡音未改。回归或寻根之路实际上是自我确认之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甫跃辉的自我认同不是在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义框架里定义,他对“我是谁”的焦虑与拷问不是高加林式的获得外在承认的焦虑;此外,回归的方式也不尽相同,重返大地的怀抱以期获得救赎的可能是高加林的方式,对甫跃辉而言,他更多地是将这一切内化为意识与情感的牵系,所谓的救赎,乃是在意识门径的幽暗地带不断徘徊、回望。
四
在百年中国激进现代性的道路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然而,文学对我们的原初承诺,也许只是那些亘古不变,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愉悦与哀戚,所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四时运转,有万物生长的喜悦;“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于是“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故而难免有追怀往昔的伤感,悼惜韶光的哀怃。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富裕和繁荣许诺着诸如满意的幸福,即便如此,我们此在感受中也一直活跃着有关自身终结的认识”。这样一种宇宙人生的感悟,时与空的悲欣,是中国诗文传统的精髓,李锐在评价沈从文的《边城》时说:“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然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我认为,要谈论甫跃辉创作与传统的关系,不得不说这“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
除那些现代性批判的篇章外,甫跃辉许多小说写的正是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的感怀,正因如此,即便他的批判性作品,也显得不够峻急、尖锐。这一点常常是我们在论述甫跃辉小说时容易忽略的。他自己对此说得很明白,在创作谈《依旧温暖如初》里写出,在《散佚的族谱》中又援引道:“写小说,当然并不仅仅是讲故事。但小说若能像奶奶的故事那样,唤起一个人内心的哀戚、忧悒和恐惧,又能将之抚慰平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么?”“大多时候,回忆只能让我们感觉到,两手空空。两手空空啊!这样的时候,是一个人最脆弱、最伤感、最孤独的时候,可也是一个人最像人的时候。我们忽然摒弃了外界的烦扰,安静下来了,沉浸在往事带来的欣喜、忧戚、悔恨、怅惘之中。”
所谓的欣喜、哀戚、忧悒、悔恨、怅惘、恐惧,都不过是世间万物在时间中次第展开、凋零的歌咏。有研究者注意到甫跃辉的“动物性”,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我更愿意改用“物性”二字。不仅大量的动物成为甫跃辉小说的重要意象,植物、非生物在他笔下也收到奇妙的效果。他观照的是天地万物。万物不是外在的孤立对象,它们被纳入甫跃辉的精神视域时旋即与人类的存在休戚相关。除了振翅高飞的鹰王(《鹰王》)、无处藏身的鱼王(《鱼王》)、未曾露面的豺(《豺》《暖雪》)、庄严的大象(《动物园》)、猥琐的老鼠(《饲鼠》)、盛开的莲花(《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校园里的悬铃木(《晚宴》),就连一阵风、一场雨的咏叹,都可能激起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歌。
在《骤风》中,突如其来的大风“沿路卷起了灰尘、杂草、果皮、纸屑、塑料袋、小树枝、铁锅、水桶、糟木板、破衣烂衫……”两个小孩、一对母子、一对恋人的故事因风而起。以骤风为中心,所有的事物被激活。由气之聚合、发散而成的风,策动了我们对小孩之间的友情、母子之间的亲情,以及恋人间的爱情的伦理关怀。在气的运动和语词的运动中,令人欲说还休的大悲痛由事物裹挟而来。《惊雷》中的空间由水所包围,雨水的属阴性和降落的急切感营造了阴郁、紧迫的氛围。中学生、小青年、中年人在此特定的氛围中展开他们惨痛的故事。在《白雨》《庸常岁月》《收获日》中,雨不但孕育了生命,还是生命的终结者。我们不难记住《庸常岁月》里,玉秀在一场大雨中“孕育了她和曹万顺的第一个孩子”,因此改善了她在婆媳、邻里关系中的地位。《白雨》开篇即是:“雨下到第26天,一个老人死了。”《收获日》的两个儿子互相推脱赡养母亲乔老太的责任,乔老太下葬当天,“令人震惊的大雨就是这时遽然降落”。
意外夭折的儿童(《八月》《刻舟记》《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玻璃山》)、误入歧途的青年(《惊雷》)、失之交臂的恋人(《骤风》)、熬成婆的媳妇(《庸常岁月》)、孤苦无依的老人(《收获日》《鹰王》《白雨》),这些在“大写的历史”之外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悲欣有如千古皓月,并不因历史风云的变化而消失。甫跃辉说:“在时间的河床,世界是纷乱的泡沫。”“人在寻灯,灯在等人”,那一弯明月,“是一盏灯。光明,慈悲,照临千古与万有。此刻,有多少人正望向它,多少目光,遂有了隐秘的触碰。”这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古典诗意在当代的承接和转化。甫跃辉是个小说家,他首先或者说本质上是个诗人,他听得懂光与阴的切磋琢磨,词与物的无望追逐:“‘刻舟求剑’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很多珍贵的东西丢失了找不回来了但又不愿意就此罢休只能聊胜于无地在不相干的事物上留下个印记然后尽力寻找。”以此而论,所有的写作者,不也如同那位刻舟求剑的楚人。这样的写作姿态里有西绪福斯式的悲壮,或者借用甫跃辉自己的比喻,这是夸父追日式的写作。
甫跃辉的大多作品,通常先将各种价值、观念悬搁起来,做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的“还原”,这是一种回归生命本身的努力。这种写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当代意义的危机,激活“枯竭”世界的生机与活力?我没有多少把握——这并非对文学价值的怀疑。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精神的回归和内心的体味,都是甫跃辉自我确认的一种方式,同时呈现了汉语写作的某种可能。在此意义上,写作对甫跃辉毋宁说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拯救。——“写作是一个无力的影子,与我互相搀扶。”
(责任编辑 王 宁)
陈林,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