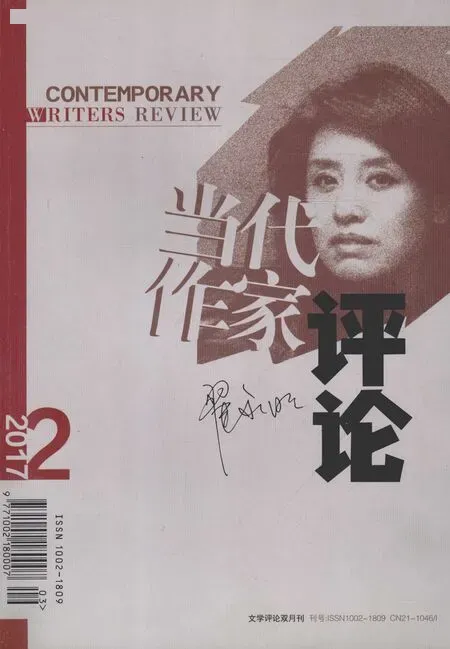《白毛女》进城与革命文艺的传播和示范
2017-11-13王秀涛
王秀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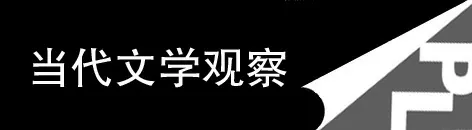
《白毛女》进城与革命文艺的传播和示范
王秀涛
《白毛女》是延安文艺的经典作品,其传播的范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逐步胜利而日益扩大。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大批城市被解放军接管,伴随着城市的接管和政权的更迭,延安文艺也随军进城,而《白毛女》无疑是被重点推广的作品之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界对《白毛女》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已经很充分,但都没有注意到接管城市与《白毛女》进城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本文意在从城市接管的历史背景下,呈现《白毛女》进城的一些历史细节,分析延安文艺经典如何在新解放区上演,并作为革命文艺的典范,为中国当代文艺的发生提供准备。
一、革命文艺进城
随着军事的逐步胜利,中共开始不断夺取、占领大城市,并对这些新解放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以军事力量来保证城市政权移交的顺利进行。接管城市是中共建国的重要步骤,也是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开端。军事接管虽然是过渡性的治理方式,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却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接收大量物质、人员,建构新秩序的同时,其中蕴含了关于新中国的设想和未来方向。对于当代文艺的建立而言,中共接管城市期间在发展方向、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为此后当代文艺的建立做了相应的准备,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文艺形态。可以说,城市接管也是当代文艺的一次预演,并提供了政策上的准备。通过新文艺的初步演练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当代文艺的方向和此后的面貌。正如叶剑英所说的,“‘军管时期’也可以给我们的共和国准备下各种政策的基础。旧有制度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将来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把他修正成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
解放战争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逐步胜利,同时也是解放区文艺逐步扩张的过程。占领城市后重建新秩序,既需要军事、政治上的保障,文艺上的宣传显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作为战斗的武器,文艺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政治、军事斗争是密不可分的,革命文艺的推广与军事胜利总是相伴而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前后,部队活动范围扩及许多城市。到城市进行政策宣传,传播解放区的文化活动,成了文工团(队)的重要任务。那时候,纵队和各师的文工团在扩大解放军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白毛女》和《王贵和李香香》进城了,《解放区的天》进城了,秧歌和腰鼓的雄壮舞姿出现在城市街道广场”。进城之前,中共就已经在文艺方面做好入城的准备和安排,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延安文艺的面貌展示给市民。譬如重庆解放后,二野六纵队文工团在重庆市青年馆剧场演出歌剧《刘胡兰》,虽然舞美、灯光仍然十分简陋,但演出“场场挤满了观众,他们被解放区文艺的新风貌所吸引,他们为刘胡兰的英勇精神所感染。演出中,剧场里静悄悄,时而听见观众抽泣声,时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口号声。戏演完了,夜也深了,可观众仍围聚在后台出口处,久久不肯离去。他们中有青年学生,有工人,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伸出热情的手,同演员们一一告别”。先锋剧团在占领保定后设立了书报阅览室,正中挂了毛主席画像,摆放了华北解放区的《人民日报》等报刊,毛主席的各种报告文章,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福贵》,贺敬之、丁毅等的《白毛女》,胡奇的《模范农家》等。“许多群众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和书籍”,有知识分子说:“写得真好,道理说得很对,让我借回去给别人看看,明天就送回来。”有学生则认为:“解放区的文章都是正经的文章,说的是事实,讲的是真理,不像国民党报纸假话连篇,逃跑叫转移,被歼还发贺电,报纸上写了许多桃色新闻,真没意思。”“骗人骗己骗不了老百姓,我们老百姓有眼睛,看看两种不同的军队,不同的文化,就什么都清楚了。像《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书,我们更爱看。八路军真好,副司令员还为这本书写序,说明你们这支军队是有文化的军队。”
接管北平、上海,同样伴随着革命文艺的传播。在北平,军管会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所有文艺活动亦着重介绍解放区情形”,“在各种机会及工厂学校中演出《赤叶河》《白毛女》等歌剧以及大秧歌剧等”。进入上海前,中共提前做了准备和安排。文工团以街头宣传为主,文工团一队复习秧歌,二队复习腰鼓,军乐队联系行军纵队。评剧团排演《小苍山》《三打祝家庄》。文工团一队在大中华唱片厂灌音,计有《解放区的天》《向解放军致敬》《军队向前进》《蒋匪军一团糟》等。三野文工团一团并全力突击排练进入上海后的晚会节目,选定了《淮海组歌》《胜利腰鼓》,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火线爱民》《支前生产》。这样的安排意在用延安文艺的经典作品来代表解放区的无产阶级文艺,“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反映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工农兵的艺术形象,用无产阶级崭新的艺术去占领上海舞台。宣传共产党,宣传解放军,宣传解放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宣传解放了的人民幸福、民主的新生活!”
上海军管会文艺处所属各室各文工团,及文协、影剧协所领导的团队,也开始用革命文艺来进行宣传工作。在短时间内,上海文艺工作团演出70次,观众达164万人,使上海市民初步接触到了解放区的艺术,在陈毅看来,老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各种文艺教育工作经验和各种艺术作品,“提供上海市的文艺教育界朋友作为求进步的参考”,“特别是歌咏、腰鼓、与东影的记录影片,对上海文艺界给了一个甚大的冲击”,有人表示,“这生动地表示了解放区人民艺术的力量,这是人民的声音”。梅兰芳、周信芳看了腰鼓后说:“这才是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结合,整齐有力而优美,值得我们学习。”
二、《白毛女》在北平和上海
在所有随军进城的文艺作品里,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白毛女》。《白毛女》自上演以来,就作为延安文艺的典范之作,成为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所倚重的重要资源。在军队中,文工团通过《白毛女》激发战士的战斗勇气和热情,在新解放区《白毛女》则成为展示解放区文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有力武器。《白毛女》是延安文艺最直接的展示,而且其表达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恰当地解释了中共解放战争的合法性。接管城市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白毛女》的上演。在合肥,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文工团演出了《白毛女》《王秀鸾》《血泪仇》《刘胡兰》和《升官图》等一些保留剧目,“根据机关干部反映,认为《白毛女》和《血泪仇》两剧,与其他已演出的各剧相比较,思想性最强”。在东北,演出最多的也是歌剧《白毛女》和《血泪仇》,这两个歌剧的演出,“成为对新解放区群众进行宣传的有力武器。同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使他们提高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而且对我军文艺工作有这样高的水平,也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羡慕”。据不完全统计,1946-1949年间,解放军部队师以上文工团(队)演出《白毛女》平均每月15场以上,观众数以千万计。
《白毛女》进入北平、上海,其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在这两个文艺最为发达、文艺工作者最为集中的地方,《白毛女》的公开上演和大力推介,无疑是对新的文艺方向的一次展示。《白毛女》在北平正式公演之前,先给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师级以上干部演出了一次,1949年2月16日晚在国民大戏院(首都电影院)演出,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当演员深夜离开戏院,“戏院门前还有一些观众在等待着演员们出来见上一面,其中有从西郊赶来的大学生,他们一再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公演?可见人们期盼《白毛女》早日与观众见面的急迫心情。”邵力子观后说:“这是一台不可多得的好戏!”声乐家盛家伦看过演出后说:“我非常激动,感到你们的方向是对的、正确的。”新民报记者王戎说:“我在蒋管区住久了,被那种腐化的糜糜之音麻木得像喝醉了酒似的。而看了你们的节目,不只是民族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内涵的战斗力,感到了艺术作品中应有的新鲜与生命。”大学生们则反映:“我到今天才看见真正的人民艺术,简直把我看痴了。”有的还写了感谢信:“今天我们获得新的、有涵养、前进战斗的艺术生命,更深地了解了你们,了解到革命工作的重要与伟大,更看到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人民为解放事业而作的艰苦斗争。”
《白毛女》在北平正式公演之前,华北大学第一文工团在3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写在〈白毛女〉上演之前》,对《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主要思想等情况进行了介绍。文章说,“北平目前广大的群众正痛恶地诅咒旧社会的封建统治,欢欣地在为新社会的光明唱着赞歌”,“共产党的文艺队伍,在中国广大的乡村里坚持斗争,10年,20年。今天,我们又回到城市里来了,我们愿意把我们在乡村里怎样工作的情形,告诉给我们的工人兄弟、学生及广大的市民,《白毛女》就算是向大家报告的一点工作吧!”文章着重强调,《白毛女》会告诉观众,“地主恶霸是如何残酷地在欺压剥削成千成万的农民,群众又是怎样进行艰苦的斗争。它表现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对照,也表现了人民的翻身”。《白毛女》公演之后,《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看了〈白毛女〉》的文章,内容是一名观众对此剧的认识,他认为白毛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中国农民迫害至为深巨,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构成了三千年历史的血腥图景,白毛女这个戏剧就用了最经济最集中的艺术手腕把它刻成了一幅缩影。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土地斗争,使这剧也跳出了历史的圈子,它已不是像过去的戏剧那样永远只是一个悲剧,叫人同情而已;它给农民指出了一条鲜明的出路,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组织起来翻身,从此以后踏上新的历史日程,永远做中国社会的主人”。因此他认为《白毛女》的优点就在于贯彻了极明确的阶级观点,自始至终贯彻了阶级斗争,贯彻了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
在不长的时间里《白毛女》在北平公演了近40场,场场爆满,观众非常踊跃。一位美国学者的亲历也验证了《白毛女》在北平演出的盛况。他在日记里写道,4月28日,“我观看了最著名的新戏《白毛女》的演出。它是由华北大学的艺术工作者剧团创作并演出的。这个半歌剧形式的戏剧是一部精心制作的作品,由四人撰写并邀请了包括20名演员和一个12人的管弦乐队。这次看戏的经历令人兴奋且难忘,虽然这部戏历时四个小时,且因为没有预订票,他必须提前一小时去剧场才能保证能买到一张票”。现场观众挤满了所有的2000个座位,甚至走廊。观众既有青年学生,也有文盲,还有“体面的绅士”。在一个小时的等待开场的时间里,一些人大唱革命歌曲。观众“情绪完全被剧情感染,在紧张的时刻,他们喊出了他们对地主的仇恨,对女英雄的劝告和对八路军到来的喜悦”。一个看上去很温和的青年人,在女英雄的同志组织她痛打地主一幕中大叫着“让她揍他!”开场前,他正读着一本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该剧在此已演出了一个多月,这在北京十分罕见。虽然该戏明天就要停止演出了,但根据剧场的上座率,再演一个月也没有问题。观看这幕戏剧的经历事实上给我一种中国革命新思想正在加强的有力证明。”
在上海,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二十军文工团自6月29日起在解放剧场连演一个月《白毛女》。有刊物专文对《白毛女》加以推荐:“在解放剧场的演出,每天早已客满,欲去观光的必须预先购票,本刊编者诚实的推荐。”文章说,《白毛女》是新型的大歌剧,有6幕32场之多,从6点半开演直到11点钟才闭幕,可是这戏情演出的紧张会使你忘记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了,忘记了一切的疲劳。因为“布景的美丽,效果的逼真,和音乐的配合,都是一流上乘的”。“全体演员的演技确是超出了上海的自认为大明星们的。”据赵景深所说,“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最流行的戏剧是《白毛女》。当时我参加文代大会,在北京不曾看到。听说有四五家剧院用各种形式来演出这个戏。我们文代的上海代表联名要求演出这个戏,结果未能实现。但因此也可以看出这戏的盛名”。
《白毛女》在上海引起了戏剧界极大的重视,“是上海戏剧工作者第一次接触到老解放区的气息,以前只有耳闻,今天却是目睹了,看了以后,除了众口齐声的赞美以后,一致地都深深地认为要加强学习”。沪剧界成立了劳军支会,以劳军的方式进行义演,8月15日和16日两天夜场在南京大戏院公演《白毛女》,解洪元任演出主任,叶志成任舞台督监。上海的艺人也深受《白毛女》的影响,以能参与《白毛女》的演出为荣。赵燕侠看了两次《白毛女》,“观后的感慨丛生,自己觉悟,演戏不是仅卖力气,应当在戏本的本身上改革,想把《白毛女》演出,赵燕侠有天才肯努力,平素唱玉堂春、六月雪一类的悲剧,还在台上真哭,至于,她饰演白毛女,要看个人的修养及体验这是不可忽略的要事。”李兰舫专程去华北观看了几次《白毛女》的演出,“回来之后,有很大的感想,看看人家艺工团每一个团员在舞台上的严肃、认真,戏班里真是惭愧弗如。就是一个农夫,也是在那里认真做戏,看看我们的龙套在舞台上的表现是什么?只是充数而已。仅仅这一点就值得作戏班的榜样,所以李兰舫对于《白毛女》他是动脑筋想准备演出时的高潮,并且希望同班的人们向人家学习。”
《白毛女》在新解放区的迅速传播,无疑显示了新的文艺潮流,市民和旧艺人的热捧当然包含了追逐审美风潮的意味,譬如有人反映苏州地区《白毛女》的演出情况时说,“虽然演出过几次,但前后不满十场,群众也只是觉得新奇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解放区,革命文艺已经成为未来的主流,代表了新的文艺方向,并借助于政治的强大的组织力量一步步主导城市文艺的格局。有观众对城市的文艺宣传工作提意见,扩大革命文艺的演出范围:“自人民文艺工作者演出《赤叶河》《白毛女》等新型歌剧以来,对市民的教育意义很大。但并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而只是在剧院中出演。其中有少数人不能深刻地接受剧情的教育,而且当出现地主行凶的场面时,他们还鼓掌来欣赏演员的演技。由于票价贵,而迫切需要新社会教育的工人及劳苦大众,却没有看的机会。所以,为了更好地提高劳苦群众的觉悟,我建议咱们的文艺工作团体轮流到各区扩大公演,或定出廉价售票办法。这样,对群众宣传教育才能达到它一定的目的。”
三、《白毛女》的移植与改编
随着《白毛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很多剧种进行了移植和改编,超过10个剧种的《白毛女》相继上演,同时还被改编成连环画、鼓词、幻灯片、皮影戏,等等。上海解放后,“上艺”、“文滨”两个剧团立即同时改编新歌剧《白毛女》。1949年8月,沪剧界几乎所有主要演员都参加演出《白毛女》。接着,“上艺”、“中艺”、“英施”、“文滨”又各自上演此剧。1951年秋,文牧、俞麟童、李智雁、莫凯、张智行、张幸之集体移植改编,“上艺”、“中艺”、“英施”、“艺华”4个剧团同时在光华、中央、九星、新光剧场上演。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民办公助的上海沪剧团携带新创作的《罗汉钱》及加工的《白毛女》赴京参加。《罗汉钱》获剧本奖,《罗汉钱》及《白毛女》双获演出奖。
东北电影制片厂将新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电影,上映后引起轰动,1951年中秋节,全国25个城市、共155家影院同时上映影片《白毛女》。据相关资料统计,一天的观众达47.8万余人,国内首轮观众数量更是高达600余万,上海就达80万,在甘肃兰州,11天连续放映了205场,观众达135327人次。
不仅在城市,《白毛女》的影响力也向周边扩散,解洪元的弟子孙介峰带了戏班,在上海的郊外引祥镇演出,“因为天气热,营业未如理想的发达,前后台吼嚷着一片的亏本声”。孙介峰立即排演了《白毛女》,“果然在营业率上起了极大的效用,三天的票子,不到一天,就被抢定一空”。他们认识到,“都市以外的农民观众,欣赏沪剧的目标也改变了,唯有多多表演与广大群众血肉相关的剧本,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风花雪月,专门演些爱情镜头的戏,将在新的时代面前,走向没落”。
戏剧界改编《白毛女》的非常多,但各个剧团之间的差异,难免出现偏差,“有的改编后不合情理,亦‘马虎’上演”。文管会认为:上海解放以来,剧艺同人竞相编演老解放区名著名剧,这是剧艺同人致力新时代文化事业的表现之一,弥足珍贵,通过这种编演来介绍老解放区的生活情况与文化成果,对于上海市民的教育作用极大,因某些剧场之编导与演员不明原著精神,草率从事,以致歪曲内容,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有投机取巧,以图借名著名剧之名欺骗观众,遂行其牟利之目的,殊属非是。因此文管会文艺处“为确保原著精神,正确的政治思想计”做了几条规定:凡将上述著作,企图改编成舞台剧表演与广播剧,滑稽戏以及评弹说唱和词者,请先取得本处之同意;其改编成之原稿,须有本处研究,予以同意后始得抄写或油印,开始排演或试播试习;经过试唱或排练成熟时,须经本处审查其彩排或试听其播唱,加以正式承认后,始得公开演出或播唱,其公演与播唱中途,如发现与本处所承认者有所不符时,本处得随时予以纠正或停止;本处同时代理与保障原著作者之经济权益;老解放区之名著名剧一律不能被同时在上海摄制电影。据文汇报报道:剧团纷纷改编解放区名剧《白毛女》上演和广播,有几家正在上演,如呈后剧院的沪剧《白毛女》,由丁荣娥、解洪元演。中央戏院的沪剧《白毛女》,由施春轩、筱文宾演。“他们的剧本和彩排文艺处审查通过和承认的。而另外几家如王山樵等广播团所广播的,新乐剧场等演出的《白毛女》,其剧本彩排和试播未经文艺处审查同意的,需先让文艺处审查过后,才能继续演和广播。若是态度严肃的,文艺处愿协助演出。”
《白毛女》也被改编成连环画,但同样存在投机问题。据统计《白毛女》连环画有17种之多,出版商“抢头奖似的,大家抓住一种两种流行的戏剧,日以继夜的,草草率率的,赶编赶绘成连环图画出版,唯恐比别人家迟了一步”。“连环画图画出版者并没有认识连环图书是教育大众的好工具之一,而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去做,却像搞一种投机事业一样,‘一窝蜂’似的你也做,我也做,谁做得快,谁就抢到钞票”,“十分之八九是抱着‘抢钞票主义’”。改编的连环画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因为要减少页数,以减轻成本,便尽力地压缩画幅与说明,于是就只能拿他们认为原著中的重要情节来绘,而删去他们认为次要的或无关紧要的;又因为眼光不同,这一个编者删去了这些段,而另一个却删去了那些段,结果,完整的《白毛女》,就有的截去了臂有的截去了腿了;另外,由于绘画者大都生活在南方都市里,不但没有到过北方,不熟悉老解放区的农民生活,也很少在南方的农民中生活过,因此,原著描写的是北方农民的生活,他们绘的却是他们自己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或从别的书本上描下来的农民生活,拿这些“貌是神非”、“七拼八凑”的东西,来给读者看,而让他们认为:哦,老解放区的农民是这样的,或者这样生活的,这样的“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还能对读者大众起教育作用吗?在有几种里面,他们认为原著中次要的或者无关紧要的,而删去的地方,却正是全书主题所在,这一删,全书没有了主题,只剩下了一副空骨骼——没有思想的一个故事罢了。
《白毛女》移植过程中的乱象表明,革命文艺进城后,虽然代表了新的文学潮流,但也面临着城市原有文艺生产机制的制约,商业投机在一定程度上对革命文艺造成了阻滞。城市文艺的原有机制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功能、职责存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革命文艺的推广和深入还面临着不小的困境。
结 语
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关于解放区文学运动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谈道:“《白毛女》《血泪仇》,为什么能够突破新剧的纪录,流行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呢?其主要原因就在:它们在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赋予了这个主题以强烈的浪漫的色彩,同时选择了群众所熟悉的所容易接受的形式”,“解放区的文艺,由于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又采取了群众熟悉的形式,对群众和干部产生了最大的动员作用与教育作用:农民和战士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之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他们愤怒地叫出‘为喜儿报仇’、‘为卫仁厚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响亮口号,有的部队还组织了‘刘胡兰复仇小组’”。第一次文代会把《白毛女》作为延安文艺的典范,被树立为代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作品,剧本《白毛女》也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作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优秀作品为当代文艺示范。无论是第一次文代会,还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选,都意在把延安文艺的经验推向全国,而《白毛女》在接管时期的大规模推广无疑是这一政策的缩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初期的城市文艺改造研究”(13CZW077)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王秀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