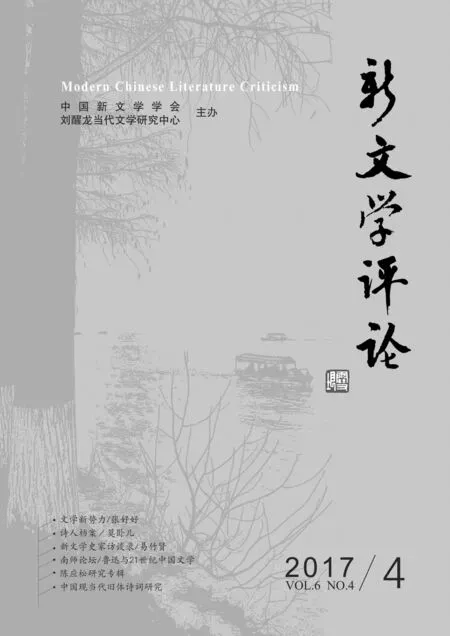论新世纪女性写作对鲁迅“女性关怀”的呼应与传承
2017-11-13岳争艳
◆ 岳争艳
在启蒙思想盛行的“五四”时代,鲁迅作为男性作家率先叙述着中国妇女虽生犹死的悲惨境遇。在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鲜活的生命被中国“吃人”礼教、罪恶的社会制度束缚压迫下的惨状,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妇女受压迫社会根源的探索与思考,对女性的关怀跃然纸上。同时,鲁迅将女性的关怀置于其“立人”的思考背景中,认为女性要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有自主的经济权,要有不依附男性独立坚强的人格,这是女性走出困境的第一步。鲁迅“妇女观”的深刻与伟大之处在于,其不仅是反封建、反压迫的重要突破口与切入点,更是站在妇女解放、人人平等的思想启蒙高度上,鲁迅所希望的是包含女性在内的全人类都能获得正当的幸福。
新世纪以来女性书写迎来盛赞一片,被当代文坛称为“她世纪的‘她写作’”。之所以被文坛称赞为“她世纪”,不仅在于女性作家书写的质量与数量俱佳,还在于新世纪以来写作姿态明显改变,在于其“完成了从‘闺房’到‘旷野’,从‘个人’到‘万物’的转变”。相比较九十年代女性“私人化”狭小书写空间而言,新世纪的女性书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囿于女性幽闭的身体感受,不再是封闭房间的“独语”,而是力求突破性别藩篱的桎梏,突出了社会性别意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大众、关注生活、了解社会,展现了女性写作的更多可能性,体现了文学的人文情怀。
方方、迟子建、王安忆、孙惠芬、葛水平、北北、潘向黎、须一瓜、林白、魏徽、乔叶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女性书写撑起新世纪文坛的半边天。在她们有关女性的书写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笔触是从人性、人的价值的角度来关照女性的精神境遇,将女性放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来关怀女性的生存困境、情感诉求以及在日益物欲化的社会女性面临新的矛盾与抉择,与“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的女性关怀精神一脉相承。本文将选择新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写作为例,从对底层妇女生存境遇的反思、对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的呼吁、对至纯至真爱情的追寻等三个方面来论述新世纪女性写作与鲁迅先生“女性关怀”启蒙话语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地方,探讨其价值与意义。从中我们既可以体悟到鲁迅先生作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其思想的深邃性、永恒性与划时代性,也可以看到当代女性书写的文学自觉,彰显了文学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
一、 对底层女性生存境遇的反思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其一生都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并以极深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怀中国社会处于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生存状况,控诉封建“吃人”礼教是导致妇女悲惨命运的根源。旧中国的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座大山的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奴隶一般的待遇,可谓是遍体鳞伤。在鲁迅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形色各异受压迫的农村妇女形象,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药》中的华大妈等。鲁迅痛斥就是“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各种罪名加在她身上”,批判所谓的女子“节烈观”“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唤醒当时社会的人们“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鲁迅先生用笔触表达着对旧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罪行最严厉的控诉,给世人以警醒。
农村女性在崭新的新世纪,不再受到类似于祥林嫂、华大妈等传统女性的社会阶级压迫,但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新时期,以农村女性为代表的底层女性面临着新的困境与压迫。中国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差距日益增大。面临日益凋敝的农村,包括女性在内的乡村人对代表金钱、富裕、美好的城市展开了他们所有的想象,伴随而来的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市流动人口比例逐渐增多,产生了诸多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安全稳定问题、乡村空巢老人问题等。当代作家们也将当前的社会问题写进小说,通过文学来反映社会问题,表达作家的思考。男性作家在小说书写中习惯将这些社会问题坚硬化、冲突化、暴力化,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与血腥暴力中凸显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相比较而言,女性作家的底层书写更加温和与内敛。在迟子建、方方、须一瓜、孙慧芬等作家笔下,她们更多是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柔和的情怀来感知社会底层女性生存之苦,不是高高在上地俯视,而是真真切切感同身受地思考,虽对女性自身弱点也有批判,但更多是温情的关怀,并在小说中揭露造成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原因,认为社会制度因素、家庭伦理因素、传统乡村封建习俗残存等共同压迫着女性。其认识问题的深刻性与尖锐性,与鲁迅对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有着内在继承性与延续性。
当代女作家迟子建曾经评价鲁迅《祝福》是讲述了祥林嫂在自尊被剥夺后“青春走向枯槁和寂灭的过程”,而她创作于2003年的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则将底层女性蒋百嫂“心中不能言的痛”表达出来,谴责造成矿区女性不幸命运的社会黑暗面。作者在谈及小说写作的灵感源泉时曾说,“中国频频发生矿难,看着电视上女人们那一张张悲伤欲绝的脸,我体味着和理解着她们的痛苦,并且探究着造成这‘不幸’的缘由”。作家在作品中的情感是克制而又冷静的,没有写痛失丈夫的女性如何终日充满哀容,而是写她对夜晚的惧怕,黑暗与夜晚对于蒋百嫂来说无疑是痛苦难熬的,一旦停电,必将失态。“蒋百嫂跺着脚哭叫着,我要电!我要电!这世道还有没有公平啊,让我一个女人呆在黑暗中!我要电,我要电啊!这世上的夜晚怎么这么黑啊!”蒋百嫂惧怕黑暗、憎恨黑暗,这黑暗是什么?是夺走蒋百嫂丈夫的矿区,是为了一己之私,视底层人命为草芥的官员,是这不公平的社会黑暗侧面……笼罩于小说全篇的都是压抑与死亡的气息,“黑雨”、“鬼故事”、“悲曲”这些都隐喻着底层民众生存环境的恶劣与不堪,作家的悲悯情怀跃然纸上,社会现实的批判诉求显而易见。有评论者称本篇小说有一种“痛彻肺腑的抵达心灵的力量”。的确如此,我们跟随作家完成了灵魂的洗礼,对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城乡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变革的区域性差异,使得在受各种传统习俗影响最为深重的中国农村,女性在性别政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仍没有多大改观,男权中心观念仍然占据家庭性别政治中的统治地位。”当代农村新女性也许不再会有祥林嫂似的被逼再婚的悲剧,不再有旧社会奴隶一般最底层的地位,但是她们遭受男权中心文化的压迫以及承受的不公平待遇依然清晰可见。当代文坛的常青树方方在小说《奔跑的火光》中将当代乡村女性的生存之艰难、命运之悲苦为我们深刻呈现,我们了解到当代乡村女性最真实的生存状况。小说中的乡村女性英芝,不喜欢读书,厌倦做农活,还整天做着白日梦,想轻轻松松赚大钱,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不安分的一面。作家将这个“既粗糙又精细”的农村女性追求理想生活愿望破灭的过程呈现出来。英芝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是不受约束、不受管制自由的生活。英芝一开始喜欢唱歌,就跟着村里年长的混混到处走场,开心快活。后来她遇到了爱情,结婚了,却遭受公婆的白眼,希望搬出去单过。但丈夫是个窝囊废,不思进取,英芝又妄想靠自己的努力赚钱盖房子,摆脱公婆的挑唆与非议,以为这样就可以一切太平,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没有一技之长的乡村女性想要挣钱谈何容易,最后她突破底线,跳起了脱衣舞。房子没盖好,却遭到丈夫棍棒与拳头殴打。英芝一把火点在了丈夫身上,了却了丈夫的生命,也燃尽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英芝的悲剧固然有自身的弱点在其中,她的不安分与轻浮是导火索,但真正的缘由是乡土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英芝靠唱歌自食其力养家糊口,还要受到公婆的冷眼。丈夫天天赌博吃喝玩乐,公婆不仅任其放纵,还教唆儿子殴打儿媳,认为英芝不守妇道。英芝想离婚,老实巴交的父母却认为在农村,离婚是丢尽脸面的事情,坚决阻止,当英芝的生路断绝时,只能走向飞蛾扑火的绝境。英芝的悲惨命运是想要改变命运而不得的农村女性命运的缩影。方方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英芝?》一文中,表达对“英芝们”命运不公的同情,“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倘出生在了一个贫困的乡下,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她要么无声无息地生死劳作都在那里,过着简单而艰辛的生活,对外部生机勃勃的世界一无所知;要么她就要为自己想要过的新生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这代价有时候比她的生命更加沉重”。方方在此道出了底层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无力感,作家对压迫在农村女性身上的男权文明礼教进行批判,引发我们对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反思。


二、 对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的呼吁



三、 对至纯至真爱情的追寻

新世纪以来,女作家书写最多的也是当下人尤其是女性对爱情的追寻,对和谐婚姻的渴望。在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当今,坚贞永恒的爱情、鲁迅与许广平式的携手同行、志趣相投和谐夫妻关系离当下人渐行渐远。如果说在鲁迅生活的时代,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想要追寻爱情,需要排除的难题首先是封建礼教和旧式家长制度约束的话,新世纪以来,阻挡女性对美好爱情追寻的是都市物质文明对人性的异化,是当下社会中人道德感的缺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匮乏等症结。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作家们通过女性特有的敏锐纤细的心灵感悟当下男女尤其是女性对纯真爱情苦苦追寻的过程,体现了女性作家对当下人性的深刻反思,对和谐两性关系的美好憧憬。


在方方的《树树皆秋色》中,作家将高级知识分子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心理描写得细致入微。华蓉作为一名单身女博导,才貌双全,收入稳定,但是人到中年,感情一直空白,华蓉不是对爱情没有憧憬和渴望,而是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对世俗的带有功利性的情感不屑一顾,渴求一份超凡脱俗的真正理想的圣洁爱情。一个陌生电话引出的神秘男子老五,让华蓉仿佛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电话里的老五幽默、机智、善解人意,虽素未谋面,但华蓉依然陷入了爱情漩涡中不能自拔,与其说华蓉是与未谋面的老五在“电话恋爱”,不如说她是与自己假想的理想男性恋爱,从而完成自己理想爱情的追寻。须一瓜笔下的陈阳里和方方笔下的华蓉其实都在追求理想两性关系:陈阳里追求的是忠贞不贰的爱情,寻爱无果,决绝地离别世间;华蓉追求的是心灵相通、精神交流的高品位爱恋,依然追寻无果,最后将自己的情感寄情于山水,通过与大自然的相融相通来弥补自己的情感缺失。

结语

注释
:①《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境遇与策略》,《山东文学》2010年第12期。
②张莉:《社会性别意识的彰显——论新世纪女性写作十年》,《文艺争鸣》2010年第8期。
③鲁迅:《关于女人》,《鲁迅全集》第5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④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⑤迟子建、萧夏林:《鲁迅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3期。
⑥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⑦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⑧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⑨鲍焕然、舒杰:《转型期小说中农村家庭女性地位的悲剧性探析》,《理论月刊》2005年第10期。
⑩方方:《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英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