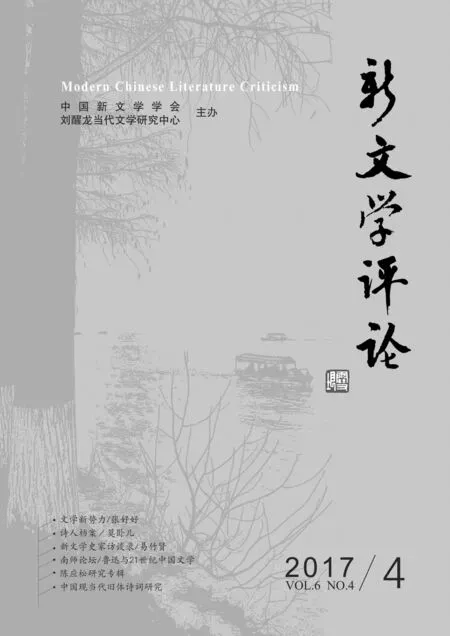活在生命的光辉与秘密中
———莫卧儿访谈
2017-11-13莫卧儿
新文学评论 2017年4期
◆ 老 贺 莫卧儿
莫卧儿
: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起初使用这个笔名,了解仅仅停留在词语的发音和大致意思上,知道它是一个印度古王朝的名字,那个朝代的艺术在历史上盛极一时,辉煌精致的泰姬陵就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这使我对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古王朝充满时间和空间上的想象。加上“mowoer”的发音我感觉很圆润,富于女性化,大约在2006年底吧,我用了这个笔名。老
贺
:什么时候与文学结缘的?莫卧儿
:应该是读小学的那些年就已经结缘了。语文课上有中外名家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课外,老师会开书单,让我们去读世界名著,自然那时不会都读得懂,但是肯定有文学启蒙的作用。再就是写观察日记,比如自己种下一颗蓖麻籽,它是怎样发芽、长叶的;一条蚕是怎样从虫卵中钻出来,直到最后吐丝作茧的。现在这个年纪回头去想,观察是一切文学的开端,有了仔细观察才有知觉材料,才能有展开想象、运用各种技巧手法的基础。然而,要严格地追溯起来,与文学的结缘恐怕更早,比如四五岁时在黑暗中想象隐藏其间之物,蹲在大石头下观察蚂蚁的生态,翻阅图文并茂的小人书,背诵儿歌……这些我不认为和文学没有关系。老
贺
:接下来想问问你个人的文学成长经历。你觉得一个作家或者诗人的形成与童年经历相关吗?重要吗?莫卧儿
:早些年并没有怎么想过这个问题,觉得走上写诗这条路是很自然的事,小学和中学有语文课熏陶,大学进了文学社,工作后自然有了文朋诗友,一直写到现在。但三十五岁以后,尤其是这几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开始思考得比较频繁了。我觉得一个作家、诗人的一生,几乎就是在复制童年的影子,你以为你走得很远了,其实你是在不断地回头,向着自己的发源地,这个发源地指心灵,也指地域。一个人的性格、看待世界的方式,大体上青少年时代就形成了,而创作需要使用的肯定是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觉得童年就像一个寓言,其中之谜有些可以试着言说,有些则无法轻易言说。老
贺
:每一个作家、诗人的成长都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谈谈你的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时候?此外还有其他写作阶段的转折性时刻吗?莫卧儿
:有一次转折非常明显,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次事件之前,我比较喜欢写在日常事务中的发现,以及沉浸在悲欢离合中的抒情;那次事件之后,我更关心写作素材的真相、真实。当时惨剧发生后,周围许多人整天沉浸在无边的哀伤之中,我渐渐觉察出一种莫名的不真实,于是背上背包去灾区行走,并不确定要干些什么,就觉得那样会踏实一些。果然,在真正的灾区所听所看、所感所知与之前的浅表理解差异巨大,真相之上覆盖了太多虚假的事件与情感。回来之后,我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实这个事件只是一个由头,这个由头牵出了一个话题,即作家、诗人的文本道德心和对世界的认知力对他的写作起着致命的关键作用。缺少了这个,你写下的永远是浮表而不是本质,是片面而不是全面,是煽情、逃避、掩盖,而不是真实、真相。你还完全可能沦落为某个阶层和势力的宣传工具。过这一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然而过不了这一关永远不配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换句话说,即便你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超高的技巧,倘若没有文本道德心和足够的认知力,写下的东西将不值一提。以上是一个显性的转折,此外还有一次隐性的带点神秘色彩的转折。在正式开始诗歌写作后的四五年间,我一直为一件事苦恼:很多生活材料都能处理了,不少修辞手法都慢慢会用了,但总不能得心应手。比如使用比喻吧,本体和喻体在诗行间都有,可惜二者在行文中总是硬邦邦的,没有交融,缺乏美感与境界。而我想要的是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的“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的状态。大概是2006年夏,有一晚在后海和朋友喝酒,半醉半醒之间突然脑海里蹦出一句“行云必经哭泣方作流水”,当时浑身一激灵,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降临了。说来也怪,那天之后的诗,我大致能处理得比较圆融了。事后总结,其实就是在思想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加之人生经历和写作经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突破了瓶颈,使诗歌写作上升了一个层面。《苏北女人》正是在这一话语场域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艺术思考,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抵抗偏执的社会现代化的文化路径。小说叙述了一个苏北村庄的农事生活,运用对称、互文等叙事策略揭示了中国农村在现代化挤压下的循环与陷落的历程,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关于古典田园的想象和当前农村境遇的书写。作品朴素单纯的农事经验世界和主要人物的精神均与古典中国田园有同构性质,并作为文化基质与“现代”形成了抵抗的张力,同时参与了“现代”进程。
老
贺
:能不能说一说影响你的书,谈两三本就可以。莫卧儿
:一本是《西藏生死书》。生死是个循环,死是终结亦是开始,了解死才能更好地活。这本书有着强大的力量,引导我调整甚至改变了生死观、世界观,给人以从善从宽的力量,使其生活在生命的秘密与光辉之中。另一本是朱光潜先生的《谈美》,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大家的深入浅出之作,理清了很多创作中易混淆的问题,比如艺术和人生的距离、艺术与游戏的区别、美感与快感的区别、创作与想象的关系等,本书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明白畅晓,充满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阅读了这本书后,对待当下诗坛的乱象种种、是非曲直,都能迎刃而解。还有一本米沃什的《诗的见证》,这本由黄灿然先生翻译的小书很晚才引进国内,它对现代主义提出的质疑与拷问、探索与预见都是具有先知性的,尤其适合当下中国现代诗的写作者阅读,能引发诸多思考,并带来个人或整体写作积极改观的可能性。老
贺
:有深刻影响过你的诗人、作家或者艺术家吗?莫卧儿
:读得比较多又被意识到对自己有影响的有保罗·策兰,他对情感和语言的节制力于我有较大的影响;特朗斯特罗姆的深度意象曾让我着迷,精读过;索德格朗的死亡意识与瑰丽想象印象深刻,但不确定是否影响了我的写作;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辛波斯卡的诗歌切入现实的角度我很欣赏;东欧作家群,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赫伯特等,接受得更多的是他们的观点,写作技巧在其次,包括国内的鲁迅、张承志类似。拉美的聂鲁达、马尔克斯等作家的想象力,日本的太宰治、川端康成等作家的物哀写作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叔本华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随笔很棒,许多观点也影响过我。艺术家基弗、欧姬芙的作品,以及宋画,我也很是欣赏。老
贺
:你的新诗集《在我的国度》与第一本诗集《当泪水遇见海水》相比,变化很大。第一本虽然语言考究,情感也很热烈,但多数还属于青春少女的心理体验;新诗集就完全不同了,进入了生命内部。无论是情感、身体、现实感受,还是日常场景都能转化成深度的生命体验,并用独特、准确、鲜明的意象表达出来,诗歌的格局、精神的宽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想请你谈谈这个变化的原因。莫卧儿
:第一本诗集《当泪水遇见海水》收录的是2000—2007年的作品,新诗集《在我的国度》收录的是2008—2015年的作品。大家很容易看出来,两本诗集的出版时间相隔了八年。八年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有很多可能改变的机会。2003年我从四川西昌去到成都,2004年又从成都来到北京。其间,工作岗位从铁路局机关到记者,再从记者到编辑。多年来远离亲人旧友,情感、工作、生活等个人问题都需要自己判断处理,并且要有承担一切责任的承受能力,自然而然人就比先前独立得多,看问题的角度、深度也有所改变。由于工作关系,在京编辑过近百种文学、历史、学术类图书,这十年的阅读量比我过去二十多年的阅读量还要大。此外认识了当代艺术各门类的工作者,并与之有过或深或浅的交流,其中有的非常优秀。这些年我渐渐有了比较宽阔的文化视野,多年的生活历练与文学经验也在写作中有深度体现,而诗歌风格由最初的细腻狭窄转变为情感与智识交融。这个过程是逐步的,但也是必然的。老
贺
:我发现你的诗与当下很多诗人不同,当下不少诗人只有语言上的想象力,但是缺少文化想象力。文化想象力是能不能通过认知与思考,对这个世界,对生存方式,对未来,对终极有新的建设与构想。你的一些广受好评的诗作《一个终生以自己为敌的人》、《布拉格丛林》、《巨兽》、《南方之忆》等,都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感受和精神符号。除了这些作品,你自己比较满意的有哪些?莫卧儿
:诗歌是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有机结合,你举出的这些诗歌相对来讲想象力的比重大一些,我也有一些偏重于生活体验的诗歌,像《南瓜》、《草丛中的河流》、《不爱你的时候》、《蒸鱼》等,诗中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情感,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老
贺
:你的不少诗歌有奇异的想象力,独特的生命体验被语言击中,在极具实验品质的语言中幻化出可感的世界。曾有人说创作到了关键的时候,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感觉,在那个状态你敢不敢往上,你敢不敢有担当最考验人。请谈谈你心目中的诗歌先锋和先锋诗歌。莫卧儿
:我理解的诗歌先锋,与年龄无关,与精神状态有关,必须对新鲜事物保持永远的探索欲,敢于求新;与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无关,与精神的自由有关;与姿态的高低无关,与承担文本的责任心有关。先锋诗歌,我的理解是诗歌中必须有体验与语言的双重险境,这种险境是指你创造了前人没有的语言方式、意象,完全有可能忍受不被理解,甚至被诟病、指责。当然,你的创造必须经得起深刻度、想象力、张力等诗歌硬件标准的检验。戴着镣铐跳舞也跳得好,这才是本事,而绝不是把前人的文本一一否定,不是搞搞口语诗、写写下半身就先锋了哈。老
贺
:先锋首先与自由相关,不是某种形式代表先锋。另外我觉得先锋主要是面对个体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原创,原创就是先锋,你觉得呢?莫卧儿
:对,超越自己。一点小欣慰,多年来我大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一首诗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新颖的意象,宁愿放下,过段时间再来写。如果一口气写个七八年,除了语言简练了些精致了些,没有太大变化,没有质的飞跃,“思而不学则殆”。这也可以理解成诗人的文本道德之一,对自己如何要求,决定了你最终达到的高度。老
贺
:我发现,你有不少诗歌都提及了死亡,比如《一个终生以自己为敌的人》中“那个一分钟前细细描眉一分钟后爱上死亡的人”,《大于》中“绝望大于傲慢爱情大于死亡”,《这个秋天》中“每个夜晚都有流星欢笑着扑向死亡”,等等。请问你是有过死亡这样的经历呢,还是另有所指?莫卧儿
:死亡在这些地方出现,更多是一种隐喻。隐喻什么呢?有失望,有终结,有消逝,还有别的。为什么用死亡来隐喻呢?因为死亡是生命的结束,但从宗教的观点来说死亡同时又是另一个崭新世界的开端,寓意深刻,张力很大。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诗人在选择词语的时候,会有意识地选择最能表达你意思的有终极感或者说有极致感的词语,这是一种对词语的敏感。像我要表达“一天”,会选择从“黑夜”到“白昼”这样的词,中间的灰色地带就暂时忽略。一语命中,快速抵达,是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点。关于死亡,我需要多说几句。刚才你提到的诗集《在我的国度》收入的是2008—2015年的诗歌精选,也就是说2016、2017年的作品并未收入,而在这两年中,我自己亲身经历了一次濒临死亡的过程,于是写下了真正有死亡意识的诗歌《女入殓师》、《猫眼耳坠》、《我和死亡有过两次交谈》等。曾经有人说,能把情诗写好的人是优秀诗人,我补充一句:能把艳诗和死亡诗写好的才是优秀诗人。为什么呢?因为艳诗写情欲,使人飞升到无限高处;而死亡引领人下沉到无限低的地方,比如深渊、地心。当你的笔端纵横天地两极驾驭虚空,中间状态的那些日常生活,状物和叙事的描摹技艺应该不会太难哈。
老
贺
:即便都处理死亡题材,不同的诗人也是不一样的。有死亡倾向的诗人,像顾城、海子,他们笔下的死亡都有锋利的一面,但是你笔下的死亡给人深厚宽大之感,你的诗歌实际上指向一种存在。比如《诗人》中“吹一个巨大的肥皂泡,能最快看到彻底的死亡”,《妙峰在不远处》中“有些什么藏在视野之外,远远地尚未出生”。这种指向和当下很多诗人的指向不同,他们的诗更多指向生活和现实,而你这种具有终极存在意义的诗歌写作,类似宗教,请问你是否有宗教背景呢?莫卧儿
:我没有正式的宗教背景,但是作为一个有道德心的严肃的写作者,在无数次写作过程中,都会追问、拷问自己作品的终极意义和揭示的世界本质。这与当下中国人信奉宗教的过程其实有点像。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一生下来就接受洗礼这种宗教仪式的,多半是在之后的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事件,依靠自身的认知、内心力量无法得以解决,于是开始寻找一种可以救赎、解脱的方式,很多人找到了宗教,开始修炼内心。这种找寻、信奉与修炼的过程和我写作的不同是,我是自觉的,他们是被动的。有关宗教的书我倒是看过不少,佛教、道教、基督教都有,现在有一些经书我也会阅读。老
贺
:能否简单说说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莫卧儿
:即便现代诗用不着押韵,诗歌还是存在内在的节奏,有经验的写作者或者读者阅读中能感觉得到诗歌内部或舒缓或急促或迂回或直线的节奏,这和音乐是相通的;而一首诗的肌理又和绘画互通款曲,诗歌也有留白、工笔、写意等技术;说到雕塑,诗行中词语的堆叠、铺陈排比、删减可一样也不比雕塑少;要是说到摄影,诗歌也有画面感,至于是抽象还是写实,诗人说了算,与电影的联系有点像是一个诗歌画面变成一组诗歌画面的感觉。老
贺
:写作至今,你有哪些诗集以及其他文学作品问世?近年写作有什么计划?莫卧儿
:2005年,有一本由汉语诗歌资料馆整理印刷的诗集,只是印刷成册,没有出版。那是我初学写诗的一些习作,现在回过头去看比较幼稚,但还是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当泪水遇见海水》。2011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女蜂》(中国商业出版社),反响还不错。今年出版的诗集《在我的国度》(长江文艺出版社),是我个人比较看重的一部诗集,经过多年的体验、阅读、写作训练,在这部诗集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风格。对于正式出版的诗集,我都是比较慎重的,之前两部诗集相隔了整整八年。如今步入中年,生活与写作渐趋稳定,接下来我打算加快步伐,明年起大约两三年出版一本诗集吧。老
贺
:在现实生活中,诗歌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