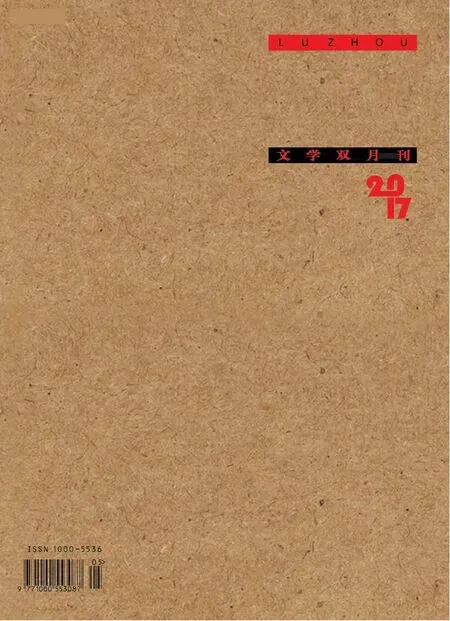王洛宾与韩生元
2017-11-13方惠民
方惠民
王洛宾与韩生元
方惠民
2016年是“著名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先生逝世20周年,2017年元旦是“新疆花儿”开创者和集大成者韩生元先生无常6周年。二十世纪50、70、80和90年代,王洛宾曾当面向韩生元学艺,两人一见如故,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花儿”是王洛宾人生转折点
2016年12月17日,我们几个参加中国文联东西部地县文联培训班的学员从兰州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经过的会宁、静宁、西吉等县镇、乡村,专程拜访将台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碑后,来到西北交通枢纽六盘山,准备登临山顶,领略毛泽东“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豪情。车子从福银高速拐到一条县乡道路不久,我们看到转弯处竖着一个“隧道封闭请绕行”的牌子。312国道封闭了,上不了山,怎么走?正犹豫间,向导兼驾驶员的固原摄协叶鹏举秘书长说:“马上就到和尚鋪了,到前面看看情况,再定咋走!”
“是五朵梅与王洛宾相遇的那个和尚鋪吗?”因那天起得很早感觉疲倦的我,被这个意外的惊喜刺激得睡意尽消。
“就是呀!六盘山下第一村和尚铺。”
说话间,车子驶近不深的一条河谷,烟雾濛濛中一个不大的村落进入眼帘。站在连接312国道的一座桥上望去,一条小河流经村子中央,各家各户簇新的红砖瓦房高低错落,有着与关中一带农村传统平房建筑相似的风格;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家畜家禽以及狗吠声也听不到,这就是传说中的丝路古村和尚鋪?其他人继续坐车往前走,我提着相机进入村子,想寻访一下当年五朵梅车马店的位置。许多人家大门紧闭,生火冒烟的也不多。敲门,不应。好容易等到有个中年男子从巷口走过来,我赶紧上前打问,这个行色匆匆的村民告诉我:“冬天六盘山景区封山,交通不便,旅游区也没生意,许多村民都外出打工或做买卖去了!几十年了,村子换了几茬子人,原来五朵梅的车马店早没有了。听老人说,就在河边靠山的地方。究竟在哪儿,我也说不上,新修的五朵梅客栈就在桥那边的王洛宾文化园里边。”我有点失望,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想想看,快80年了,原来的车马店怎么可能保留?
去往王洛宾文化园的路上,远远看到一个背着一大捆木柴的老者走过来,我赶紧过去问候,打听王洛宾和五朵梅的事。老者说:“王洛宾,额(我)知道呢,民歌王么,在这哒遇上了五朵梅了。我们这六盘山的人,都知道这个事!纪念馆开张的那天,王洛宾儿子也来了,热闹地很!”陪同我们的固原市文联郭宁副主席介绍说,和尚铺的文化园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王洛宾文化园,2010年向公众全面开放,成为著名文化胜景。因为和王海成有过几次交际,我用微信把现场拍的照片发给他,正在北京的海成先生问参观王洛宾文化园没有?我告诉他冬季闭馆了。他说留下遗憾好,不然哪有下一次。
同行者纷纷在“王洛宾拜师五朵梅”雕像前合影。我看着手持记谱本的青年王洛宾和身着传统回族服饰漫着花儿的美丽女子五朵梅,心情既兴奋又惆怅。原来王洛宾的西部民歌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启的,真是不虚此行!
1938年4月,参加西北抗敌服务团的王洛宾和萧军、塞克等人自西安至兰州途中来到了六盘山脚下,向来干旱少雨的六盘山在那几天却下起了连绵大雨。王洛宾一行只好住进了“五朵梅”开的车马店。一天夜里,在滂沱的雨声中,他听到了女掌柜“五朵梅”唱起“花儿”:“走咧走咧者,越哟的远(哈)了,眼泪花儿飘满了,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王洛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五朵梅演唱的“花儿”曲调抑扬顿挫,歌词自然纯朴,夹带着大西北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了他一种全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自己在北师大的课堂里从未接触过的。晚上,王洛宾躺在床铺上,颤抖着手记下了这首《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的曲谱,成为第一个谱录传播花儿的现代音乐家。王洛宾被五朵梅的花儿留住了,在五朵梅客栈多住了两天。谁也不会想到,一次在车马店和女老板“五朵梅”的邂逅,一首来自六盘山的“花儿”,下定了王洛宾前往大西北去搜集民歌的决心。
由于种种原因,王洛宾先生再也没有机会重返六盘山,再也没有听到五朵梅的“花儿”。但是关于五朵梅和她的“花儿”却在当地流传着。
韩生元开创风搅雪式“新疆花儿”
1938年,17岁的韩生元刚刚从战乱初定的南疆回到迪化,辗转来到乾德县。1934年初的呼图壁,韩生元的恩师和引路人、教他6年“花儿”的著名“花儿”歌手马长贵因急病无常了。失去了相依为命的马爷爷,流落到迪化、昌吉一带的13岁流浪儿韩生元被第二次进疆的马仲英部收容,在马虎山旅当了一名马夫。盛马大战之后,马仲英流亡苏联,马虎山代理36师师长,率部从喀什移驻和田。在南疆3年,少年韩生元经常跟着军需官到当地的巴扎、街巷给团部买物资,交往了很多穷苦的维吾尔人做朋友。具有很高语言天赋的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还学会了不少的维吾尔民歌,他用从马爷爷那里学来的“河湟花儿”,夹杂着维吾尔语,在各种场合下演唱民歌,军营里的各族官兵都喜欢他。冶团长一高兴了就喊:“尕穆合买,来一个‘河州三令’。”正当这个懵懂少年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军旅生活,畅游在民歌海洋的时候,驻和田、喀什的马虎山、麻木提发动了第二次盛马大战。这场发生在1937年春夏之交、震惊全疆的喀什之乱,以苏联帮助下的盛世才省军全胜、36师完败而告终。部队一夜之间解散,士兵或逃亡或被杀。幸运的韩生元离开部队后,一路躲避盛世才省军抓兵,一路唱着“花儿”,唱着维吾尔民歌,问着道路,一直朝北走。为了混口饭吃,他把汉语和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混在一起唱新疆曲子,唱自编的“花儿”。这种多语言多语种演唱的“花儿”风趣诙谐,生动活泼,接地气。当地人舍不得他走,管他吃、管他喝,有的帮他找事做,有的极力挽留他,还有的要招他当上门女婿。但韩生元思念故土和亲人,尽管已经是个孤儿,还是想回到祖父韩忠、父亲韩德奎、养父马长贵生活过的地方。在维吾尔族朋友、柯尔克孜族老乡的帮助下,他从叶城、英吉沙、喀什、巴楚、阿克苏、焉耆等地方流浪、游历大半年,终于回到省城迪化,之后又跟着呼图壁老乡到了乾德县的马场湖村,扛活为生。
后来人们把这种多语言交织演唱的“花儿”称作“风搅雪”。韩生元以后又学会了哈萨克语和哈萨克族铁尔麦。他不停地从各民族民歌演唱艺术的精髓中汲取营养,借鉴了维吾尔族音乐的快节奏,吸收了哈萨克族阿肯弹唱的幽默,形成了演唱中少拖腔、曲调中少花音、唱词和曲调铿锵有力、洒脱自如的独特风格,创造了融合新疆各民族艺术精华的新疆“花儿”。
初会在自治区成立大庆演出现场
1953年10月1日,新疆省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韩生元作为“民间歌手”代表参加了大会。接到开会的通知,他兴奋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想着自己一个“泥腿子”“要要吃”,成了“民间歌手”,当了代表,“花儿”要登上大雅之堂了;又琢磨着大会上给代表们唱哪些“花儿”,填些什么新词。为了参加这次盛会,哑巴妻子特意为他做了一件新黑卡叽布对襟夹上衣、一条新蓝布裤子和一双新布鞋。会议进行了10天,其间,32岁的“民间歌手”韩生元可以说是见人就唱,大会小会都唱,一休息就唱,为代表们唱了几十首自己编的“花儿”。闭幕式文艺晚会上,当主持人介绍迪化专区乾德县代表韩生元出场时,这位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的回族青年大方地走到舞台中央,手抚前胸,道了一声萨拉姆,面对台下鞠了三个躬,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只见韩生元用深沉宽厚的嗓音唱道:
解放的“花儿”劲头大,泥腿子有了文化,
第一次参加文代会,穷苦人心里乐开了花。
文代会上摆擂台,诗人歌手走上来。
演出结束,韩生元被安排在包尔汉主席跟前合影。从此,韩生元成为新疆登上大剧院大舞台唱“花儿”的第一人。
此时,原本被军区内定参加新疆首届文代会的王洛宾却与早就想见面的大名鼎鼎的“民间歌手”韩生元失之交臂。
王洛宾1949年从青海马步芳军队中起义、参军,随一兵团进疆。王震、马寒冰等领导重视人才,当年12月就任命他为新疆军区文艺科长。如鱼得水的王洛宾深深扎入新疆各民族民间音乐的海洋,改编、创作了《我不愿擦去鞋上的泥》《在银色的月光下》《哪里来的骆驼队(沙里红巴)》等多首新疆民歌。1953年新疆首届文代会召开的时候,王洛宾却因违反军纪长期逾假不归,被新疆军区军法处判处两年劳役,还在服役期间。王洛宾是多么渴望在文代会与各族各界文艺工作者倾心交流,听说乾德县的回族歌手韩生元能用多种语言演唱民歌、“花儿”,如果能当面请教,该有多好。然而,命运却跟王洛宾开了个玩笑,因为自己的随性,被判罚劳役,失去爱妻,3个儿子无人照顾,错过首次文代会,错过向韩生元学歌的机会。
服劳役期间,王洛宾被独臂将军左齐带到二军文工团,以监督使用的形式担任音乐教员、创作员,经常有机会到喀什、和田一带采风。到了南疆,王洛宾如同鸟儿飞进了林子,除了完成教学,他把时间都用在了采集民歌上。如果不是遭遇这样的突变,他不会有机会如此真实地感受新疆民歌,特别是南疆维吾尔民歌,也没有机会一头扎到生活的最基层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955年9月自治区成立前夕,文艺界承担了许多演出活动,王洛宾作为部队音乐工作者参加大庆节目的创编。在昌吉回族自治州选送的农牧民文艺调演节目现场,他亲耳听到了韩生元演唱的赞颂自治区成立的新编“花儿”,忙问旁边的观众,这个大个子的歌手是谁?当听到这就是“花儿”唱家子韩生元时,王洛宾激动地一边鼓掌一边站起身来,向韩生元挥手致意。演出结束后,他追到后台去找韩生元:
“韩兄,久仰啊,终于见到你了,我是王洛宾。我要跟你学民歌,学‘花儿’啊。”
韩生元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儿不高但英姿挺拔、双目炯炯有神,着55式校官服的军官,两只大手紧紧攥住王洛宾的手:“我说首长,你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年长我几岁,我该喊你大哥才对。”
王洛宾说:“你能现编现唱,出口成章,还懂几门少数民族语言,我自愧不如啊。”
两人寒暄着,谈论着,相见恨晚。这时军区政治部通讯员来叫王洛宾去参加创作会议,王洛宾拉着韩生元的手,不舍地说:“兄弟,你如果识字的话,成就应该在我之上,你可不要荒废了。我以后还要找你学歌。”王洛宾曾经告诉他的学生:“韩生元是一位农民诗人,他的诗情画意般的民歌,铭刻在了我的心间。”5年后,王洛宾又因历史问题被判刑,关进新疆第一监狱长达15年。王洛宾想学“花儿”的愿望,再次被阻隔。谁也没有想到,直到20年后,二人才终于得见。
二十年后重逢在马场湖
1976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晴空万里无云。烈日下,韩生元正在红旗公社马场湖大队老龙河东岸的水稻地边上看庄稼。他前几年眼睛患了白内障,又有青光眼,视力越来越不好,不能参加集体劳动,队上就给他安排了看庄稼的活,一天算8个工分,算是照顾。无风的大热天,汗水湿透了他的夹衫,尽管口干舌燥,韩生元仍然用鼻子哼着水红花令,站在田埂上,眨巴着眼望着北去的老龙河出神。这时,10岁的二儿子不拉子突然在河西喊了起来:“阿大,家里来了两个人,阿妈让你赶快回呢。”韩生元跨进院门,看到门口放着辆自行车,槐树底下,小板凳上坐着两个人,一位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一位是头戴劳动帽、身穿褪色蓝中山装的老者。韩生元道了一声赛俩目,小伙子赶紧起身,自报家门:“韩叔,我是红旗公社宣传队的张世才,这位是王……”
这时老者站了起来,一把握住韩生元的手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老王,王洛宾呀。”
“哎呀,王老师,你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我这个眼睛不好,看人都是黑影子多。”韩生元眯着眼端详着王洛宾的花白胡子,感慨着:“老哥,几十年了,你我都老了不少。听说你蹲了笆篱子,可苦了你了。”
“我蹲笆篱子也没有忘记音乐、放弃写歌。这不是刚刚出来,就找你来了嘛。”
一席话说得韩生元心里热乎乎的。急忙招呼客人坐到小方桌前,打着手势让哑巴妻子马秀芳拿黑砖茶,找冰糖,泡糖叶子。韩生元虽然是个唱家子、舞家子,但“花儿”换不来粮食,七个子女嗷嗷待哺,家里一年四季为不饿肚子而奔命,算是全大队最穷的一户。家里珍藏的一块40公分长的大茯茶砖,是“文革”前作曲家田歌来学莲花落的时候送的,地道的安化边销黑茶,韩生元把这茶叶锁在柜里十几年,一直舍不得喝,平时也不让孩子们动。王洛宾一听韩生元要拿黑茶招待,急忙阻止:
“兄弟,我一个特赦战犯、劳改释放犯人,就是过来向你学歌,喝开水就行了。”
韩生元说:“老哥你说撒呢?在我这没有劳改犯,只有唱歌的,只有好朋友,何况你是个大音乐家,我们西北的回汉各民族都爱听你的歌呀。老回回有一句话:‘朋友来了,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你们来看我,就是最尊贵的客人。”说着轻轻撕掉茶砖外层的牛皮纸,拿来一把英吉沙小刀,眯缝着眼睛,一层一层慢慢撬下茶叶块,放进一个铜壶里冲泡,妻子马秀芳从柜里取出几颗冰糖,放进瓷碗里。不一会儿,黑中带红、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黑砖茶端到客人面前。因为中午在米泉县文艺宣传队被张世才、赵光鸣、鲍维垣等队员招待吃了羊肉抓饭,喝了河南产的红薯干酒和不知从哪搞来的白兰地,口渴得厉害,两个人端起瓷碗连嘘带喝,很快干了两碗。
王洛宾已经很久没有喝到这么香的茶了,解放前在马步芳军队天天喝盖碗子,也不觉得香甜到哪儿去。此一时彼一时,自己现在生活无着,盲流一样,前途未卜。韩生元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有家有舍,可以自由歌唱,心灵不受约束,让人羡慕。好在生命还在,歌还在,这是最重要的。为了自己挚爱的音乐,一切的苦难和屈辱都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轻轻打着拍子,唱起了自己五十年代在南疆军区采风创作的歌曲《沙枣花儿香》。韩生元听到王老师先唱了起来,也站起身,清清嗓子,眨巴着眯缝眼,连唱了《花花尕妹》《三十三担荞麦令》《麻青稞令》《送大哥令》等几首自己编创的“花儿”,年轻的宣传队员张世才情不自禁地跳起回族的踏脚舞来,王洛宾也脱下帽子,起身跟着走起了回族舞蹈的步子,晃着头,摇着身子,边跳边笑,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
人们啊,要把不快乐的事情全忘掉,才能让新的快乐进来。
歇了一会,喝了几口糖茶,韩生元把哈密、吐鲁番民歌《沙里洪巴》用维汉语间杂着唱了两遍,这是王洛宾20年前约定的,一直想听的。唱到“烂皮鞋、炕上坐”等少儿不宜的歌词,韩生元自己先笑起来,解释说后面还有几段呢,现在不让唱了。里面的衬词“沙里洪巴”是维吾尔语“夏日木胡玛来”的音变,思念故乡的意思,“亚里姆”有爱人、亲爱的朋友几种意思。
《沙里洪巴》(根据韩生元演唱录音记词)
那里来的骆驼客,哎亚里姆嘿呀嘿,
哈密来的骆驼客,夏日木胡玛来呀嘿。
骆驼驮的个啥东西,哎亚里姆嘿呀嘿,
花椒胡椒姜皮子,夏日木胡玛来。
花椒姜皮子啥价钱,哎亚里姆嘿呀嘿,
一两二钱三分三,夏日木胡玛来。
门前挂的烂皮鞋(hai),哎亚里姆嘿呀嘿,
有钱没钱都进来,夏日木胡玛来。
有钱的老爷炕上坐,哎亚里姆嘿呀嘿,
没钱的老爷坐地下,夏日木胡玛来。
有钱的老爷你天天来,哎亚里姆嘿呀嘿,
没钱的老爷你三天来,夏日木胡玛来。
王洛宾赶快用一张纸记了下来,恍然大悟地说:“这后面肯定还有更黄的,过去拉骆驼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嘛,打情骂俏调侃招妓都可以即兴编唱。《哪里来的骆驼客》这个民间小调在北方流传了几百年,我小时候在北京就听几个维吾尔人唱过,只是听不懂。1938年在兰州听人唱过汉语版的,当时便记录下来。1949年进疆时在哈密又搜集到这首歌的别的版本,衬词包含了几个民族的语言。后来我重新填词编曲,改名为献给地质队员之歌——《哪里来的骆驼队》。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说我的歌是抄他们的老歌,还拐了调,让他们都听不懂,其实是有的歌词发音不准,走了味道了。我的歌主要是唱给懂汉语的人们听的,我根据西部少数民族民歌改编的歌曲,华人世界都喜欢听。”
王洛宾意犹未尽地对韩生元说:“韩老师我还想听几个原版的民语歌,听曲子。”韩生元又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唱了《马车夫之歌》《挖渠歌》《黑眼睛的姑娘》《燕子》《沙女与冬布拉》《百灵鸟》《哭嫁歌》等民歌,用西北方言演唱了《张连卖布》《李元贵担水》几个传统新疆曲子剧。
太阳西斜,王洛宾生怕韩生元一家为准备客饭作难,借口晚上要赶回县城排练节目,起身告辞。韩生元看他们的确有事,就没有再留。临走时,王洛宾面向韩生元和妻子儿女连鞠三个躬,一再道谢。
为了弄清多种版本的《沙里洪巴》,笔者特意向作曲家、木卡姆研究专家马成翔求证。马成翔先生说这首歌曲是流传在哈密、吐鲁番等地的一首民间歌曲,原作《夏日木胡玛来》,是维吾尔古典音乐《哈密木卡姆》第五部《胡普提木卡姆》第一分章第十三曲。解放前在骆驼客中比较流行,曾称为《骆驼客》。新疆音乐人赵松崎把《沙里洪巴》改编为现代“花儿”三声部民间说唱版,以西北民间“袖笼交易”为素材展现丝路古道上浓郁的民间贸易生活画卷,融进了回、维吾尔、汉族(新疆曲子)的音乐元素,使用了“沙里洪巴嗨嗨嗨”的衬语,沙漠中遥远驼队的声影,夹杂了维吾尔语、蒙古语的叫卖声,使得音乐更有情趣,深得百姓喜爱。
王洛宾的学生,原吐鲁番市文化馆馆长张世才告诉笔者,王洛宾是一个“善良的老头儿”,为人从不设防,对谁都以诚相待,重获自由不久,见谁都特别亲,对谁都特别和善。1975年5月王洛宾从新疆第一监狱刑满释放,没有单位接收,没有户口,无处安家,监狱就安排他去了乌鲁木齐河滩西边的东戈壁农场新生队,可以参加劳动,也可以自由行动。一天,第一监狱二分监区区队长的外甥、下乡知青张世才来看望王洛宾。张世才热爱文艺,小时候就喜欢王洛宾的歌,因为有舅舅的关照,他去监狱看过王洛宾几次,还跟王洛宾请教音乐上的问题。看到王洛宾出狱后没多少事做,就问他能不能给米泉县的知青宣传队排练节目,还想拜他为师,王洛宾马上就答应了。过了几天,王洛宾花30元买了一辆狱友的飞鸽牌旧自行车,修了修,就骑着来到了古牧地中路县影剧院的米泉县知青文艺宣传队,为他们作曲,排节目。
张世才说,王洛宾虽然自由了,但坏分子的帽子没有摘,在新生队的时候,为了糊口,曾经骑自行车去乌拉泊军火库干过活,去50公里外的芨芨槽子化肥厂打杂看工地,这种劳动不能让他高兴起来,因为被剥夺政治权利,心情是苦涩的。王洛宾为宣传队写了歌曲《穆萨明天去北京》,后来参加了昌吉州、自治区文艺汇演,还得了奖。张世才后来被抽调到昌吉州造纸厂工作,王洛宾还为他们写了一首《造纸工人之歌》。宣传队一帮子男女知青,精力充沛,活力十足,既能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又能搞来肉和酒,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月,这对王洛宾吸引力太大了。他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来,认真给队员们教歌。到1975年冬天,他正式收张世才为徒。拜师宴上,给在场的宣传队员们唱了很多自己写的歌。十几年没有这样畅饮了,那天,王洛宾喝醉了。
过了大半年,从南郊看工地回来的王洛宾又骑着自行车来宣传队,打听“花儿”歌手韩生元。宣传队的青年因为和韩生元一起排过节目,基本上都熟悉。吃过饭,就由张世才陪王洛宾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去了离县城8公里的马场湖。张世才回忆说,当年自己准备骑车驮着王洛宾下红旗公社,但王老执意不让,硬要他这个小伙子骑坐在后座上,一路小下坡,风驰电掣地就到了,有几段直路上王老还双手撒把了呢。
九十年代匆匆一面
1990年7月中旬,米泉县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暨阿肯弹唱会在哈熊沟举行。王洛宾听说米泉县委特邀他参加,爽快地答应了。他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六十、七十年代落难的时候,米泉县的人不止一次地帮助过自己,所以这个草原盛会一定要来。开幕式上,观看了刁羊、赛马、摔跤、姑娘追及阿依特斯表演后,王洛宾问身边的文化馆长焦江,怎么没有看到韩生元,他应该来漫个“花儿”呀。焦江告诉王洛宾,这个开幕式以哈萨克族演员为主,没有通知韩生元。王洛宾不以为然地大声说道,韩生元会唱哈萨克语歌儿呀。又对时任县委书记熊辉银说,米泉县的“花儿”很有特色,很有艺术价值,要好好收集整理,让韩生元这些艺人好好发挥一下。焦江拿出《韩生元“花儿”专辑》征求意见稿让王洛宾过目,王洛宾一看整理了韩生元的60多首“花儿”,一些记谱也很规范,很肯定地说,没有问题,可以出书。
开幕式结束,王洛宾没有参加参观活动,让司机径直把车开到县文化馆,找到业余作曲周柏林,让他陪着去一趟韩生元家。周柏林80年代中期曾经几次坐公交车背着米泉大米找王洛宾看谱稿,王洛宾感动地说,没有想到基层文化馆的群众文化干事这么执着。随即帮周柏林改了稿子,并且推荐到北京的一个歌曲类刊物发表,两人也成了忘年交。
午后,王洛宾带着自己特意购买的茶叶、方糖、布料、毛毯等礼品赶到韩生元家。院里静悄悄的,两间土坯房的门紧闭着,大槐树下的小菜园里,辣子茄子西红柿豆角等蔬菜各自成行成畦,长势喜人。难道韩家人出门了?
这时,韩家13岁的外孙阿丹从外面进来,一看来了客人,进到房里喊了起来:“阿爷,来客了,一辆军车,3个人。”一会儿工夫,已经双目失明,戴着墨镜的韩生元穿着自己外出演出才穿的黑色中山装,拄着拐杖,在孙子的引领下走出门:“安赛俩目而来空,你们是谁呀,都好着呢吧?”周柏林走上前去,大声说:“韩老,我是文化馆小周,王洛宾老师看你来了。”韩生元一听是王洛宾,急忙往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来寻找王洛宾的手。此时的王洛宾,看到双眼已瞎、微微驼背的韩生元,想到自己须发皆白,不禁悲伤起来,落下泪来,拉着韩生元的手,使劲摇晃着,说不出话来。韩生元让孙子阿丹去抱西瓜切了吃,说道:“王老师,现在是斋月,我和你弟其家(弟媳妇)都封着斋,天热,中午乏得就想睡觉,见谅啊。你们吃瓜。”
王洛宾连忙说:“我们不渴。韩兄弟,一晃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我这次带来了砖头录音机,让咱们来几段切磋切磋。”
“实在抱歉,王老师,我们白天封斋不能娱乐、唱歌。你们今天就站哈(住下),晚上开斋以后我们切磋。这会儿喝些茶,休息一哈,你看咋样?”
王洛宾在西北呆了几十年,对回族的习俗非常了解。“是这样啊,今天打搅了,我们先告辞,开斋节以后再来。”
韩生元一家不便挽留,送客人上车返回了。
此后,两位传歌者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卞之琳教授称赞道:“自古代西域音乐在汉唐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原的上千年之后,现代新疆音乐在抗战和解放初期又一次大量流入内地、海外,起桥梁作用的人,他的名字叫王洛宾。”著名音乐家、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坦言:“王洛宾的西部少数民族特色民歌大气磅礴、苍凉而内热。他是中国音乐界持久深入最基层的人之一,他走到了生活的最深处。”
韩生元虽然未上过学,可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的作词编曲水平,显示出他非凡的艺术才能。他7岁开始学“花儿”,90岁去世,传承新疆花儿80余年,代表作品经整理和记录的有1000多首。
王洛宾曾经对韩生元说:“我是把新疆多元民族音乐艺术介绍出去,让更多的华人了解新疆;而你本身就是新疆多元文化的代表,你能用多种语言演绎民歌、传承‘花儿’,生命力更强,你是个伟大的歌者。”王洛宾晚年充实而忙碌,满载着荣誉和幸福。韩生元2008年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于2011年1月1日无疾而终,他终生没有离开过新疆。
2016年12月28日,笔者应韩生元家人之邀,参加了韩老归真6周年“尔麦里”纪念活动,同日,也是王洛宾诞辰102周年。不知是否机缘巧合。
仅以此文纪念两位伟大的世纪传歌者。
责任编辑 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