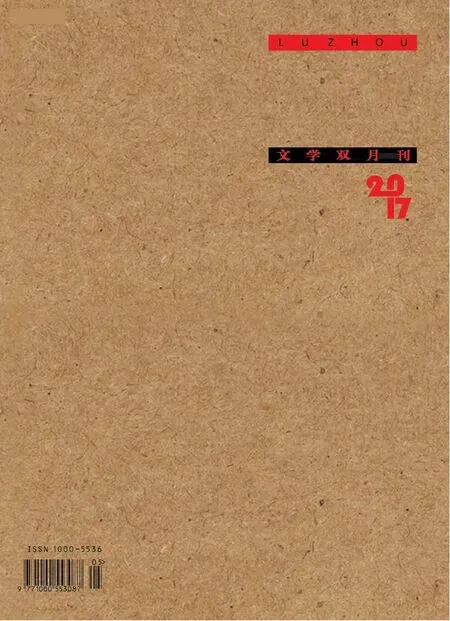父亲的田园
2017-11-13谭会东
谭会东
父亲的田园
谭会东
父亲22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运输第二团修理连工作,直到60岁退休,一直是个工人,但我觉得他更像个农民。闲聊起来他总是讲小时候农村的事情,讲地里的农活,讲山里的植物和动物。关键是他在新疆五十多年确实也一直没有丢下农事。
像他这样的人在兵团有很多,生长在内地的农村,青年时到新疆来支边。很多人去了农场,更多的人来的时候还没有农场,后来的农场是他们在戈壁滩上刀耕火种、一步十滴汗地开垦出来的。至于住,可以这样说,兵团人的居住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全过程。早先来到戈壁荒原的人,就地挖个坑,再找些树枝搭在上面,盖些土,层面斜着挖个沟好下去,这叫地窝子。就这,在早期也是稀罕东西。早先来兵团的年轻人基本都是单身,极少有带家属的。所以挖出来的地窝子都分男女。后来有的人结婚了,也没有单独挖地窝子的,那时候,人们顾不上为自己做啥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起早贪黑,为的就是赶快开出更多的地。那么结婚的咋办呢?
现在到位于石河子的兵团军垦博物馆去参观,可以见到一个地窝子坡面结构的模型,美其名曰“公共洞房”,虽然是地窝子,但平时并不常住人,专门是为新婚的职工当洞房用的,两个人结了婚,就到这里来住几天,再让给新结婚的同志。然后两口子就分别回到各自的集体地窝子。很多内地的朋友看了不理解,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
去年去石河子南郊的军垦第一连,见到了一个隔成几段的地窝子。就是在地上开出一条十几米长的沟,上面铺上树枝和草,盖上土,里面就是一个长长的通道,再用树枝靠一边打成一道一道的篱笆,抹上泥,把通道隔成一截一截的,留出一边让人进出。每一截的外面挂上个布帘子就成了一间,结了婚的一家一间。老连长胡有才说,这房间根本不隔音,谁家小两口说话,大家都能听见,更别说干别的了。在这里大家都没有秘密,两口子也都不会吵架,怕丢人。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刚躺下静了没一会儿,有个捣蛋的家伙突然喊道:“男人们,预备——开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地窝子住了没多久,大家就抓紧时间利用农闲打土块,盖房子。十间八间一排,每间上面用苇把子弯成弧形并在一起,然后铺些麦草再抹上泥。每间一户,前面开个窗和门,从正面看很像一排窑洞。再后来才有那种两面坡的土木结构的房子,还是一排一排的军营式排列,每户从一间增加到一套两间。
我的父亲1958年来到石河子,他倒没有住过地窝子,但窑洞式的平房和土木结构的平房一直住到2008年。
住平房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点东西,养个鸡鸭什么的。从我懂事开始,家里的院子里就种着果树,边上是一块菜地。每年春天,父亲都会从小伙房边上的煤棚子里拿出农具,带着我们把菜地翻一遍,然后种上些茄子、辣椒、豆角什么的。菜地的边上种几棵南瓜。盛夏的时候,一日三餐的菜就从地里随手摘,有时候竟然吃不完,要送给邻居。邻居家也种着些瓜菜,都相互换着样子送着吃。再吃不完就可以晒菜干儿或者腌咸菜了,这些东西到了冬天就是好东西了。
种菜是父亲的拿手好戏,他说都是种菜但是不能都说种,豆类的要说是点,瓜类的可以说是种;茄子、辣子要先育苗,种的时候要叫栽;香菜、芹菜一类的要叫撒。我们从小就跟着父亲做这些其实都是种菜的活儿。最好玩的是南瓜,要对花儿,就是把一个没有结瓜的花儿摘下来,轻轻撕去花瓣,把花心放到结瓜的花里面,然后把结瓜的花收拢,外面用个线轻轻绑一下。这样结出来的瓜才能挂得住。我问这事为啥,父亲说这叫授粉。我说授粉不是有蜜蜂吗?父亲说,多了可以,少了就只能人工授粉。秋天渐近,架子上坠着一个个的南瓜,很是好看。
小伙房的南边是个半地窝子式的鸡窝,里面常年养着十来只鸡,鸡苗是自家老母鸡孵的。有些年,父亲去集市买些鸡蛋回来,手抓鸡蛋握一个桶儿,对着灯泡一个一个地看,选出一些放在纸箱里,纸箱的底下铺着棉絮,然后挂一个灯泡在箱子里,掩上盖子。不到一个月,小鸡一个个地孵出来了,听到箱子里响动,我们都趴上去看,看着小鸡自己顶破蛋壳,湿漉漉地钻出来。很奇怪,每次父亲选的蛋都能孵出小鸡,几乎没有瞎的。父亲说是有诀窍的,能做鸡苗的蛋对着光看里面有一个小黑点,后来,我看了很多蛋,都没有发现小黑点。
鸡食是用拣剩下的菜叶子,或者拾一些连队分白菜剩下的白菜帮子,剁碎了再拌些麸皮,还要稍微放点盐,拌匀了就可以喂了。家里养了鸡,就随时能吃上鸡蛋,鸡肉倒不能随时吃,因为一只鸡要自然长大需要很长时间。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宰上一两只,其它的就让它长,长得越大越好。所以,小时候鸡肉是最好吃的东西,凡吃一次鸡,就要把肉啃光了,连上面的油水都嗍得干干净净,像出土的化石一样。父亲常说,这样的骨头连狗都不吃了。但是,如果一只鸡病死了,父亲绝不会让我们吃,也不会让狗吃,而是埋在院里的果树下,说是可以做肥料。父亲说人吃了病死的鸡会生病甚至会要命,狗吃了病死的鸡也一样。再说,就算狗吃了死不了,也不能让狗吃,因为,狗如果吃了带毛的鸡以后就野了,会冲进鸡窝抓活鸡吃。
不是所有的鸡病了都会死。比如感冒,鸡感冒了和人一样会打喷嚏,无精打采,父亲就会用人服的感冒药喂鸡。一手抓住病鸡的头,捏住两腮,鸡的嘴就张开了,用个小勺子盛着药水灌下去,再抖一抖,确保鸡把药都喝了。这样竟然治好了好几只鸡的病,要不然我们就要损失很多的鸡肉了。还有个办法就是在鸡小的时候打预防针,父亲专门去兽医站买注射器和疫苗,给它们挨个打,预防效果很好。最难治的是积食,鸡如果积食了,十有八九要死,因为鸡的胃叫鸡嗉子,宰了吃叫鸡胗子,里面有很多小石子,用来磨碎食物,如果鸡吃多了,或者吃下难消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会和那些石子纠缠在一起,结成一个硬块,直到撑得鸡嗉子无法蠕动了,鸡就会被撑死。所以,父亲嘱咐我,每次给鸡剁食的时候要剁碎一点,拌的时候要适当加点水。
有一回,家里的一只鸡积食了,眼见着它的嗉子撑得圆圆的歪在一边,用手摸摸,沉沉的,硬硬的。这是只小公鸡,还没有打鸣呢,撑死了多可惜呀。最后实在不行了,父亲说我给它做个手术,如果成了它就活了,如果死了正好有鸡肉吃了。
说做就做,父亲找来半根钢锯条,磨了一把锋利的小刀,然后把酒倒到小碗里点着,把刀在上面烧了烧。手术开始了,父亲把鸡脖子下面的毛剪掉。为啥不拔掉呢?因为剪了以后还能长。剪完以后,胀鼓鼓的鸡嗉子裸露了出来,父亲让我抓住鸡的爪子,不让它动。然后用锋利的小刀割开了它的嗉子,果然里面已经结了疙瘩。取出疙瘩,父亲又用消了毒的针和棉线给它缝上了。缝好以后,我的手累得酸酸的。父亲说松手!我一松手,这只小公鸡站起来就跑了,并且活了下来。
后来连队里的娃娃们都长大了,不方便跟大人睡一张床、一间房了,各家都在院子里加盖一间两间房,比单位的公房矮小一些,安顿孩子住进去。我家的院子小,只能占用原来的菜地盖房子了。菜地就没有了,只剩下院子中间的两棵树。
那时候,修理连有一大片公共菜地,连队的女同志除了在车间上班,就在菜地种菜,也没有个单位名称,就叫菜地。种出来的菜按时给每家分,象征性地收点钱,收的钱够给菜地的女人们发工资就够了。后来,菜地不集中种了,分到每家自己种。我家分到了大约一分半地。正好院子里的菜地没有了,这里就成了新的菜地,面积比院子里的菜地大,可以种更多的东西了。每年春天,父亲还是带着我们到菜地翻地、种菜。每隔一段时间,要去上面放水浇地。再后来,上面不给水了,各家就挑自来水浇。再后来自来水收费了,挑水浇成本太高了。加上连队的运输和修理业务很多,人们都忙了起来,更没工夫管这些菜地了。连队决定把菜地种成树林。
没有菜种了,父亲也还是没有闲着,他又开始专心养花,院子里用水泥板搭了两层台子,上面摆满了花盆,月季、夹竹桃、朱顶红、菊花、仙人掌、紫罗兰、石榴、灯笼花、臭梅梅、兰花、金橘、大叶海棠、昙花、文竹……各式各样,窗台上也是满满的。院墙边上还种了刺玫瑰和牵牛花。一进院子,花香扑鼻,沁人心扉。特别是夏夜的晚上,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人们吃了晚饭就坐在院子里聊天。切一个西瓜、泡一大壶茶、炒一盘瓜子,吃着、喝着、聊着,微风吹过花香和小声一起飘向远处。因为父亲花养得好,到家里来串门的人自然就多,聊够了,走的时候再掐一枝月季回去栽,或者挖一两棵兰花回去种,有的来的时候带一两株新的花卉交流一下。没菜种了,连队又兴起了养花。
后来,连队盖了新连部,对外称友谊综合机械厂。新厂部是栋两层楼,人们搬进去以后发现一盆花都没有,毫无生气。那时候还没有啥花卉市场,只有几十公里外的华侨农场有花卉苗圃,市里有钱都买不到盆花。小家户可以慢慢养,这么大一栋楼就难。不知是谁出了主意,去老谭家借吧。于是,厂领导找父亲借花,说是先借,再慢慢分栽或者扦插,等养多了,再把我家的花还回来。父亲答应了。那就拉吧,整整拉了四拉拉车,几十盆花就上了厂部大楼,一去就是几年。那几年父亲也没有闲着,还是继续用业余时间种花,很快,院子里又摆满了花盆。再后来,厂里也不说还了,父亲也没再提要的事情。父亲说,当初借花的领导都调走了,现在的领导又不知道这事,借的时候又没有打条子,反正花开着就是让人看的,就让大家看吧,那么多人一起招呼这些花也好。再说,再拉回来院子里也放不下了。
九三年九四年的样子,我家住的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成了危房,我们搬到旁边新一点的一排平房,原来院子里的两棵苹果树太大了,搬不走,就让它长在原地吧。老房子拆了,苹果树成了厂区的公共果树,开了花谁都说好看,结了果谁都能摘着吃。还说,老谭家的果子就是甜。
新院子更小了,隔壁邻居家的李子树的枝杈都伸了过来。邻居说长过去了就是你家的了,你们就摘着吃吧。但父亲每次摘的时候都喊一声:摘个李子吃喽。也不管人家有没有人。新院子摆不下原来那些花盆了,父亲就把花送给左右邻居,只留了几盆。另外,还在院子里放了个旧水桶,里面栽一棵丝瓜,瓜秧就盘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院子里总算增添了一些生气。有一次,我回家,看见铁丝上挂着几根丝瓜,瓜秧上还开着几朵黄花,很是好看,让父亲站在丝瓜藤下照个相,他说不照了,这有啥照头,以前要是有相机就好了。虽然这样说,但他还是照了,照之间还说等一等,拿把梳子把头梳了梳。
有一年,父亲发现院墙的角落里长出了一棵树苗,自己看看,是棵李子树。原来,邻居家李子树上的果子熟透了掉在那里,发出了一棵新苗。父亲把它移栽到院子靠中间一点的地方,好让它多照点阳光。经过两三年的栽培,这棵李子树很快长高了,到后来竟然超过了院墙,每年还开花结果,只是没有邻居家的李子甜,父亲说是因为没有嫁接。
后来,修理连和旁边的四连跟整个汽二团一起都不复存在了,一大片地成了开发楼盘的好地方。市政府决定在这里搞旧城改造的试点,把所有平房都拆了,盖廉租房,对原住户优惠,均价700元。因为修理厂和四连是国有单位,职工们住的都是公房,自己盖的小房子住了那么多年也够本了。何况还是先盖好楼房再搬,搬完了再拆。新楼房的价格也便宜,加上贷款政策,都买得起。搬新楼的时候高高兴兴,拆旧屋的时候也和和气气。旧厂房、旧平房、旧校舍、旧菜地、旧操场一年之间变成了一片新楼房,编号七小区。
小区的中心是原来的树林和菜地,土质很好,作了绿化,当年就见到了效果。父亲舍不得院子里的李子树,索性挖了出来,就栽在单元门口的人工草地上,还在人工草地的边上栽了一排黄花菜。不知是谁“告密”,没过几天社区就知道了这事儿,社区的人找父亲,说小区绿化是统一的,不让私人栽树,更不能在人工草坪上种菜。父亲知道自己做得也不太合适,但还是抬杠说,小区的树只能绿化,我的李子树还能开花结果,不是更好吗?黄花菜名字是菜,实际上是花,比单纯的草坪也更好看。好在,社区的人只是说这样不规范,并没有动手拔他的李子树和黄花菜。不过走的时候说最好还是老爷子自己把它们移走,过两天市委书记要来视察小区建设的成果呢。父亲又抬杠说,可以,等市委书记来,他要是说让我移走,我就移走。先让它在这长着,我保证只种这棵李子树和这些黄花,绝对不会种菜的。社区的人无奈地了。
过了一年多,我回去探家,看见那棵李子树还在那里,上面结了不少果子。草坪边上的黄花菜也在盛开着。我问父亲,市委书记来说让你移走了吗?父亲说,市委书记那么大的官,哪管得了这么小的事情。他来视察的时候还真从这过了,好像没看见,社区的人忙着汇报工作,也顾不上说这些小事情,最后就没人管了。现在看也不是很好嘛?再说,广场和开发区的路边都栽了苹果树,满树的果子红红的,也没有人去摘呀。城市里种果树才显得市政府有水平,光种些榆树杨树松树柳树什么没啥意思。
后来有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碰到市委书记,我跟他说起父亲在小区种李子树和黄花菜的事情。书记听了哈哈一笑,说我知道我知道,兵团老职工住进小区,还想种点果树和花花草草都是可以理解的,以后会好的。
母病
从我记事开始,母亲就一直生着病。父亲常说:“你妈从小就爱生病,是小姐的身子丫鬟命,跟自己吃了一辈子的苦啊。”
母亲只上了五年小学,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村里就让她做了记分员,每天记工分,因为身体不好,不用参加体力劳动。因为表现好,母亲十几岁就入了党,那时候在农村入党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说起母亲那时的病,还有一段传奇故事。说有一次母亲发烧在家里躺着,姥爷每天出去劳动前把饭做好,水烧好,母亲一个人在家躺着,一身汗一身汗地出,姥爷回来了,母亲总说一个人在家害怕,说房子要倒了。姥爷不相信,想是孩子病了,烧糊涂了。有一天姥爷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喊:“老王老王你家房子山墙倒了!快回去看看吧!别把你家鸿姣压着了!”姥爷撂下锄头就往回跑,跑到院子里一看,山墙倒了一半,半间屋子敞开着。姥爷忙着喊:“鸿姣、鸿姣……”一转眼,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院子地下,脸上挂满了泪花,已经哭不出来了,脸色蜡黄,浑身都让汗湿透了。一群人跑到倒下的山墙边上看,墙根塌下去一个坑,边上露出一个洞,洞口露出一些玉米粒和豆子,原来墙根下是一个很大的老鼠窝,不知挖了多少年了,把房山墙都挖倒了。可母亲怎么知道墙要倒呢?人们都问她,她也说不清,就是觉得房子要倒了,那天她昏昏欲睡,突然觉得房子要倒,就使出浑身力气跑出来,跑到院子里就倒在地上,然后房山墙就轰隆一下倒了一半。
姥爷赶紧找人修好了房山墙,一家人又住了进去,说也怪,从那起母亲就没再发烧过了,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但还是很弱,老是咳嗽。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组织安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也是浪漫的。
1958年,父亲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跑出了家乡——山东烟台牟平武宁镇南自格庄,先到济南,再到宝鸡,在宝鸡正好碰到兵团汽车运输第二团人事科在招人,几个人凑上去问了问情况,先问能吃饱饭吗,一年拿多少钱?接待员说有饭吃,现在加入兵团,晚上就有红烧肉吃,还能穿军装。几个人一听,那不是当兵了吗?人家说就是当兵了,但是和当兵有些不一样,我们是搞建设的。不管了,只要能吃饱肚子,还能穿军装为啥不去呢?于是问我们能去吗?接待员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有证明吗?几个人面面相觑,还是父亲仔细,带着《高小毕业证》,上面有名字,有照片,在那个年代足以证明身份了。接待员说这个可以,一数四个人,都要了!开了介绍信,嘱咐说到兰州与大部队汇合。接待员给四个人买了火车票送他们上火车,到了兰州,四个人进了营房,按照身材领了棉衣、棉裤、军装和棉鞋,当天就吃上了传说中的红烧肉。一周后,他们一行坐着火车来到红柳河,下了火车又坐汽车来到哈密,在大营房驻扎下来,和各地来的人一起休整,不久就到大南湖开铁矿,炼钢铁。一年后,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运输第二团修理连,来到石河子。
来的都是单干户,只有少数是有家的,安下身紧接着就是安家问题,单位领导安排石河子市几个单位的年轻人每周搞舞会,主要是运输单位的男职工和纺织厂的女工,目的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找对象的机会。父亲长得帅、舞跳得好,自然被人关注,但是父亲在舞会上并没有找到意中人。他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一是奶奶有交代,找对象一定要听老人的意见;二是自己有老观念,找老婆还是找同乡人;三是父亲觉得离家在外的女单干户都野得很,于是一拖再拖。当时领导还有一种安排,就是单身青年可以回老家找老婆,带老婆回来的,可以报销两个人的路费,但条件是要找好,把人带回来领结婚证,或者在家把结婚证领好了把人带来。
1964年,父亲坐上火车辗转十几天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带个老婆回来。这算是组织安排,他要完成任务,那次回来他确实带着老婆回来了。很多年以后,听父亲说过一次,他和母亲其实早就认识。
母亲怎么说都算是美人,哪怕放到今天来说也是。听父亲说,母亲十五六岁就参加了村里的吕剧团,有一段时间排演《白蛇传》,母亲饰演小青,人长的美、唱腔也美,每次出场,总是引起满场掌声,听完了更是掌声雷动。剧团是业余成立的,在农闲的时候各村转着演,一群小伙子在本村看了,又跟着到其他村看,那时候的文化活动确实很少,有一台乡村版的《白蛇传》那就算是大餐了,怎肯放过?特别是要看那剧里的小青,总是看不够。
父亲探亲回家说第一件事就是找老婆结婚,奶奶一听自然很高兴,而且是特别高兴,按老家的规矩,长子没结婚,次子就不能结婚,哪怕次子已经找好了对象也要等着,甚至长子没对象,次子连对象都不能找,不能乱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老家还有两个叔叔没有结婚呢。
可探亲就那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到哪去找个媳妇呢?奶奶犯了愁,但这个媳妇还必须要找到,自己要满意,儿子也要满意才行。
按理,应该是奶奶打发人去寻摸,但自己是个小脚儿,又不常出门,爷爷四十几岁去世,奶奶一直守寡,很少出门了,加上自家又是富农出身,跟大家交往得少,这一来可犯难了。只能问问儿子了。奶奶问父亲你自己有没有看上的人啊。父亲想了想,自己离家八年没回来,我看上的人现在是啥情况呀。于是试着问,屈家滩有个演小青的王鸿姣不知道结婚了没有?奶奶一听,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叫人打听一下。
打听的人当天下午就回话了。人还在,没有结婚,老母亲已经过世了,她跟老父亲一起生活,因为家里也是富农,成分不好,没人敢找。奶奶一听,笑了,那就赶快去说媒。相亲的时候父亲说,我认识你,你唱小青。母亲说,我也认识你,你经常来看戏。
这就算对上了。两家说好,孩子在老家领结婚证,办了婚事再一起去新疆。姥爷那时很穷,只能买一个烟台钟表厂出的座钟作为陪嫁送给他们。婚事办了,过了春节,还不到正月十五,两人就回新疆了。
来了当年母亲就开始咳嗽,新疆比胶东冷,水土不服,咳嗽更厉害了,最后咳出了血。到医院化验,是肺结核。肺结核就是传统说的肺痨病,在那个年代得这个病常常是要命的。但是,医生说,幸亏发现得早,而且现在已经可以根治肺结核了,只要配合治疗,家里照顾得好,营养跟上,病情是可以好转的。
刚开始,母亲还能下床,只是到了晚上咳嗽很厉害,开始是痰中带血,后来是一口半口地吐血,再后来是大口吐血,一升容量的搪瓷缸子一天能吐大半缸子,脸上没有血色,翻身要靠人帮忙,甚至自己已经无法翻身,父亲把母亲推过去侧躺着,如果不动,她自己都平躺不过来,医院给母亲报了病危,每天增加巡诊密度,每次巡诊都仔细询问病情变化。父亲拿个本子记录着母亲每次吐血的时间、吐血量和症状。医生嘱咐父亲好密切关注,照顾好病人,让她吃好,让她高兴,让她安静。后来,医生看着很快消瘦下来的父亲,都很关切地嘱咐他也要好好休息。
父亲不敢告诉家里的人,这么好端端一个姑娘,跟你到了新疆就病成这样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交待不了呀。其实后来,母亲的病情还是让老家的亲戚知道了,而且,母亲留给家人的印象就是在新疆病了大半辈子,直到去世。舅舅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说:“我姐如果不去新疆,不会得那么多的病,不会走得那么早。”
父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在晚上没人的时候一个人悄悄地哭,哭一阵又赶紧到病房看看母亲。每天看着母亲大口大口地吐血,父亲几近绝望。到后来,医生每天过来巡诊,也不说什么,更多地是安慰父亲,建议维持病情转入常规治疗。但父亲依然坚持要用最好的药,病情虽然很重,但人还在。父亲二十四小时守着,半小时翻翻身,晚上母亲睡着了,父亲就趴在床沿迷瞪一会儿,稍微有点想动赶快起来看看。在医生的精心医治和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母亲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了。渐渐能自己坐起来、能下床在病房里走走了。
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只有十几元,母亲来到兵团,单位已经不招收正式工人了,只能当家属,在五七排上班,工资更低,住院报销只能是正式职工的一半。父亲向连队打报告,借钱看病,每天三顿饭多掏点钱,在病号饭之外再加点营养,自己隔几天再做点更好的。母亲在老家没吃过什么苦,吃饭也挑,刚到新疆吃不惯羊肉,喝不下牛奶。
有一天,母亲说想吃饺子,父亲赶紧跑出去买菜买肉包饺子,医院离连队有五公里,那时候没有公交车,父亲也没有自行车,只好步行。父亲下好了饺子天快黑了,赶紧把饺子装进饭盒,用布一包,抱着就往医院跑,外面冰天雪地,晚上也没有路灯,深一脚浅一脚,连跑带滑地一路快走,眼看就要到医院了,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饺子摔了一地,父亲气得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完了把饺子从雪地里拾进饭盒包好接着走,到了医院,母亲坐在病床上饿得哭了好一阵了。父亲到开水房,用开水把饺子洗了洗烫了烫,赶快送到病床前,母亲看着饺子,眼里含着泪笑了。
母亲的肺结核竟然完全治愈了。最后的检查显示,结核部分已经开始钙化,呼吸功能逐渐恢复,出院前,医生对父亲说,多亏了你的照顾,要不然这个人早就没了。
肺结核只是母亲来新疆后的第一场大病,之后,几种大病不断地侵袭了她羸弱的身体。
1965年,就在母亲的肺结核确诊治愈不久,母亲怀孕了,爸妈都十分高兴。可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母亲又患上了急性肝炎。医生说,得了肝炎还是先不要孩子的好。但他们太想要一个孩子了,只能一边看病,一边祈祷母子平安了。怀孕七个月,孩子就早产出生了,是个女孩,就是我姐姐。刚出生的女儿体重只有七百克,一出生就进了保育箱,父亲说当时看着孩子太可怜了,隔着肚皮都能看见肠子,像一只猫那么大,也不哭。父亲一边照顾着母亲,一边看着保育箱里的孩子,心痛得泪流满面。生了姐姐,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孩子早产,又吃不到母乳,生命迹象也比较弱,医生给孩子报了病危。看着保育箱里吃不上母乳的孩子,母亲也在哭。
也许是经历了母亲的上一次大病,父亲变得坚强了,他在母亲面前总是笑嘻嘻的,夸女儿长得多么多么漂亮,哄着她吃饭。
老天有眼,有一天保育室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细细的,越哭声音越大,“孩子哭了!孩子哭了!”护士跑了告诉爸妈,他们俩听着孩子的哭声,高兴地笑了。姐姐终于挣脱了早产体质的纠缠,用哭声开启了成长的历程。
父亲把母女接回家,除了三顿饭,还要熬中药、烧牛奶,烧好了放在窗台上凉着,一会试试温度,不烫手背了,就赶快端过去喂,一边喂药,一边喂奶。喂完了,赶紧又去洗衣服和尿片。
真的是老天有眼。母亲的肝炎竟然也痊愈了。姐姐也奇迹般地很快长得和足月婴儿一般的体重和身高了。很多年以后,母亲因为子宫肌瘤到医院看病时,当年给她看病的医生认出了她,对父亲说:“哎呀,老谭啊,没想到这个人还活着,和她一起来住院的好几个人都不在了呀。”很多年以后,父亲看着姐姐总是说,你在保育箱里,隔着小肚皮都能看到肠子,谁敢相信你都长成个大姑娘了。的确姐姐现在身体很好,每天锻炼,如今虽然已经快五十的人了,看着只有四十出头。
生了姐姐之后,母亲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父亲说在怀我的时候,母亲的身体是最好的,母乳很充足,所以我生下来就是个胖小子,吃得好,睡得香,一直都是个大个子,体质好,很少生病。
直到弟弟出生,母亲的身体都还不错。
母亲的第三场病是哮喘,那时我们姐弟三个都在上学,母亲已经四十多岁,在五七排的汽车配件加工厂做钣金工,父亲在供应科跑采购,一年到头地出差,家务活几乎都落在母亲身上,加上她的工作耗费很大的体力,每天跟铁打交道,一天八小时手头搬起放下的重量至少有半吨重,还要操作氧焊和电焊。那段时候,母亲在大夏天也咳嗽,一串一串止不住地咳,有时咳得喘不过气来,脸憋得通红。赶紧给她捶捶背,她咳得说不出话,有时捶得重了,她就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挥着,示意我们轻一点。
父亲相信中医,带着母亲看遍了石河子的中医,终于在中医院找到了良方,但是那服药需要一种特别特殊的药引子。服药的同时,要吃用很小的蟾蜍碾成的粉,小蟾蜍还必须是茄子地里的,抓回来以后要放到那种没有蛋黄的鸡蛋里,再用泥巴裹上,放在瓦片上烘烤。瓦片又必须是在屋檐墙根下受了雨水,放了三年的老瓦片。烘烤透了再打开泥巴,取出装着小蟾蜍的无黄蛋,整体碾碎,用温开水冲服,作为这味良方的药引。
其中的关键是这种无黄蛋,据说这种蛋是母鸡受了惊吓后产生的鸡蛋,概率很低。我家的鸡下过一两个,像鸽子蛋或者鹌鹑蛋那么大,煮了吃,剥开蛋皮里面只有一个圆圆的蛋清。但是要用的时候又没有了。先要找这种无黄蛋,好在那时候连队家家养鸡。需要十个,很快找到了三个。我和弟弟到连队菜地的茄子地里去找小蟾蜍,晚上打着电筒,很快就找了七八只,装在罐头瓶子里拿回家,由爸爸打开无黄蛋的一头,把小蟾蜍放进去,再用泥巴裹上,放在瓦片上烘烤。那时候住平房,房顶上了瓦,幸好剩了一摞放在屋檐墙根下,受了三年雨的。
做好药引,坚持吃了三个疗程的中药,母亲的哮喘真的减轻了,甚至几乎没有了。只有在很安静的时候,你靠近听她的呼吸,还能听到轻轻的哮音,但她再很少那样咳嗽了。
母亲45岁时开始经常头痛头晕,确诊为高血压,开始终生服药。出院后不久,母亲申请退休。她所在的五七排是集体企业,都是所谓的家属,所谓退休也不能像正式职工那样按月拿退休工资,只有一次性的3000元不知如何定性的钱,但母亲并没有说啥,她说大家都这样啊。
退休不久,母亲的情绪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变得爱发脾气,我印象中母亲一直都是很温和的,和父亲从未红过脸,但退休以后总是和父亲生气。有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随意聊天,突然不知哪句话没说对,母亲就把脸一拉不吭声了,放下碗,想哭的样子。赶紧问咋回事,她说没咋回事,就你们说得对。后来父亲带母亲去医院检查了一次,回来说是更年期综合症,过几年就好了。
可是没多久,母亲又被查出有子宫肌瘤,确诊后,很快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在家休息,心情还是时好时坏。
1996年父亲58岁,来新疆已经工作了38年了,按照60岁退休的政策,到退休还有2年,那一年,他说想退休了,实在干不动了,要给年轻人腾位子。他说自己生于1937年腊月,但单位档案里给他登记成了1938年,这样把年龄弄小了一岁,他就要晚退休一年,实际上再有一年就可以正式退休了,如果按30年工龄退休,他又多干了8年了。
其实父亲想等到60岁再正式办退休,因为那样可以拿到百分之百的退休工资。但是母亲希望他马上退休,因为母亲希望父亲尽快带她回一次老家。父亲开始很不情愿,母亲就时常跟他生气。有一天傍晚,母亲吃了饭就躺下了,父亲收拾餐桌。等到正式要睡觉的时候,父亲叫母亲起来躺好睡,但母亲自己起不来了。父亲急了,赶快出去找公用电话打120,救护车来了,医生初步判断是脑淤血。送到医院,确诊是脑淤血,好在出血位置不在关键位置、出血量也小。住了一个多月,母亲出院了。人沉默了许多,有时一个人坐在窗前默默地流泪。父亲看这情形,向单位打了退休报告。
回老家,算起来母亲自到新疆来总共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五岁的时候,爸妈带着我和姐姐回去一次,是过年,老家的房子里冬天也没有火墙,但是有火炕,不过只有睡觉的时候觉得暖和。第二次是我弟弟三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弟弟回去了一次,我也想回,但是我已经上二年级了,要上学,那一次他们回去的时间好像比较长,回来的时候弟弟说着一口胶东话,逗得我们咯咯笑。第三次就是爸爸退休以后带她回去了一次,那一次,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回老家。
父亲退休了,我们开始准备爸妈回老家的事情。母亲出院以后,行动迟缓了很多,手脚无力,走不多远就要停下来歇歇,也不能提重物。我们很担心他们回去的路上会出事。走的那天,我们们送爸妈上火车,车要开了,母亲隔着车窗向我们挥手,脸上展开灿烂的笑,露出整齐的牙齿,眼睛眯起来,弯弯的,像个孩子。
这次回去,他们本来要多住一阵子,但是还不到一个月,就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要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们去车站接,车厢里的旅客都下完了,还没有见他们。见父亲一个人下来,说上去把你妈背下来吧。我上了车,看见母亲坐在硬卧铺上,很疲惫的样子,表情有点呆滞。我上前喊:“妈!妈!”母亲叫着我的名字把手伸过来。我背着母亲下了车,又把他们送上长途班车,由姐姐陪着他们回了石河子。
那一次回去,他们有点住不惯。母亲的病情虽然没有恶化,但是行动不便,父亲很累,累的瘦了好几公斤。关键是在舅舅家,父亲和舅舅吵了一架,主要的焦点还是舅舅认为母亲跟父亲到新疆来吃苦了,要不然不会病成这样,甚至提出来让母亲干脆住在老家不回来了,由他们照顾。父亲很委屈,气不过他们,干脆问母亲你愿意留下吗?母亲说:“我跟你回去,我的孩儿在家。”
在他们回新疆的火车上,父亲发现自己小便带血。回到家就去检查,诊断为膀胱癌,马上手术,取出了一大两小三个肿瘤。在父亲住院期间,母亲时常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等我们回去了,就问我们,你爸爸好了没有?我们说快好了,快好了。
父亲出院后,身体恢复得很好,定期灌注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有一天,他从医院回来,看母亲侧着躺在院子里地上。原来母亲自己在院子走,被墙角的砖头绊倒了,自己没有力气起来,一个人在地上躺了不知多长时间。父亲赶紧扶起母亲,姐姐赶回家把母亲送到医院检查,是手臂骨折。我从乌鲁木齐赶回来,看着坐在床上的母亲,赶快走过去抓住她受伤的手臂,她抬起另一只手,摸摸我的脸,笑着轻轻地说:“东东,东东,东东回来了。”然后只是笑,笑得很灿烂,露出整齐的牙齿,眼睛眯成一条缝,弯弯的,像个孩子。
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又承担起照顾母亲的任务,每天三顿饭,打扫房间,洗衣服。本来他做手术的时候是把烟戒掉的,但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抽了,一天两包。我回家的时候问他,他说不抽没办法呀。我知道他压力大。1999年,父亲在复查时发现膀胱肿瘤复发,再次作了手术。家里两个老人病在床上,我们姐弟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子欲孝而亲不待。但是父亲在半年后就康复了,还是尽心照顾母亲。
2000年,母亲再次突发脑淤血,昏迷了过去。送到医院就不行了,我连夜赶回来,守在病床前。一遍一遍地喊她,她怎么也不吭声,静静地躺着,不吃不喝,呼吸很重、很慢。我用棉签蘸着水不断地湿润她的嘴唇。妈,我回来了,妈……母亲还是一声不吭,一会儿她的眼角流出一滴泪,沿着两鬓往下,遇到白发停了下来,慢慢地渗入发间。我拿起毛巾给母亲擦去泪痕。妈,你听见了,是吗?
住院一周后,母亲进入休克,医生宣布脑死亡。我们默默守着她,她的头发竟然白了还不到一半,脸上只有少许皱纹,脸颊还泛着红晕。母亲的呼吸渐渐弱了,我们流着泪,但不敢哭出声,世界静极了。母亲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呼出来,仿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像是想说话,又像是在微笑,然后就永远地睡着了。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安放在石河子南郊的公墓,父亲坚持要个合葬墓,树一个双人的墓碑,属于他的一半先留着。每年清明,我们都要给母亲扫墓,把墓碑擦了又擦,然后用新油漆仔细地把母亲的名字描一遍。每年除夕下饺子前,我和弟弟要去烧纸,第一盘饺子一定先盛给母亲,放在她的遗像前。
父亲常说:“我对不起你妈呀,没有把她照顾好,你舅舅不愿意呀。”其实,我们也常想,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如果母亲没有来新疆,如果没有石河子的医疗水平,在老家农村,她多病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好像是在2008年的夏天吧,我下班走在果树巷,突然有人在身后喊我:“这不是王鸿姣的儿子东东吗?”我转过身一看,是妈妈生前的同事张阿姨。张阿姨老了,拉着我的手说:“东东啊,我们是来要退休工资的,听说兵团有政策解决五七工的退休工资啦,你妈妈走得早,要是她还在,也可以拿上。你带我去见司令员,我们都要上了,每人出一点,给你妈也凑一份,交给你爸爸养老用。”我一时不知所措。旁边的阿姨说你别为难孩子了,他妈妈都走了那么多年了。说着几位阿姨就走远了。
又一年春节回家,我跟父亲说起这事,父亲说五七排老姐们儿都解决退休工资了。“我妈……”我刚要说啥,父亲说:“你妈走得早啊,算了,不说了,说了让你妈知道,她又不高兴了。”
责任编辑 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