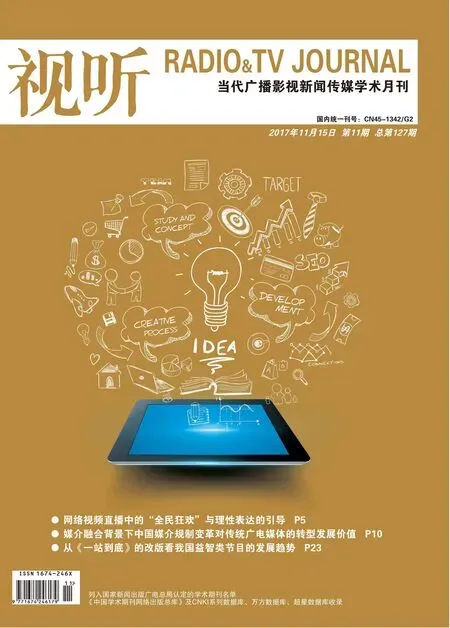后乡土社会及秩序重构
——以广西为例
2017-11-09何小民
□ 何小民
后乡土社会及秩序重构
——以广西为例
□ 何小民
“后乡土社会”是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以两种社会属性的矛盾共存为内涵属性。对后发展地区来说,它的变化主要是外生因性的,并显示加速特征。当前我国乡村变革正处于后乡土社会的发展关键期,合理认识这一社会形态、应对相应问题,对于传统乡村实现新阶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土社会;转型;外生因;社会控制
乡土社会是指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自然形成、持久稳定的传统乡村社会。它是封闭的完全社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在特定有限的空间内完成,不同人、不同代之间高度相似,社会结合方式高度稳定。费孝通先生精湛阐述过它的礼俗控制、血缘密切、熟人社会等次级特征。与之相反,现代社会是高效、理性的产业社会和功能社会,比如企业即是其中多见的、以利润为目标的组织。现代社会因分工而差异,因差异而导向多样化的社会状貌。
乡土社会的理论框架,主要依托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理论,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理论。前者立足于成因,认为共同体源自本能的中意、习惯和记忆,“社会”则基于目的。后者立足于结合特征,认为原始社会是以同而和的机械团结,现代社会是以异而和的有机团结。乡土社会无疑是共同体性的,符合滕尼斯所谓“生机勃勃的有机体”①,但费先生称之为“有机团结社会”②,则违背了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提出的“有机团结”概念原意。而社会学家们普遍认可,传统社会必然转型为现代社会。
处于从乡土到现代转型过程的地域社会,相应包含共同体瓦解而功能社会形成、同质性减退而分工形成的嬗变,我们称之为“后乡土社会”。探求后乡土社会的规律,有助于对后发展地区的社会变动建立解释力、预见力和问题解决力,达成高效有序的转型发展。
一、以冲突为主调
后乡土社会作为过渡类型,以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元素的矛盾共存作为其内在特征。在现象上,前后两种社会可以互不妨碍,比如年轻人既过传统节、又过现代节;甚至互为促进,比如共同倡导某种价值主张。但是,两种社会的建构取向存在根本的差异。我们将传统乡土概括为“纵向社会”,现代社会为“横向社会”。
纵向社会,注重时间上的承袭与延展。因而,“现在”被“过去”同化而近似,社会呈现时间静态,我们称为历时同质。这种社会通常存在悠久的风俗习惯,人心信而好古,崇尚创世神话,遵从历史经验和长者权威,作为国家则注重经学和史学,显示鲜明的文化个性。相应地,这种社会在横向上欠缺整合,空间差异敏感,正如古人所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称为共时异质。
横向社会,注重社会与外部的开放交流。因而,“这个”与“那个”相互同化而近似,出现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现在”与“过去”则往往日新月异,即共时同质和历时异质。这种社会通常容量大、密度高、关系多样,一个人可能承担多个社会角色。另外,与横向交流相关的行动较为频繁,比如通讯、运输、旅游、交友、聚餐等等。
应予说明的是,横向社会并非有意排斥传统、偏信“外来和尚会念经”,而是持有开放的经验源,将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一并对比检验,择其利者。而客观结果上,传统经验当中未能通过检验的部分,将面临颠覆。
因此,后乡土社会作为从纵到横、从一维到多维的质变,天然地包含不稳定、不均衡;后乡土社会是一种以冲突为主调、以过程调适为目标的社会类型。
二、内生因和外生因
社会变动的起因,区分为内生因和外生因,共同推动乡土社会的质变,构成后乡土社会演进的基本驱动力。
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内生因,迪尔凯姆归为人口过度增长、生存竞争加剧,必然以分工来建立新型的社会团结。用费孝通先生的经验论解释,人口过载即内环境变动,环境变动导致传统经验效能下降,进而导致社会转型;原有土地养不活、原有房屋住不下,就会另寻高效的方法。韦伯以经济史分析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是科技、商业、资本制度等理性要素的发育,人口增长是有利条件。
外生因,即外部现代性的进入,造成乡土社会系统的开环和变质。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西方现代科技和公共管理方式进入日本;鸦片战争后,欧洲廉价工业品冲击中国乡村的传统生计方式,同时催生负责购料的“洋买办”。
以此理解广西乡土的现代化,我们看到内生因驱动乏力、外生因后继有力的情形。
传统广西人地关系并不紧张。1936年广西人口密度为65.82人/平方公里,在所统计27省中位列第17。远低于第一的江苏(379.02)以及随后的山东、浙江、河南、安徽。③另外,尽管广西地少山多,山地、丘陵占75.6%,但地貌以中低山和丘陵为主④,没有高山荒漠。民国中期,除桂东南各县外,大部分地方垦殖空间巨大,“荒地3000余万亩、荒山16000余万亩,都蓄有无限富源,大有希望,亟待开发”。⑤这就意味着,只要愿意开深山、种碎地,总能装下新的人口。
相比之下,地势平坦而人口稠密的华东地区,或者地处高寒荒漠而耕作艰难的西部省份,人地关系饱和而缺乏弹性。正如历史学者分析清末人口问题时说:“易垦的荒地已垦殖殆尽,一旦灾害来临,已很少有度荒流徙的回旋余地”⑥,后果必然是毁坏社会的逃荒或战乱。
宜居的条件,养成广西乡土安逸自足的特质,原住民与外来移民和睦共处的状貌;另一方面,导致广西乡土在现代化转型中陷入滞后。2015年7月我们在田林县者苗乡渭龙村的社调,全村青壮年600余人当中,外出务工者达450余人(约75%)。看该村历史,并不是村里土地养不活1300余名村民,而是本地缺乏产业,按老办法难于增收。而他们的务工地广东珠三角和江浙地区,产业发达,经济富庶,却正是传统上人多地少的地方。
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影响,一是家庭增收。该村脱产村干的月收入为1000余元,而村民去广东中山灯饰厂务工能拿五六千元,有说法是两公婆下广东三年、回来起平房,外出动力强劲。二是传统秩序难以为继,人员缺乏导致田地丢荒、村干难聘、传统节庆活动难召集。留守者似也无必要维持传统的劳作,他们利用外出务工亲人寄回的钱,到圩市买米买肉买家电,山区圩市在非圩日也有了商业。
可见,外部产业社会将青壮年拉出乡土、将现代商品推进乡土,在这种交互中,乡土面临外生因性的改变。就广西的情况,当具备了基本的交通通讯条件,乡土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是横向传播、横向交流的产物。
三、越来越快的演进
乡土社会出现了任何外部元素、致使原有功能结构发生改变,严格来说,即进入后乡土社会阶段。往后的进程,与城市影响力扩张、交通通讯发展有关,呈现越来越快的速度特征。
城市,是现代产业和现代性的发源地,是以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类型。不难理解,在城市市场饱和以前,城市产品(包括有形工业品、服务和资本等)欠缺进村的动力。通常是城郊农村以地利之变,主动地靠拢城市现代生活。
而随着城市产品增多、市场饱和,城市在城乡关系中开始变得主动,加强向农村市场推送产品,以及相应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同时,向农村吸收与产业日益壮大相匹配的劳动力。

近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对比(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得益于城市科技发展,出现了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传播,传统的城乡交流管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在此以前,城市通过城郊乡村,以及以乡镇圩市为节点,先近后远、近强远弱地进行现代性辐射。靠近城际交通线的乡村,容易变成工商业繁荣的圩镇,比如传统柳邕公路沿线的大塘、迁江、芦圩,桂梧水路沿线的阳朔、平乐、昭平等。不靠近城市和圩镇、交通艰难的山村,维持着牢固的乡土性。
现代传播根本改变了传统的空间渐进方式,城乡空间距离压缩,传播交流变得高效。通过高速公路,过去的天堑之隔可能仅多了几分钟车程;通过互联网,村民掌握的大量信息不滞后于城市市民,乡村青年可能比城市老人更时尚。
交通通讯变革得益于城市,反过来又服务于城市产品进村和乡土转型,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再加上前述城市产业发展的过程性,我们说,后乡土社会的变动通常是先慢后快、越来越快。
除了城市发展因素,政策因素也能影响后乡土社会的演进。对比欧洲、日本等发达社会的实践,产业社会是在自身进入成熟期之后,才随着农机、化肥等工业品渗入农村,解体乡村共同社会。⑦中国的政情特点,可以未雨绸缪,调配资源建设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提早预备城市产品进村、村民交流外部世界的管道,乡土社会的转型过程进一步被压缩。
四、中国定量
从整体上观察中国的乡土社会转型,似乎难于找到一个时间开端,因为古来即存在战乱、饥荒或政治引致的人口迁徙和族群融合,打破乡土的封闭和稳定。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变动实质是传统乡土的量性调整,此后人们依然承袭、或者致力于往后延续固定的社会结合方式,社会走回到纵向轨道上。政府反对散漫和反复的人口流徙。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和民国政府均注重发展现代工业,以增强实力和摆脱危机。理论上,乡土社会的变迁路径是:城市工业发展、农民进城务工、城市产品进村、传统乡土解组解体。但从城镇人口比例变化看,这个过程并不匀畅。我们观察比较四个时间节点:⑧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镇人口占比仅增加5%,可理解为,由于战乱、政治割裂等原因,城市未能充分发展和影响乡土。1949年之后的“前三十年”,城镇人口占比仅增加7%,可理解为,由于城市工业尚欠发达,以及城乡二元化政策因素,城市现代性未能有效地带动乡土。改革开放后,城市工业发展,政策步入开放。在较短时期内,大量农民流出乡土、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市产品涌入农村,传统乡土难以为继。
特殊的国史国情,恰好为中国的后乡土社会定位一个大致的入点,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至于它的出点,在于乡土性完全继替为现代性、乡村全面进入现代社会之时。
五、推进、控制与关怀
作为乡土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后乡土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它的阻碍不仅欠缺可行,也欠缺道德合理。现代秩序以其高效和理性,增加创造,保障自由,促进合作而减少冲突,比如以产业分工取代自给自足、以法律权威消减族长权威、以科学精神抑制原始迷信,整体上让生活更富足更美好。而乡土秩序与匮乏经济相适应,在低效之外,也未必是道德乐土,“不成文的物理的禁律和特权支配着日常生活”⑨。当今世界不存在社会越传统、就越美好的关联。
因此,应该一方面积极推动乡土社会转型,一方面着眼于危机干预,确保转型顺畅,降低转型损耗。这是后乡土社会的发展要求,也是当前政府及相关社会机构的应有担当。
(一)推进乡村社会开放
破除保守思想。上世纪80年代钱穆先生以“安足静定”和“富强动进”概括中西文化差异,很大程度也是乡土性与现代性的鲜明对比。乡土社会缺乏竞争合作意识,多见安土重迁、循规蹈矩、小富即安的习性。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对比宣传,激励求富求强、锐意改变、勇于冒险、敢于承担的创业精神。比如2013年广西上林县农民赴非洲淘金的新闻轰动一时,其中包含的强劲进取精神,无妨出现在基层媒体和宣传栏上,激发村民“人能我何不能”的思考。
提升城乡交流。改善乡村交通通讯设施及服务,提升城乡之间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效率,鼓励经商、投资、务工、旅游等开放交流活动。当前广西各级政府推动的电商进村、手机讯号全覆盖、乡村道路硬化等,即是有利于破除乡土壁垒、推动城乡交流的基础工作。在这种交流中,通过能人带头,引导乡村社会主动借鉴外部经验,分析内外部资源机会,与外部搭建有效的分工合作,则是对城乡交流意义的深化与提升。
把握乡镇节点。乡镇圩市具备人口集中、商业繁荣、交通基础好等现代要素,并且与周边农村文化相同,交流频密。在人流物流中转及其他社会化服务的方面,仍能发挥城乡交流节点的作用,能作为外部新观念、新习惯、新秩序导入乡土的有效管道。应做好这一层级的社会服务和示范建设工作。
(二)理顺乡土转型衔接
成熟的社会类型,存在自足的功能和控制系统,使自身免于崩溃。两种类型的交接处,则容易出现青黄不接,导致功能中断和秩序混乱,需要理顺前后衔接。
1.功能衔接。以家庭监护为例。2015年田林县者苗乡有两所全托制幼儿园,青年父母外出务工,将幼儿托管于此,年底返乡时团聚并缴齐学费。若交由留守老人照管,父母担心山区沟多河多、监护不及。——在传统社会,父母不会长期离家,母亲从事简单劳作并照管幼儿;在现代社会,出现女性全职就业,幼儿就近安排在社区幼儿园,上下班接送。而在后乡土社会阶段,经济社会欠缺均衡稳定,就业机会、工作时间和生活成本决定了打工父母难以将孩子带在身边,只能委托给老家的全托制幼儿园。
在后乡土社会里,类似的变动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要分析认识每一种变动背后包含的功能缺失危机,衔接好“破”与“立”。砍掉村口的大树,要给老人准备自由交流的其他场所;宗族关系逐渐衰微,需要政府接手扶危济困的担当。
2.控制衔接。后乡土社会对社会行为的约束,容易出现规范缺失和规范冲突两种情形,需要进行“补”和“调”。
规范缺失。2005年有新闻媒体溯源调查深圳“砍手党”团伙案例,发现这些青年凶徒全部来自广西边境地区一个夜不闭户的小山村,村邻评价他们为“在家都是好人”。⑩显然,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道德不再管得住村中青年,这是值得深思的失范现象。直观的经验是,应该在他们脱离乡土之前,进行现代法治教育,补上现代新规范;或者,在城市的一侧,延续某些乡土控制力,比如城里的亲戚同乡能督导他们,或能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
规范冲突。相对于上述“两不管”,这里属于“两头管”;同一社会存在两套规范,造成冲突。比如,城里人觉得农村人“唠叨”,农村人觉得城里人“势利”,往往是两种社交习惯、两种时间观念差异造成的误会。调适冲突的一种方法是,给不同规范划清各自的应用范围。比如,公交车上强调给老人让座为美德的一方,与强调个人选择权的一方,爆发争吵,时常见诸报端。公交公司于是划分“爱心专座”,在专座上有让座的义务,非专座上有不让的权利,即有利减少冲突。将来,所有乘客形成了关于让座道德的共识,则“爱心专座”的使命宣告完成。从喻体回到本体,也就是走完了后乡土社会的冲突过程,进入现代社会新秩序。
(三)关怀转型障碍人格
后乡土社会当中的中老年成员,曾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对乡土形成习惯、记忆和悦纳的态度,并且由于年长,人格固化,对环境变化缺乏适应力。在乡土转型带来的冲突和动荡面前,包括乡村由传统变现代、由繁荣变凋敝,或者生活空间从乡村移入城镇,他们感受不到“老经验”的价值,认识不清新的物事,失去从容的空间。他们容易将现代社会的高效、理性感受为混乱、被动、冷漠和功利,出现恐慌、失落、焦虑、挫折感等负性情绪。
我们在桂西、桂北山区农村走访了解,这一群体对新环境的不满包括:人多车多、没有熟人聊天、什么都要钱、住不惯楼梯水泥房、担心不能在祖屋终老,等等。有的老人因为照看孙子的原因,不得不住到城里,感到左右为难。后乡土社会应该为这“转型的一代”提供关怀和支持,为传统人格保留或构拟易于适应的社会空间。
这里回到前文的一个观点:从乡土到现代,是社会建构取向上的变动,不是华屋丘墟的现象性改变。因此,我们不必刻意地求异求新,防止落入“伪现代”的陷阱。事实上,水泥地并不如草地灌木更宜人,包装食品并不如小锅菜来得营养健康。尤其在文化习俗方面,传统经验的优劣很难进行短期检验和简单评价。承载乡愁的古井、古树和古街一旦被毁,山歌唱本一旦消失,将很难接续,无从后悔。村庄状貌层面的“现代化”,应该多一点从容、理性和智慧。
注释:
①[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4.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5.
③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8-49.
④莫大同.广西通志(自然地理志)[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45.
⑤钟文典.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51.
⑥王育民.中国人口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558.
⑦[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M].严立婴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201.
⑧“19世纪末”数据见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其余见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⑨[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98.
⑩见2005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文章《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
[作者系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公务员培训处(研究生工作处、干部继续教育学院)副调研员、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