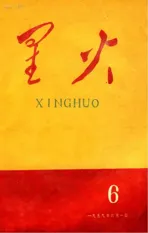脸 面
2017-11-03王志远
○王志远
脸 面
○王志远

王志远,江西鄱阳县人,1969年10月生。2001年6月至今在南昌从事纸媒编辑工作。现供职于江西工人报社总编室。作过田,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乡聘用干部、县报记者。有散文、报告文学在不同层级报刊发表。获第22届、23届、24届江西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三等奖、二等奖、二等奖。系江西省作协会员。
一
沾满了银白色油漆的刷子在铁栅栏上笨拙地上下左右地点点戳戳、拖拖扫扫,不时地有油漆防不胜防地滴在地上。还好,宏的手伸得老长,身子前倾,生怕捅破蜂窝那般小心谨慎,他的鞋子,包括时新的衣裤竟然不像在与油漆打交道:一丝一点的斑迹都没有。
刷子走过的地方,原先显得老旧甚至有些锈迹的铁栅栏顿时就有了崭新的精神面貌。这符合宏的性情,无论何时,从头到脚干净整洁,帅气、阳光;也符合年节的味道,喜气洋洋。
小院墙的两扇铁栅栏已经有一扇穿上了全新的银白色的“外套”,在上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宏正在另一扇铁栅栏上尖着心眼地做着努力:他不允许哪怕是一丝油漆滴在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
宏的三层楼房已经建好大概五六年了吧,每一年,也只有在这个年节的时候,一家人才有机会短暂地在自己的楼房里放手放脚地自由活动。
该打扮的地方都安排稳妥了,比如热水器、空调、电动水泵丢在水井里驱动的自来水以及现代整体厨卫等等,都一一根据村子里的整体发展形势到岗到位。
人家有的,我没有办法,也只得跟在后面拖了。宏笑眯眯地说。他指的是家中的一些基本装修和现代化物件不得不“跟上形势”。宏笑起来很好看,跟即将盛开的杜鹃花那般招人喜爱。今年春天的脚步比较快,年节后几天就是立春,春天一来,村子周围的山上满是灿烂的杜鹃花。当然了,杜鹃花灿烂的时候,宏与村子里的大部分男女正在天南地北也许并不灿烂地弯腰帮老板干活。
一个村子里的人,大体知道一些彼此的性情,宏严肃的时候有一股子阳刚之气,他不时地与我搭话的时候当然不用严肃,不严肃的时候他的话语很柔和,像早晨下肚的温开水,给人心气舒畅的感觉。
你看我家里吧,一年到头没有人在家,乱七八糟,灰尘打滚,收捡了两三天才算像个样子。宏跟我说话的时候,刷子继续生硬、笨拙地在铁栅栏上戳动,并且继续尖心地小心着油漆的侵袭。
宏笑道,其他的地方都收捡得差不多了,趁过年把这个铁门也漆一下。
你家里不错,搞得挺好的。我也习惯地笑眯眯地“勾引”宏的话语。
不行哦,村里许多人家都买小车子了,我还骑个摩托车。没有办法跟上形势。
宏的“自贬”也是大实话,在经济建设上他家正在爬坡的关键时段。他的女儿正在上大学一年级,儿子在县城重点高中鄱阳中学读高二。一双儿女的开支、消费几乎掏光了他每一年的积蓄。早先他的女儿从本地的初中学校考到县城的一所民办高中,他和老婆跟到县城陪读。学校为了吸引生源,为家长提供了住宿,一家三口在狭小的单间里梦想花开。没有脱离家长视线的孩子基本能在正常的学习轨道上运行。三年的时光,宏与老婆一起在学校周围摆摊卖水果,一日三餐到点了,老婆按时回那个单间为孩子烧制可口的饭菜。能保证基本的日常开支就行,陪读的家长态度很坚决。社会上流行陪读,你要是落伍了,孩子的行为习惯以及学业就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宏这样解释自己三年的“卧薪尝胆”。
并不是每一户人家都安排陪读,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的成绩都值得家长去陪读,就算有家长陪读的孩子最后也不一定都能梦想成真。我们上兰村上千人口,每年金榜题名的也就那么两三个,部分孩子念完初中或者高中,部分孩子没有念完初中或者高中,然后离开村子,踏着父母的足迹,重复着父母的故事。
现在宏的家庭是个什么状况呢?我和村里的人以及村子里的人和我,也只有年节的时候匆匆地见面打个招呼,不坐下来深挖细究,谁都不知道彼此骨子里的细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构。年节很热闹光鲜,年节很忙碌紧张,年节也很短暂易逝,一眨眼的工夫,大家又要等上三百多天才能互相敬个烟,聊几句闲话。
宏尖心地为他的铁栅栏院门化妆,说话的时候偶尔停下几秒手中的刷子,回过头来友好地给我一个微笑。
宏在女儿考取大学以后,迫于经济压力,再次外出赚钱,如今在福建泉州一家小型个体服装厂做小组的主管,他老婆在鄱阳县城继续陪读,并就近在一家餐馆打工。宏的收入不错,管着十几个人,月薪近七千元。其他员工呢?宏说,每月的收入四千元到八千元不等,大部分是年轻的男女。宏说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小年轻不好管,每日里像劝新媳妇上轿一般百般呵护,稍有言语不慎,人家就会发脾气,有的女孩子还会哭泣起来。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与他们友好往来,比如不时地请他们吃夜宵。宏说,员工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大部分只上过初中,有的只有十五六岁。
我不想自己的孩子也过那种没有身份地位,没有节假日,没有五险一金和各种福利的生活。宏说,他们厂子里员工的收入并不稳定,要看老板生意的好歹。有活干和没活干,加班和不加班,决定了打工者的收入。但是老板也很为难,员工不好留,常常是说走就走。宏说他一手托两家,既要对老板负责,也要尊重员工,管理起来,不讲究艺术不行。今年四十三的宏只上过初中二年级,做人处事却有自己的根底。
我们村子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行业不同,估计情况与你们厂子里的员工差不多吧?
是这样的。宏回答得很利落。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在外面混,有知识和没知识,是两回事。
你还是蛮有眼光的,两个孩子都在接受不错的教育。
怎么办呢?只有苦自己了,每年都积不到钱。宏笑得没有拘束。宏虽然“自贬”在经济上落伍了,但骨子里自然坚定自己的家庭在村子里还是有一定脸面的。我从他的笑意里看到了坚定与自信,更有脸上长光的内心自豪。事实上在村人眼里,宏的家也有楼房和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并且女儿考取了大学,怎么说也有不少的脸面。至于谁家脸面背后的沉重与无奈,自然无人有闲心去过问了。比如宏的经济负担较重,自己工作的厂子兴衰不定,长期与老婆跨省分居以及对于儿子学业的牵挂。
宏的老婆系一条做家务的围布走上来打断了我们的闲聊。
女人说,你没听到打爆竹的声响啊?说完这一句话,女人可能是为自己冒然打断我们的兴致而感到不安,瞬间冲我笑了起来,问我,进来坐一下?我摇了摇头。
我问宏的老婆,谁家做什么喜事?我也得去打个爆竹。
对方回答,老敏的儿子带了老婆回来。又说,这些日子,我家里光是打爆竹就不晓得花了几多钱,还要喝酒送礼,这样那样的开支,驮重得很。每年回来过年吧,将近两万块钱就这样东撕西扯的算不出账目来,一年下来的一点积余基本打了水漂。
关门躲债,打开门行人情,现在到了这个形势,该花的钱也省不掉。宏一边回敬他老婆的话,一边起身准备去村里的小店买爆竹。买多大的呢?宏问老婆。女人说,起码要二十块钱一封的吧。
我在心里盘算,那我也买二十块钱一封的。许多人情往来,每年回家过年都有新的发现,跟不上节奏,总归是件丢脸的事情。上门打爆竹,也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风俗。
什么情况下打爆竹?你想象得出来的任何动响都要打爆竹,每封爆竹少则二十元,多则三五十元,甚至一百元。
平时建房子开基,你得上门祝贺,打爆竹,爆竹越多,主事者越体面。年节的时候,有的人家爆竹炸响,整整轰动一个上午。房子封顶,打爆竹。新房落成上门喝喜酒,得拎上一封偌大的爆竹。有人带女朋友回家过年,自然要上门道喜祝贺,打爆竹。考取大学摆酒,除了常规的送礼,也一定要打爆竹。婚姻方面,程序较多,每一个程序,你都得上门打爆竹。谁买了新车回家过年,通了人情往来的,也不能不上门打爆竹。新亲戚上门做客,打爆竹……
二
春节前后是乡村集中办喜事的高峰期,在我的村子,几乎是每日里爆竹声声。拎爆竹上门的人喜笑颜开,主事者神采飞扬。但是事后摸摸口袋,双方暗自叹气。累积下来,过一次年,单是打爆竹就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主事者也麻烦,对于上门打爆竹的人,需要每人发一包香烟,我们上兰村的习惯,打发的香烟的价码是十五元一包左右。如果一百个人上门鸣响爆竹,主事者就要付出千余元的香烟。
丙申年腊月廿八这天上午,地处赣东北的鄱阳县上兰村,因为老敏家儿子的出息,爆竹炸响,接二连三,烟花呼啸,冲天而起;同时,另一户人家为孙子办周岁酒,也是轰轰烈烈不甘落后。整个村子里的空气融合着年节的喜气,想不激情抖动都很难。
令人亢奋而又长脸的日子当然不仅仅在腊月廿八这一天,此前五六天以及此后至元宵节,都是我的乡亲以各自的方式集中展示各自脸面的最佳时期。最常见的繁华是应和各种喜事的烟花爆竹的高调喧哗,最常规的举止是互相敬各种上档次的高价烟,最基本的现象是村子里的微信群里不时地有人发那种一两分钱的红包。
五十出头的老敏没有理由不脸上放光,上门打爆竹的通了人情往来的村人没有理由不暗自承认老敏的福气真好,当然了,当面的时候同样洋溢着祝贺的喜悦之情。但是这其中,不排除怀着并无恶意的羡慕妒忌恨,却又喜笑颜开的祝贺者。这样想啊,老敏的儿子大学毕业不到两年,就带回老婆了,而且是广州城里的念过大学的漂亮妹子。自己的儿子呢?没上过大学,到处托人找对象,一个年节下来,操的心都是儿媳妇在哪里。如果儿媳妇有着落了,又要操心钱在哪里。在我们村,讨一个老婆的行情已经飙升到近四十万元。老敏的儿子就不同了,已经确切的消息是,对方的父母说,五六万元就行了,你们一个乡下的家庭,能有多大的能耐呢?前三个月吧,老敏夫妻就应女方家长的邀请去了一趟广州为儿子定亲。回来之后,老敏的老婆想不振奋都按捺不住自己,振奋的消息自然很快就在村子里传播开来。
贺喜的众人先后散开之后,老敏告诉我,女方家长确实不要男方什么彩礼,但是儿子的婚事费用二十来万块钱还是要花的。老敏说,儿媳妇说了,在广州买房子的事情他们年轻人以后会提上日程,目前不作考虑,但是要求男方家长在景德镇市买一套房子,也就五六十万块钱的行情吧。为什么选择景德镇市?老敏的儿媳妇说了,骑电动车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近,以后来来往往就有了准确的落脚的地方了。老敏家也是楼房,虽说是二十年前的建筑,但里面的装修还是蛮亮堂的。上兰村毕竟不是城市,老敏这样想,就一个儿子,在景德镇市买一套房子也不是很为难。老敏是石匠师傅,现如今的工价,如果能接到房子做,两三百元一天还是有的,但是老敏估算着还缺一半的钱。怎么办?儿子上面四个姐姐以及其他亲友都表了态,该借的一定负责到位。老敏不断地分我烟,他相信,我抽得越多,他的心情会更加地愉悦。老敏说,钱的问题不大,钱的问题不大。就算钱的问题真的很大,老敏可能认为,都没有儿子带了老婆回来的喜事大。这确实是一件很有脸面的大好事。
老敏分烟我推脱不掉,他再次敬上一支有档次的香烟的时候,我突然重视起他的一双手来。这是一双热爱绘画和书法的手。很小的时候,老敏,也就是当年的小小敏上小学,有空的时候也同小伙伴一起玩耍,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喜欢趴在桌子上画各种旁人看不懂的图画。课本上见缝插针地画,作业本撕下来画,地上捡到纸片拿过来画。小小敏的画都是有故事的,什么故事呢?他认为是什么故事就是什么故事。他指着一幅幅线条型的画,逐一向伙伴讲解画的意思。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小敏做石匠的父亲将儿子拉回来一起上户操持泥瓦刀。小敏的父亲对儿子说,道理再简单不过,纵有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读书能算账、会写自己的名字也就够了。小敏的父亲平时在四乡八村做上户石匠,不用作田还受人尊重,他希望儿子也尽快过上这种长脸的日子,有一技在身的村里的后生,不说别的,光讨老婆的时候就很吃香。很吃香的小敏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与邻村的一位漂亮姑娘走进了洞房。
刚成家的那些年月,做石匠的小敏倒是像一个上学的青年,房间里有纸有笔有墨汁,还有一两本老旧的《战斗的青春》《暴风骤雨》之类比较显摆的书籍以及几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皱皱巴巴的杂志。实际上小敏不怎么看书,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书,有空闲的时候小敏写些毛笔字或者自作主张地画些自己想象的图画。当然了,小敏用过的纸先后都被他老婆扯去上了厕所。
小敏成了老敏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活法并无多大的脸面,但是一切埋怨都化成了空气。大概是十年前吧,村子里开始作兴陪读的时候,老敏毅然将老婆派了出去,他希望唯一的也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能够为自己争取一些光彩。
老敏到底为自己争取到了脸面,儿子成了大学生,而且毕业不久就带回了老婆。村子里的非大学生也有因为外出打工带了外省的女孩回家做老婆过日子的,但毕竟是少数,而且这个少数的群体当中,有一部分人的老婆最终丢下出生不久的孩子回了自己的娘家。大学生自己找老婆回家不是新鲜事,但是老敏基本可以肯定,大学生的老婆大体上是不会跑的。这又是一层很有脸面的光亮。
儿子上了大学以后,老敏曾经的兴致重新激活,闲空的时候,他牺牲打麻将的爱好,作古正经地在房间里临摹绘画,为此,他在二楼专门设置了一间很像样子的书画室,有时候也会写写毛笔字。最近两年,老敏专攻梅兰竹菊水彩画,旁人看了点头称赞:真是不得了,真像。他的四幅装裱好了的长条形的梅兰竹菊水彩画还卖了好几百元。老敏去集镇装裱的时候,人家看看画又看看他粗糙坚硬的双手,摇头表示不相信是他亲自画上去的。老敏的脸上顿时充满了光彩。
老敏说没有时间,去年一套梅兰竹菊从开春动手,直到年底才完成,每天收工回家只想躺下睡觉,实在太忙太累了。老敏现在增加了春兰夏莲秋菊冬梅之类的绘画内容,今年不晓得能不能完成一两套。我在重新审视老敏一双手的时候,老敏自己轻描淡写。更要紧也更有脸面的事情是想办法买房子以及准备好儿子的婚事。都已经怀上了,老敏神秘地说。
三
正月初二拜年,主要目标是岳母或者外婆家。对于其他常规的亲友,骑摩托车或者开小车子,一两天的时间蜻蜓点水般进门放下礼品就抓紧赶下一家,所以到了正月初三、初四,拜年基本接近尾声,然后抓紧打牌、赌钱,抓紧办喜事、喝喜酒,也赶时间陆续外出上体制的班或者打老板的工。
丁酉年正月初三,我老婆经过多方打听,得到确切消息,这一天中午,我们上兰村共有四户人家办喜酒,项目分别是儿子周岁、新楼落成、女孩儿考取大学以及嫁女儿。所有喜事的日期本来是不一致的,但只有在年节的时候村子里才有人气,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同一个热闹的时段将家中的喜事解决掉。有喜事的不办掉总归是个疙瘩,没喜事的往日里送多了别人的礼金,也想立个项目扯个心里平衡。比如孩子周岁甚至是满月,就可以出手热闹一场。
接下来一直到正月十三,村里以及亲友当中谁家会有什么喜事,我家女人也大概心中有数。
这样一来,家中大部分日子除了来了亲友拜年并且确实愿意吃中饭的,基本不用另外考虑自己动手解决饮食的问题。
老婆正在翻家里前几年办喜事的礼簿,看看谁来了谁没来,谁送了多少礼金。来而不往非礼也,一个地盘上的人,基本的为人处世的规则还是要有个分寸的,要不然,抬头相见低头也避不开,脸面就不好安放了。
老婆跟我搭话的时候,我定了一条原则,对于乡亲们的喜事,贺礼宁可多送、送错,不可漏掉一家,具体操作你自己执行。
老婆好笑,你带回了几多钱嘛?
一万五千,基本够用吧。
我怎么执行?我一个人能同时吃四家的喜酒么?
还有儿子,我们大家分兵出击,确保一个中午全部拿下来。我们当中有不愿意吃喜酒,或者实在撑不下去油水的,也务必主动上门上个礼金。
老发家在我们做喜事时没有来,要不要去?
我略略想了想说,也不靠他一家的花销,还是去吧。
老婆答应要得、要得。她知道我心不在焉。
因为今年春节手头有一份单位交代的返乡调查的任务,我因此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真正地了解自己的村子和那些长期在外生存的乡亲。往年,我没有在意这些细节。我带着家小在南昌谋生,离开村子十七八年了,虽然每年都会回来那么三两次,但是每一次都像匆匆的过客,更别说过年的时候,因为紧张繁忙,几乎没有访过几户人家。就算是现在,村子里绝大部分人家的大门,我仍然没有时间进去。
我家的房子就在穿村而过的马路边上,我只要抄着手在自家的大门口做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就一定能候到愿意与我聊上几句的男女或者是老少。起初我的房子在村头的位置,后来每次回家都会发现村子里的楼房一年比一年增多也增高。现在,我家的位置成了中心地段,我离开村子头一年花费四万多元建的当时还算挺不错的两层半楼房早已变得毫不起眼。当然了,我也可以主动出击,在村子里面四处转悠,然后站在某一户人家的大门口“问寒问暖”,人家感动于我的热情到访,实际上我在无孔不入地打捞自己想要的素材。
我抽着烟,清闲地看着来往的行人,看缓慢进出村子的小车;我相信在大家眼里,我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很友好很好讲话,很乐意同任何人互相敬烟,互相散漫地闲扯。说穿了,我也只是村子里的一员,何况在经济收入方面,我的家庭不及大多数外出打工的人家。
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林推着他的母亲缓慢地走了过来。林的母亲前几年突然中风,开始时她凭着一支木棍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地活动着身体,后来就坐上了轮椅。林的母亲肥胖肥胖的,虽然比我大许多年岁,但是往常,我同村里人一样打趣地叫她胖子或者死胖子,胖子不介意,嘻嘻哈哈地习惯将每一件很正经的事情往玩笑的路子上扯。现在,林的母亲变得呆滞起来。
林俯下身子推着轮椅,见了我,他点头、微笑,算是友好地打了个招呼吧。我曾经打发老婆拎着一箱牛奶去看望过林的母亲,林的友好应该与此有关。乡亲们过日子,容易记恩,哪怕一点点人情,人家也不容易忘记。往日里,有人进南昌看病,硬着头皮找我带路进医院,跑程序,我都会安排老婆帮忙;也有平时要好的,会在入院前在我的住所过一两天。大家都记着恩。我回去过年的时候,这些“麻烦”过我的人会送上一只自己养的鸭子或者是刚做的几块年粑,我不得不收下的时候,对方才算松了一口气。我家要是做什么喜事,对方通常也会赶来上个礼,就算对方的喜事我不曾去过,人家也不计较。
林不抽烟,但我仍然很容易跟林搭上话。我说你真好,孝子。推着母亲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林笑嘻嘻的没有什么言语。我说年都拜完了?林说还没有呢,各种杂事比较多,反正也不急,要过了元宵才出门。
林说的“杂事”,眼下是推着母亲去本家一位侄子家里包红包,顺便去小店里买一封上门的爆竹。侄子今天“查家”,林说。
他的本家侄子过了年虚岁算是二十九了,折腾了好几个年,终于在看老婆时有一位十几里之外的姑娘答应了这门婚事。我们这里将“相亲”说成“看老婆”。在我们这一带,婚事定下的当天,男方要现场包给女方一万元左右的“爱情包”,接下来才谈具体的其他的行情价码、程序走向以及执行日期,总计费用近四十万元。这笔钱说起来吓人,实际上按照习俗,结婚不久,女方会带回来九成左右,小两口的日子从此欣欣向荣,只是累弯了男方父母的背脊骨。做父母的不愁扯借,伤脑筋的是儿媳妇难找。“查家”是第二个程序,女方姑娘本人以及她的父母、三姑四姨什么的全部来到男方家里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名义是“查看男方的家事”,然后男方的众位亲友以及本家赶来给女友送红包。女友收的红包越多,男方越有脸面。男方自己呢,也要包给上门“查家”的女人相应的红包,其中,未来的媳妇要给最大的红包,一万元左右,媳妇的父母各两千元上下。
林摇头,老婆真难讨。我说这种“查家”的事情你们做亲戚的一般要包多少钱啊?林说最少两百块吧,不然出不了手。
说到红包,林摇头,这样那样红包的他费了好几千块钱,接下来还要破费。确实,看望老人、病人,要给红包;亲戚当中的结婚查家、考取大学要包红包;新客过门、新生儿进门,也要出手;亲戚当中的长辈有逢六十及以上整数生日的,少不了也要送红包。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数目,都有约定俗成的大致规矩。
我说你负担蛮重的,楼房做起来不久,现在你母亲的身上又要花钱。不过你们夫妻赚钱还算厉害哦。林说这都是小事,也积不到什么钱,无非是过日子马虎一些。
林说的更重要的家事是每天担心女儿与外省的男人谈恋爱谈跑了。
我们站在马路边上随意闲聊的时候,村子里不断地响起剧烈而又欢腾的爆竹声。
林夫妻与儿子、女儿都在福建石狮一家鞋厂做工,收入好歹看老板的生意,林不怎么计较。舍得吃苦,活路总是有的,他说。儿子和女儿初中都没有毕业,他时刻将女儿带在身边,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至于儿子,只要谈到老婆就是好事,外省不外省的也不十分在意。又不是大学生,跑到外省去做什么。林这样看待自己的女儿。
稍微不注意,她就谈了一次恋爱,跟外省的一个小青年。林不客气地说,我及时将他们打散了,而且警告下不为例。
女儿要是跟别人跑了,林认为,这总归是件折面子的事情。
看着林远去的身影,我就想啊,我的乡亲在年节的时候各有各的荣耀与脸面,也各有各的不为旁人所注视的忧虑与艰难。林四十二三岁吧,正是外出打拼的重要时段,他这样耐心细致地推着自己的母亲,可能在心里感叹,他这次服侍过母亲之后,基本就要等三百多天以后的下一次过年了。
四
当然了,这篇文字省不了老荣,省了老荣就像米粉蒸肉少了一味佐料。
老荣个子不高,任何时候都是兴高采烈的像是中了彩票,说话像打爆竹一般节奏极快,声音响亮。老荣另一个很好记的特性是苍老,白发丛生,外人看上去只道六十开外,实际上他只有四十七八岁。老荣很好玩,平时在村子里的微信群里喜欢发些搞笑的东西,尤其是那种有男有女耍色情嘴皮子的视频。有的时候老荣也发正经的视频,通常是《超好听——打工的人》《催人泪下——新打工谣》以及《男人不好当》之类的通俗歌曲。
跟老荣聊家事,得知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聊起女儿,我跟他开玩笑,那你也进账四十万啊。
老荣说,进账个屁,跑了,跑到四川去了。
老荣的女儿已经做了母亲,因为至今未见面,男方也未给一分钱,所以女儿的结婚喜酒一直没有办法操办。
老荣并不恼怒,说,正月十三我儿子结婚,女儿可能会回家一趟吧。
听口气,就算女儿无法赶来参加她弟弟的婚礼,老荣也照样豪迈地过着自己本来的日子。
大概是三四年前吧,大家都知道了老荣的儿子会赚钱,很显眼的招牌是他儿子过年的时候开了小车回来,老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像一位得胜的将军那样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往年春节期间大家在谁家吃喜酒,老荣会假装无意地提及自己的儿子,人家问他儿子每月的收入,老荣笑嘻嘻的不说话,只伸出一个指头。人家问,一千?老荣头歪向一边,好笑!切,一万!于是个子很小的老荣的儿子会赚钱的消息很容易就在众人心目中扎下根来。
我问老荣,你儿子具体做什么事情呢?老荣说,修车,学修车。
老荣原先做石匠,但是十年之中有两次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现如今他的大腿上还嵌着一块钢板。老荣快人快语,说话的时候像是介绍别人的大腿曾经折断过:现在长肉了,嘿嘿,钢板的四周都长了肉,无论何时都可以去医院拿掉钢板。
当年的赔偿款早已花掉了,可能是考虑手术的费用,老荣一拖再拖,致使钢板成了他腿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荣自然不希望初中毕业不久的儿子重复他的手艺,于是送他进厂子里学做衣服。老荣自己也丢了泥刀,学起了电焊。老荣说自己现在成了老师傅了,嘿嘿,什么都会焊,我在杭州吧,什么都会焊。
老荣的儿子吃喝花销,到年底积不到一分钱。赚不到钱的年轻人又想学修理汽车,老荣说这是好事,学吧。
现在还在学。老荣告诉我,到去年是第三年,现在过了年算是第四年。头一年师傅只给两百块钱一个月,第二年给了五百,去年是三千块钱一个月。
老荣特别强调,一年一个师傅,嘿嘿,一年一个师傅。老是待在一个师傅手里,技术有限,一定有限。
谈起儿子开的小车,老荣嘿嘿嘿地笑,按揭,按揭买的。有车子吧,讨老婆方便,楼房是基本条件,我也做好了五六年。万事不缺,只缺儿子一个老婆。不过儿子马上要结婚,也不缺了。
你儿子结婚,都花自己的积蓄?
积个屁,嘿嘿,借的,四十万,借了十几万,不借怎么行。但是我有信心,还起来也快。
老荣对什么事情都很豪迈。老荣不提这些年来自己有意无意地在公众场合宣扬儿子一万块钱一个月的事,旁人也不会点破。老荣清楚,儿子很快能顺利结婚了,嘿嘿,嘿嘿嘿,怎么说也是一件很有脸面的事情。
与老荣不同的是平,这几年见到平,他总像赌博输了很多钱,又像前一天夜里被盗贼洗劫了一般,脸上没有什么气色。平比老荣年长四五岁,但表面看上去起码比老荣要年轻六七岁。我与老荣正在有一句没一句瞎聊的时候,平拎了一封圆圆的大爆竹走过来。他应该是去谁家打爆竹贺喜,但是他的神色却像是在逃债。
我与平是本家,向来关系不错。我跟平打招呼的时候,他冷静地回应着“打爆竹”三个字,然后继续赶路,表示自己确实很忙。
平的冷静是向来的性情,他上过高中,因此冷静之中又有自己独立的对于生活、对于做人的思考。他惯于省俭,早年时常不穿袜子,夜里想看电视就蹲在要好的人家不走。平因为有裁缝的手艺成了村里最早的外出打工者,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吧,当时外出谋生的全村仅有三四个人,平是其中一位。平很快竖起了楼房,当时花费六七万元。他儿子读书有那么几分吊儿郎当,平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并带着儿子跟自己一起进了石狮的一家服装厂。
七八年前的一次公众场合,平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说,读书上大学也就那么一回事,我家吧,可以肯定,三年就能竖起一幢楼房。平说话的时候意气风发。后来回家过年就见平走到哪里都抱着孙子,很悠闲。现在村里人建一幢有气派的楼房要四五十万元。据说平的儿子、儿媳妇与公婆相处不怎么和谐,也积不到什么钱;他自己的体力呢,再也不能靠熬夜加班来赚更多的钱了。他的脸色暗淡或许跟这些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形势在变,他们父子的生存方式已经很吃力地在逆水行舟。平可能自我感觉在众人面前很没有面子,跟我的交流也少了起来。我的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才不会伤害到平,所以我也不好在他面前过多地谈什么。
据说平已经安排老婆专门照料孙子读书,他希望从小学开始就重视孙辈的未来。
五
我早年刚离开村子到南昌时,水也才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我与水的家隔一条马路对门而居,每一年回家过年基本上最先与水接触,水总是很阳光地问一句,回来了?我说是哦,时间真快,又是一年。在这样的一问一答中,时间的动车就开进了2017年,不知不觉地,水已经四十来岁。水见了旁人一般不再有什么言语,默默地做着手上的事情。他仿佛做错了什么,总认为自己抬不起头来。也不知道水是怎么过来的,比较明确的是,他前几年买回了一个柬埔寨的胖子姑娘做老婆,但是两年后,姑娘跑了。水的父亲跟我说,准备推倒老旧的砖瓦房子,无论如何都要在原址建一幢全新的楼房,并且定了开基的日期,就在正月十三。我正月初七正式上班,赶不上去水家打一封祝贺楼房开基的爆竹,但是我相信,楼房建起来了,水的运气也一定会高涨起来。
春是水的侄子,同样是我的对门邻居,和他父亲一样不怎么爱说话。春的母亲跟我们谈他儿子时好笑,说这几天到处看老婆,但是春低头不说话,老是相不中。这次看老婆没有着落,可能又要等到下回过年的时候了。
春白皙、帅气,性格明显是内向的那种。我说厂子里姑娘肯定很多,他可以自己谈的,你不要急。
春的母亲说,鬼哟,一天到晚不说话,人家女孩子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问她家的情况,春的母亲说,他们夫妻在温州帮人做服装,好的时候夫妻两个一个月下来一万块钱还是有的。
不好的时候呢?
春的母亲报以微笑,没有正面回答。
她的女儿在杭州。
做什么呢?我每次都要反复追问才能捞到一些具体的信息,无论跟谁交谈大体上都是如此。
做医疗用的吊针皮管。
她的女儿一年能上交父母两三万元,儿子一年要少交一两万元。春喜欢玩手机,换了又换,现在玩的是名牌,花了六千多块钱。春先是跟父母在温州同一家服装厂,后来说坐久了太累,去年下半年改道杭州,进了一家汽车螺丝厂。
我笑道,你家春才二十五岁,你慌什么嘛。
他的母亲说,也是,前些天算命的说,春的婚姻还没有通呢。她这样解释儿子屡次失败的相亲,仿佛这样一解释,她和家人的脸面照样不差。
我问春的学历,他母亲笑道,初中毕业上过职业高中。
什么专业呢?
女人笑了起来,不晓得,老师安排的。
我与春的母亲闲聊的时候,不远处的小店门口聚集了一群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
我赶过去凑热闹的时候,很快理清了其中的原委。村子里上游的北面有一座乡镇管理的好几百亩水面的水库,这些年来,不知道外地承包水库养鱼的老板下了什么东西,水库里流出的水在大热天浑浊发臭,总而言之,环境污染吧。
许多人在口无遮掩地声讨老板不道德,认为村子里的井水肯定也有问题,那么今天,一定要打电话请老板过来论个清楚明白。
甚至有人跳起脚来骂,这么大的村子,要是连自己的井水都保护不了,丢脸,丢了祖宗八代的脸。随即有人附和,是这样的,我们在外面辛苦寻钱,家里却被搞得一团糟,这个不行。
有人上来咨询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入手,我一时不好随意表态,但给出了六个字:依情、依理、依法。我建议大家定出两三名代表,先找村委会干部谈一谈,长期以来,村干部应该知道水库遭受污染的事实。
我本来也可以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但是我妹夫的车子在按喇叭催我快一点动身。明天初七上班,我今天必须赶回南昌。
当天回到南昌住地不久,就有人在村里的微信群里晒出了村民代表与老板签订的确保养鱼不污染水面的协议,村党支部书记也在上面签了字。
随后有人发了这样的内容:“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