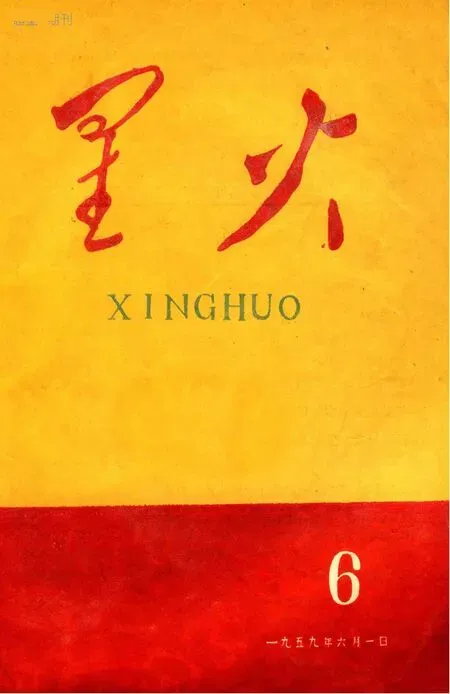妩媚与柔软
2017-11-03武向春
○武向春
妩媚与柔软
○武向春

武向春,公职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昌市散文学会副会长。文学作品散见于《花城》《散文》《美文》《福建文学》《湖南文学》《天津文学》《星火》等刊。作品入选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选》(2014)《2015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南昌散文十三家》等选本。出版多部散文集。
一
有人形容傅雷孤傲有如云间鹤,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那般硌人,温润软糯向来不是他的美德,他的侘寂、骄矜以及突兀崚嶒,好比是墙上种的铁蒺藜,看起来是一种设防,却难免给他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事上的矛盾与倾轧。
当张爱玲以傅雷为原型写下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她用男主角罗教授来影射傅雷:他古怪、贫穷、神经质,但他在美国欧洲都读过书,对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研究,对音乐史非常精通。他谁都看不起,对女人总是酸楚与怀疑的。
傅雷就这般在小说中豁朗朗与我们觌面相见。虽被妥妥帖帖地安置于人间腠理之间,与世无隔,却与傅雷抗争前沿斗士的形象大相径庭,难免令人生出欹斜颠覆之感。
张爱玲宣称:“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她当然有资本说这话,她向来不乏张扬的才情。她擅用犀利的讽刺、精巧的挖苦,将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心龌龊写得十分不堪。这篇小说的源起,当然不是源自宽厚的心性,反倒暴露出写作者某种特别的心性,或者可以说——心志的卑琐。
张爱玲说她从前的老女佣性子慢,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斯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张爱玲在讲傅雷的故事时,一反惯常的伶俐,忽然端出那个老女佣的作派,逐样翻检各色包裹,在众人前一一打开,让人看到里面难堪的私密物事。
“耶稣的被出卖,要从犹大的童年受伤害说起”,当我们和犹大一起重温成长的经历,会对犹大的叛徒行径生出慈悲的谅解。张爱玲与傅雷都经过烈火的焚烧与冰冷的淬炼,他们都曾在日与夜的交界、黑暗与光明的交界、清醒与恍惚的交界行走,不同的人做出此或彼的事,可以是对的,即便不堪,亦有不堪的理由。
当所有的恩恩怨怨皆随辰光而逝,尘埃落定,宛如花落鸟衔碧崖前,僧袍翻飞在风中,一切皆有了禅意的虚空。隔了辰光,我们依然要承认,傅雷是广阔而尖锐的,在任何年代,个性化的思想起初都曾局促地生存过,于大众而言,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周旋,不断地回退。然而在傅雷身上,始终闪烁着这一光辉,让我们能看到这一切仍在薪火传承,从未止息。
二
《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故事宛若东方版《洛丽塔》,亨伯特大段的独白:“我爱你,我是个怪物,但我爱你。我卑鄙无耻,蛮横残忍,等等等等。但我爱你,我爱你。”
在小说中,傅雷化身罗先生,而成家榴则化身殷宝滟。在张爱玲的笔下,傅雷的形象难免有些不堪:他的眼睛是单眼皮,不知怎么的,眼白眼黑在眼皮的后面,很后很后,看起来并不觉得深沉,只有一种异样的退缩,是一个被虐待的丫环的眼睛。而成家榴则是个美得落套的女人,大眼睛小嘴,猫脸圆中带尖,青灰细呢旗袍,松松笼在身上,手里抱着大束的苍兰、百合、珍珠兰,有一点儿老了,但是那疲乏仿佛与她无关,只是光线不好。她的歌声亦美,当她在水中唱歌,贞亮的声音,白鸽似地飞起来,飞过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女人低陷的平原,向上向上,飞到明亮的艺术的永生里。
当她向张爱玲细述她和傅雷的爱情故事,她眼睛里充满了眼泪,饱满的眼,分得很开,亮晶晶地在脸的两边像金刚石耳环。她偏过头去,在大镜子里躲过苍兰的红影子,察看自己含泪的眼睛,举起手帕,在腮的下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细心地擦了两擦。
他们相识在课堂,傅雷戴着黑框眼镜,把两手按在桌子上,忧愁地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一切人都应当爱莎士比亚。”他用阴郁的,不信任的眼色把全堂学生看了一遍,确定他们不会爱莎士比亚,然而仍旧固执地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挑战地抬起了下巴,“伟大的,”把脸略略低了一低,不可抵抗地平视着听众,“伟大的”,肯定地低下头,一块石头落地,一个下巴挤成两个更为肯定的。这架势不像是在上课,倒像在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背诵那段精彩的“to be or not to be”。
一个矫揉造作,一个滑稽可笑,然而他们却相爱了,当着他太太朱梅馥的面相爱了,有一天他递给她一封信:“……在思想上你是我最珍贵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王后,我坟墓上的紫罗兰,我的安慰,我童年回忆里的母亲。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我的滟——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即使仅仅在纸上……”
在张爱玲的笔下,成家榴仿佛是《聊斋志异》里的花妖狐媚,妖而不色,媚而不淫。狩猎男人的痴情而不谋求终身厮守,这段爱情中,消遣的成分多于感人的成分。然而她创造了光,创造了五彩斑斓的世界,她让他成了俘虏,自顾自地燃烧成了炽热的火焰。而她则是诱饵,是甜蜜的陷阱,她令他欲罢不能,自己却轻盈抽身而去。纵有千般不是,然而她依旧是深深扎在他心中央生嫩的蔷薇刺,心上感到分明的生疼,却痛得隐晦,生生难忘。当然她亦不乏良善。她家境宽裕,家里甚至有包用的裁缝,这使得她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应时按景给傅雷家带点什么来:火腿、西瓜、代乳粉、小孩的绒线衫……然而她从来不使他们感觉到被救济。她给他们带来的只有甜蜜、温暖、激励,一个美女子的好心。
傅雷夫妇两个时常吵架,傅雷脾气暴躁,甚至要打人。她知道他们夫妻是为她争执,然而她还是要堂而皇之地到他们家里来,带来了馄饨皮和她家特制的荠菜拌肉馅子,去厨房里忙出忙进。她在他面前娇嗔无比,凝视的眼神里有直白诱惑。但她却是清白的,他的妻子疑心她,却又被她的一种小姐的尊贵所慑服,觉得自己湫隘。
张爱玲笔下的朱梅馥亦是极美的,削肩,披着宽大的毛线围巾,扁薄美丽的脸,温柔的头发宛如圣母一般垂在脸上。然而比起成家榴,未免有些家常。她虽受的是西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很起劲。她亦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然而她在傅雷身边似乎永远只扮演伴读书僮的角色,只负责在旁边为他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从未曾想过要喧宾夺主,更不会去占据书房的中心位置。
朱梅馥关心傅雷的一饥一寒,夫妇与朋友同去游天台山,登山途中,肚子饿了,她拿出为傅雷准备的一缸子猪油黑枣给大家解饥,一层黑枣一层猪油,一层层放在白瓷缸里,蒸得稀烂。然而在傅雷眼里,她的好总归是家常,有时亦如这猪油黑枣一般,甜得发齁,令人起腻。小说中,他对成家榴评说他的婚姻:“因为她比我还可怜”——他刚回国时失望而又孤独,娶了这苦命的穷亲戚,还是一样孤独。
而成家榴在他眼中就好比是十六世纪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画笔下的女子,肌肤若冰雪,绰约宛若处子,缥缈如鸿影,不知何处来,亦不知往何处去,眉梢眼角的妩媚与惆怅,能触动“最复杂最细致最轻灵的心的颤动”。唤起神秘的东方想象,他对她的爱,就好比是细颈大肚的长明灯,玻璃罩里火光小小的颤动是忽明忽灭的节拍,然而世上哪有什么长明灯,最终还是澌灭在黑暗中。
任何细微的事物都有永恒的自由。日后,当他穿行在生命黑暗的河流里,他终究不会忘掉那段爱恋,草长莺飞,春色无边,他们活得青葱烈马,恣纵而不傥。在他心中,她永远是那胭脂凝妆的娇俏模样,风掀起的裙边,阔大清凉的一叶,永远唤起他心中的妩媚与怅惆,无边无际。
三
生活中崇高的事物,譬如爱情,一旦出自庸人之口,就会变得伧俗不堪。张爱玲绝不是庸人,然而《殷宝滟送花楼会》却为了讽刺,将事物夸大扭曲到流于荒诞。反倒失去了深度,在里面,读者窥到了人性中毫无知觉的自私和情有可原的冷酷,然而,长日将尽,却看不到慈悲。分明是文学体裁,然而高度重合的人物特征,张爱玲生生将这段情事演绎成了一段流言。这篇小说的发表,导致成家榴匆匆嫁了空军军官,这桩仓促的婚事不久以离婚告终,傅雷则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曾说:“《金锁记》的作者人品竟是这样低劣,真是错看她了。”
张爱玲完全忽略掉了傅雷于那个年代的意义:磅礴无边的夜色,傅雷发出的声音是远处传来的海浪的呼啸,亘古不屈。张爱玲的思辨力并不孱弱。她的此举,不过为了回击一段因文学评论而起的私人恩怨。倘若她的内心足够温暖,她会把傅雷和成家榴的爱情写成一个美好而深邃的故事:人迹罕至的冬天,漆黑的森林里,枝头的残叶上覆盖着糖粉一般的冷霜,有风呼啸而过,森林里面住着孤独、纯洁、笨拙且不善于处世的人物,他蕴含的哲学思想使得他通身散发着月华般的光芒,虽然微弱,却足以影影绰绰地照见森林轮廓。富贵出身的她,有着大小姐的无所顾忌,但仍旧有一颗在旧式道德与新式文明之间徘徊的灵魂。她被他的光芒吸引,情不自禁地走近了他。虽然他们的爱情,终究只是一场春梦,然而哪怕是只有一颗砂糖的爱,依然在人性的黑暗中呈现出爱的底色——那是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
四
傅雷与张爱玲,都是天才式的人物,两强相遇,当然有心契神合的地方,然而他们的脾气,一般乖僻固执,龃龉与冲突在所难免。
她偏爱薄弱狭小的题材。而他却喜欢史诗般阔大的题材,他的表达公式是有情操的,而她正年轻,正是喜欢炫技的年纪。
他们的童年都刻着深深的伤痕,张爱玲自是不消说。傅雷幼年丧父,性格刚烈的寡母奉行的是斯巴达式的严苛教育,“既无伯叔,终鲜兄弟,复寡朋友”,“茕茕独立”,“尘世的荒凉落寞”,养成了傅雷谵狂的禀性。傅雷的书橱上有一个《封神榜》中雷震子的头像,雷震子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傅雷常以雷公自况,他的批评性的言论辐辏成行:
在文艺方面,傅雷素来口味挑剔,他说司汤达的作品太偏重于家常琐屑,莫泊桑的布尔乔亚看来太怪腻,罗曼·罗兰的那一套新浪漫气息令人头疼。比对他对张爱玲的文艺批评,绝不是特别苛刻或掺入个人恩怨,他盛赞张爱玲作品“太像奇迹”,而她的《金锁记》则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
然而他认为与《金锁记》相比,《倾城之恋》标志着迅速崛起的张爱玲,旋即又走向了下山之路,而且正在一步步地下着山。他说《倾城之恋》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他批评张爱玲题材的狭小:“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的,灰暗,肮脏,窒息与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
傅雷进一步批评张爱玲的炫技:“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那么充其量也尽能制造一些小古董。”
傅雷并不否认张爱玲出众的才华,但他却说:“才华使人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然而不能珍惜自己才华的人,亦易为才华所累。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
柯灵公允地称这篇文学评论为“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然而年少成名的张爱玲,像一株生机勃勃的藤蔓,谁也不知道那藤蔓下一刻会往哪里蔓延,因此也就感觉处处蓄势待发。
她势必要回击傅雷,她驳斥他的观点:说她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傅雷崇尚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他立志要像普洛米修斯那般,从天上窃取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张爱玲偏要令光辉灿烂的英雄沙尘濛重,不独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世界虽然辽阔,但英雄同样局限于男女情事,甚至更为卑琐。张爱玲借成家榴的口说出她对傅雷的怨毒:“他那样的神经病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四十年以后,当张爱玲不再年轻气盛,往昔冲突、憎恨、误解终于烟消云散,张爱玲终于认同了傅雷的观点。她在那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惟一的爱情。”倘若她进一步地了解傅雷,或许,她会认为,傅雷尽管会固执乖戾,然而所有的批评都是从善意出发,是推心置腹的表现,不羼有任何杂质。
傅雷与成家榴的爱情虽然因那篇小说拐了一个弯,然而却远未终止。接下来的故事有如仁慈博爱的教义:圣母是慈母,耶稣是娇儿,天地间是无边的爱。当耶稣向鸟兽说教时,称燕子为我的燕姊,称树木为我的树兄。他们之间就有那般和谐。
而成家榴也远不是张爱玲所描摹的那种肤浅女子: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傅聪去香港参加演出,成家和与成家榴姐妹热情接待了他,令傅聪“在多少年离乡别井,思亲怀国之后,受到了慈母般的温情”。傅雷为此写了很热切的信致谢。
晚年的成家榴依然有着无猜的心情,傅雷坚强的气禀、宣泄如沸的热情仍旧占据她的思念。她对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过往的一切像尘土一样,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吹走,然而一切的一切,宛如波提切利的代表作《维纳斯的诞生》:掌管着爱与美的女神,站在贝壳的中央,初生般美丽。
五
关于傅雷与朱梅馥的婚姻,张爱玲只见其小,未见其大。傅雷曾说:“自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相比成家榴的妩媚,朱梅馥有如高僧隐士,隐藏得深沉,初见平平,却渐看渐佳。朱梅馥的平淡与柔软并未削弱傅雷平素的阳刚之气,傅雷的暴烈,到朱梅馥这里,像风穿行在藤蔓之间,她的错落变化,既疏可走马,又密不透风,终究是令他锋芒收敛,渐次趋向安宁。
朱梅馥爱傅雷,就好像包法利深爱爱玛,或许包法利不够懂爱玛,然而,宇宙之大,于包法利而言,大不过爱玛衬裙的丝裙边。世间有一种爱,原本不是建立在知音般的相契与呼应,而是平淡而柔软地爱着,通过寂静战胜时间。
然而张爱玲却处处鄙薄着,《殷宝滟送花楼会》那篇手稿留存至今,张爱玲端庄雅正的簪花小楷,在柔婉之中隐然有刀光剑影之气,仿似兵家写散文,细节虽丰惟但关键处却语焉不详。
张爱玲以为他们的婚姻那么庸常,就好比是春天的窗户里太阳斜了。远近的礼拜堂里敲着昏昏的钟。连朱梅馥打理的家政也是庸常不堪:仆人们搭了铺板睡觉,各有各的鼾声,在灯光下张着嘴。竹竿上晾的蓝布围裙,没绞干,缓缓往下滴水,“搭——搭——搭——”寂静里,明天要煨汤的一只鸡在洋铁垃圾桶里窸窸窣窣动弹着,微微地咯咯叫着。令人生出一种亵渎般的感觉。
在书桌上绿玻璃罩的台灯映照下,朱梅馥和孩子每人咀嚼着极长极粗的一根芝麻麦芽糖,小孩也探过身来看看母亲手里的报纸包,见里面还有两块糖,便满意地又去吃他的了,再想一想,还是不能安心,又挨过身来要拿,手臂只差一点点,抓不到,屡屡用劲,他母亲也不帮助,也不阻止,只是平静地想着她的心思,时而拍拍她衣兜里的芝麻屑,也把孩子身上掸一掸。小说中,张爱玲依然借了成家榴的眼光打量朱梅馥,成家榴回过眼来看了傅雷一下,很明显地是一个问句:“怎么会的呢?这样的一个人……”
同样是描写朱梅馥,杨绛却使一切事物都沐浴着爱娇的气韵:她称羡傅雷书斋的格局,她说书斋里的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送给梅馥的。傅雷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个人有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啊!梅馥是文静的,但不细心,傅雷则一板一眼,有条不紊,看完了书,一定要放回原处,梅馥则粗心大意,看了书随手一放。遇有这种情形,傅雷会批评她乱拿乱放,梅馥并不介意,总是笑着说,保证下次改过。而下次又是依然故我。
他们的家居生活和缓细密,朱梅馥带着女性特有的温暖、唯美的气息,阔大而家常。他们的家居生活是“日日是好日,叶叶起清风”般的绵长。
朱梅馥与傅雷处处不同,然而她与他的搭配浑然天成。傅雷性情犹史诗般夸张,狂暴,热情,绝非一般人能够容纳,然而朱梅馥仿佛是某一段清澈的河流,抑或是草木幽深的森林里成千上万的细小叶片,有着与众不同的清凉与安宁。
六
虽然天才很多时候是使性的,张爱玲那般贬损傅雷,然而,在小说中,她劝成家榴另觅他人,成家榴带着笑叹息了:“爱玲,现在的上海……是个人物,也不会在上海了!”纵是不甘愿,张爱玲还是认可傅雷是上海标志性的文化人物。
在草长莺飞,春色无边的季节,当我们因为傅雷重新打量上海这座城市,当我们追忆、回想、凝视这座城池的光辉岁月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必定绕不过这傅雷。
傅雷出生在上海,他曾短暂地离开上海,终究难舍故土,回到了上海。在傅雷年少失怙时,他与寡母在上海相依为命,锦瑟年华时,他在上海遇见心上人成家榴,上海亦是他与爱人朱梅馥终老之地。在死亡彻底的安静中,他的才华长存于世:
傅雷是天才的预言家,他的识见,今天听起来依然如此高亢及富有启示性。他深入地解析“文艺”是什么,他提出的历史观充满真知灼见。他对历史的诘问,对畸形现实生态的疏离,既是一种批判,更是一种姿态。他相信:天下无论怎样经散纬脱,脉散丝分,最终都必须遵从万世的法则、永恒的秩序。
而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更臻炉火纯青之境,他的译文丰沛而娴熟,饱满的张力,谨慎的节奏以及色彩变幻的辞藻。读了他译作的人再也不能将他的影子从心头抹去。
阅读《傅雷家书》,往往细处动人,有与古意相似的从容,一方面,他唠叨、牵挂、敏感、苛求、事无巨细皆要嘱托。另一方面,他又有着超凡的领悟力、渊博的学识、澄明的人生哲学,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有时候,甚至会令阅读者中断家书的绵延性,停在某些才华闪烁处赞叹不已,感受到不同艺术的殊途同归。
直到今天,当我们谈及傅雷,我们依然要承认他浪漫气息很重,感情用事,不是很沉着的人,然而他那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就像傅敏在编《傅雷家书》时,他谨将此书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那本书又何尝不是献他的父亲傅雷与母亲朱梅馥,献给他们曾经被温暖的光和无穷的诗意照耀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