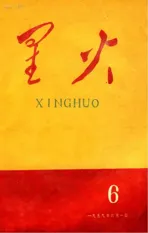喊 惊
2017-11-03吴文星
○吴文星
潮散文
喊 惊
○吴文星

吴文星,1994年生,江西瑞金人。有习作发表于《诗刊》等刊,曾获“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第四届野草文学奖”“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奖”。现就读于赣南师范大学。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楚辞·招魂》
一
“狗娃儿,唔惊唔吓呵,在哪东南西北吓着哩来归困觉了,狗娃哎,来归困觉了,在哪沟儿坎儿、山里坳里跌了撞了,吓着哩来归困觉了……社公老太各路菩萨佛祖保佑我家狗娃平平安安、脚踏四方、方方顺步,石头都不会绊倒一次呵,床公床母呵,保佑我家狗娃吃得困得,一觉困到大天光呵。”傍晚时分,外祖母靠门站着,手持三支线香,引颈西望,对着即将沉下来的茫茫夜色,高声呼喊。喊声由低到高,悠扬苍茫,邈远空蒙,一阵一阵,似徐徐吹过的晚风,越过田野,穿过村庄,攀上远处黛色山脉,纷纷扬扬,浩浩荡荡,漫浸在寂静如水的夜色中。
打记事起,每当我精神萎靡,吃不下饭,露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外祖母必说我是受了惊吓,要为我“喊惊”招魂。说来也奇怪,只要经外祖母这么一喊,第二天我就能活蹦乱跳,恢复如初,“病”就这样神奇地祛除了,远比打针吃药看医生来得管用。母亲不会“喊惊”,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把我送到诊所查病打针,或是带回一大堆的西药让我吃,折腾了好几天,却不见什么起色,就算有效果也来得慢,远不及外祖母的“偏方”效果好。至今我也不能以科学来解释这“偏方”的奇效,这让外祖母在我眼中从小就有一种神祇般的光环。我知道的是,每当我“丢了魂”的时候,外祖母一声声熟悉而悠扬的喊惊声又会把我召回家。
记忆中,村子里会喊惊这门“手艺”的人并不多,外祖母并非神婆,但喊惊是她的“专利”。据外祖母说,喊惊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受惊者被吓的路口喊惊,另一种如果受惊者已记不清被惊吓的具体地点,也可以在自家门前喊。家乡的喊惊一般就这两种,但据说广东惠州地区却分路口喊惊、求神喊惊、设坛喊惊三种,形式也和外祖母口中的略有不同。就我所看见的,喊惊并不简单,可以说是程序繁杂,毕竟,要把丢了的“魂”给找回来,马虎不得。在喊惊之前,要确定你是不是受了惊吓,以及施吓者的身份,即“查症”,外祖母的话是,有的是阴人吓的,有的是活人或者动物吓着的。外祖母往往会用酒饼(农村用来酿制烧酒的一种白色饼状的酵母)和黄栀子(栀子树的果实,成熟后呈橘黄色)用布包住捣烂,敷在手心,不断擦拭,用外祖母的话说,男左女右。待擦到大鱼际开始泛青时,外祖母便能根据手掌纹路脉络大概推出受吓者受惊的地点和施吓者的身份,完成这一步,就算是“确诊”了。接下来就要做好喊惊的准备,路口喊惊的话,需要准备好香烛、纸钱、元宝,虔诚者还会备上“三牲(三种家禽,一般是鸡、鸭、鱼)”和“水饭(粥加凉水)”。傍晚时分,外祖母便带着这些供品来到受吓者受惊的三岔路口,点燃香烛,焚烧纸钱元宝,把供品摆好后,就开始向着空蒙的夜色高声呼喊:某某哎,唔惊唔吓呵,在哪东南西北吓着哩来归困觉了呵……这样把之前的喊词喊上七遍,喊一句就在路边拾一个小石子,拾够七个就可回家。把这些小石子压到受吓者的枕头底下,并在枕头上拍三下,念一遍“床公床母呵,保佑某某吃得困得一觉困到大天光呵。”就算完成了整个喊惊仪式,受吓者“丢失的魂魄”也就招回来了。这里之所以用“某某”,因为村子里找外祖母帮忙喊惊的可不少哩!
小时候,以为喊惊是外祖母的专利,在村里,我没听过除外祖母以外的人喊惊,长大后才知道,“喊惊”作为民俗,早在西周时就已盛行。《楚辞·招魂》中记载的招魂与外祖母的喊惊相类似,可见喊惊的文化渊源颇深,清人宋湘所作《盂兰词》这样描述:“鬼不怜人人怜鬼,盂兰大会夜如水。削竿挂衣钱剪纸,蜡泪倒流风旋起。”那是乾嘉年间的事,如今,惠州地区,衣服已多挂于屋檐或放在筲箕里,也有拿在神婆手中的,至于家乡,甚至用不到受吓者的衣物了。
二
童年的时候,喊惊对我来说意味着神秘和庄重,像个神圣的宗教仪式。看着外祖母准备好香烛、供品,口中念念有词,虔诚而庄重的样子,让我对这个繁杂的仪式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充满敬畏。有时掉魂掉得严重,就要连续喊上七天,每天喊七七四十九遍。我像个等待受洗的基督徒,小心翼翼地待在家里不敢出去,生怕不小心破坏了这个仪式,再也找不回魂魄。
夏天是最热闹的季节,也是外祖母的季节。山里的孩子,在这个季节最野,在荒岗野地里乱钻,掏螃蟹,逮青蛙,黏知了,摸鸟窝,下河洗澡……不管水深路野,哪里有险往哪里钻,免不了要迷路,跌跌撞撞,受了惊吓。邻里邻舍的父母都带着孩子来请外祖母帮忙喊惊,于是到了傍晚,外祖母往往忙得不可开交。忙完“查症”又忙着准备喊惊的香烛供品,一个接一个地喊,整个村子在她的喊声中慢慢沉入梦境,喊完全部孩子,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喊累了,她就一手扶着门框喊,一直以来,简陋的柴门总有一处被磨得又黑又亮。得亏那时候外祖母有一副天生的好嗓门,喊了许多年,时间没有收回这副好嗓子,在一阵阵喊惊声的淬炼中,嗓音反而愈发变得淳厚、敞亮、高昂有力。有时来的人多了,外祖母就早早地开始喊惊。那时太阳还没下山,外祖父还在田间干农活,一边是外祖母苍茫悠扬的喊惊声,一边是外祖父急促有力的喊风声,两相呼应,成了村子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故乡的村庄,就在这一唱一和的喊声中,卸掉了一天的疲累,开始享受一个有歌谣入梦的夜晚。
背井离乡的日子,外祖母常常来到我的梦里,唤我回家。夜阑人静时,记忆就不自觉地回溯到那些与她有关的日子。外祖母手艺很多,除了喊惊,她还会编竹篓,扎扫帚,给发烧的小孩扎耳朵放血,治咽喉肿痛,用草药医治那些被狗咬的人,做衣纳鞋,做好吃的黄元米果、籼米冻……她还认识许多草药,她把那些草药洗净晒干之后,储存起来,在那个医疗机制不太健全的年代,那些草药治好了许多村里人的伤风感冒。小时候,最喜欢吃外祖母做的籼米冻了,炎炎夏日,一碗晶莹剔透又清凉可口的籼米冻,加上少许白糖或陈醋,就是一顿珍馐美味。籼米冻不仅卖相好,与超市里的果冻并无二致,吃起来还滑润清爽,绝对是降温消夏的必备食品,许多漫长难熬的夏天,都在一碗碗籼米冻的滋润下,变成了快乐而易逝的时光。
三
喊惊声从远古穿越而来,跨越千年,至今仍余音绕梁。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外祖母凄婉悠扬的喊惊声中寻寻觅觅,走进走出,跌倒了又爬起来,逐渐长大。可是外祖母,她为我,为许多人喊惊,卖力地喊,无休止地喊,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外祖母就像那些被时间磨砺千年的喊词一般,无形中被岁月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近年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她的嗓音不再如从前那般铿锵有力,变得浑浊而嘶哑,她开始记不清那些熟悉的喊词。她终于把自己给喊老了。
我见证了许多事物的老去,都没有外祖母的慢慢老去来得触目惊心。春天的时候,外祖母得了一场重感冒,喉咙受到重创。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拢着一只烘箩(农村一种竹篾编制内盛瓦缸的取暖设备)坐在断墙下,静静地晒太阳,见到我来,想和我打招呼,却只能发出一些“呜呜嗯嗯”的喉音。她努力把嘴唇往上拢,想叫出我的名字,却发不出声来,最终只能任由干瘪的嘴唇向两边落下去。她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转身去把家里的零嘴都拎出来让我吃。那一刻,我内心突然滋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我害怕她就这样永远地保持缄默,陷入寂静无声的泥淖里,让我再也听不到那散落村庄、田野和山坳的喊惊声。时间和人一起,把她消磨得疲惫不堪。
她年轻时就患上了皮肤病,是顽疾,说是坐月子时去干了农活,感染上了痒病,之后就一直没有根除。几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她都要走上几公里到镇上的小诊所去打针,尽管去一次只能维持几天的效果,病痛不断地抽走她身体中残存的那点青春。她把裤腿卷起来让我看,像受伤的猎物向猎人展示伤口。我注意到,那不是一条正常的腿,首先是出奇的小,和七八岁的儿童的腿一般粗,腿上几乎没什么肉,只剩下一圈皱巴巴的皮慵懒地耷拉在上面,老年斑星罗棋布般占领了整条腿。最令人咂舌的是,由于整日用手抓挠,整条腿坑坑洼洼的伤口与老年斑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还在流血,红色和黑色像下围棋一般,都想霸占这副了无生机的皮囊,用血肉模糊形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外祖母都在扮演一个喊客的角色,她把许多人从荒野里喊回家,从小喊到大,从懵懂喊到成熟,喊不回来的是时间,是自己的青春。
“一觉困到大天光”,这是外祖母对许多人的祝福,可她自己却不在此列。近年来,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人老了,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她早早地就上了床,可直至深夜,还能听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有时实在睡不着,她干脆爬起来,在她的老式衣柜里摸摸捡捡,整理衣服,或是把归置好的东西又倒腾出来再整一遍,或是早早地到厨房去,把明天要煮的米先浸在水里,准备好锅碗瓢盆,以此来消磨无眠的漫漫长夜。到她觉得实在没什么值得动手时,她才躺回到床上眯一会儿,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公鸡打第一声鸣时,又见她窸窸窣窣地爬起来,在黑暗中迎接新的一天。失眠让她的世界始终亮如白昼,却更加照出她的衰老,她的疲惫。
不知道人的衰老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不是始于记忆的丧失。或许当一个人开始丧失记忆,与此同时,她也迷失了方向,丧失了温暖。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经常把我的名字叫成我哥的名字,有时刚和她说完我在某地读书,转瞬她就自问自答地说:“你是和你妈在一块工作吧,离得近好啊,相互有照应,菩萨保佑我阿文顺顺利利、步步高升,赚得多嘞。”像一个不堪负重的行者,在时间的无涯里,丢包袱一般,她把许多记忆弄丢了。我想或许她并不是盼着我长大,只是时间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在她心里被无限地拉长了,产生时间溜走很多的错觉。她不能相信,自己已经满头银发,半个身子埋进土里了,一手拉扯大的外孙身上却丝毫没有变化,年年月月,他一直在读书,却不见长大,那样的话,时间怎么是公平的呢?或许我尽快步入社会,赚钱很多一直是她的一个愿望,她希望我能在经济上接济她一点,因此她总认为我已经是个有经济能力的社会青年了。外祖母虽育有三子两女,可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子女都是庄稼人,经济条件不太好,也不是什么孝顺的儿女,在老人的赡养问题上都采用能避则避的策略,互相推诿。她年轻时辛苦操劳一辈子,老了,境况仍然丝毫没有改善。她很希望自己的外孙能够早日长大,给她一点哪怕只是经济上的安慰。
在那些记忆逐渐流失的日子,她终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慌乱来。外祖母是属于旧时光的,一生都在黄土地上耕耘的她,“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这样的词对她来说太陌生、生硬了。外祖母只是在不咸不淡的平静日子中,安静地、本分地履行着大自然对她生命所做的安排,一切都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她自然有过反抗,也是顺其自然的。那些儿女们偶尔给他买的鱼肝油、合生元、脑白金,据说是可以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的,她都很自然地接受它们,每天按时服用,能不能见效就不是她能预料的了,她只是以天性的本能去对付时间,想留住一些东西。可真要流走呢,留不住呢,那她也没办法,她必须接受。
四
外祖母曾多次把我喊“回家”,可是如今,她自己却离“家”越来越远。去年冬天,她生了一场大病,三个儿子商量了好一阵子才答应把她从县里的医院转到市里去接受治疗。不能说外祖母不会感到心寒,也是从那时起,她的记忆丧失达到了极限,她开始对“家”有十分强烈的归属的渴望。她出院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去接她,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她像个孩子一样,死死抓住铁栏杆不肯上车,她说她不想来这,她要回家。她甚至不认识她的儿女们,她说要“娇子”去接她回家,别的人她都不要,可是当时母亲就在她身边搀着她,她认不出来。她盯着母亲,直勾勾地看着她,带着几分恍惚,最后突然拼命地甩开母亲的手,大叫着:就是你,就是你,你把我家那个老不死的拐走了是不是?
很多时候,我觉得人就像是一只陀螺,被时间这条看不见的鞭子抽打着,无法停下来,即使是原地踏步,亦被速度控制和奴役。可是外祖母这只陀螺,却终究要停下来了,她毕竟是累了。她一生都在琐碎的生活中忙碌着:小时候忙着长大,分担家务;长大后忙着结婚生子,盼孩子长大;后来忙着抱孙子,忙着老去,忙着了却这样那样的日子。夏天的时候,她忙着翻拣晒谷坪上的谷子,忙着晒干刚摘的青菜;冬天的时候,她忙着缝缝补补,为家人准备好过冬的衣裳,忙着敲碎小石潭冻起来的冰棱,洗掉一家人的脏衣服;春秋时分,她忙着播种和收获,在田头地垄卖力地挖坑刨土;晴天,她忙着到山上打两捆干柴,雨天她忙着奔回家里收衣服……现在,她老了,她想要“回家”。
外祖母的家不大,是一幢只有三间小房间的土坯房,逼仄而苍老。这几间昏暗潮湿的土坯房承载了她的一生,她在这里结婚生子,在这里养儿育女,在这里生病老去,在这里晨钟暮鼓按部就班地经营着生活的柴米油盐。可是现在,她整日待在这个土坯房里,却越来越找不到家的位置,不知道这昏暗的小房子,把外祖母的家藏到了哪个角落。患病之后,她性情乖戾,像小孩子一般淘气,时常把喂到嘴边的饭菜弄得满身都是,故意把手边的碗碟摔碎,无缘无故把身边的人骂一顿……她时常吵着闹着要回家,母亲和姨妈们耐心地照顾她,跟她解释这就是她的家,好说歹说哄住她一会儿,过一会她又用狐疑的眼神盯着母亲,接着跑到各个房间看一遍,出来后大声吵着这不是她的家,她那老鬼都不在这,他的床也不在了,墙上挂着一个陌生男人的照片,她不认识。其实外祖父的遗照已经挂在墙上好多年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外祖母和我们告别的一种方式,她知道不久后,她也要随外祖父而去,她用这种不讨喜的方式来折腾我们,消磨我们的耐心,让我们对她感到厌烦,以至于在她离开时,我们不至于悲痛欲绝。她大张旗鼓地喧扰我们,恰恰是为了静悄悄地走。
长大后,我不再让外祖母为我喊惊了,从前我是她忠实的拥趸,如今我开始“迷信”一种叫科学的东西。村里请她喊惊的人也少了,谁家孩子有个伤风感冒、精神不振什么的都往医院、诊所送,他们不再请外祖母去给他们“查症”。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他们非但不相信外祖母的“医术”,甚至到处造谣诋毁她的人品。门前的桂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好多年,都不再有人来采去做桂花糕。
五
很多年后,我终于明白,外祖母想回又回不去的那个“家”,不在那个晦暗潮湿的土坯房,不在任何一个可触可感的地方,它早已不是一个空间概念,那是一段时光,一段回忆。
那个家,有她曾经懂事孝顺的儿女们,有调皮捣蛋的孙子们,有蜷在柴堆晒太阳的阿灰,有欢声笑语,有轻浅时光,日子有盼头,那时,外祖父也还在。外祖父的去世,首先让外祖母感到这个“家”的缺失,一些时光从此隐退,寂静的空气里,一种崩塌破碎的气息正在慢慢酝酿,弥漫了她整个黯淡的晚年。那段时间,她整日坐在那幽暗逼仄的小房间里,不进食,也不睡觉,头发一下子由灰白变成了银白,瞬间老了许多。似乎是为了赶上外祖父的步子,来填补他们之间相差的那六年的距离,以为这样,就可以向外祖父靠近些。她的目光,穿过小木窗外照进来的一束阳光,许多尘埃在那里翻滚,跌落,最后逃出视线之外,她怔怔地望着对面空荡荡的床铺,眼睛都不眨一下。以前,那里睡的是外祖父,现在,只剩下几块寂寞的杉木床板,孤零零地躺在那,偶尔发出一些沉闷的“吱嘎”声。
外祖父去世的日子,在惊蛰的前两天。那天,外祖母把她一生的眼泪都哭出来了。我从没见过她那么长时间那么歇斯底里地哭过,即使是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她也有相当的克制。她的哭声推开那扇老式木房门,拂过庭前的桂花树,越过刚刚翻过土的田野,传到了全村人的耳朵里。
外祖父得的是肺癌,从医院回来,已经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那天下午,我在离外祖父几十公里的家里坐着,忽然有一种气闷心慌、心神不宁的感觉。半小时后,姨妈来电,电话那头,她泣不成声地说:“外祖父走了,你们过来吧。”来不及锁门,我和母亲便匆匆往外祖父家里赶。我知道,就算没有那通电话,外祖母撕心裂肺的哭声也会把我们的灵魂第一时间召回到外祖父身边。她的哭声,把这个噩耗传递给村里的人,于是,更多苍老和年轻的灵魂都陆陆续续聚涌过来,来送走一个安静而淳朴的灵魂。外祖母的哭声,让我想起那些没有风的夏天,那些在田间地垄劳作的日子。那时候,没有风吹过,感到热了,外祖父就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身子,拄着锄头,双手曲成喇叭状放在嘴巴前,铆足了气劲,对着眼前开阔的田野,大喊一声“呜哎”,外祖父管这叫“喊风”。说也奇怪,经他这么一喊,马上就有一阵清凉的风拂过我们满是汗水的脸庞,好不惬意。遗憾的是,外祖母的哭声毕竟不像外祖父的“喊风”那般灵验,也没有她的喊惊声那般的奇效。她的哭声响彻了整个春天,可最终,她也没能把外祖父的魂灵给哭回来。
惊蛰之后,很快就到了谷雨,播种的季节,他们把外祖父种回了地里,一如他曾经种下的那些稻子、桂花、菖蒲草。打那以后,外祖母再没喊过惊。
六
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外祖母,离开阵阵喊惊声,我继续生活了许多年。这期间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听了许多风格不同的歌谣,看了许多不同的风景,可所有这些,都抵不过故乡的一声喊惊声。我离开乡村,开始在城市生活,在霓虹闪烁的夜晚寻欢作乐,为生活、为所谓的梦想、为许多填不满的欲望摸爬滚打。可在夜幕降临、人走茶凉之后,孤独寂寞像潮水般涌过来,生活的失魂落魄在刺眼的灯光下暴露无遗的时候,我突然十分想念那些故乡的傍晚,那些悠扬苍茫的喊声。恍恍惚惚的梦里,我看见外祖母正倚着黑黢黢的门框,大声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