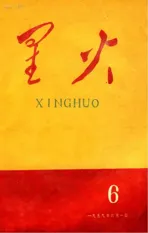猜测上帝的生活
2017-11-03李路平
○李路平
猜测上帝的生活
○李路平

李路平,作品见于《红豆》《广西文学》《诗探索》《诗刊》《星星》《南方文学》《鸭绿江》《星火》《创作评谭》等,曾获全国高校征文诗歌类二等奖,入选《2014中国最佳诗歌》《2013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等,2014年第七届中国·星星诗歌夏令营学员,江西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广西文学》杂志社。
一
单行道车辆稀少,路灯昏暗,似乎行人也避让了,稀稀拉拉各有心事,相对无言低头而去。经久耐用的方格砖把底部的泥土翻上来,隔不远塌下一块,砖头东倒西歪,就像满怀恶意,等待着那些三心二意或漫不经心的人,随时准备来一下,让他们尝尝生活的苦头。亚热带的密叶树木分布在路旁,昏暗的灯光映现绿色,透出新鲜树叶的经脉,脆弱而真实,为夜晚的道路笼罩了一种隐秘的气息。他就在淡绿的光影下,在高大板根切割出明暗的树窝里。
路这边的店铺半开半闭,店主面目慵懒,对行人无动于衷,握着手机,把一具具肉身留在原地。树应该都上了年龄,一排望过去,高高低低的板根错落有致,这个城市另外一条主干道两边专门开辟出很多景观,一段一段,比如藤蔓植物景观、椰树景观,其中就有段板根景观。我数次经过那里,竖着牌子的地方树木幼小,根本还没有形成板根,它所要宣扬的东西仿佛不争气似的,全部藏在自己的寂静与孤独里。这条路上的树从一块块没有铺地砖的方格子里钻出来,除了它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的植物,所以他才能安然地蹲靠在那儿,裸露的泥土上扑着黑黑的影子,树身干净,曲形的板根像一双大手将他抱在怀里。
他戴着顶无边帽或是瓜皮帽,一看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穿着浅黄的土布衣服,弓身驼背,目光斜靠在地砖上,脚上踩着一双布鞋,和脚下的泥土不甚分明,灯光轻缓地铺洒在他身上,在春天清凉的夜里,流淌着一股暖意。他的怀里抱着一把二胡,一手摁弦,一手拉弓,舒缓的音乐在绷着蛇皮的音箱里喷溢出来,却听不出是什么旋律。这些老旧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已经过时,关于它的点滴散落在混乱的记忆深处,数出《梁祝》《二泉映月》,便好像已将脑袋掏空。他的姿势,他隐藏在额头倾泻的暗影里,许久不变的双目,可以猜度他沉浸于自己制造的音乐里,这或许是漫长时光压榨之后,他所能交付出来唯一的东西,那么形上,是路上奔驰的单一声调的另一种节制呈现,仿若那些采集光影的人,在乏味刺眼的光线里分割出异彩,在一颗裹藏的心灵的操控下,引人入幻境。他也许另有所想,在这条音乐之河里思绪难抑,回想往昔、爱情,或者白天的苦难,他屈膝、咆哮,或者静坐,一切都被河流所吞咽、咀嚼,最后化为平静,在这个夜晚飘逸出来,与微风缠绕,在微光里游行,像一群无形又不忍离去的鱼群,荡漾的水波以他为圆心。
身前的小碗将一切交托无遗。小碗总是无法装满,碗里总是无法出现面额大一些的纸币,只有零星的硬币和浅绿色的纸币,夜晚的灯光洒进碗里,好像绿色又深了一些。这种绿颜色却没有树叶般的活力,它淤积在粗糙的碗里一动也不动,像是残渍留下的霉斑,这多少会让无意看见的人心生厌恶。但路过的行人有几个能视若无物呢,遇见行乞或卖艺的人,差不多都会不由自主地扫一眼他们的碗钵,但仅仅只是看一下罢了,他们早已被世间的不善所拖累,与其被伪善欺骗,大部分人选择压住内心的善,而以怀疑和冷漠应对。因而那些就要经过他的人,通常在两三米开外,就会从走踏的这排地砖换到另一排,尽管前路平坦,他们还是走出了一个优雅的弧形,且不回视。那些鱼群一般的乐音忽然变成了一股无法摆脱的气味,在他们的身后回旋、消散。他们并不需要它,有的耳朵里喷洒着摇滚的旋律,有的专注于电话那边甜蜜的耳语,有的像一个梦游的粽子,直到他面前才恍然发觉。
我时常就是这样的一个粽子,也时常对依凭残缺伸手讨要的人群敬而远之,他们游离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不经意就会出现在面前,让人措手不及。但我并不排斥凭藉一技之长在街巷里讨生活的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一样,我尊重他们的劳动,就像期待他人也能如此待我,甚至在初次见到他们时,我已决心以对一个听众或观众的要求,主动给予他们微薄的回馈。我曾因此迁怒于自己的无力,就像遇见世上一切令人遗憾的事情,除了自责,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软弱的人从来如此。
二胡的声音牵着我走到他这里,这个瑟缩在板根窝里的人始终没有抬头。墙板一样的板根包围了他的大部分,他只有三分之一显露在我面前,微光照射在那双黝黑的手上,那么坚硬的颜色,似乎一切都无法将它穿透,只有琴声悠扬,如虚无的流水安抚着夜晚。我躬身在墨绿里投入一点紫,随即又在乐音中化开,一圈圈的涟漪如推叶片般,将我越送越远。
二
他每天都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清晨或傍晚天气稍凉的时候,会扣上一顶帽子,草绿色,大多数人军训时都曾戴过,这是一种廉价、劣质的迷彩帽,因长久没有清洁而遍布污垢,远远看来迷彩却更加鲜明,端端正正地佩戴在毛发稀疏的头顶,露出一张黝黑的脸。他的脸从未有过完整的表情,比如拉动额头的纹路、带出眼角的褶皱、拧眉、眼珠活泛流光、多于八颗牙齿的笑容,这些仿佛永远无法在这张脸上呈现。
更多时候这张脸更像是一个面具,一个与所谓的“脸”完美合一的道具,而他就躲藏在这个面具之后。偶尔会“露”一下脸,短暂的时间里可以看见他的眼珠滚动一下,抿抿嘴唇,接着近于无声地朝向堆满各色废弃物的三轮车,低头对着车座的部位唱歌。也许没有人真正听清了他唱的什么,反而更好奇他的唱姿,弓着身子,双手舞蹈般向前一伸一曲,仿佛劝世之人,尽管苦口婆心,但仍然无法说动在场的任何一个,他只好将目光转向虚空,一些不会撇头、不会离去的事物,它们不会厌烦也不会反讥,能够虚心听他劝诲,因而也不会给他伤害。
真的不会有人给他伤害吧,他不是环卫,更像一个拾荒的人,每天比准点的上班族更早出现在这个“T”字形的三角地带,却要比上班族更晚离开,带着两三米高的纸板杂物,摇摇晃晃消失在暮色笼罩的十字路口。这里是城市最为破陋、最想遮蔽或改造的地方,自建房屋歪歪扭扭地挤占原本狭窄的巷子,越往里路便越窄,最后成为一个金字塔尖的模样。往上攀升的楼房用倒金字塔来形容也相差无几,有限的基地上建起一层后,第二层开始就往外挑出一米多,每一个窗台又钉上防盗网,有的再外挂空调或抽油烟机,原本隔门两三米的租户,到楼上打开窗子就可以握手而谈了。每天租住在这里的人三三两两最先打破城市的寂静,随后便慢慢热闹起来,独来独往或拖家带口,开始往外丢生活垃圾,不一会儿他的面前就会被各色的垃圾袋包围。用“包围”没有丝毫的夸张,时常他的三轮车上已经捆绑得摇摇欲坠,他还在低头翻捡着那些未曾挑拣出来的废品。摆在他身旁的垃圾更像是摆上餐桌的饭菜,被他挑挑拣拣之后,只剩下小小的一堆,其余的东西被一个神秘的胃消化了,只有这一小堆残骸,再无法提炼。最后他也会将原本杂乱的地盘收拾好,临走前变得干干净净。这个地方需要他,进出巷子的人并未露出嫌恶的表情,反倒是穿过十字路口朝这走来或是往十字路口而去的行人,路过时都小心避让,并不时回头看几眼。他也已经将这块场地当作家了。
这个城市属于南方少数几个最靠南的省份之一,夏季时间几乎占了大半年。他与其他拾荒者不同,从不沿着街道挨个垃圾箱翻捡过去,而是仿佛无处归依的游魂一样浪荡在大街上,没见他有过探头探脑在垃圾桶里翻找的时候。他就守着一块地方,停下车子,在车身上支起一把大大的遮阳伞,顷刻在阳光里挖了一个洞,车座便完全陷进阴影里。所有的废旧物品都像是自行跳上他的三轮车似的,没多久就装得差不多了。他不懒散,也不勤快,每次到手的废旧东西,都会被他拆解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般分好,缓慢地把线路上的铜或铝与塑料分离出来,把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拧开倒掉、压扁,把木板、纸板和泡沫分别捆在一起,把笔、损坏的玩具、玻璃珠这些小玩意单独放开来。做累了他就席地而卧,靠着纸板,或者一条乌黑的毯子,身边都是没有整理完的垃圾,苍蝇在他的身上飞落又飞起,从未见他驱赶一下。有时候车斗还未装载,他就仰躺在里面,因为车斗太小,双脚被围栏高高架起来,和任何被他丢进车里的废品一样,他随手也把自己丢了进去。有几次阳光猛烈,他弯腰钻进了车底下,勾着拖鞋的两只脚曲折地伸出来,把匆忙赶路的人吓得往边上跳,但他依旧泰然自若的样子,几个钟头一动不动。
他没有成为附近住户的谈资,也未曾遭受到他们或城管的驱赶,没有人打听他的来处,也不关心他的去往,他时常端起别人丢弃的快餐盒,挑挑拣拣吃进一些,但似乎从来没有因此生病,每天还是上班那样赶到这个一无所有的地方,稍微安顿,便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从没看见枯坐在巷口晒太阳的老人和他说过话,他们依靠着早已被摩擦光滑的墙面,眼睛半闭,似有似无地注视着擦身而过的人。没有人经过时,他们也会长久地注视着他,即使目光对视,也不流露好奇、亲近,彼此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然而他似乎也并不孤独,在杂味熏天的物件里翻来翻去,丝毫未受影响,仿佛这些气味完全不存在,他手里拿起放下的,如同菜市里的蔬菜,颜色鲜艳有样子,他的眼神里好像也流露出了亲近。偶尔还会有流浪汉从别处来到这里,他时常会端出一些剩菜残羹来招待,他们欢笑着吃完,便躺在这些快餐盒旁边,交头接耳,说着不甚明白的土话,远看像难兄难弟,近看又像朋友知己。有几次一个穿着干净的醉汉也加入进来,三个人席地而坐,一瓶白酒对着一些吃食,谈笑风生,好像凭空多了桌子椅子,多了楼房和空调,所有的行人都是从他们的世界之外走过,他们端坐在自己家里,犹如漂浮不定的游云,怡然自得。
每次从外面往回走,先在主干道转上有坡的岔路,顺着斜坡走上去是一只拴在水泥墩子上的猫,毛色枯黄,了无生气,天气舒爽时会爬到主人搬出来的空椅上睡觉,傍晚天黑就钻进放倒的纸盒子里,等着开超市的主人关门,把它锁进去。接着要穿过一家小餐馆,不大的店面却时常聚集了乌压压一群食客,晚饭时外边的路面也摆好了桌子,每张桌面上都坐着个铝制面盆,盛着满满一盆酸菜鱼,每个人都在狼吞虎咽。再往前走就会遇到他了。也许他的年纪要比我大一些,可以叫哥或者叔,但只是想想罢了,他站着的时候时常都背着人,捣鼓着三轮车上的零碎,见谢的头顶也与肤色相同,套在身上的迷彩服沾着尘屑,应该是刚睡醒不久吧。
三
好像从未有人与他说过话、打过招呼。
单位虽然是个文化单位,但在食堂里和饭桌上,却常常给人进错了门的印象,闹哄哄一群人,端碗、打饭乱糟糟的,转身就会撞到人,似乎女性优先的优雅也被丢到一边了。也许不该苛求,在这样的单位里女性似乎更占优势,男性反而有些“弱势”。食堂也不做闲饭,只能先到先得,由此大概也管不了礼貌或礼节,活命要紧,但校园里排队——这个时常被当作文明标志——的景象是没有了。男人们好像在办公室里压抑了半天,坐上餐桌便“咆哮”起来,天南海北,上天入地,国内外局势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动不动就要灭这个灭那个,时不时就要夹杂几句粗口,国骂反倒显得文雅些了,仿佛谈论这些不加上这样的声调和口气,简直就没有男子气概。
我时常会有意无意拖延去饭堂的时间,可能天生没有与人争抢的性格,宁愿在大部队变得稀稀落落的时候,装起电饭锅里煮烂的饭,然后随便找个地方吃掉。可是这样子也时常有尴尬的时候,饭堂里已经满满当当坐稳了人,要找一个位子着实不大容易,又不愿单独与女性围坐在一起,这让我变得犹豫,端着碗多找几次才能最后坐下来。有段时间我坐在那个最大的餐间里,所有的大桌子都坐满了,午饭时间成为这个单位最活跃的时刻,调侃、卖萌或高声谈论,仿佛每个人都找到并融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里,唯独门口的小“课桌”始终空着个位子。选来选去,还是和他面对面坐在了一起。
他是一个安静的用餐者,对周围的喧闹和讲述的各类事情并不烦躁与好奇。他也是所有用餐者里年纪最大的,估摸有八十多岁了,银灰色的头发依然茂盛,国字脸上是漫长岁月蜷曲的皱纹,眼神还是很有力量,只是丧失了着力点,对人只看一眼,便低下头继续吃饭。他的牙齿应该还很有嚼劲(换了假牙也未可知),与饭堂里所有人分享同样的吃食,每次都能吃干净。他的碗是老式的搪瓷碗,外面花白相间,手感较重,肚子要比开口大一些,像一个钵,看着也用了许多年头,而别人用的都是轻便材质的不锈钢碗,属于公家财产。他一手护碗,一手握着调羹,一勺勺将饭菜送进嘴里,细细咀嚼,慢慢吞咽,金属调羹与搪瓷碰撞的声音,是他用餐时发出的最大声响,在这个欢闹的空间里,一下下撞击着我的耳膜。
我初来这里,除了部门同事和其他有限的几个人,绝大多数的人于我而言都是陌生的,单位的人事变迁与蒙灰往事也概不了解,只是这样面对着一个老人,竟让我惭愧不已。那是内心最深处发散而来的愧疚,一种作为晚辈甚至是子孙的负疚,缘何让这样一位老人在该尽享天年之时,还蹒跚着来到食堂,在哄闹的空间里咽下无差别的饭菜?我无法知晓他,咽下用以维生的米饭之后,是否还暗自咽下了什么,一些难以言表而又不愿吐露的东西,甚至是一声叹息、一阵疼痛或一阵快慰,在共享食物的人群里,没有一个人能与他共享内心,一个步入迟暮之年的老人的内心!我想到了他的子孙,他们是怎样的一些人?在围着饭桌分享食物与快乐的时候,是否会想起这个老人,这个他们称为爸爸或是爷爷的老人?是什么缘由让他们决定,撤销他在桌边本该有的一个位子?那个颇为重要的位子,如今又是谁安坐着呢?他会是一个暴躁乃至无情的老人么?极致到子女无法接纳的地步?抑或是他们在很远的地方生活与工作,只在单位不开饭的周末,将他接回家里照顾?这些我无法看见,所以也不能表决,我只是不愿猜想那些更为冷酷的境地,让他独居的种种,那样的猜测是如此冒昧乃至冒犯,我有何权力胡乱揣度别人的生活呢?
谈笑风生的人们并没有谁主动与他交谈,他们的快乐和他没有丝毫关系,他像一个局外人,只是偶然要与他们共用一间食堂,这更像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两相对照之下,因他的无言,像极了一个满怀心事的人,而他们似乎也找到了对他敬而远之的理由,找到了交谈甚欢的理由,也找到了将他彻底遗忘的理由。第一次坐到他面前我便全然获悉了一切,不需要谁的暗示、提醒,对视的第一眼已让我羞愧不已,那并非他强加给我、无法摆脱的情绪,而是我尚未丢弃且人所共有的情感。我忽然理解了在场的所有人,理解了端坐他面前意味着什么,也切身感受到了将碗中的米饭咽下,只是完成了吞咽的一部分,还有无法估量的一些东西,也随之咽进了我的身体里,它们并不如食物一般香美,有时会难以下咽,甚至令人反胃。
我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菜,无法抬起头看他一眼,他似乎也正专心致志于眼前的午饭,就像面对他曾经要完成的所有工作一样,这成为他要攻克的一个堡垒,只有将它拿下才能算作胜利。他先我而来,我吃到一半时便听见他的勺子刮擦碗底的声音,接着喝完了小碗里的汤。我下意识把面前的餐巾纸推到他那边,听见他和善地说了一声“谢谢”,我以微笑作为回应。他捡拾好桌上的餐具,推开椅子站起来,白衬衫里的身体已经微驼,左手撑起一根木手杖,右手端起碗筷,举步前对我说:“小伙子,你慢慢吃。”
四
在我所租住的那条街道,有一个小动物协会,时常看见一些人带着自家的猫狗进进出出,有的大概是给宠物做护理,有的是要出门,便临时将自家的宠物寄养在那里。协会二楼的窗户全部糊上了一层动漫片里猫狗的照片,白天半开的窗户常常传来狗的叫声,没有风的时候,那里散发着一股特别的气味,那是房间里所有动物一同制造出来的。也许正是这个缘故,紧挨着宠物楼的小餐馆已经换了几任老板,现在它的落地玻璃上还贴着店铺转让的信息。
这个房间里住着一条无人认领的狗,是西伯利亚雪橇犬或萨摩耶,它的毛始终蓬松、灰黄,像幼犬成长时要褪去的那一身雏毛。它很喜欢隔着铁丝网做的栅栏朝屋外张望,半个身子露出来,不鸣不吠,看着路上的行人,眼神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最后望向被墙体阻隔的拐角,仿佛期待着下一个人的到来。有那么几次,我故意放慢脚步,吹起口哨或者发出怪异的声响,就为了能够吸引它的注意。然而它只是多看了两眼,目光并未在我的身上停留几秒,便又扭过头看向另一处,我顺着它张望的方向看过去,却并没有看见更为吸人眼球的事情。它只是那么执着地张望着,我每次路过那里,几乎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其他的猫狗软趴趴地伏在地板上睡觉,只有它好像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只是它的眼神里似乎还有除了好奇之外的另一种东西,也许是期待,可是它在期待什么呢?
重新回到这个城市时,我想租住下来以后就养一只狗,只是事情并未朝着我希望的方向走去,我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一楼的一室一厅,春天的几个月里,室内阴暗,并且潮湿无比,透明的水从地板之下洇上来,在墙边慢慢聚成一摊,长裤子洗好晾上窗台,没有两天,便有一种腐坏的味道从窗外扑进来。干净的水尚且会腐坏发臭,我又如何能让一条狗生活在这里?这段日子经过小动物协会门口,看见它,又开始萌生领养它的冲动,犹豫间,想到它是否正在等待原来的主人呢?果真如此,那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五
买回来的薄荷由绿变黄,我给它浇水,搬到太阳下,有时候也陪它一起晒,有一根细株抽得特别长,两边的叶子慢慢变大,变绿,心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