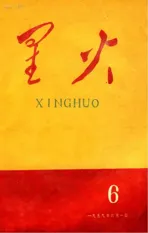树林的覆影
2017-11-03○存朴
○存 朴
树林的覆影
○存 朴

存朴,本名李家淳,江西石城人,现居深圳。著有散文集《私人手稿》《慢生活》。曾获第三届广东省散文奖优秀奖,《慢生活》入选2012年度香港国际书展。
心理学家认为,童年印象将持久和深刻地影响个体生命,隐秘地存在于人的精神之源。哲学家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到很多年后才悟出这句话的内涵。
对潜意识最敏感的作家和艺术家而言,童年的养育充满寓意地辐射到作品里,比如德沃夏克、舒尔茨、梵高,背负自身的远方,毕生都在回望童年梦境。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我最牢固的幼年记忆停栖在树木间。那些古老又茂盛的乔木,樟、木荷、柞、松、杉、乌桕、苦楝、黄檀、榉、柘、枫、油桐以及灌木与花草丛集的植被,展现在推门而见的原初视野;连绵起伏的山峦与蜿蜒曲折的河岸,像一幅绿色长卷,成为内心镜像中的葱茏背景。
五岁时,背一个小竹篓,跟屁虫一样,随姐姐去林间采粽叶,走得累了,躺在草窠里睡觉,被蚂蚁咬得哭鼻子,被二姐宠爱地笑话了好些年。被她唤作“少爷”的滋味和那时的林间花草一样馥郁。
阳光温煦的暮春早晨,稻田萌蘖出一片青绿,风吹栎树的响声与河床里跌宕而下的湍流声,宛如二重奏在耳边回荡。一根碗口粗的松枝压在肩头,我闻到汁液的气味,还有身体与重负的承受关系。那是父亲从河水中打捞上来的一段松枝,从河边到老屋,经过栎树林、田埂路,短短五十米,我体验到六岁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
七岁那年,独自去二里外的山坳里放牛,一场暴雨浇透夏日傍晚。雨雾中,松杉林和坟茔幻化为神鬼出没之地,虚设的恐惧感清晰地包抄而来,以二姐神奇地来到面前而消散。夜里做梦,也是风翻雨刮乱云飞,惊吓之际,云散雨住,花香拂过鼻息,似有若无。
八九岁时,和小伙伴去附近的松林里砍柴,稍大的孩子带来扑克和香烟。扑克用来“赌博”,赢的躺树下睡觉,还可以享受一颗香烟的待遇。输的,负责砍柴。第一次,认识了赌博游戏和尼古丁的苦涩。有时候游戏改在树上玩:人群分成两组,每组三两个人,各自找一棵粗壮的老松,两棵树要保持一定距离,爬到高处的身体尽量隐藏在针叶间,然后往对方身上投松籽,被打中者视为“牺牲”,退出游戏。照例是,赢方躺在树下吹牛,输方去完成当天杂务。这样的少年玩耍,我选择做旁观者的时候居多。做完分内事之后,喜欢在树林中行走,甚至窥探一丛野刺玫、一脉草叶下的泉流、一群列队而过的蚂蚁;相对小伙伴无忌的喧哗,一个人坐在树下,嘴里叼片叶子,缓缓沉入远处山垭的夕阳和空中无声飞行的鸟群,更能俘获我的目光和内心。我成年后不太乐于群体聚会、公众场所拙于言辞的性格,或许与此相关吧。
十岁之前除了上学,很少去相邻的街上玩。因为家庭劳作,我的活动半径围绕着山林与田野展开,目力所及,绿意汹涌。老屋前面有条沙土公路,第一道绿化带是道路两侧几十年树龄的乌桕、油桐和苦楝,第二道是田野、山冈、山冈上的松杉林,海拔更高处,峰峦间各色乔木、灌木簇拥出混沌的绿色屏障。
那时候烧柴煮米,土灶是永远填不满的窟窿,日子都在与一捆捆柴火、一碗碗饭食搏斗。由近至远,我们不停地在山岭间跋涉。一日之内,穿林越涧,爬坡过冈,渴了喝口泉水,饿了摘几枚野果。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山中掉进野猪陷阱,大脑一片空白,慌神中庆幸洞底没有困兽、竹刺和铁钉之类。头顶一小片光亮激起我自我救赎的勇气,手脚在冰冷陡峭的洞壁上抓蹬,最绝望的时刻是快到洞顶时重新跌落。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像一只野兽挣脱出去,那种身处险境的孤独和惊魂之后的虚无,让我坐在洞口,半天起不了身。年长后,认识了一些人事,知道人间如丛林,有花果山,更有野猪林。
在林中,一旦独处,身体内部的反应很容易被光线、声音、颜色和气味之类激活,自我意识超越外在事物;精神视域与客观存在之间维系着一种奇怪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融合。“山中七日,世上千年”,时间在山林的纵深里似乎过得缓慢,呆上半日,恍若隔世。时间又流逝得极快,转眼之间,春华秋实,沧海桑田,如雾亦如电。飞禽走兽,花果流泉,古树庞大树冠与几百几千年不萎败的长势,让你体察到万象丰沛和永恒性;被白蚁蛀蚀的腐树和满地的枯枝败叶,又让你觉得一切空无。有与无,一念间,一霎时。
随着足迹的深入和拓展,我几乎熟悉方圆十几里内每一处风景。油桐在农历五月细雨中的香气和形态,秋天的乌桕树缀满白蜡色坚果,苦楝枝杈上夏天拉弦似的蝉鸣,音画般的四季特征。一旦和生活底色嫁接,容易催生想象与现实的冲撞与糅杂,精神底蕴的通感式交集愈发密织。至今固执地觉得,没有经历过树林、田野这类乡野生态熏染的人,不免有个体经验的缺陷。一方林相美好、自然地理较为完整的水土,具有深邃、厚重和静穆的诗性品格;树林的覆影,含蕴着异于动荡尘世的人文风貌,比如敬重、内省、自由、丰沛等等。历史上那些隐者、高僧,林泉栖身,参悟自得,大抵也有这种缘起吧。
第一份工作在离家十五里的石田初中。学校坐落在大片稻田和树木的交接地。在那里待了一年,教课之余,我喜欢去林子里、田陇间散步,青春期的孤独与向往,停泊在流云与枝丫上,时间被大把大把地挥霍掉,许多乌托邦式的意念,到夜晚,归于沉寂。
稍后分别去过两所学校,小镇上的母校小松中学和去北十里的桐江初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的小松中学,校园内林木阴阴,读书时喜欢坐在树木与清风里翻书,等到住进教工宿舍,特意走到院子里那棵蜡梅树下,仔细端详树上的鳞芽,回味某个寒假一位头发卷曲的年轻画家写生的情景;晚自习,透过灯光里的枝叶,张望近在咫尺的教室,那些课桌前的身影,让我拥有老农一样的安慰。
桐江初中靠山而建,与石田初中不同的是,前者满坡香樟,清气飘散。后者杉林森森,鸟雀糜集。清晨沿着山脚,边跑步,边聆听稠密鸟声;静夜伴林涛鼓荡,在灯下临帖和写几行所谓的诗歌,耳边如有《安魂曲》。尽管作不成诗,写不好字,倒也在那里度过相对宁静饱满的四年。
随后是离开。当下说得烂俗的一个词语“迁徙”,在临近而立之年,标签一样贴上我的额头。南昌、东莞、佛山、广州、深圳,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晃荡。我对千篇一律的房屋和街道无感,却对一个地方的林木长势格外关注。一个林木繁茂的城市,会让人产生一见如故的幻觉。凝神树梢,另一个烂俗的词语“乡愁”就会暗自蔓生。有一年在北京八大处,徒步去某大学看望同学,不期然在老山看见熟悉的马尾松,我停下来,对着一丛松针出神,也没好意思对同学提起。去某地旅行,我会以挑剔的眼神审察一番,看看别人的地盘都有些什么树木,如果有幸住在树木蓊郁之所,睡眠就如平缓的河流,绵长而深致。
后来入住佛山某小区,不免受了树木诱惑。这里的街道、空地和公园,可以找到岭南地区大部分植物家族,仅住所周边,就有凤凰木、重阳木、木棉、紫荆、榕树等几十个树种。站在高处看,房子空隙处,绿色延伸至远。而窗前,树叶披散,荔枝、芒果和龙眼终年播撒芬芳,仿佛日子也被多了一丝恩宠。在肇庆森林公园,深谷里看见过桫椤,这种珍稀植物,有“活化石”美誉,据说1.8亿年前为地球最繁茂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属爬行时代的两大标志。
前些年换工作的原因,大部分时间住在深圳山海相连的某个地方,周末才回佛山。如果说初来深圳那几年,它留给个人太多的灰色地带,那现在,中年心境和环境更迭,让我对这个毗邻香港的临海城市有了更多认知。大海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丛林,只不过肉眼看不见;海岸线以内,梧桐山、七娘山、马峦山、笔架山和深南大道一线,同样满足着个人对树林的偏好,这个城市像森林那样的包容度,也是个人心仪之处。空闲时单车出行,走绿道看树看花,可以消弭身心内外的尘埃感。不过,深圳的文化积淀和历史维度,不如香港厚重,亦有遗憾的地方,就像生态系统完整的一片树林,肯定不是徒有物质外表,还要有内在的深广度,才会生生不息。
不出门的日子,我喜欢坐在窗前发呆。窗前是幼儿园的后院。细叶榕、白玉兰、紫荆、秋枫,几种树木掩映成一小片树林。靠围墙的空地上,还有五棵芭蕉。每天早晨,幼儿园的男童女童做完操,被老师领着,从前院来到后院,在树荫里做游戏、唱歌、跳舞、自由戏耍。透过树叶,看见红红绿绿的童装,歌声与笑声,穿过树叶滑进耳膜,那么真实、纯粹。我倾向于认为,一个绿荫铺地的院子,就是一个有着灵性之梦的地方。
周末,院子安静下来。安静里,有树叶被风翻译的响动、鸟雀的低语。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带来无关紧要的思绪,杂乱而缤纷,像羽毛抖展,像芦苇摇曳。这样的时辰感到安宁。眼睛着意于枝头,我忘了手里还装模作样拿着本闲书,当阳光爬过窗台,恍惚如梦。有时候,夜里下雨,雨水绵密地弹拨五棵芭蕉,细碎地洒落在树叶上,音乐般的动静,很容易让一段睡眠消弭,潜意识流水一般,在无羁的沙床起伏。
芭蕉树其实不算好看,宽大而纤薄的叶片,单纯的绿,柔弱的样子,不若某些色相俱佳的植物。喜爱芭蕉的人却很多,诗人以其入诗,画家以其入画,作曲家以其入曲,芭蕉这种不起眼的植株因之艺术化。听雨打芭蕉,我倒是想起松尾芭蕉。他的俳句,形式简单,又蕴含深意。他的居所名叫“芭蕉庵”,据说庭院内就有一株芭蕉树;不知是先有笔名“芭蕉”,后建的芭蕉庵,还是反过来。相对中国古代格律诗,俳句作为江户时代独特的诗歌形式,更出乎自由向度,说它是性灵写意也不过分。
黑夜里,树叶被雨线覆盖,宛若京剧中西皮流水的表述。小时候听它,咿咿呀呀的,没有什么亲近感,现在不同,它刚劲又柔软的融和韵味,契合个人心性。
院子里的树木,开花的有两种,紫荆与白玉兰。两种树都高大,树梢几乎贴近五楼,树冠披展开来,在夏季让房子里变得清凉。我在四楼窗口闲坐时,正好对着紫荆、玉兰。花叶养眼、入心,人就不至于有那种风烛残年般的空寂感。玉兰花初夏开放,洁白清雅,香气幽长。紫荆花开在秋天,紫里透红,香气柔薄。紫荆花不像玉兰花那样耐活,一边开,一边落。曾见一位小女孩,蹲地上把花瓣捡起来,用裙角拢了,放到旁边水池里,来来回回,不一会,水面上便撒满花瓣,红红白白。她坐在池边,像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神态郑重。另一个小女孩凑过来,问她什么,她就笑笑,略微羞涩地起身离开,边走边回头。还有一位男孩,长相憨实,喜欢走到芭蕉树下,揉捻着近前的叶片,用鼻子嗅嗅,然后取出随身的小水壶,往芭蕉叶上浇水。一股清水缓缓倾泻,在叶面凝成水珠,连缀如白珠子。小家伙不停地抖动叶子,白珠子滚动、跌落,他跟着傻傻地笑。某个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听到院里传来孩子们的喧闹,便到窗口张望,一眼看见那位小男孩,正向芭蕉叶上浇水,随着水珠在绿叶上滚动,他似乎忘了团队游戏。没等浇完那壶水,一个老师模样的女人追过去,一把抢过水壶,扔在地上,三两下扯烂一片芭蕉叶,往男孩脸上一丢。那张笑脸顿时萎了下去,哭声穿过树木,在院子上空徘徊。我的目光暗了下去。
那几天翻书时,总有一丝不安。那些永远也翻不完的书籍,我曾经那么饶有兴致地打开,写写画画,随手记录几行字,等我例行公事般拿起一本书,忽然兴味索然,字里行间,仿佛飘浮着什么梦魇。我怀疑,若干年后,当男孩女孩到我这样年纪,是否记得幼儿园后院的生活片段;如同若干年来,我坐在窗前,对着一片树木,翻检往昔,竟茫然无措。
春分这天,在麻地小公园闲坐。风过榕梢,黄叶坠落,使人讶异不同地域上季节秩序的巨大差异。几十棵大叶榕环绕着公园围栏,枝柯交错,荫蔽成林。这些榕树都有三十年以上,最高拔的一棵,枝柯越过栏杆,横跨人行道,伸展到旁边一栋宿舍楼的五楼,浓密的枝叶,覆盖了那层楼房的阳台。从低处看,阳台晾晒的衣服,像悬挂在树枝上,风起时,叶梢间翻卷出花红柳绿。这样的生态,改变了那栋老楼的外在气象,也让居住者的日常生活添了新意,比如视线、空气与鸟鸣之类带来的不同感受。每次从绿荫下路过,我会抬头看看树梢,以及树梢之上碎片状的天色,有种攀缘而上的冲动。不止一次梦见爬树。梦里,身体在上升与下坠之间对抗着,及至爬上枝头,像一片叶子缀在云端,感觉像一只蝴蝶,轻盈自在。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里,虚构柯西莫的树上生活时,也许头脑中同样摇曳着这种轻盈感。
小公园距住所不到百米,所在地方原是稻田与山冈。大概早年间桑麻遍地吧,村子就叫麻地。三十多年前,村人挖山填土,建起新村小区,辟出一块地建起公园,半截土冈成了果园,种满荔枝。原村子只剩下一个名字,面貌大变。一个地方能否给人好感,可以从某些微小细节中找到,这细节隐秘地存在着,不足以对人提及。寄居多年,我常来麻地村打发时间。果园,林木,安静的道路——靠近,是一种眷恋。春分这天,坐在满地落叶的榕树下,听了会手机音乐,被空气里的馥郁樟香吸引。果园那边,四棵古樟终年撑起绿云,新叶嫩绿而纷披。四棵樟树,树龄最长的一百五十年,最短的,一百一十年,加起来,不到五百年。一棵百年老树已是饱经风雨,迄今保持着勃勃生气,那种耐心,让人默然敬畏。
老家比邻老屋那棵五百年古樟,被水泥马路摧毁,至今,我都不敢去怀想少时光景。我曾长时间以那棵古樟为傲,在它苍古又芳华如初的荫护里,我年少的认知从树底下一条毛毛虫,到树洞里的八哥、乌鸫,夜里发声的猫头鹰、啄木鸟,以及春天的米黄色细花和冬天垂挂而下的冰棱,让我的童年生活意象丰盈。怀想一棵消失的古樟,就像寄望找回时间一样绝望。那年九月,几个手持铁锯的陌生人以修路的名义,将古樟伐倒。人们围在树边,像分享一个猎物,没来由地兴奋,又像围观一具于己无关的死尸,神态麻木。除了砍树者。他们用坏七块锯片、十几把利斧,把樟树肢解,砍削成木片,再把木片拿去熬樟油;他们挥舞着斧头,拉着钢锯,彼此说说笑笑,吹着口哨,开着黄色玩笑,那情景像村口架起一座焚尸炉,烈焰熊熊,烟雾弥漫,曾经枝杈连云的“水口树”(也称“风水树”,往往是村庄开基之初,由先人手植),转眼烟消云散。
我在果园边的樟香里独坐,似乎这样,就可以曲径通幽,寻找失散的时光。最长的一次,从午后到黑暗降临,我在樟荫里独坐很久,那些从树枝上升起的光影,隐隐触动眼底的泪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