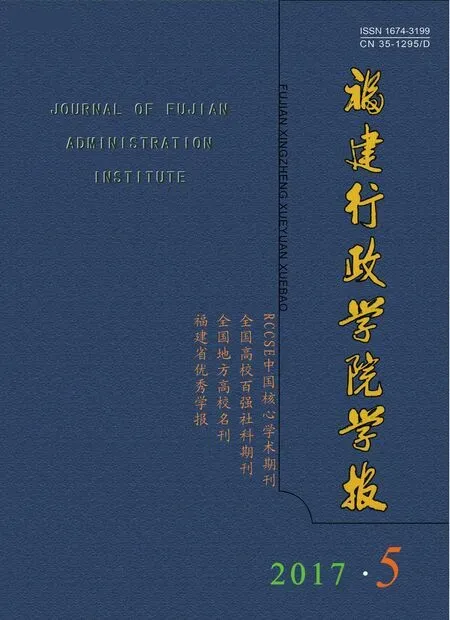朱熹论“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由知“当然之理”而知其“所以然之理”
2017-10-19乐爱国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朱熹论“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由知“当然之理”而知其“所以然之理”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对于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熹把“四十而不惑”解读为知事物当然之理,把“五十而知天命”解读为知事物当然之理之所以然,无疑是一家之言。讨论朱熹的解读,需要对朱熹的“理”包含“当然之理”和“所以然之理”两个层次以及“即物穷理”包含由知“当然之理”而知其“所以然之理”的过程,有深入的了解;同时,研究朱熹的解读,又有助于对朱熹的“理”以及“即物穷理”有深入的把握。
朱熹;孔子;不惑;知天命;当然;所以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对此,冯友兰早年所撰《新原道》,以所谓“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来解读。他认为,“三十而立”属功利境界;“四十而不惑”属道德境界;“五十而知天命”为认识到超道德价值,有似于所谓“知天”;又经由“六十而耳顺”,即顺天命,而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属天地境界。[1]18-20冯友兰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中又对此作了阐释,其中对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说,依据《中庸》所谓“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以为“不惑”为“知人”,“就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有所理解,有所体会”;“知天命”就是“知天”。[2]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把“不惑”解读为“知人”,把“知天命”解读为“知天”,类似于清代毛奇龄为批评朱熹而撰《四书改错》中的解读。朱熹《论语集注》注“四十而不惑”曰:“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注“五十而知天命”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3]54即把“不惑”解读为知“事物之所当然”,或称“当然之理”;把“知天命”解读为知“事物所以当然之故”,或称“所以然之理”。由此,不仅可以看出朱熹在工夫论上讲由知“当然之理”而知其“所以然之理”的过程,而且也可进一步看出朱熹在本体论上所谓“理”的内在复杂层次与结构。
一、朱熹的解读
对于孔子所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西汉孔安国解“不惑”为“不疑惑”,“知天命”为“知天命之终始”。北宋邢昺疏曰:“‘四十而不惑’者,志强学广,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禀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学《易》,至五十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也。”[4]所谓“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即《易传·说卦》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安国、邢昺的解读,影响很大。后来的程颐也作出类似的解读,说:“圣人言己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则无所疑矣。知天命,穷理尽性也。”[5]
朱熹对孔子在“三十而立”之后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作了解释,说:“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养之功,而知见明彻,无所滞碍也。盖于事物之理,几微之际,毫厘之辨,无不判然于胸中。……无所疑惑,而充积十年,所知益精,所见益彻,而至于是也。盖天道运行,赋与万物,莫非至善无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则所谓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谓性,性之所具,是之谓理,其名虽殊,其实则一而已。故学至于不惑而又进焉,则理无不穷,性无不尽,而有以知此矣。”[6]641在朱熹看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把握“天理”的两个阶段:“四十”把握事物之理,即事物“当然之理”,“五十”把握天所赋予事物之理,即事物“所以然之理”。
朱熹讲“理”,有多层含义。他的《大学或问》认为,天下之物,“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6]512;又认为,天地间的事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所以,要“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6]526-528朱熹门人陈淳曾言:“理有能然,有必然,有当然,有自然处”;还说:“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当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则贯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该,而正就事言者,必见理直截亲切,在人道为有力。所以《大学章句》、《或问》论难处,惟专以当然不容已者为言,亦此意。熟则其余自可举矣。”对此,朱熹说:“此意甚备。《大学》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后来看得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得不容已处,即自可默会矣。”[7]由此可以看出,在朱熹那里,“理”主要可分为:“当然之理”,即所谓“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之理”,即“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朱熹较为重视“当然之理”,以为把握了“当然之理”,“所以然之理”“自可默会”。当然,朱熹又强调把握了“当然之理”还要进一步把握其“所以然之理”。
朱熹所谓“所以然”,按照唐君毅所说,兼“当然者之所以然”和“实然者之所以然”二义[8],但主要是讲“当然者之所以然”。据《朱子语类》载,问:“《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9]414在朱熹看来,“事亲当孝,事兄当弟”“天之高,地之厚”,这是“当然之理”;“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这是“所以然之理”。又据《朱子语类》载,广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9]414广曰:“大至于阴阳造化,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9]415在朱熹看来,“当然之理”只是“指事而言”,就阴阳消长化生万物而言;“所以然之理”是“指理而言”,就太极而言。
同时,朱熹又认为,“所以然之理”较“当然之理”更高一层。据《朱子语类》载,郭兄问:“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层。”[10]朱熹还说:“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其事‘所当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以至于天地间造化,固是阳长则生,阴消则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万事,一事各有一理,须是一一理会教彻,不成只说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万物万事,吾知其为万物万事而已!’”[9]414-415在朱熹看来,“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阳长则生,阴消则死”,乃至天之高,地之深厚,都是“当然之理”;而比“当然之理”更上面一层的是其“所以然者”,即“所以然之理”。因此,朱熹又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头处。”[11]“知事物之当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则又上面见得一截。”[12]555-556显然,朱熹讲的“所以然之理”,是“当然之理”之所以“当然”之理,是较“当然之理”更上面一层的“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就是说,先要知得“当然之理”,然后进一步知得其之所以“当然”的“所以然之故”。对此,朱熹还说:“大凡为学,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里来。譬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里头别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壳,固不可;若只去其皮壳了,不管里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则无缘到得极至处。《大学》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谓于事物之理各极其至,穷到尽头。若是里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极其至也。如今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会得,而中间核子未破,则所理会得者亦未必皆是,终有未极其至处。”[9]415在朱熹看来,格物穷理,一方面要穷得事物的当然之理,“天地造化之理都理会得”,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穷得所以然之理,深入理会“极其至处”,即太极之理。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朱熹对“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作出解读。他说:“不惑,是随事物上见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亲,须知其所以亲,只缘元是一个人。凡事事物物上,须是见它本原一线来处,便是天命。”[12]552不惑,是知事物“当然之理”;知天命,是知“当然之理”之所以然。问题是,“五十而知天命”,朱熹《论语集注》注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作如何解释?朱熹说:“天命是源头来处。”“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四十时是见得那‘率性之谓道’;五十时是见他‘天命之谓性’。”[12]553显然,在朱熹看来,“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即《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命”,即天之所命。朱熹注“天命之谓性”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3]54这就是程颐所谓“在天为命,在人为性”[13]。
朱熹认为“四十而不惑”为知事物“当然之理”,“五十而知天命”为知其“所以然之理”,知天之所命,与孔安国、邢昺的解读有相近之处。如前所述,邢昺说:“‘四十而不惑’者,志强学广,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禀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学《易》,至五十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也”;朱熹亦说:“‘四十而不惑’,于事物当然更无所疑。‘五十知天命’,则穷理尽性,而知极其至矣。”[12]556当然,朱熹也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把“四十而不惑”解读为知事物“当然之理”,而不同于邢昺所谓“志强学广,不疑惑也”。
但无论如何,朱熹的解读,与孔安国、邢昺的解读一样,都试图以人在为学成人中对于事物认知的不断深入为依据,并且都根据孔子学《易》而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安国、邢昺是从“志强学广,不疑惑”而深入至“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讲的是,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化。朱熹则是从知事物“当然之理”,而深入至“穷理尽性,而知极其至”,以达到知其“所以然之理”,知天之所命,讲的是,由知“当然之理”到知其“所以然之理”的深化。
二、后世的争议
朱熹对“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读,旨在讲人对于事物之理认知的深化,由知“当然之理”到知其“所以然之理”。清代毛奇龄批评朱熹的解读,在《四书改错》说:“若‘不惑’、‘知天命’,则以经证经。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穷理尽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诚明,知天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凡着层次,必以当然、所以然分别之。实则知当然便应知所以然,无大深浅,岂有十年知当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14]显然,与朱熹的解读强调知“当然之理”与知其“所以然之理”的差别不同,毛奇龄认为,“当然”与“所以然”,“无大深浅”,而强调知人与知天的差别,讲人的认知对象的变化,由知人到知天,把知天与知人分割开来。
孔子讲“知者不惑”,又答樊迟问“知”曰:“知人。”《中庸》引孔子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应当说,毛奇龄释“不惑”为“知人”,释“知天命”为“知天”,是有一定根据的。问题是,毛奇龄的这一解读是否一定与朱熹的解读相冲突?《中庸》说:“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这也可以作为毛奇龄把“知天”与“知人”分割开来的依据。然而,朱熹注曰:“知天知人,知其理也。”[3]38显然,在朱熹看来,知天与知人并没有多大差别,不可分割开来,都是要知得“理”,只是有知“当然之理”与知其“所以然之理”的深浅差异。
朱熹强调知天与知人的密切关系。他注孟子所谓“知其性,则知天”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3]356以为知人之性,就能知天之理。朱熹还说:“性,以赋于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脱模是一个大底人,人便是一个小底天。吾之仁义礼智,即天之元亨利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来也。故知吾性,则自然知天矣。”[15]并且认为,在“五十而知天命”中,“‘知天命’却是圣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来”[16]。显然,在朱熹看来,天与人是统一的,知天与知人亦是统一的,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知天命”就是知人之性来自天之所赋。由此亦可看出朱熹为什么不把“不惑”和“知天命”分别解读为知人和知天。与此不同,毛奇龄把知天与知人分割开来,实际上是把天与人分割开来,以为不仅要知人,还要知人之外的天。
需要指出的是,毛奇龄强调知人与知天的差别,把知天与知人分割开来,这就需要把《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分成两截:“穷理尽性”为知人,“至于命”为知天,这就是他所谓“不惑是穷理尽性,知天命是至于命”。这不仅与朱熹所谓“‘五十知天命’,则穷理尽性,而知极其至矣”相冲突,而且也与邢昺所谓“孔子四十七学《易》,至五十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也”相冲突。
至于毛奇龄《四书改错》解“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强调知人与知天的差别并因而讲“不惑是诚明,知天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后来的戴大昌所撰《驳四书改错》指出:“毛氏谓‘以经证经’,既将‘不惑’、‘知天命’分属知人与知天矣,又谓‘不惑是诚明,知天德(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夫‘自诚明,谓之性’,乃不思不勉、生知安行之圣人,固即所谓‘聪明圣知达天德’者,有何可分为四十、五十乎?且夫子不以生知自居,故自言进德之序,岂四十不惑而可以自诚明属生知者释之乎?”[17]在毛奇龄看来,“不惑”是知人,是“自诚明”,“知天命”是知天,是“聪明圣知达天德”;而在戴大昌看来,“自诚明”和“聪明圣知达天德”都是就生而知之的圣人而言,而不可分作“四十而不惑”和“五十而知天命”,况且,孔子不以生而知之的圣人自居,因而不可能说自己四十而“自诚明”,五十而“聪明圣知达天德”。
后来的刘宝楠撰《论语正义》,注“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指出:“夫子言‘天生德于予’,天之所生,是为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与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亦孟子知天命生德当在我也。是故知有仁、义、礼、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于仁、义、礼、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圣人之知天命也。”[18]可见,刘宝楠将天与人统一起来,讲“天心与己心得相通”,并将知人与知天命统一起来,由此讲“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完全不同于毛奇龄以知人与知天相分离的解读,而较为接近于孔安国、邢昺的解读。
三、现代的质疑与辨正
如前所述,西汉孔安国注“五十而知天命”为“知天命之终始”。东汉郑玄注“六十而耳顺”曰:“耳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对此,南北朝的皇侃疏曰:“云‘六十而耳顺’者,顺,谓不逆也。人年六十,识智广博,凡厥万事,不得悉须观见,但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19]问题是,孔子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什么至六十才能“闻其言而知其微旨”?唐代韩愈注“五十而知天命”曰:“天命深微至赜,非原始要终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学《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知天命’。”又注“六十而耳顺”曰:“耳,当为‘尔’,犹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顺天也。”[20]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天,这样能够说得通,但问题是,“六十而耳顺”的“耳”为“尔”,需要有文献依据,至今未果。
朱熹注“六十而耳顺”另辟蹊径,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3]54依《中庸》所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而把“六十而耳顺”解读为“不思而得”,并且注“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曰: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3]54朱熹还说:“四十时是见得那‘率性之谓道’,五十时是见他‘天命之谓性’,到六十时是见得那道理烂熟后,不待思量,过耳便晓。”[12]553“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顺是事理皆通,入耳无不顺。”[12]558应当说,朱熹无论是对“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读,还是对于“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解读,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有其合理而深刻之处,且与前人有所不同,有所发明,并由此而发展了儒学。
冯友兰并没有依据朱熹的注释,而是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解读为知人、知天,这与毛奇龄《四书改错》中的解读有相似之处,同时也与对“六十而耳顺”的解读有关。清代阮元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在为宋代俞玉所撰《书斋夜话》做提要时,引该书“经传之文……‘耳’即‘而已’,‘尔’即‘如是’”一条,案曰:“凡云‘而已’者,急言之曰‘耳’,古音在第一部;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尔’,古音在第十五部。如《世说》‘聊复尔耳’,谓且如此而已是也。二字音义绝然不同。”[21]在这里,阮元强调“耳”与“尔”不可混同。但是,他所谓“凡云‘而已’者,急言之曰‘耳’”之说,则为今人所采用。冯友兰《新原道》说:“‘六十而耳顺’。此句前人皆望文生义,不得其解。‘耳’即‘而已’,犹‘诸’即‘之乎’或‘之于’。徐言之曰而已,急言之曰耳。此句或原作‘六十耳顺’,即‘六十而已顺’。后人不知‘耳’即‘而已’。见上下诸句中间皆有‘而’字,于此亦加一‘而’字,遂成为‘而耳顺’。后人解释者,皆以耳为耳目之耳,于是此句遂费解(此沈有鼎先生说)。六十而已顺。此句蒙上文而言,顺是顺天命,顺天命有似于我们于《新原人》中所谓事天。”[1]19-20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明确把“四十而不惑”解读为“知人”,把“五十而知天命”解说为“知天”,同时还把“六十而耳顺”解读为“顺天命”。这就能够说得通了。问题是,阮元引《书斋夜话》一条,原文为:“经传之文,结以‘与’字即是‘欤’字,‘耳’即‘而已’,‘尔’即‘如是’,‘诸’即‘之乎’两声合为一声,盖省文也。”所以,他所谓“凡云‘而已’者,急言之曰‘耳’”,概是就句子结尾的虚词而言,与“六十而耳顺”之“耳”,恐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对于阮元之说,今人多有批评,钱钟书《管锥篇》称之“失当逞肊矣”[22]。因此,“六十而耳顺”的“耳”即“而已”之说法,尚待进一步论证。
另一方面,汉儒的解读受到重视。杨伯峻《论语译注》注“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曰:“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了;五十岁,懂得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23]显然,这一在当代影响很大的解读是依据汉代孔安国、郑玄的注释。
此外,近年来,台湾学者程石泉所著《论语读训》(原名《论语读训解故》),载陈铁凡《敦煌论语校读记·敦煌论语集解》残卷S.4696作“六十如顺”,并引陈君按:“此又如、而通用之一例。”同时又据于省吾《双剑誃论语新证》所谓“六十而耳顺”之“耳”字乃衍文,提出:“‘六十而顺’乃一通行语句。”[24]这一说法,经电视名嘴传播,在大陆不胫而走。但是,据1982年台湾影印出版的《敦煌宝藏》(第37册)所载,斯四六九六号为“六十如耳□”[25],而非程石泉《论语读训》所载“六十如顺”。1992年大陆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第六卷)载S.4696(见图1)。[26]显然,程石泉《论语读训》所载“六十如顺”有误。其实,也有台湾学者对程石泉的说法提出批评。蔡仁厚赞同朱熹对“六十而耳顺”的解读,并且认为“‘五十而知天命’表示天人上下通而为一,‘六十而耳顺’则表示物我内外通而为一”,反对将“六十而耳顺”之“耳”视作衍字而改为“六十而顺”。[27]
四、结 语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对于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以及“六十而耳顺”的解读,历来是众所纷纭、莫衷一是。朱熹的解读无疑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家之言,但是在当代,朱熹的解读却一直被忽视,甚至逐渐被淡忘。究其原因,这并不是由于朱熹的解读缺乏合理性和深刻性,不具现代性,更多的是由于朱熹学说的复杂性所致。

图1 《英藏敦煌文献》S.4696
按照朱熹的解读,“四十而不惑”是知事物当然之理;“五十而知天命”是知事物当然之理之所以然;“六十而耳顺”是“不思而得”;“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可见,朱熹的解读涉及其学说的两大概念:“理”与“诚”。因此,要理解朱熹对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读,就要对朱熹的“理”有深入的把握。
如前所述,朱熹的“理”有多层含义,主要有“当然之理”与“所以然之理”两个层次。然而,现代对于朱熹的“理”的阐释,较多地只是讲“所以然之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理气关系以及朱熹所谓“理一分殊”,忽略了对朱熹所谓“当然之理”及其与“所以然之理”的相互关系的阐述,因而也就无法理解朱熹把“四十而不惑”解读为知事物当然之理,把“五十而知天命”解读为知事物当然之理之所以然。
由于对朱熹“理”的阐释,大都只是讲“所以然之理”,因此,对于朱熹“格物致知”的阐释,也多把“即物穷理”的“理”只是理解为“所以然之理”,并且只是注重于“理”与“物”的关系。朱熹解“格物致知”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3]7《易传》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朱熹讲“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表明“即物而穷其理”,不只是在“即物”中而获知“理”,而且还包括从“已知之理”到“求至乎其极”的穷究过程,其中也应当包含了由知“当然之理”而知其“所以然之理”的过程。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朱熹对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读。
由此可见,讨论朱熹对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读,需要对朱熹的“理”包含“当然之理”和“所以然之理”两个层次以及“即物穷理”包含由知“当然之理”而知其“所以然之理”的过程,有深入的了解。一些学者忽视朱熹的解读,或许就在于对此不甚了解。同时,研究朱熹对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解读,又有助于对朱熹的“理”以及“即物穷理”有深入的把握。本文对于朱熹解读的讨论,其目的正在于此。
[1] 冯友兰.新原道[M]//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8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64.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1.
[5]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六[M]//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1135.
[6] 朱熹.四书或问[M]//朱杰人.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7] 朱熹.答陈安卿(三)[M]//朱杰人.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2736-2737.
[8]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5.
[9] 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383.
[11] 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一百一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25.
[12] 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M]//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204.
[14] 毛奇龄.四书改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29-430.
[15] 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26.
[16] 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79.
[17] 戴大昌.驳四书改错:卷十八[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54.
[18]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45.
[19] 何晏,黄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
[20]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1:2.
[21] 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40.
[22] 钱钟书.管锥篇: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23.
[2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13.
[24] 程石泉.论语读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
[25] 黄永武.敦煌宝藏:第37册[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344.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第6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40.
[27] 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9-11.
Abstract:A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what Confucius called “At forty I had no more doubts, and at fifty I knew the mandate of the heaven”, people have long been unable to decide which is right, to which public opinions are divergent. Zhu Xi interpreted “at forty I had no more doubts” as knowing “ As It Should be”, and “at fifty I knew the mandate of the heaven” as “The Reason Why”, which is undoubtedly the statement of one school.The discussion of Zhu Xi’s interpretation requir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following: Zhu Xi’s “Li” contains two levels of “ As It Should be” and “The Reason Why”, and his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extend Li” includes the process from knowing “ As It Should be” to “The Reason Why”. A discussion of Zhu Xi’s interpretation will help to deeply grasp his “Li” and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extend Li”.
Keywords:Zhu Xi; Confucius; No More Doubts; Knowing the Mandate of the Heaven; As It Should be; The Reason Why
[责任编辑:林丽芳]
ZhuXi’sDiscussionon“AtFortyIhadNoMoreDoubts,andatFiftyIKnewtheMandateofHeaven”:FromKnowing“AsItShouldbe”to“TheReasonWhy”
LE Ai-gu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B244.7
A
1674-3199(2017)05-0112-09
2017-07-28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07)
乐爱国(1955—),男,浙江宁波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