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手”之间,从聋到龙
2017-10-19郑璇
文|郑璇
挥“手”之间,从聋到龙
文|郑璇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殊教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聋人教育学科带头人。先后于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聋”这个字的写法非常有趣。它是一个形声字,上面的“龙”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下面的“耳”是形旁,表示它的意义和耳朵有关。但是,老祖宗造字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龙这个声旁呢?因为龙是吉祥的动物,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用这个字来给聋人群体命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给予聋人们希望,期望聋人化身为龙。因此在各地讲学时,我经常会向大家这样解读“聋”字。

聋作为一种“隐形的残疾”,它不会在身体表面刻下烙印,聋人看起来四肢健全、头脑聪敏,与常人毫无差异,只要不与人交流,那么谁也看不出他和常人有什么不同。海伦·凯勒有一句名言:“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与人。”听力障碍本身并不是聋人的真正麻烦所在。在身体外观健全的表象下,他们真正的障碍—语言交流障碍经常被人们下意识地忽略。2010年世界聋教育大会将聋人定义为“语言和文化的少数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聋人就像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人”。语言交流障碍制约了他们和外界的沟通互动,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交往和生活质量,使他们常被社会大众误读和曲解。
纵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十聋九哑”早已成为历史,助听器和电子耳蜗可以帮助大部分聋人听到声音。但即便如此,主流的语言学习对聋人来说仍是一个艰难的关卡。对听力健全的孩子来说,语言的学习在出生后就开始了,5岁时就能基本完成本族语言的习得。而对聋童来说,情况却大不一样。绝大多数聋人孩子的父母是听人,不会手语,不知如何与孩子交流。即使费尽心力教孩子学说话,孩子学到的也多半是简单的发音技能,并没有像同龄孩子一样完整地习得汉语的词汇和语法。直到他们7岁进聋校,才开始真正学习汉语、接触手语。也就是说,他们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语言发展的“窗口期”。
所以,除了口语康复,聋人孩子也有必要学习手语,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沟通障碍,促进早期智力和认知能力发展,建立良好的自我身份认同。手语不仅可以为听障人士营造信息无障碍环境,也可以拓宽健听人的眼界,维护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和谐。常言道,多一种语言,就多一个世界。作为一名聋人教师,我以手语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做沟通听聋两个群体的使者和桥梁。博士毕业后,我选择来到重庆,投身当时西部唯一的聋人高等教育办学点—重庆师范大学,开启了我的“唇耕手耘”的特教生涯。
跨越语言沟通障碍是聋人成长与发展的关键,语言教育是聋教育的核心问题。在重庆师范大学高等聋教育的学术工作中,我开创了由大学语文、手语、人际沟通3门课程组成的聋生沟通能力提升课程体系,进行了面向听人的手语教学改革,出版了面向特教同行和聋人群众的手语教材。2009年以来,我独立承担了面向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空乘服务专业本科生的手语课和面向聋大学生的10多门专业课。8年的教学实践使我逐步形成了以聋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以沟通能力为中心的双语共融教育模式。我认为,良好的汉语能力和手语能力是聋人在社会中生存所依赖的双翼,其关系密不可分,需要同时发展。良好的汉语能力(包括口语能力和书面语能力)可以大大方便同听人的沟通,而良好的手语能力则是让聋人找到安身立命的身份归属感的必要前提。
弘扬聋人文化,倡导聋听融合一直是我的主要工作目标。在重庆师范大学,我长期坚持对本校教师进行手语培训,强调在教学中通过有效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并建立了一支以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的手语翻译团队,在重庆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支持下,面向本校聋生和校外社会聋人提供课堂翻译、手语导医等服务。此外,通过每周一次的手语角活动宣传和推广手语,鼓励聋人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手语教学、手语视频拍摄、手语歌编导表演、聋人微电影拍摄等活动中来。有了良好的手语翻译支持体系,他们得以平等地选修课程,参与活动。不少聋生还在学生会中担任干部,和健听学生携手合作。
在这8年里,我坚持做好聋生的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不少从小在聋校长大的同学在汉语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始打开紧锁的心门,愿意同听人交往。一位家长曾激动地给我发来短信:“谢谢郑老师对孩子的教育。孩子自从上了重庆师范大学,写的句子通顺了,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心里有什么想法能用手机打字给我们看,有什么事情也都会和我们说。”而从普通学校考进重庆师范大学的重听学生也学会了手语,在和他人的相处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一位从四川普通高中考来的学生原本性格非常内向自卑,在班上很少说话,像个“隐形人”,到了重庆师范大学后,她的手语表达能力不断提升,充分发挥出了自己文化成绩好,知识面广的优势,获得了全班同学的信任,先后被选为学习委员和团支部书记,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离校时,面带微笑、自信阳光的她已和昔日判若两人。这些都是双语双文化教学带给学生们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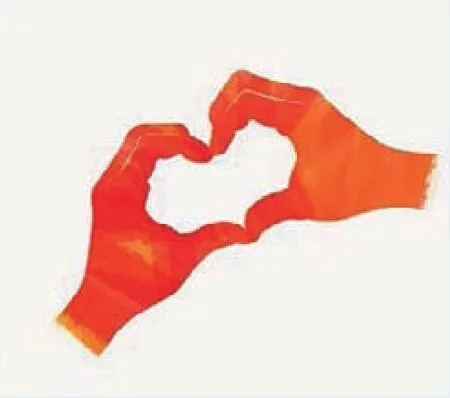

2016年秋,我作为公派聋人教师前往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下属的孔子课堂从事为期一年的教学工作。在这所世界唯一的聋校孔子课堂,我利用自身的多语优势,将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播撒到美国聋人孩子的心中。同时,我还与美方院长凯瑟琳·约翰逊(Kathryn Johnson)博士合作共同研究双语聋教育课题,作为中国聋人“大使”促进中美聋教育合作交流。美国是在手语研究和聋教育领域领跑全球的国家,在这里,我也切身感受到了聋人的种种“福利”。公寓为我免费安装了火警闪光报警装置、在剧院看演出既有字幕屏也有专业手语翻译员、在手语译员的支持下可以用可视电话自由拨打任何号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内也能看到这些情 景。
在美国聋校,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我的美国同事中既有聋人,也有听人,学生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和残疾程度也是千差万别,甚至还有好些盲聋学生、智力障碍聋生、自闭症聋生……我的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交替应用美国手语、中国手语、英语和汉语4种语言,去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时候,大脑中不免会“短路”,出现语码混用现象,为此还闹过小笑话。比如,美国手语中的数字“9”和中国手语中的数字“3”打法刚好相同,有一次学生问我“你家有几口人”,我用中国手语回答说“3个人”,孩子们却惊讶地挑起眉毛:“哇!9个人,这么多!”



如果说语言是冰山在海面上能够看见的一角,那么文化就是在水下的不为人知的那一部分。它悄无声息地潜藏于海面之下,许多人意识不到它的力量有多强大。事实上,掌握一个群体的文化心理,其重要性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学习他们的语言本身。全世界的聋人,尽管所使用的手语有所差异,但我们所共享的视觉性文化却颇为相似。我曾多次到美国的聋人朋友家做客,和他们一起出游……聊天时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让我们心有灵犀,相视而笑。
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我认可象牙塔内低调而自在的学者生活,但自身的聋人身份和我所从事的专业—特殊教育,却又决定了在潜心学术、修炼自我的同时,还需要常怀一份济世之心。于是,我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努力地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能让自己保持内心的平和,也能力所能及地多做点事、帮到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