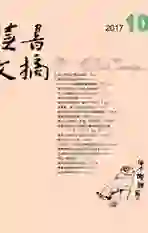1925年,一场关于新性道德的论战
2017-10-16章雪峰
谈“性”起风波
1921年1月,章锡琛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九年之后,被商务印书馆高层看中,正式担任 《妇女杂志》 主编。这是章锡琛首次独立管理、运营一个出版实体。
1925年1月,章锡琛、周建人推出了《妇女杂志》 第11卷第1号“新性道德号”。重头文章有章锡琛的 《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的 《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 和 《现代性道德的倾向》、沈雁冰的 《性道德的唯物史观》、沈泽民的《爱伦凯的〈恋爱与道德〉》、文宙的 《离婚防止与新性道德的建设》、默盦的 《近代文学上的新性道德》。
这些重头文章,众多作者阐述的重点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内核却是一致的,即全部是爱伦凯在其著作 《恋爱与结婚》 中的观点:一是恋爱自由,二是离婚自由。爱伦凯认为,“恋爱必须绝对自由,就是说,必须完全依从当事人的选择。旁人,无论是社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父母,无论是法律,都不当加以一点限制或干涉的”。
其中,章锡琛的文章最为抢眼,也使他在后来成为了攻击方的头号靶子。他的文章提出了新性道德的四个内容:一是离婚自由,“结婚的双方无论哪一方,感到他们的婚姻生活上有了极大的障碍,非分离不可时,便应该任其分离”;二是关于妇女贞操,只要不损害社会及其他个人,超出两人的性关系也不能认为是不道德的,“性的道德,完全该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的标准;从消极的方面说,凡是对于社会及个人并无损害的,我们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三是恋爱自由,“两性的结合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四是关于性的欲望,“性的欲望乃是人类天然的欲望”,“把供给男子的性欲满足认为女子在结婚生活上的义务”是不道德的,女子同样也有满足的权利。在以上的基础上,章锡琛的惊世骇俗言论出台了:新性道德,可容忍婚外的性关系即不贞操,“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
果然,“新性道德号”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议。
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陈大齐 (1886—1983),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也是 《新青年》 的作者之一。他于1925年3月14日在 《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发表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猛烈抨击新性道德是一夫多妻制的“新护符”,是一种纵欲,破坏了恋爱的专一性,将会危害社会。陈大齐宣布:“中国现在的家庭大有改革的必要。而我的偏见以为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最合理想,古来一夫多妻的坏风俗非极力打破不可。今以改革自任的新性道德家竟有许可一夫多妻的言论,竟挺身出来作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我不得不提出一种抗议了。”
有人指责,章锡琛与周建人只好应战。章锡琛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 答陈百年先生》,周建人写了 《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 答陈百年先生》。本打算在 《妇女杂志》 上发表,但却被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阻止了。于是章、周二人只好转投对方阵营——《现代评论》。
恰恰在这时,《现代评论》 对于章、周二人上述两篇文章的处理却出了问题。在发表陈百年另一篇文章 《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 的同时,虽然发表了章、周二人的文章,但却是延迟发表的,同时对章、周二人关于是否发表的来函迟迟未复;在发表时,又是在杂志末尾的“通讯”栏中删节刊登。延迟发表、来函不复、擅自删节,对于论战的双方如此厚此薄彼,惹火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鲁迅。对于这场论战,鲁迅旁观已久,本不便介入的。因为论战双方,陈百年与自己有同事之谊,周建人则与自己有兄弟之亲。但《现代评论》 对论战文章的错误处理方式,终于使鲁迅忍耐不住了。
鲁迅在1925年5月15日的 《莽原》 周刊第4期上,发表了章、周二人的后续文章,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同时还在 《编完写起》中表达了对陈百年的不满:“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而不像论是非,莫名其妙”,“诚然,《妇女杂志》 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
这一期 《莽原》 出版之后,鲁迅于5月18日收到陈百年的来信,解释了 《现代评论》 延迟发表章、周二人文章的原因。在信中,陈百年还表示自己不再就此事写文章论战,以平息事态。于是鲁迅就将此信发表在5月29日出版的 《莽原》第6期。然而,章、周二人在陈百年造成的外部压力和王云五造成的内部压力下,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不得不再次著文,为自己一辩。鲁迅考虑到他们二人已没有任何刊物可以发表答辩文章,只好在陈百年已表示偃旗息鼓的情况下,再次伸出援手,在6月5日的 《莽原》 第7期上发表了章锡琛的 《与陈百年教授谈梦》 和周建人的 《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并写了“编者附白”将 《莽原》参与论战的经过进行了说明。这已是章、周二人和陈百年关于新性道德论战的尾声了。
后来,论战的范围不断扩大。上海 《晶报》 及《时事新报》 副刊 《青光》 等报刊,陆续出现了拥护陈百年而批判章、周“新性道德”的文章。而拥护章、周二人的也不少,顾均正撰写了《读 〈一夫多妻的新護符〉》、许言午撰写了《新性道德的讨论:读陈百年先生的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声援章、周二人。
到了1925年8月,鉴于章锡琛渐渐出格,王云五开始采取措施,将章锡琛从 《妇女杂志》 调到国文部编章学诚的 《文史通义》 选注。周建人呢,则调去主编一个即将于1926年1月创刊的新杂志——《自然界》 杂志。《妇女杂志》 改由杜亚泉的堂弟杜就田接棒主编。
为何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大约在1925年12月底,王云五代表商务高层,正式辞退了章锡琛。章锡琛15年在商务印书馆的职业生涯即“商务十五秋”,至此正式结束。“十五年的职位,就此断送”。
那么,王云五究竟为何辞退章锡琛?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 因为“猥亵”。据赵景深回忆:“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 《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
(二) 因为“赤化”。就在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中,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惨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身在上海的章锡琛激于爱国义愤,以妇女问题研究会代表身份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积极声援爱国群众运动。章锡琛的这一个人举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商务“在商言商”、不主动介入政治的立场。
章锡琛的三公子章士敭持此说,“这一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先生以‘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声援群众运动,更使王云五吓破了胆,遂以审查杂志清样为借口,无理干涉编辑工作,先生被迫提出辞职表示抗议,于8月底脱离 《妇女杂志》,同年12月底,被商务当局借故辞退”。
章锡琛本人也认为有这方面的因素:“有人并且以为我去年所以被商务印书馆辞退,也因为那些大老板把我当作共产党看的缘故。”
但在笔者看来,“赤化”、声援五卅惨案,只是章锡琛与商务高层渐行渐远的表现之一,但不是直接导火索。
可以举出一个反例。当时和章锡琛一起同在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也曾于1925年5月31日,“‘满腔愤怒地来到血案的发生地”。事后,叶圣陶挥笔写下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发表在 《文学周报》 《小说月报》 上。章锡琛只是参加声援大会,叶圣陶可是直接留下了文字证据,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却未闻商务高层以此为由,将叶圣陶开除。
另一个反例是,沈雁冰、陈云、杨贤江在1925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時,在1925年5月,更是成立了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董亦湘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虽然这些党员及组织,商务高层未必完全知情,但是以沈雁冰、陈云与张元济等的终身友好关系,其身份或活动不可能完全保密。所以,要开除“赤化”分子,首当其冲的人,还轮不到章锡琛。
事实上,章锡琛对于政治并不热衷,这一点从他身边同事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民党,频频参与政治活动,而他则一生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未加入中国国民党,却热衷于参加学术性团体,分别于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2年发起“妇女问题研究会”、1925年参加“立达学会”等,可以看出。在笔者看来,章锡琛出面声援五卅惨案,不是为了哪个党哪个派,只是坚守一个中国人、一个文化人的本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三) 因为“声援罢工”。章士敭也赞同这一原因,即指章锡琛声援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罢工,“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印刷所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职工会和工会,于1925年8月和12月先后两次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父亲虽然是编译所的职员,却积极加以支援。罢工取得了胜利,但父亲的行动引起了商务当局的注意,这可能也是他在这一年年底被商务辞退的原因之一”。
但是,此说几乎不成立。章锡琛声援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罢工,只是章锡琛与商务高层渐行渐远的又一个表现罢了,但却也不是他被辞退的原因。要知道,这两次罢工都是由陈云和沈雁冰直接领导的。既然未闻罢工领导者陈云、沈雁冰被辞退,何来罢工声援者章锡琛被辞退之说?
(四) 因为违反“竞业限制”规定。所谓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对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协议或技术保密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即:劳动者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经营同类业务或到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其企业管理当然没有先进到与核心员工签订 《竞业限制协议》 的地步。要是签过,陆费逵不可能于1912年刚刚离职商务之际就创办中华书局,章锡琛本人就更不可能于1925年刚刚被辞退就于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了。但当时的商务,对于还在职的员工,不能在外从事与本企业业务相冲突、相竞争的业务,还是有所规定和限制的。而章锡琛所触犯的,恰恰就是这一条。
1925年8月,刚刚由《妇女杂志》主编调动岗位到国文部,但仍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章锡琛,在胡愈之、郑振铎、周建人等人的鼓励下,在商务印书馆之外,私自创办了 《新女性》 杂志。
从 《妇女杂志》 调岗,是章锡琛人生中的重要关口之一。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章锡琛好友胡愈之的身影:“愈之首先创议另外自己来办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期刊,仍请章锡琛、周建人主编。这个期刊就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份创刊的《新女性》 杂志。因愈之、振铎、锡琛等都在商务工作,所以决定由我出面,《新女性》 创刊号发行人署名吴觉农。”这也是 《新女性》 杂志的发行地址在吴觉农家里 (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十九号) 的原因。
这里的吴觉农 (1897—1989),是胡愈之和章锡琛共同的老乡和朋友,是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关于创办 《新女性》 的建议,胡愈之本人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我同章锡琛差不多同时进商务印书馆,大约在一九一四年,两个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关系很好。章锡琛为了写妇女问题的文章而被解职,我感到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商量另外办个杂志,叫 《新女性》。《新女性》 就是我和章锡琛他们几个人办起来的,钱也是大家凑起来的。开头很困难,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印刷费都是大家凑起来付的。”
支持的朋友中,还有鲁迅,“鲁迅先生还答应经常写稿来尽力支持”。胡愈之、吴觉农等则“鼓励章锡琛公开主编 《新女性》,他果然专心致志地办起杂志来。章锡琛的事业心很强,对出版业务相当有经验,他一个人从编辑、校对、付印到发行,什么都干。这样就为这个杂志撑起了场面”,《新女性》 就这样办起来了。
《新女性》“原想在第二年一月出刊的,为了及早回击这帮封建卫道者,结果提前了两周,在1925年12月中即刊出了1926年1月的创刊号”。“然而,《新女性》 创刊号刚印出,商务当局还是把章锡琛辞退了。”
所以,直接导致章锡琛被辞退的导火索,是他在商务印书馆之外,私自创办了 《新女性》,从事了与商务印书馆相同的竞争性业务。章锡琛的朋友中,多人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唐锡光说,“商务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商务的职员不能自己经营和商务性质相同的业务;《新女性》 杂志和 《妇女杂志》 性质相同,显然违反规定。商务知道章锡琛在筹备 《新女性》,就在一九二五年底把他解职了”。
周振甫持同样观点:“商务里有一个规定,商务里的职工不准在外搞有损于商务业务的事。商务要章或者停办 《新女性》,或者离开商务。”
叶至善也如是回忆:“商务当局得知了这个消息,就以章先生违反聘书的规定为借口,把章先生辞退了。”
让人十分意外的是,向商务当局提出解聘章锡琛的,是他在 《东方杂志》 的引路人和老领导杜亚泉。而杜亚泉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也是对章锡琛在馆外编辑 《新女性》杂志不满,据章锡琛说:“杜亚泉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不道德的行为,要求王云五把我解雇。”
因此,王云五之所以辞退章锡琛,主要还是因为他私自创办 《新女性》、违反“竞业限制”规定。但是,矛盾的爆发,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章锡琛首先是在 《妇女杂志》“猥亵”风波引发商务高层不满,继而在声援“五卅惨案”和内部罢工的问题上与商务高层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等到私自创办 《新女性》、违反“竞业限制”规定的导火索一点燃,王云五终于辞退了章锡琛。章锡琛晚年忆及此事,不无惋惜,“我的将近十五年的饭碗便因此敲破了!”
(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柳斌杰 主编 章雪峰 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