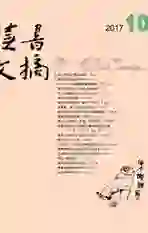两则苏共史料的启示
2017-10-16乐朋
乐朋
斯大林发“红包”
发“红包”,即用封口的大信袋给党政军高级干部送一大笔钱。其钱数多少,按级别和“贡献”而定,通常为官员月薪的一至二倍。这“红包”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魯晓夫取消。而据苏共元老、曾为第二把手的莫洛托夫回忆,它是二战结束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施并制度化的。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实行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原则,官员薪金大体与工人的平均工资持平。如1918年列宁的平均月薪为807卢布,仅比工人月薪420卢布高近一倍。但斯大林出任总书记后官员薪金大幅上涨,并允许给某些人特别高的工资。1923年下半年,俄共中央组织局编制高级干部的“职务名册”,大致一万名左右;这些高官不但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仅以工资论,斯大林是中央委员兼民族人民委员,领双薪、约860卢布,但此时工人的平均月薪仅10卢布。“廉价政府”,名存实亡。
事实上,斯大林发“红包”早已有之。1932年为在党内确立优势,斯大林常给各地省委书记发“红包”并附上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红包”和“条子”实际上就是拉拢、收买,即变相行贿。它明确无误地引导高级干部:只要跟着斯大林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样样有。党的决议、纪律制度、法令政策,都无足轻重;照斯大林的旨意行事,一切就妥了。“红包”的大小,显示着高级干部在斯大林眼里的分量和信任度。上下级的同志平等关系,变成父与子、主与奴的人身依附关系,一言堂、家长制,愈演愈烈。“红包”败坏党风政风,也腐蚀高级干部,权力腐败逐渐滋生、蔓延。
与“红包”制并行的,还有特权制。如给高官配置豪华别墅,搞特供、让高官享用质优价廉的各种商品,子女免费保送重点学校,提供特殊的优质医疗服务以及警卫、厨师、保姆等。勃列日涅夫时期,位居权力核心的政治局委员在国家银行都有不受限制、可随意提款的账户。一个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在册权贵”即特权阶层,就这样悄然生成。
对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些顶级高官而言,工资、“红包”已经失去货币的意义。他们早就生活在“共产主义天堂”了。1947年币制改革后,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是工人平均月薪的20余倍。但他的工资袋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的,从未打开过。他的钱没处可花,从不需要购买东西,一切全由公款买单,包括吃、穿、住、用以及大批服务人员的开销等。他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连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
莫洛托夫坦承,他也不知道自己挣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莫洛托夫这番谈话,说明超级权贵有多腐败!待到被逐出权力高层、强制退休,他才关心起自己的养老金,先是每月120卢布,后又增至300卢布。失势的莫洛托夫再也享受不到优越性了。
我不敢说是“红包”葬送了苏共和苏联。但由斯大林发“红包”而逐步形成的“在册权贵”,当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负全责。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与特权,不是小问题。若待遇过高、特权多多,难免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以致忘了初心、变质腐败,那就很可怕、很危险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抵制特权思想、不搞特殊化,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这确是切中要害的治党、反腐之关键所在,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方能免蹈苏共覆辙,立于不败之地。
执拗的“灰衣主教”
历经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的苏斯洛夫,自1948年接替日丹诺夫到1982年去世,掌管意识形态长达38年。他作为苏共最权威的理论家,却被人称为“灰衣主教”。
我不知“灰衣主教”的出典,是因为他常身着铁灰色西装,还是由于马列经典有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一说,遂以“灰衣”喻理论的缘故;但可肯定,“三朝元老”苏斯洛夫靠僵化思维、固守教条而稳居权力核心圈,对苏联后期的停滞不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有小学文化的苏斯洛夫,1921年入党后才上速成中学,再就读于国民经济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并在莫斯科大学和工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师。他跟斯大林私人秘书麦赫利斯熟识,当麦调入 《真理报》,办报著文均须引用列宁、斯大林语录,而这恰是苏斯洛夫的强项、特长。他总能找出恰到好处的领袖语录,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话也能很快觅得。麦赫利斯的举荐、提掖,让苏斯洛夫引起斯大林的注目;加上在“大清洗”运动中表现突出,苏斯洛夫仕途上节节高升。1947年由斯大林提名,45岁的他出任苏共组织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接手传媒舆论工作;后又兼 《真理报》 主编,一面卖力组织对“机会主义”的大批判,一面大肆鼓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深得领袖赏识。1952年进入中央主席团 (政治局),跻身苏共核心领导层。
“灰衣主教”并非浪得虚名。马恩列斯的语录,他格外用功,背得滚瓜烂熟,用来得心应手。1964年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命苏斯洛夫作大会发言、批判个人崇拜。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等替他拟好稿子,苏斯洛夫看了认为力度不足,有一处需用一段列宁语录加以提炼、点睛;布尔拉茨基想自己动手,苏斯洛夫抢先说:“这个我自己来,我现在就去找。”他跑到办公室,熟练地拉开小抽屉,然后快速翻检语录卡,一看不是,又默读另一张,还不对,最后抽出一张,他得意道:“就这张,这张合适。”布接过一瞧,觉得真是一段好语录,挺管用。多年后布尔拉茨基回忆说:“当我看到身为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找一段语录,就像找一个小玻璃珠子,就像过去的君主选捻珠一样,我不禁失笑起来。”其寻章摘句、翻检语录的本领,超一流!不过,一个理论家居然靠搜寻领袖语录吃饭,一切用语录来解决问题,岂能不陷于教条主义?
苏斯洛夫的死搬教条,有时执拗到锱铢必较的程度。因在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中抢先发难、立有头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苏斯洛夫格外倚重。不久他上升为二号人物,主持中央书记处,掌控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大权。苏斯洛夫则投桃报李,为勃列日涅夫炮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并对这个理论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了权威论述。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恪守斯大林教条“准确性”的“灰衣主教”,也闹出洋相、笑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的表述,每次写作班子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苏斯洛夫都很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改的理由,据称是“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两种表述没有实质性差异。“灰衣主教”执拗地改“和”为“—”,真正原因还在彰显其理论、表述的正统性、权威性。凡是斯大林、日丹诺夫、苏斯洛夫钦定的概念,一个字都不能改,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动!名为维护概念的“准确性”,实则维系其绝对权威,马列主义在他手里变成了“宗教”。只管在字面上竭力固守教条,不顾它与现实生活如何脱节,与社会实践如何背离;“灰衣主教”就是这么个闭眼不看事实、持极“左”教条的理论家。如同阿尔巴托夫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所说,“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 (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 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 《真理报》 的近期社论 (它们很快就会过时) 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 (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 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教条盛行、禁锢思想的苏联,许多人不得不扮演“夜间人”的角色。
一个党、一个国家,确像邓小平说的,“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斯大林、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种下的意识形态苦果,终化为苏共和苏联的不堪承受之痛!
(选自《钟山风雨》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