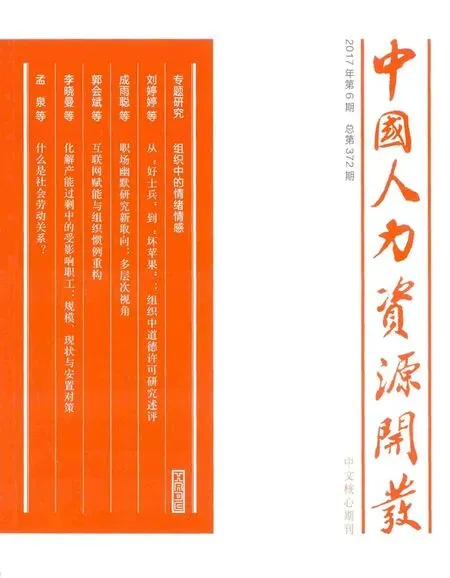两种“劳工力量”的再解析
——以S市和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为例
2017-10-13黄锐波
● 黄锐波
两种“劳工力量”的再解析
——以S市和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为例
● 黄锐波
赖特将劳工的力量分为“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并认为这两种“劳工力量”将对劳资关系博弈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赖特关于两种“劳工力量”的认知和阐述有其局限性。现实劳资关系博弈过程中,两种“劳工力量”的生成与演变,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本文以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为例,对两种“劳工力量”的生成与演变展开具体分析,认为两种“劳工力量”在劳资博弈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需跨越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生产过程的界限,立足于国家、市场与社会更广阔的视阈,才能获得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劳工的力量 劳资博弈 码头工人 工业行动
劳资关系博弈中,工人是如何通过集体力量向资方施压来获得自身待遇改善的呢?理性认识和评估“劳工的力量”,是劳动关系和劳工问题研究不能回避的现实命题。根据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Olin·Wright)的论述,工人阶级的力量分为“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结社力量”是指“来自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权力形式”,即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结构力量”则指“工人简单地由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结构力量”由两种“讨价还价的能力”组成:一种叫做“市场讨价还价能力”(market bargaining power),包括了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较低的失业率即所谓的“紧凑型劳动力市场”(tight labor market)和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另一种叫做“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这是一种“从卷入于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力。在那里,关节部位上的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在比该节点本身更为广大的规模上导致生产的解体。”(赖特,2006;2007)可见,赖特致力于从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生产过程去阐释工人的“结构力量”,并将工人的“结社力量”归结为工人的结社权及集体行动权。赖特对两种“劳工力量”的描述,将工人阶级的力量由“抽象力量”还原为“具体力量”,展现了工人阶级实质性的影响力。据此,西尔弗(Beverly J.Silver)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中,对赖特所阐述的两种“劳工力量”寄以厚望,视其为“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劳工抗争”进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源泉(西尔弗,2012)。
一、S市和H区码头工人工业行动的案例回顾
(一)S市Y公司码头工人两次工业行动案例回顾
2007 年 4 月 6 日上午八点,S 市 Y 公司的管理方正准备给码头吊车司机开班前会,此时,一名吊车司机在会上提出了要提高工资的诉求,理由是他们获悉其他港区的码头员工即将加薪,因此也要求提高工资。吊车司机提出的诉求,现场未获管理方的回应,却在工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晚七时许,一百多名吊车司机在Y 公司所在码头的某酒楼集合商议停工,Y 公司得知情况后派管理人员与工人沟通,由于相关条件未能达成共识,工人拒绝继续谈判,回到公司停车场集合,导致当晚码头作业陷于停滞状态。4月 7 日凌晨一点左右,三百多名码头工人在饭堂聚集,码头公司相关负责人多次与工人协调未果。此次Y 公司自发停工的码头工人,主要由塔桥司机和龙门吊司机两个工种构成。塔桥司机大多都是从龙门吊司机成长起来的老师傅,塔桥司机的工作难度和技术要求,比龙门吊司机要高。塔桥司机的(税前)工资在5300 元至8000 元之间不等,龙门吊司机的(税前)工资在3900元至5000 元之间不等。工人集体停工的主要诉求包括:每名吊车工人每月增加工资1000 元;提高奖金系数、设工勤奖、合理分配奖金;增加房补二百到四百元;支付加班工资;成立公司工会等。
Y公司码头工人的集体停工事件引起了S市政府当局的高度重视。4月7日上午,S市劳动保障、交通、工会等有关部门赶往现场开展协调工作,答复了工人有关工资、工时等方面的问题,并向工人解释了涉及劳动争议的法律法规。时任S市委书记和市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务必重视码头工人反映的问题,认真研究工人提出的合理诉求,畅通与工人的沟通渠道,进一步加强管理,尽快化解矛盾,并安排一名副市长专门负责协调解决此事。副市长随即带领S市交通、劳动保障、总工会及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到现场,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随后协同市、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工人代表见面,提出企业和工人要以大局为重,维护Y公司码头的国际形象,共同营造S市和谐家园,并表示市政府将成立工作小组,督促资方履行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
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4月8日凌晨3点左右,由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所有在职工人每人每月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加薪3%,另加500元,工人们随即回到岗位复工。2007年4月历时3天的工业行动结束后,受S市总工会委托,由某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律师担任工会的谈判指导和法律顾问,协助码头工人开展后续的一系列工作。劳资协商工作历时一个半月,成功追讨了过去八年的加班费,其中4000多万元直接补给工人。另外,Y公司答应给工人增加4000多万元的住房公积金。
2007年4月份停工事件以后,Y公司码头工人在S市总工会的指导下组建了工会,选举工会干部和代表,并于每年底通过工会代表与资方进行薪资集体协商,工人每年薪资涨幅达10%左右,这一薪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得Y公司劳资双方的关系得以维系稳定。时隔六年,2013年9月1日,因不满工资过低、公司承诺的工人子女奖学金没兑现等,Y公司800名塔吊龙门吊司机再次集体停工,要求加薪3000元/月,所有箱船作业全部停歇。9月2日,经资方与工人代表协商,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工人涨薪1700元/月,薪资涨幅达30%,工人答应9月3日复工。
(二)H区K公司码头工人工业行动案例回顾
2013年3月28日,H区K公司的码头工人,因过去十几年间工资有减无增,工作环境恶劣且存在极高的人身危险,合约条款不合理等,在K公司码头发起集体工业行动。参与集体行动的码头工人约100人,都是K公司外包商的雇员,主要从事码头吊机、拖车等不同工种。外包,即劳务派遣,指将承包合约之一部分甚至全部,委托或发放给承包合约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以减少人工成本。K公司将不同工种分为公司工和外包工,大部分吊机操作及货柜司机工种被外包给第三方,有些外包公司还将业务再次转手,进行“二包”、“三包”。公司工由K公司直接聘用,薪酬待遇、就餐及轮休时间、年终奖等福利相对较好;外包工则由外包公司聘用,工作时间通常是连续24小时,就餐及轮休时间不固定,各外包公司之间工人的待遇也有差别。
在码头职业工会组织下,K公司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持续发酵,参与集体行动的码头工人由最初两家外包商的部分工人,扩展到与K公司有外包业务的五家外包商近五百名工人加入工业行动行列。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引起了H区社会各界人士和社团的关注和介入,获得了800多万元社会基金的支持。从四月中旬开始,在H区政府劳工处的协调下,相关外包公司的资方代表与工会进行了共五轮劳资谈判。在劳资双方的连续谈判中,工会代表坚持每8小时加薪100元,即整体加薪约23%的诉求。K公司的其中两家外包商则提出加薪5%、另有2%福利津贴的“5+2”方案。谈判过程中,相关外包商的代表一直表现得态度强硬,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径直离开现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症状表现为胸骨后剧烈疼痛,同时也会有心律失常、心脏衰竭等症状,病情处于危重状态[1] 。在患者发病早期对其进行快速急救和护理是减少病死率和赢得有效治疗机会的重要措施。临床护理路径是一种重要的护理选择,注意针对疾病实施程序化、时间化和多元化预见性护理,因而能够及早发现病情,遏制并发症,提升护理质量。将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效果,现将此次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在持续的工业行动中,码头工人的集体行动形式多样,包括:一、在K 公司所在码头搭建临时帐篷,席地而睡,致使码头一度无法正常运作。二、到K 公司的资本集团大厦外安营扎寨,向资本雇主施压。三、向政府官员表达诉求,4 月 26 日晚,趁H 区政府举行劳动节酒会,工人游行到酒会地点,有出席酒会的工会代表呼吁政府领导到外面听取工人心声,但未获回应。其仅有的公开表态只是在酒会上致词时,谨慎表示,政府高度关注,希望双方互谅互让解决事件。H 区时任政府领导在回应码头工人工业行动事件时则表示,劳资纠纷发生以来,政府非常重视事态发展,多方斡旋。同时强调,政府没有既定立场,不会只争取一方的支持,政府也不该透过公众的喊话,去为任何一方争取利益。四、社会同情者利用诸如“撑到底”等话语来支持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也构成了码头工人的力量资源。
5月3日下午,码头工人接到“最后通牒”,K公司的四家外包商突然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对所有工种自本月起统一加薪9.8%,并派发4000元的红包,但不会再谈判,将于5月6日向H区政府书面确认加薪方案。5月6日晚,参加工业行动的近五百名工人进行集体表决,最后逾九成工人同意复工。工会代表称,将争取在5月9日复工,同时与资方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最后商定。至此,H区持续了40天的码头工人工业行动最终落下了帷幕。

表1 S市与H区码头工人工业行动案例资料整理汇总
二、两种“劳工力量”的生成与演变分析
根据案例回顾,不难发现,同样是码头技术工人诉诸涨薪的集体工业行动,S市码头工人历时短暂、速战速决,第一次行动获得了预期的涨薪目标,并成立了企业工会,随后还成功追讨了过去八年的加班费及住房公积金等权益;第二次行动的诉求也迅速取得了较理想的成果。而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历时月余、声势浩大,不仅拥有巨额的行动基金,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但最终却以小幅涨薪、部分工人遭到解雇而告终。S市与H区两地码头工人工业行动的不同结果,既引人深思又令人困惑:为什么同样是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在更加自由的H区,反而比在更加缺少自由的S市要更加艰难?笔者认为,要解开这个疑惑,须对赖特所阐述的两种“劳工力量”加以详细分析。那么,S市与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中,工人的“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是如何生成与演变的呢?
(一) S市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结构力量”的发挥与“结社力量”的限度
S市码头工人的两次工业行动中,工人的集体行动诉求之所以能够获得资方和政府迅速的回应,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行动结果,要归结于S市码头工人的“结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毋庸置疑,码头技术工人(塔吊和龙门吊)凭借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在码头货运行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是稀缺和重要的。码头技术工人的集体停工,完全可以导致作业流程需要严密配合的码头货运业陷入“瘫痪”状态。因此,S市码头工人的“结构力量”完全符合赖特所阐述的部分逻辑。
然而,笔者认为,S市码头工人两次工业行动的成功,其“结构力量”之要素构成,除了赖特所阐述的劳动力市场要素和劳动生产过程要素之外,还有其他的“结构性要素”不容忽视。
首先,“资本构成的性质与劳动所涉的产业经济地位”是S市Y公司码头工人工业行动成功的“结构性要素”之一。作为华南地区发展迅速的城市,S市的主要经济支柱以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港口物流业为核心。Y公司由某大型外资集团和S市旗下的港口集团合资成立,其中,外资集团持有六成左右股份,S市政府下属的港口集团占四成左右股份。Y公司于1994年正式营运,负责经营和管理Y公司所在港口码头的11个泊位。2006年,Y公司所在港口日均吞吐量为2.5万TEU,Y公司曾获得全球物流学会(GIL)颁发的“2005—2006年度全球最佳集装箱港口”之称号。Y公司在S市经济支柱产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基于Y公司如此特殊的“资本构成”和“产业经济地位”,Y公司码头工人集体停工后,S市政府当局才高度重视,派出了一名副市长专门负责介入、协调解决码头工人的停工事件,敦促劳资双方“共同维护Y公司港口的国际形象”。可见,工人的“结构力量”的发挥,不仅关乎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生产过程的影响因素,还取决于工人在特定的劳动体制或劳动关系中,是否与相关的利益主体存在紧密的“利益关联”。换句话说,工人劳动关系所涉的行业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关联的对维系和稳定产业经济的影响力,是劳资关系博弈过程中工人“结构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其次,“劳动关系的法律性质”决定了Y公司当局必须直面码头工人的行动诉求。S市码头工人的两次工业行动中,参与行动的码头工人与Y公司的劳动关系性质是“直接雇佣”关系,这种“正式工”的劳动关系与H区K公司码头工人都是“外判工”的法律性质不同。S市码头工人基于“直接雇佣”劳动关系的法律性质,将Y公司资方和S市政府共同带入到劳动争议的诉求主体,使得Y公司当局对于直面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责无旁贷。加上Y公司有相当的政府股份比例,S市政府作为雇主方也被拉入到劳动关系争议的直接主体中来。与H区K公司码头工人的“外判工”的劳动关系法律性质不同,H区的资本雇主利用本地完善的法律条款和成熟的法治条件,一直规避劳动关系争议的主体责任。H区码头工人停工期间,K公司当局一直回避码头工人的诉求,还向H区政府申请对码头工人在K公司码头席地而坐等行为实施禁令。在劳资谈判期间,K公司的代表一直也只是作为“列席方”参与其中。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由于“劳动关系法律性质”的差异,造成了两地码头工人在劳动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不同,两地码头工人“结构力量”的发挥也由于劳动关系的法律性质差异而变得分殊化。
最后,“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S市码头工人工业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不可否认,S市码头工人两次工业行动的成功,与S市总工会的积极介入是分不开的。S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城市典型,一方面产业经济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各种劳动关系争议事件一直此起彼伏。作为党群关系部门,S市总工会一直致力于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2007年4月Y公司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在S市总工会看来就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以往劳动关系争议所不同的是,过去大多数劳动争议都体现为工人们致力于争取“底线型利益”如讨薪等,而Y公司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却提出了“共建、共享”的诉求,并要求“成立工会”。这种“增长型利益”诉求给S市总工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触动。如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一套适合S市本土要求的劳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当时S市总工会与S市委、市政府达成的“政治共识”。尤其是到了2012年左右,在全国总工会的推动下,各地出现了一波积极响应全总要求,踊跃探索地方工会改革的新浪潮。在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开放”的情况下,促成了S市总工会、Y公司和码头工人顺理成章地达成某种“政治默契”。S市总工会在后来致力于把Y公司工会打造成S市劳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样板”,可见,S市Y公司码头工人两次集体工业行动的成功,与“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S市码头工人两次工业行动的成功,归因于多种“结构性要素”相结合,从而令S市码头工人的“结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集体工业行动的方式,码头工人实现了涨薪和成立工会的目标。然而,S市码头工人劳动关系的紧张状况却依旧存在。尽管S市总工会对外宣称Y公司码头工人有“组织起来的自信、理性和尊严”,但是,这仅仅局限于码头工人中的“正式工”为主。对于在Y公司港口区从事码头货运的众多其他工种和广泛分布于各外包公司的“劳务派遣性质”的码头工人而言,Y公司工会也许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组织影像”。在现有劳动体制下,这种“结社力量”的限度,反映在“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各种待遇上的差别就是现实。
(二)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结构力量”的限度与“结社力量”的影响
相对于S市码头工人工业行动的速战速决、成果显著,2013年H区K公司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历时月余、声势浩大,却最终只取得了9.8%幅度的涨薪,部分工人遭到解雇,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意外。然而,深入探究,H区码头工人的“行动失败”又是情理之中。H区码头工人“行动失败”的主因要归结于工人的“结构力量”受到限制。
首先,K公司及其背后的资本集团在H区经济链条中的“霸权地位”,是K公司码头工人的“结构力量”发挥受限的原因之一。K公司在其港口拥有四个码头,与其他企业合资经营一个码头。据K公司母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K公司在2011年和2012年总盈利分别为30亿及35.8亿元,2012年K公司母公司的税前盈利率达到32%。K公司码头工人发起工业行动后,H区付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表示:单在工潮头10天,货柜码头效率降至正常时候的50%,造成的损失已达数以亿元计。他还称,已有付货公司担心H区今后还会出现码头工潮,已经改用其他港口,或将H区列入“观察名单”。H区付货人委员会主席也表示,受到工潮影响,不少工厂将区域内生产的成品转到其他港口出口,在H区货柜码头未能回复正常运作时,许多运至H区的货物被迫转运至邻近港口,影响涉及许多行业,造成的损失已达数以亿元计。以上多方数据表明,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所具备的“威慑力”本来是相当明显的。然而,为什么K公司和资方谈判代表在码头工人集体工业行动过程中一直态度强硬呢?这与K公司及其资本集团在H区本土经济体中的霸权地位是分不开的。K公司背后的资本集团在H区的产业分布遍及各个行业,资本集团担心一旦对K公司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采取妥协,会激起资本集团在H区本土其他产业链条中工人的“行动效仿”。因此,守住码头工人工业行动的“第一道防线”,也就守住了资本集团在H区其他产业链条中的“战斗堡垒”。码头工人发起工业行动之后,资本集团一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动用了旗下的媒体和报纸,对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进行舆论反击。正是在这样一种“强资本”的态势下,K公司码头工人的“结构力量”才显得势单力薄。
其次,K公司码头工人“外判工”的劳动关系法律性质,造成了劳资对抗过程中,K公司雇主方可以规避劳动争议的法律主体,从而影响了劳资谈判过程中工人“结构力量”发挥的针对性和直接性。K公司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中,率先发起工业行动的工人均是码头外包公司的“外判工”。在劳资关系结构中,正是基于这种“雇佣劳动关系的法律主体转移”,造成了劳资争议一旦进入法律程序,直接的谈判主体将不再是“劳动力的使用方”而是“雇佣关系的发生方”。K公司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发生以后,无论工人的行动方式和抗议声音何其激烈,K公司及其资本集团均以没有直接雇佣劳动关系为由,采取回避的态度。在法治条件和法律体系比较成熟发达的H区,K公司及其资本集团甚至还可以向政府申请财产保护禁令,来对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进行限制。
最后,当H区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最终发展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时,码头工人原来比较清晰的“涨薪”诉求,被这场具有多重声音的社会运动所淹没。H区政府基于本土社会的复杂性,在“政治机会结构”尚未具备成熟、开放的条件下,对这场充满多重声音的社会运动浪潮采取了“回避”的立场和态度。而码头工人原来诉诸“涨薪”的经济诉求,不可避免地随着这场声音复杂的社会运动的结束,最终归于失败。虽然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持续月余、形式多样、多方支持、行动基金多达800万元,但是,码头工人却不得不面对接受不到10%涨薪幅度的最终结果。
诚然,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基于“结构力量”受限导致最终的结果未必尽如人意;然而,这场经由码头工人发起的诉诸“涨薪”的集体工业行动,最终演化为历时月余、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所展示的“结社力量”却余音未绝。虽然码头工人最终并未实现 “涨薪”的最初诉求,H区社会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却因为支援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而汇聚到一起,通过社会运动表达了各方的呼声和诉求,将H区积累了多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得以展露,足以引起H区政府、资本集团和社会各方的集体反思。一个成熟的社会,通常能够将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来,从而令社会发展与社会运动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和张力(赵鼎新,2012)。由H区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所演化而成这场社会运动,通过社会结社与理性表达的方式,可以避免“原子化的个体”诉求无力之后走向“极端化的暴力行为”、也避免由“失去理性的乌合之众”带来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因此,K公司码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对于H区未来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积极正面的社会意义。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如何构成H区“社会反向运动”的部分内容并与其他复杂的社会运动区别开来?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能否引致未来H区经济复苏进程中劳工政策的调整?这些问题,都将是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所展现的“结社力量”以及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三、两种“劳工力量”的再认识: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多重互动
通过对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工业行动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在劳资关系博弈这一主题中,工人阶级的“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之生成与演变,不仅是限于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生产过程的“局部现象”。两种“劳工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机理,需置于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重互动的视阈中,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洞悉。
(一)国家视角与两种“劳工力量”的再认识
1985年,由彼得·埃文斯等主编的《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面世,该书收入了卡茨纳尔逊(Katznelson)从国家角度比较英、美工人阶级形成的著名论文,引起广泛关注。实际上,从国家视角考察劳资关系博弈现象的理论传统由来已久。
奈特尔(Nettle)最早提出“国家性”(stateness)的概念,认为“在强大国家里更容易出现反制度运动并非是一种巧合”。“国家性”较弱是英美两国的工人运动未走上激进化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Nettle,1968)。“国家”作为一个“概念变量”还体现在国家“政体类型”(regime type)的差别上:即自由国家或专制国家。熊彼特指出,由于德国存在着压制性和排斥性(exclusive)的劳动体制,这种专制国家的暴力使用迫使德国工人运动采用激进化的方式,走上与国家对抗的道路;而英国的工人运动则由于自由国家的存在,从而走上较为温和的政治发展道路(Schumpeter,1950)。卡茨纳尔逊进一步分析了同是“自由国家”的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也有所不同,强调公民普选权实施时间及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差别,是英美两国工人阶级形成模式存在差异的关键原因。(卡茨纳尔逊,2009)。维多莉亚·哈特姆(Victoria Hattam)则更为详细地阐释了英美两国工人运动的道路分殊在于两国司法体系的差异上(Hattam,1992;1993)。
为了突出国家维度的影响,蒂利(Tilly)、麦克亚当(McAdam)和塔罗(Tarrow)等人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来进一步阐述国家制度、策略与集体抗争行动之间的互动原理。“抗争政治”理论认为,一定的制度结构塑造了策略的行动;运动的组织者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选择其目标、策略和手段;政治环境设定了运动的因由、塑造了运动的议题主张和行动策略;政体中的特定的组织形式和行动者的结构位置,使得某些动员策略更为有效,或者更有吸引力(刘春荣,2012)。诸如政权的开放性程度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公共政策和精英联盟、制度中的积极分子、精英分化、决策过程、政治的空间管制能力、镇压意图和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能力等等,均构成了影响集体行动策略选择和发展走向的“政治机会结构”。黄冬娅还从“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角度出发,将国家区分为三个概念层次:即“稳定的政治结构”(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包括国家渗透能力、战略和策略)和“变化的政治背景”(包括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和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三个层次上的诸多要素都对社会抗争的兴起、形式和结果以及对抗争主体的身份认同和行动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黄冬娅,2012)。
可见,在“策略——关系”的“国家”概念视野中,国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面目”,这对于观察和分析“国家角色”对劳资关系博弈的多重影响极具理论启示。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中,工人的“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之生成与演变,实际上受到S市和H区两地具体、特殊的政治环境、政策条件的深刻影响。S市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过程中,政府部门、地方工会积极介入、妥善周旋,及时回应和解决了工人的行动诉求,并向第三方法律机构开放了介入门户,避免了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进一步升级,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过程中,政府当局态度暧昧、消极回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介入和声援,最后发展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无不体现了两地码头工人的“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之生成与演变,在“策略——关系”的“国家”概念视野中,有着不同的机制、机理过程,从而造就了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走向和行动结果大相径庭。
(二)市场视角与两种“劳工力量”的再认识
从市场视角对两种“劳工力量”进行考察,离不开对“全球化”这一维度的分析。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而获得确认。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致力于构建全球性生产网络,其目的是试图以一种“空间性解决方案”(spatial fix)来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资本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过度积累”的问题(Harvey,2001)。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的资本积累,资本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对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了广泛的重新组织。资本的积累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戴维·哈维将这种变化称为“弹性的积累”(Harvey,1990),即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表现出充分的“弹性”(以灵活生产、临时性劳动力使用、国家干预撤离及私有化为特征)。
贝弗里·J·西尔弗(Beverly J.Silver)在哈维的空间调整(spatial fix)的分析基础上,加入了技术调整(technological fix)、产品调整(product fix)和金融调整(financial fix)分析变量(西尔弗,2012),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对劳动控制策略的变化以及对全球劳工运动发展趋势的影响。。
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下,但两地码头工人却无独有偶地处于同一个资本集团的雇佣关系中。毋庸置疑,两地码头工人共同的资本雇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强大的“调整”(fix)策略和能力。但是,资本雇主的这种“调整”(fix)策略和能力,在S市和H区两地具体环境中的表现却有所差别。S市Y公司因其拥有部分政府股份背景,加上资本集团在S市本土及其他领域均有广泛的投资涉及,国有资本的股份构成、官方工会所蕴含的不可推脱的工人立场取向以及与跨国资本的种种缠斗和博弈,造就了S市码头工人在两次工业行动中,地方政府和地方总工会的介入拥有较大的斡旋余地和筹码。而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缘于资本集团在H区本土的“霸权地位”以及资本跨国流动的“威慑”,造成了H区政府当局在介入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中如履薄冰、迟疑不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虽指向共同的资本雇主,但是基于资本在两地所具备的“调整”(fix)策略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造成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呈现不同的走向和结果。
即便如此,S市和H区两地码头的工人却通过各自的集体工业行动,彼此呼应了对同一个资本雇主的抗争,传递了体现“劳工力量”的强大信号。正如西尔弗所说,不管资本如何通过各种调整策略来强化对劳工的控制并弱化劳工的团结,试图消解劳资冲突和劳工运动,处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因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全球政治进程而被彼此联系在一起。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劳工运动的“个案”之间,会基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通过传播和团结得以构成联系,这种“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会促成劳工国际主义的新发展。(西尔弗,2012)。
(三)社会视角与两种“劳工力量”的再认识
卡尔·波兰尼将劳工抗争与社会运动的发生置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中予以审视。波兰尼认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嵌入关系”,市场原本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但是由于土地、货币和劳动力(人)的商品化,造成了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市场力量在商品化的推动下变得“野蛮”,从而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脱嵌”,这将引致社会对市场的“反向运动”,也即通过社会抗议运动将市场重新拉入到对社会的“嵌入”关系中来,从而实现对市场和商品化之野蛮力量的“重新驯服”(波兰尼,2007)。
从社会视角看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最值得关注的是“劳务派遣”现象的产生。与波兰尼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早期土地、货币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所不同,“劳务派遣”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关系的商品化”,这比“劳动力的商品化”在程度上更递进了一层。然而,由“商品化”所引致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反向运动”却依然符合波兰尼的逻辑路径。S市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中,由于Y公司的管理当局致力于强化对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的管制,对于主要码头工种严禁外包,特别是严令禁止二包、三包。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关系的商品化”所带来的劳动关系恶化和劳资剧烈冲突。而H区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主要由K公司的“外判工”发起。K公司对码头工人工种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区分为“公司工”和“外判工”,特别是对于同一岗位工种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导致了“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歧视。因此,K公司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从开始的“码头静坐”不断发展升级为“社会运动”,与“劳务派遣”这种“劳动关系商品化”的恶果是紧密相连的。无论K公司及其背后的资本集体如何在劳资谈判过程中如何规避“直接雇主责任”,由“劳动关系商品化”所引致的劳资冲突的事实以及所带来的多方损耗,却是“社会反向运动”的切实体现。
波兰尼立足于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史,用“市场社会”的概念重塑了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重申了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嵌入关系”,深刻地警示“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并强调“社会的发现”具有更重要的人类价值。波兰尼的“社会”概念,涵盖了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社会的各种保护性组织以及市场中各种非商品化的关系纽带等(波兰尼,2007)。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的工业行动中,两种“劳动力量”的生成与演变,基于两地码头工人劳动关系商品化的程度有所不同,两地码头工人劳动关系受保护的程度和“嵌入社会”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两地码头工人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市场社会结构”及其对于“社会”的“脱嵌”程度,导致了两地码头工人所发起的“社会反向运动”的剧烈程度、发展走向和结果不一。
四、结语与讨论
赖特透过对劳动力市场与劳动生产过程的观察,对工人的“结构力量”赋予了实质性的内涵,并将工人的“结社力量”视为天然的集体影响力。然而,通过S市和H区两地码头工人工业行动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工人“结构力量”的发挥,并不局限于劳动力市场与劳动生产过程;工人“结社力量”的产生也不是天然而成。两种“劳工力量”的具体发挥,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失衡”状态,进而导致工人的集体工业行动呈现不同走向。两种“劳工力量”的生成与演变,受制于“关系——策略”概念中的国家角色、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调整能力”以及特殊的“市场社会结构”之多重互动与影响。
泽尔博格等人早就指出,各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人运动模式呈现“例外主义”(泽尔博格,1986)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工人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工人的“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的运用机制、机理和结果大相径庭。由此可见,赖特所提出的两种“劳工力量”之具体发挥以及西尔弗对“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劳工抗争”前景之乐观判断,仍需持审慎态度并有待于进一步拓宽观察视野。
1. 埃里克·奥林·赖特(著),胡丽娜(译):《工人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妥协》,载李友梅等(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19页;及转引自:沈原(著):《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2. 艾拉·卡茨纳尔逊(著),方力维等(译):《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载彼得·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 第349-378页。
3. 贝弗里·J·西尔弗(著),张璐(译):《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7-238页。
5. 卡尔·波兰尼(著),冯刚等(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 刘春荣:《社会运动的政治逻辑:一个文献检讨》,载《集体行动的中国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7.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版。
8. Aristide Zolberg, How many exceptionalism? In Ira Katznelson & Aristide Zolberg(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446-448.
9.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New York:Routledge,2001:315、369.
10.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0:121.
11.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Row,1950:341-343
12. Nettle P,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1968.
13. Victoria Hattam,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1820-1896.In Sven Steinmo et al.(eds.),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33-166.
14. Victoria Hattam, Labor visions and state power:the origins of business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A Reanalysis on Two Types of "Labor Power"——An Example of Industrial Action by S City and H Region Dockers
Huang Ruibo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Research Institu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Wright classified the labor power into “structural power” and“associational power”,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two types of “labor power”would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labor-capital disputes. Wright has his limitation on cognizing an elaborating the two types of “labor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laborcapital disput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wo types of “labor power” are often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Taking the S city and H region Dockers’ industrial actio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will carry out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labor power”, and demonstrate a brief that the two types of“labor power” won’t play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market and production process,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thereby obtaining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
Labor Power; Labor Disputes; Dockers; Industrial Action
黄锐波,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讲师,管理学硕士。电子邮箱:hruibo@163.com。
■ 责编 /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