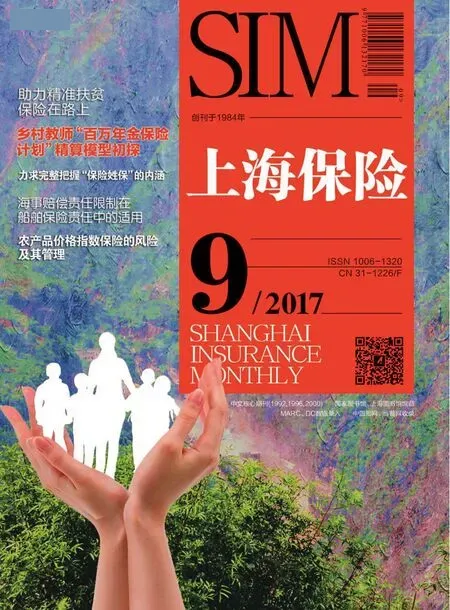论格式化保单条款下对保险消费者之保护
2017-09-29丁旭明华东政法大学
丁旭明 华东政法大学
论格式化保单条款下对保险消费者之保护
丁旭明 华东政法大学

一、引言
现代合同法的发展是在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原则下背反与角力下激荡前行的,在私法自治原则下,因合同当事人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容易产生一些订约不公平的情况。在坚守合同订定必须遵守诚信原则之下,国家公权力此时不应仅扮演中立旁观者的角色,而必须适时介入。有些格式化合同条款经由监管机构或公会自治组织事先审查,调整其中部分不公平的合同条件,藉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达到保护消费者之目的。
格式化合同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由一方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在实务中,使用格式化合同条款的,多半发生在经济实力强弱不等的合同主体之间,使得在交易上屈居劣势的一方,纵使发现交易内容、合同条件对己不利之处,也仅有接受或拒绝的选项(take it or not),而无与强势一方具有对等谈判协商、交涉的能力和可能。由于保险商品保障的内容,是通过一系列合同的条款构成,而这些所谓的格式化保单条款是由保险人所拟定,其条款内容通常是对保险人有利,而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权益保护则产生不利的后果,再加上保险业专业程度较高,一般保险消费者难以了解和读懂保单的内容,特别是除外责任条款与不承保事项的设定,会大大限制保障的范围,因此,如何贯彻对价平衡的原则,便成为保险监管机构保护保险消费者最为关切的重要事项。
保险实务中,除极少数险种经由当事人洽商而订立保险合同外,大多数都是使用格式化保险合同的。为确保条款接受方权益,保险监管机构需要事先审查保险商品的内容,即通过立法及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尽量对保险消费者调处到一个可以公平接受条件的地步,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对保险商品的合理期待,最大限度体现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两大原则。本文意在研究通过如何对格式化保单条款提供者在內容制定与解释上予以必要的规制的同时,在订立合同程序上对保单条款接收方予以更周全的保护,并期待“保险消费者”之法律界定能在未来《保险法》修改中得到明确和重视。
二、格式化保单条款存在之法理
为符合私法自治的精神,《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但目前实务中,保险合同订立除极少数情形外,大多使用格式化条款,这与私法自治中合同订立贯彻内容自由的原则相左。同样,这种附随性质的保险合同也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规定的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的原则有相违之嫌。
然而,格式化保单条款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现代保险的经营中追求危险的标准化及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因网络交易活动大量增加,对交易效率(成交速度)要求增大,使得通过个别磋商的交易形态比例愈来愈低。除了通过保险经纪人或企业专业人士与保险人磋商能获取较好的承保条件外,大多数的保险消费者因囿于保险与法律知识之不足,其经洽商订约的效果往往还不如格式保单合同中提供的各项条件更为有利。由于保险消费者没有谈判能力与保险人对等地洽订保险合同,于是,取而代之的便是由保险人单方面拟定各类格式化合同条款,供不特定的多数人选择使用。
保险人拟订的格式化条款内容通常是对己有利,且其中的风险大小与价格高低等产品特性,亦唯保险人所知悉,因此这些对保险消费者是显失公平的。有鉴于此,德国将消费者保护视为公法的领域,特将投保人与保险人间使用的保单条款,交由法律强制对其进行规范。德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特殊情况或法律有特别规定下才可适用例外条款,通常情况下,标准保险合同条款须由保险市场参与者——保险人、保险代理人、投保人(保险消费者)及相关专家共同参与拟订草案,该草案再由专家学者审核通过后才供业者使用,其目的无非是为保险消费者把关,减少对保单持有人因不公平的条款可能带来的各种伤害。
与德国相比,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保单标准条款或保单示范条款,由当地保险同业公会邀集专家学者研拟保单条款内容,报送保险业主管机关审核通过后业者才能采用。2006年9月,台湾地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人身保险商品送审规则》,该规则明确指出,除非较示范条款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外,保单条款均应比照示范条款及现行相关法令规定订立;送审商品条文如与示范条款不一致时,应据实划线表示并制作对照表,不得有任何的隐瞒。
中国大陆对保单条款的监管则是采用分级管理办法。根据《保险法》第135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应当报保监会批准。至于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则报请保监会备案。”紧接着该法第136条规定:“保单条款必须合法、合规,违反者保监会责令其停止使用,限期修改;情节严重者,保监会可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申报新的保单条款。”最后,该法第170条又规定:“使用未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监管机关将责令其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停止承接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
由上可知,海峡两岸均未如德国那样全部采用标准保险合同条款,个中原因,可能是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来审查保单条款,也有可能是为了保持市场适度的竞争,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私法自治无法遂行,还是公法基于对消费者最低保护要求之理由,这些均是构成保险实务中普遍采用格式化保单条款的直接原因。
三、保险消费者采用“核准”格式化条款的必要性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为此,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强调,由于金融商品设计的复杂度,必须对消费者加强保护,由此提出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无独有偶,英国保险法百年改革中,也认为欲精确地处理一般消费者保险合同权利义务上的关系,亟须在保险法上单独界定“保险消费者”,以与企业保险者进行区分。鉴于保险合同当事人间的不对等性质,且保险业和经济、社会具有密切的关系,欧盟法院也认为保险业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必须从消费者观点出发审慎处理。
受保险业发达国家的影响,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十条”)中首次提出“保险消费者”的概念。但遗憾的是对此未予明确定义。不过,循着近20年保险法发展的脉络,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一致认为应该将“保险消费者”与“企业保险者”进行区别对待。那么,“保险消费者”的概念究竟为何?简而言之,就是指购买保险者除企业之外的那部分自然人。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中,也将消费者定义为自然人。
但笔者认为,是否属于保险消费者,仅以自然人身份为唯一判断标准是有失偏颇的。2008年修改后的《德国保险合同法》在界定保险消费者的概念时,是以其与保险人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以及专业知识上的悬殊作为判断标准的,因此,一些非自然人的小微企业亦可作为保险消费者被纳入受保护之列。与此相反,具有专业知识且拥有与保险经营者单独议定保险合同内容、价格等能力的那些自然人,不应归入保险消费者行列。
据此笔者认为,归属于“保险消费者”应有以下二点特征:其一,保险专业知识不足。其二,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相较于德国《保险法》,英国对保险消费者所下定义则不同,适用范围上也有差异。2015通过的英国《保险法》,其中有关“保险消费者”定义,与2012年颁布的《消费者保险法》〔Consumer Insurance(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 Act 2012〕中的定义相同,即“保险消费者”系指与保险人订立或拟订消费者保险合同的个人。故此,保险消费者为自然人,缔约目的必须为非商业性质,从而将小微企业排除在外。除个人目的外,兼具商业目的的“混合用途”,亦涵盖在消费者保险合同之内,纳入其调整范围。例如:有限范围内的商业用途的私人机动车辆、私人游艇投保,这些都仍属于消费者保险合同。反之,公司车辆偶尔转为私人用途,仍然改变不了其企业车辆的性质,即便其投保,仍不能归属于消费者保险合同之内。
在德国,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内容最主要规定于《民法典》(Civil Code)中。消费者合同之条款,通常由企业经营者先拟定,消费者无法对合同内容施加任何影响。由于保险消费者对于合同的条款无置喙的余地,且其与保险人的经济地位与专业知识相差悬殊,所以格式化条款的内容的公平合理与否,必须由保险监管机构事先审查核准。笔者认为,应该学习并借鉴德国模式,采用事先经审查保单条款,坚决排除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与不保条款。唯有如此,才能强有力地保护那些没有专业知识和法律常识的保险消费者,在其通过购买保险商品实现保障的合理期待范围内,受到最低程度的保护。
四、格式化保单条款内容控制原则
为弥补保险人可能利用其强势的地位,拟订一些诸如免责条款、失权条款、概括性条款、法院管辖权条款等有利于自己的条款,造成对保险消费者在合同上的危险或负担不合理的分配的后果,得采用德国《民法典》第307条内容控制原则,将之明文规定于法律之中。
所谓格式化条款内容控制的原则,系指国家基于社会公平或是消费者保护考虑,为谋求合同当事人间实质正义,在未违背法律强制规定下,秉持诚信的原则进行调和的一种手段。一般交易条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话,将使得格式合同提供人之相对人受到利益损害,故控制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种: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不得任意排除一方应享之权利;不得任意加重一方应尽义务之规定。其实,海峡两岸已把这类规定放在《保险法》《消费者保护法》之中。
台湾地区最早有关格式化条款合同内容控制原则,见于“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该条规定格式化条款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显失公平,约定内容无效:(1)违反平等互惠原则者;(2)条款与其所排除不予适用之任意规定之立法意旨显相矛盾者;(3)契约之主要权利或义务,因受条款之限制,致契约之目的难以达成者。
从以上3项规定的内容看来,其旨在强调格式化合同条款之拟订者必须公平,不得有造成合同他方当事人购买商品或服务之合理期待目的难以达成,或与法律条款立法意旨相违背之情事。除了第(1)项外,其他两项和德国《民法典》第307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相同。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17-1条规定,格式化合同条款是否符合上项规定,由企业经营者负举证责任。
1997年,台湾地区修订“保险法”时也将类似条款内容增订于第54条第1款,规定保险合同有下列情形的条款,按订立合同当时的情形认定是显失公平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无效:(1)免除或减轻保险人依本法应负之义务;(2)使投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险人放弃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权利者;(3)加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义务者;(4)其他于投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险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以上规定的内容,与台湾地区“民法”第247条第1款(附合契约)规定是基本相同的,而与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相比则其范围较窄。该条的内容比较明确,目的在于寻求天平两端的平衡,且将判断公平与否的时点定于合同订立时,至于保险合同订立以后,因情事变更,有其他协议或弃权、禁反言情形的,造成双方权利义务倾斜的,则在所不问。
中国大陆的格式化条款合同内容控制原则,规定在《保险法》第19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2、第3款中。《保险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1)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2)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比较两岸保险法有关格式化保单条款之内容控制原则规定,台湾地区的内容控制范围较宽,符合潮流趋势,但其也存在不够周延之处。因为有能力与保险人洽商订立保险合同者,无论在专业知识或是经济实力上,其应该是属于和保险人对等的地位,这类的保险合同条款无须特别予以规范。而一般的保险消费者因其主、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与保险人对等交涉,故需特别的保护。可见,上述两者在地位上、性质上应是有所区别的。因此,限定合同条款的内容控制原则使用于格式化保险合同是比较适宜的立法。
其次,因为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关系人有影响的,除了权利的限缩与义务的加重外还有其他未虑及的因素,因此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4条第1款第4项规定对投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险人有重大不利益情形的也包含其中。如前所述,对于公平、公正交易评判的时点,规定于订立保险合同之时,也是完善立法评价准则考虑因素。这两点可供大陆今后修订《保险法》时参酌采纳。
五、格式化保单条款的解释
既然保险消费者购买保险商品采用保险人预先拟妥的保单条款,因此当发生争议后,法院自不能默视投保人购买保险商品的本意,墨守保单条款之文字解释。英国法院于1743年Tierney一案中指出,应为最有利于被保险人之方式探求其真意。这项英美法上的不利解释法则(ruleofcontra proferentem),和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保险合同解释应探求合同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文字;如有疑义时,以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解释为原则,两者意义上是相同的。疑义之利益归诸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乃基于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尽义务之未尽,故须承担由此带来之不利后果。
德国《民法典》第305(c)条第2款规定,当一般交易条款产生疑义时,应作出对提供人不利之解释。第307条第1款后段也解释因为条款不明和不易懂,都是构成对合同相对人不利的原因。

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采用格式保险合同的,当发生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条款有争议的,系按照“通常的理解”来解释。但产生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种不按照一般国家探求当事人真意的立法方式,而使用“通常的理解”的方式来解释争议的条款,乍看之下,对保险消费者保护的程度远不如台湾地区的规定与英美法上判例之见解,将保险消费者的真意表述为购买保险商品的合理期待目的。对此,樊启荣教授认为“通常的理解”是格式条款“使用的对象群”的普遍理解,是理性被保险人的理解,归根结底是法官的理解。这样逻辑推理解释最后仍由个案法官予以斟酌,和英美法上之“法官造法”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笔者认为,英美法上之“法官造法”功能,虽对伸张正义有一定的功用,但过分倾斜(judicial prejudice)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不利法律稳定性的要求与危险共同团体的利益,使用上仍然要审慎注意。
另外,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4条第1款采用德国《保险合同法》中的绝对强制规定(asolut zwingende vorschriften)与相对强制规定(relative zwingende vorschriften,德国学说将法律强制规定因作有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利之解释而变更的,称为相对强制规定或半强制规定),即“本法的强制规定,不得以契约变更之。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不在此限”。前段属德国保险合同法中的绝对强制规定,如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或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后段规定属德国法中的相对强制规定。
对格式化保单条款合理解释所必须掌握的原则是,对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无效;违反法律相对强制规定的,若有利于被保险人,仍然有效。到底是违反强制规定抑或是相对强制规定,不能仅看格式化保单条款表面上的文字义务,必须视这段文字对被保险人有利或不利而定。说明这一内容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在适用《保险法》第16条时,当投保人非故意违反告知义务时,保险人若愿意以其他保险条件同意承保时,此时就有可能由原来的强制规定变更为相对强制规定。
六、格式化保单条款纳入犹豫期、冷却期规定的合理性
犹豫期与冷却期制度是因保险商品营销渠道不同而发展出保护保险消费者的规定,而台湾地区“保险法”的缺陷,就是缺失了订约前保险人对投保人有信息揭露义务的规定。为了全面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除对保险人提供之格式保单条款内容予以控制外,在订约程序上,是否有乘人之危、轻率或无经验之情形也应关注。再者,保障保险消费者“知”的权利为当今保险先进国家的立法趋势,保险人在合同订立前的信息揭露义务,属于法定告知义务,故德国《2008年保险合同法》第7条第1款与第8条第1款,将这一项内容列为强制性规定,不得以约定的方式使投保人放弃,同时还规定投保人于收到保险单及相关文件后有14天的犹豫期。
在“放开前端、管住后端”保险监管政策转变下,为加强对保险消费者保护的配套措施,2015年10月1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增订《保险法》第48条,对于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约定不少于20天的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全部保险费。虽各方对此新规定合理与否有不同的意见,但笔者认为,将犹豫期制度纳入《保险法》中,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使得保险商品经由网上、电视、电话、社交群体媒介招揽出售的情形日益增多,冷却期(cooling-period)制度的设计尤为必要。换言之,在保险人高强度的推销技巧下,投保人因人情关系或一时的冲动购买非其本意需求的商品,因此在立法上有必要给予保险消费者摆脱这种高压销售环境后冷静思考的时间,检视其是否真正需要或有经济能力购买这种商品。特别是保险消费者在面临远程交易(distance marketing)行为下,仅凭借着保险人在网上载出数量众多的条款、艰涩难懂的保险及法律术语,对投保人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故也有必要于签订保险合同后再给予其一段合理的时间,以便冷静思考或者咨询他人,允许其有后悔的机会。美国、英国与欧盟都极力推行此一制度,但为避免消费者滥用该款而造成保险人不当成本的负担,在适用范围上加以严格限制。
虽然冷却期制度与《合同法》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格格不入,但由于个人类的险种藉由远程营销模式日益增多,为更好地保护保险消费者,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有必要借鉴并移植在国外已相当成熟的这项制度,使得保险消费者无论是藉由何种营销渠道购得保险商品,在订约程序上都能获得周全的保护。
七、结论
现行保险经营制度与环境引发“保险消费者”概念兴起。关于保护消费者的相关法条,散见于各个法律中。而在保险法领域,未将“保险消费者”概念析离出来,清楚呈现。为此,笔者认为,为使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应借鉴英国保险法改革方式或者引入德国《2008年保险合同法》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会涉及到立法体例的转变,乃至对《保险法》作大幅度的修订甚或重新制定。
2014年“新国十条”已提出“保险消费者”的概念,期盼立法部门能认真思考,将此概念纳入到《保险法》修订范围之中。因为这一举动,不仅能满足维护保险消费者最低合理期待的标准,而且还能以先进的立法思维引领亚洲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