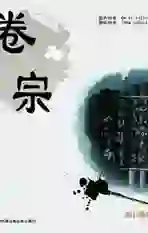封建体制下的“法效”
2017-09-06孙宇翔
摘 要:谈到中国古代依法审判制度,不免有许多学者会产生疑问,中国古代法制究竟是不是遵从依法审判的原则呢?或有赞同或有否认。笔者将立足于俞老先生“罪刑法定与非法定的和合”一文之观点,浅谈一下“法效”视角下的中国古代依法审判制度。
关键词:依法审判;罪刑法定;和合;法效
晋代三公尚书刘颂:“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中华法系之代表《唐律》:“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甚至追溯至法制公开化时期的秦,出土之云梦秦简也有赦免时不究既往的记载。这其中都蕴含着罪刑法定的精神所在,可反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这其中历朝历代是否在司法审判上都遵循着依法审判之精神呢?在此问题上我想我要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中国古代依法审判制度。
谈到依法审判,很容易把它与罪刑法定联系在一起,其实二者中间是有一些差别的。罪刑法定是西方法治自由民主下的产物,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令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俞老先生在“罪刑法定与非法定的和合”中谈到罪刑法定的四项原则,即不溯及既往、刑事立法清晰明白、禁止类推、法官应当严格解释。可见罪刑法定多从立法以及司法适用的角度谈及刑事犯罪及量刑标准是否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依法审判的概念外延则比罪刑法定大很多,可以说罪刑法定是依法審判的要求之一。
在俞老先生论文中提到的针对中国古代法是否存在罪刑法定之问题分为肯定说、否定说、以及矛盾统一体说,俞老先生本人提出了合和说,他认为法定与非法定是在封建体制中不断的冲突、融合,将公平、正义、秩序、权利与道德的合情、合理、天理、人情、国法有机的融合于一体。思考之后,赞同俞老先生观点之余,我想提出一些自己的论断。
我认为探究中国古代依法审判制度是在衡量一个封建时代法的“法效”问题,正如现在我国着力建设法治国家一样,法治所体现的法的效力要高于一切,当一切的秩序、制度设计都被纳入到法律的规制范围之内时,在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内违法必然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从司法的角度而言,司法审判必定依法进行,审判结果必定有相应之法律依据,司法解释也应严格按照律文应有之意或在合理范围之内作出扩大或缩小解释,这些都符合着文明社会依法审判的要求。但当我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具体的分析古代依法审判制度的时候,“法效”似乎并没有那么的之上,至少法是低于皇权的统治手段,从此点上看中国古代审判制度就不能说完全的依法,至少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皇帝才是司法权的最终享有者。
从罪行法定的实质角度而言,我并不赞同俞老先生文章中提及一些学者的观点如肯定说与否定说。以中华法系之代表《唐律》举例,《唐律》规定定罪判刑一定要依据刑律的正式条文,这固然属于“依法律定罪判刑原则”,但“还必须结合地考察与之有关的其他原则制度”则反其道承认了皇权的特别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罪刑法定,实现皇权专断。从此而看既不能说肯定了罪刑法定,因为并没有突破皇权的笼罩与支配,也不能因此就否定罪刑法定的存在,因为在数以万计的案件当中,大部分基层无争议案件还是会依法做出裁判结论。受此启发,我认为在封建体制这一根本束缚中不存在民主共和社会乃至法治国家的依法审判制度,只能说封建皇权越发集中的趋势之下,依法审判是在逐步转型为统治者巩固皇权,削弱地方官权的工具(如汉县道等下级官吏必须严格法定审判,不得比附,廷尉可以提比附建议,终裁大权在于皇帝),法也逐步成为皇帝统治江山的手段之一,因此“法效”在封建体制中不可能突破皇权的垄断与集中,也只能实现效力之内的依法审判,超过了这个效力范围,则难以保证案件裁判结果依法有据。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中国古代审判制度中早已蕴含了依法审判的萌芽思想,只是封建统治根深蒂固,人治思维强势保守,以至中国古代会出现俞老先生提出的“罪刑法定与非法定之和合”这一和谐而稳定的局面。
从依法审判的形式主义而论,法乃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经过制定或者认可并且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式。虽然从实质上来说,统治者专断司法大权于一身,但是往往历朝历代都会以法律来赋予其合法之外衣,如秦汉的令、唐宋的敕、格,明的圣谕等等,都为皇帝的司法专权赋予一定的法律形式,从此而看,作为皇权专断形式的敕、格、令、圣谕也并没有突破传统依法审判的形式范围。但从实质的角度而言,此法乃是一家之法,不能成为依法审判的实质内涵罢了。
在中国古代影响依法审判的诸多原因中,最大的因素莫过于皇权之强弱,皇权越集中,其下级官员司法裁判权力越会被削弱,自由裁量权会逐步衰退,越基层的地方司法则越容易实现依法审判。细想下来,却也是中国封建体制之下“法效”低于皇权的根本原因所致。其次应当是传统儒、道、墨、法思想文化的改良与融合,就像秦的“万事皆有法式”,事无巨细的法律规定到哪怕生活的一点一滴,致使依法审判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再如汉代“春秋决狱的原情定罪原则”又把依法审判推向主观归罪的极端边缘,乃至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孟子之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赋予司法审判以引用道德、文化,法断与情断兼而行之的礼法交融思想等等,这些无一不体现了文化观念对中华法系依法审判制度的强烈冲击,挖掘出文化体制左右法律思想的潜力所在!再次法理基础体系的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依法审判的强弱,法律形式越完善,依法审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法律形式越单一,依法审判的可能性也就相应缩小了,但是从汉的“决事比”以至唐的比附类推,明的比附援引等也都使得依法审判与罪刑法定有了一些例外补充,这也正体现了俞老先生的观点,此乃中华法系之特色“罪刑法定与非法定的和合”,是特定封建体制之下相融相生的产物,我们确实不能以文明社会法治国家的“依法审判”去要求或者论断古代的“依法审判”制度,应当具体特定的去挖掘这一命题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俞荣根.罪行法定与非法定的和合——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J].中西法律传统,2003-00
作者简介
孙宇翔(1993-),男,汉族,安徽宿州,硕士学历,中央民族大学,民商法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