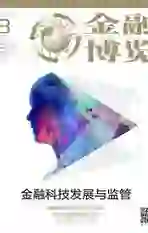《雅舍谈吃》,梁实秋讲饮食文化
2017-08-24刘清君
刘清君

脚大走四方,嘴大吃四方。看梁老先生的《雅舍谈吃》,真是吃遍了古今中外。他的脚大吗?不得而知。嘴大吗?应该也不是。那大的是什么呢?套用雨果的说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梁实秋的文章,都是以一种回味的笔触,在描写他胸怀里的汤汤菜菜,饮食男女。
梁实秋,自小生长在老北京的一个殷实的家庭。在他的文章里,他小时候的所有下馆子的记忆,几乎都是他的父亲带他去的,他尊称为“先君”。他多次提及自己的第一次醉酒,就是在一个名号“致美斋”的饭馆里,父亲不许他再喝酒,是花雕吧,他就站在凳子上舀起一大勺汤,泼在了父亲的长衫上。当时,他6岁。
梁实秋的母亲,是杭州人。梁实秋曾在《鱼丸》一篇中,对母亲的手艺有过详细的描述。他写道,二姐曾经创下一顿吃120个青蛤的纪录。
在梁实秋的记忆里,他把买回来的炒栗子藏在被窝里保温,也曾和哥哥在学校门口的早餐点徘徊,最终决定饿上一天,省钱也要一尝更贵一些的糯米藕。他的母亲,和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一样,叫他们不要在碗里剩饭,说剩饭就会娶个麻子脸的媳妇。
他的祖母在家里享受“最高规格的饮食供养”。祖母的早点,常是莲子羹,用专用的小巧的莲子碗,小银羮匙,有专人伺候。可是,这个家庭,始终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如何一路打拼过来的。在他家后院,有个大铁锅,每年的春天,总会有一天,全家的晚餐就仅吃这个大铁锅里做出来的窝头、棺材板(大萝卜)、白开水。这种忆苦思甜,梁老先生说,他是在多年后吃美国感恩节的火鸡,才算有了一些真正的感触。
一个家庭的饮食,就是一部《家》《春》《秋》。而一个城市的饮食,更是这个城市的所有记忆!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太多的北平记忆,对梁老先生来说,简直就是一部《舌尖上的老北京》,是一种北京味道!
打开这本书,第一篇就是烤鸭,说的是现在仍然闻名的北京烤鸭,也就是“全聚德”烤鸭。从这里可真是长了一点知识。我们一直说“填鸭”“填鸭式教育”。原来“填鸭”的来历,就出于北京烤鸭。北京城里本无什么鸭子,都是从通州运来的,为了促肥,通州的师傅会把鸭子夹在两腿中间,把搓得像火腿肠一样的饲料蘸上水硬性塞入鸭嘴,捋入胃中,以不撑破肚皮为度,再将其关进小黑屋,使其长肥。因为肥了才嫩。书中说,一来鸭子品种好,二来师傅手艺高,所以“填鸭”是北平所独有。
在这本书里,有不少有关饮食的小知识。培根好像说过:读书,不就是为了便于卖弄嘛!呵呵,我自己意会的,他的原话大意是:读书可以博彩,而博彩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
很多关于饮食的故事、渊源,乃至笑话、传说,在梁老先生的文章中真是俯拾皆是。比如:菠菜,原来就是源于什么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因富含铁,可以当大力神丸来用。萨其马,原来是满文,也就是满族点心的意思。核桃,又叫胡桃,胡人的玩意。就连苹果,从老先生的笔触来看,在他小时候,这玩意还都是稀缺品,都是在祭祀供神之后,才能得以享用。其他诸如印度咖喱、西湖五柳鱼(现在的西湖醋鱼)的渊源,乃至豆腐是否是修道成仙的淮南王刘安所发明,金华火腿是否是抗金名将宗泽所发明,等等的人文典故,都在书中不同的篇章有所涉及。
还是回头说老北京的味道吧!在梁老先生的笔下,有太多的老字号的大名。这些字号,可真是各有特色。例如,他常提到的“东兴楼”,是属于烟台一派,这店内会特制佳酿,专门“留待嘉宾”;也会偶尔把达官贵人的上好菜肴“偷偷匀出一小盘”,请熟客尝尝。梁氏父子,也就因此才算是尝到了熊掌的滋味。而对伙计的管理上,也有独到的一手,假如客人稍有微词,伙计就要当着客人的面,背着铺盖卷走人了。当然,“不过这是表演性质,等一下他会从后门又转回来的”。
在梁实秋的笔下,这些字号的山东人挺有意思,他们不会喊你“大爷”,只会吆喝“二爷、三爷里面请”。因为,只有武大郎才是大爷。“二爷!崩起虾夷儿了,虾夷儿不信香。”(不用吃虾仁了,虾仁不新鲜)。“厚德福”,是河南馆子,说是“时值袁世凯当国,河南人弹冠相庆之下,‘厚德福的声誉因之鹊起。”广东馆子“谭家菜”,说是有个姓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家菜,就设在他家书房,每天就开两桌,要十天前预订,“最奇怪的是每桌要为主人谭君留出次座,表示他不仅是生意人,他也要和座上的名流贵宾应酬一番。”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悉数都是为了鼻子下面的那一横活着。可是饮食口味,却着实是大相径庭。好在梁老先生长于京畿,骨子里却也留着南方人的基因,他母亲是杭州人。可能,这也就是他能南北通吃的原因吧!他写道:“提起潍县大葱,又有一事难忘。我的同学张心一是一位奇人,他的夫人是江苏人,家中禁食葱蒜,而心一是甘肃人,极嗜葱蒜。他有一次过青岛,我邀他家中便饭,他要求大葱一盘,别无所欲。我如他所请,特备大葱一盘,家常饼数张。心一以葱卷饼,顷刻而罄,对于其他菜肴竟未下箸,直吃得他满头大汗。他说这是他数年来第一次如意的饱餐!”
想起当年我在我老婆面前第一次生吃大葱,竟然也被她斥为“野兽啊!”前两年在成都,一位副校长同我们一起吃火锅,他给我倒蒜末,捂着嘴巴悄声说:“我过会儿还要见一个区长,管他呢,嘴臭就嘴臭吧,就是喜欢吃!”四川口音,抑扬顿挫。我倒一下子觉得这位仁兄挺可爱的,值得交往!
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些吃得非常之爽快的场景,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在梁老先生的记忆里,他多次讲到两个场景。一个是他在青岛的时候,有次在寓所后的山坡散步,看到有人给工地上送饭,是韭菜馅的发面饺子,说那些大汉拿手抓过就吃,热气腾腾,风中飘来的韭菜味,香极了。而每个饺子有半尺长,每人两个就够了。随后,又从水桶里舀水大碗地喝。他甚至感叹:“真是像《水浒传》中人一般豪爽。”而另一个场景,就是梁老先生记忆中,在北京的一个小吃馆,来了一个赶车的,辫子盘在头上,托着菜叶裹着的一块生猪肉,拎着一把韭黄,让掌柜的给他“烙一斤饼,再来一碗炖肉”。最后三下五除二,满头大汗地吃了個精光,挺起腰身连打两个大饱嗝。梁老先生说:上面这个场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人,心里坦荡荡的,饿来吃饭,取其充腹,管什么吃相!
前几年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子中的主角都是当地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都是自食其力,吃着自己双手做出来的食物,很满足。梁老先生在《窝头》一文中也说,“贫乃士之常,何况劳苦大众?”他自己也回忆,他所吃过的“最低级”的饺子,是抗战期间,有一年除夕,他在陕西宝鸡,流落街头,到了一个路边草棚的所谓饺子馆,所吃的二十个韭菜馅的饺子。他说店主还抓了一把带皮的蒜瓣给他,外加一碗热汤,吃得他满头大汗,十分满足。丈夫断炊寻常事!只要是自食其力,都是香的!只要是自己吃着香,何必龙肝凤髓方得快意!
当然,梁老先生也不乏偶遇。他说自己有早起的习惯,某日居于沈阳某友人家中,起床后见厨房师傅胃疼发作,遂以所带苏打片见赠。大师傅作为回报,竟将主人所藏的一罐鲍鱼给他煮了一大碗鲍鱼面吃。他自谓这是他一生都没有过的豪举,是他吃鲍鱼最为得意的一次。“主人起来,只闻到异香满室,后来廉得其情,也只好徒呼负负。”
梁老先生毕竟乃文化中人,其座上嘉宾,一般也非等闲之辈。在他的文章中,时有透露。他说,有次在河南馆“厚德福”,赵太侔先生掏出一个大洋,让伙计买来cheese(芝士),加入铁锅蛋中,发现气味果然喷香,不同凡响,从此悬为定律。而在《火腿》一篇,老先生则忆及吴梅先生与东南大学同仁聚餐:“先生微醉,击案高歌,盛会难忘,于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我原来读书,对吴梅先生也略有所闻,据说是当时以自己能唱、能演而闻名的一位词曲大家。好一个“先生微醉,击案高歌。”想想都令人神往!当然,也有文人雅士和我们芸芸众生一样者,梁老先生说,有次在重庆吃饭,有个叫杨棉仲的先生,湘潭人,风流潇洒。一下筷子就说:“这一定是湘莲!”莲子,以湖南的为好,人称湘莲。有人说:“那倒也未必。”棉仲不悦,喊来伙计,问:“这莲子哪里来的?”伙计答曰:“是莲蓬里剥出来的。”众人大笑,棉仲再问:“你又是哪里来的?”伙计答道:“我是本地人呀!”
在梁老先生的文章里,会不时露面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并且,这种露面,还真有点像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笔墨很少。难道胡适之先生还真是人中龙凤,高深莫测?梁老先生提到,一次,北大外文系女生杨毓恂小姐毕业,请外文系教授吃扬州馆“玉华台”。“胡适之先生也在座,若不是胡先生即席考证,我还不知杨小姐就是东堂子胡同杨家的千金。老东家的小姐出面请客,一切伺候那还错得了?”
还有一次提及胡适之先生,说是他来台湾,有人在家里请他吃饭,使出浑身解数做了十道菜,主人谦虚地说:“今天没预备什么,只是家常便饭。”胡先生没说什么,在座的齐如山先生说话了:“这样的家常便饭,怕不要吃穷了?”和胡先生一比,这个齐如山倒更像是个实实在在的饮食男女。梁老先生应该和他交情不错,提到过齐先生请他去家里喝奶酪,发现原来他家的奶酪竟是批量生产,运往一家店铺代售的。还有一次提到,齐先生带了他,穿街过巷地找到了一家豆腐脑小店,二人大吃了一顿。
吃喝拉撒,谁也不能免俗。文化人,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吃的问题,还真是个问题。咱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是“君子远疱厨”的一种处世哲学!一个人一谈吃,似乎就成俗人了。(现在又好像矫枉过正了)无论如何,饮食文化留下来的还真是不多。前段时间看李国文的《文人江湖》,他在对袁枚的评论中也感叹,就连梁山好汉喝的到底是咋样的一种酒,我们都不得而知。他也感谢那阴鸷的胤禛,在其文字狱的高压下,袁枚同学就只能吃吃喝喝啦,最终才有了《随园食单》这部作品的问世。
饮食文化,要往源头上去追,早一些的恐怕就是《饮膳正要》了。梁老先生对此有专门的一篇文章论述。《饮膳正要》,堪称我国第一部食疗专著。注意,是“食疗”专著,主要还是侧重于疗,而不是侧重于食。作者是元朝的忽思慧,他是元朝的饮膳太医,是个蒙古人。他的书中,重点还是在讲“谷肉果菜的性味补益”而已。所以,梁老先生看得很郁闷。认为“其最大缺点为饮膳与医疗混为一谈。”觉得其中颇有附会可笑者,例如:“鸳鸯,味咸平,有小毒,主治瘘疮,若夫妇不合者,做羮私与食之,即相爱。”老先生反问:如果吃了鸳鸯肉,便可以晨夕交颈?
食疗,固然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很多真的都是附会而已。老先生也提到,他对北京的茯苓饼没有啥感觉,觉得只是以“茯苓”之名为噱头而已。茯苓,本来是种菌核,被古人认为是集树木之灵气而成,所以想当然地被认为能令人延年益寿。而实际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已经质疑过了,这种菌核,类似于树木的“毒瘤”,你还怎么敢指望它来延年益寿呢?这种类比是经不起推敲的。梁老先生也反驳:“常饮牛乳,色如赤子,那喝咖啡的,岂不要面如炭黑了?”他觉得,这都是噱头。
文化中有好的东西,要传承;有不好的,要扬弃。我们老祖先留在饮食文化中的一些人文气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梁老先生在《蟹》这一篇中引《晋书·毕卓传》:“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又在《笋》这一篇中引苏东坡的名句:“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这些句子,读读都觉得口舌生津!
读其书,知其人。我对梁老先生还是非常钦佩的。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好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对于他的评价,是冰心写的:“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我的朋友,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这朵花,这朵华丽的花,有时候却是很朴实,有时候却是带着刺,棱角分明。
他对文化的观点,就如同他对饮食的观点一样。有点像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不相信我们古人说的什么芦苇变虾,什么石首鱼变野鸭;他不相信那些附会,不相信那些噱头;他也不相信谁的文化就比谁的高上了一等。
他回忆自己求学时在美国的饭前祈祷,他和室友闻一多,对美国房东老太太的苛刻深不以为然,对他们的半饥饿状态记忆犹新。他只是反思,我们的饭前祈祷,更应该念及我们的劳苦大众。他也毫不忌讳:“如今我每逢有美味的饮食可以享受的时候,首先令我怀念的是我的双亲……美食当前,辄兴风木之思,也许这些感受可以代替所谓饭前祈祷了吧?”他不刻意忌讳“吃在美国”,他对美国人的三明治、冰淇淋仍然保持认同。只是也会感叹:“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一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
当然,他也很谦虚,他在《吃在美国》一篇中提到:“我生平最怕谈中西文化,也怕听别人谈……除非真正学贯中西,妄加比较必定失之谫陋。”像他這样的人,都说不敢妄谈,这倒也堵上了不少人的嘴。堵上了乱说话的嘴,而不是我们那张“兼容并包”的吃饭的嘴!(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