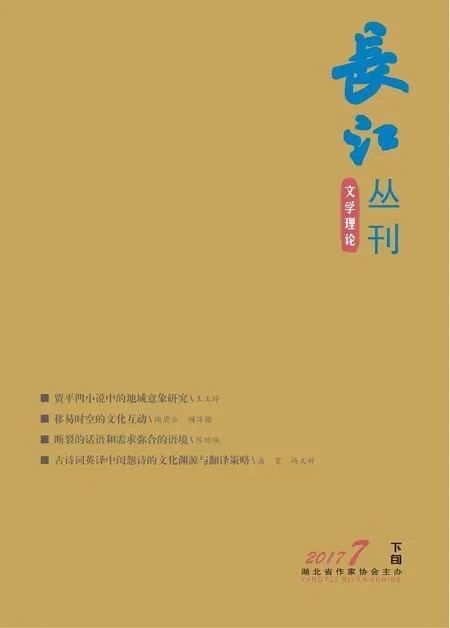五 万
2017-08-07李国胜
李国胜
五 万
李国胜
金汉发坐下后讪讪一笑,对那三家说:“劝赌必赢,你们硬要逼我上架,输了钱不能反悔的。”说着看看表,“一点半……这样,我和你们三位讲个条件。陈局长说他两点半有个会,他要讲话,三下五除二,一二十分钟搞定,尽量在三点钟赶过来。现在一点半,我舍命陪君子,和你们玩四圈,差不多正好到三点钟……”
“他三点钟赶不来呢?”坐东的刘老板说,“那你一走,我们三家斗地主?”
“不不不,”金汉发很认真地说,“我的意思是,头一局,四圈,不管怎样我都陪到底,四圈不下地,他就是来了,我也不让。三点钟他还不来,我当然不走。只是丑话说在前,第二局开始,他一来我就要下桌,赢了的钱不退的。哈哈!”
“好好好,”南家吴校长有几分不耐烦了,“说了就算数。搞吧,快点。”北家魏院长护着金汉发,说了一句:“吴校长,刘总,体谅汉发一下嘛,他不能只顾着我们这一桌。楼上楼下,八张桌子,都要他照应。”刘总不爱听这话,撇撇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说:“八张桌子?把我们八仙过海八大金刚这两桌散了,靠楼下那六张桌子,汉发喝西北风?”
这话倒也是实。金记茶室摆了八台麻将,楼上两间雅座,楼下六桌散席,有点像当年襄河客轮一等舱与大统舱一般,尊卑贵贱各居其位的格局。楼上贵宾是常客,以刘总说的“八仙过海八大金刚”为基本面,镇上七站八所的头儿,加上几个收棉花粮食的老板。楼下就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三教九流的人,随来随走,打的牌叫“晃晃”,那意思说,来个人,玩两把,起身走了,又来人补上,晃来晃去,晃去晃来。这当然不会大赌,有时一张桌子凑齐了不过三五十块头子钱,半天下来,六张桌子勉强收到三百块茶水费,也真是刘老板说的,够喝西北风。
楼上的场面可就生猛得多。打的是——按金汉发说,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部规定的国际体育竞技项目:竞技麻将”!这麻将的规则是“算番”。高级教师吴校长给他考证过,体育部什么的,那是扯淡,哪有这部?不过倒真有一个中国竞技麻将协会发布过《中国竞技麻将竞赛规则》,也巧,这规则与襄河两岸几百年来流行的“算和”大同小异。大一点的区别只是,GB麻将144张,本地早年间有过,现在都改136张了。其它什么,“花龙清龙七对独钓”,全是一样一样的。
这“算番”与“晃晃”的打法,真有天壤之别。算番的牌局,小点玩,八圈下来一两百足矣;晃晃的牌局,打大的,一场胜负可能三五万。反过来,玩算番的,半天可能有几万出进,晃晃——比如金家一楼那几桌——也就百来块钱。
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倒并不只是输赢大小。算番的乐趣在于变幻无穷。同样的十三张牌摸起来,有人能玩出大满贯,有人只能“屁屁和”,《中国竞技麻将规则》规定了64种牌型,最小的,一番;最大的,几百番都有。金记雅室打的是“20块一底”,最小的一番就是20元,大的……不好说了。64种番目全写在规则上,和了牌,按番数乘以20元即可。
这《中国竞技麻将规则》的放大影印件盖着血红大印,张挂在两间雅室里,姜太公在此,辟邪驱妖,保一方平安。桌面上和暗屉里,一分钱都见不到,全用筹码。派出所也好,纪委也好,干瞪眼。筹码不多,每家拿五千钞票买四千九的码子,金老板按行规称为茶资。按吴校长说法,谓之出师未捷先断腿。八个人就是八百。名义上说的是每天下午拿这钱安排肉酒肉饭,那几位几乎每天都有饭局的,十二圈或是十六圈打完,柜上把筹码兑清,拜拜了。平常日子,每顿只有两三位留下,金老板作陪,烟酒菜饭,三百元搞定,恰好拿楼下那笔银子对付,楼上八百元就照单全收了。
今天行市不利。电话打了几十通,只约到三个人,一桌都开不了,创下金记茶室开张以来上座率最低的黑色记录。费了好多口舌,工商所陈局长(据说工商所要改工商分局,因此镇上人都提前称之为陈局长)总算答应,下午开个短会后过来。那三位一点钟就到了,心焦火辣,无奈之下催老板上阵。
这几个人是衣食父母,怠慢不得,汉发老板只好坐了上去,心中默念“劝赌必赢劝赌必赢劝赌必赢……”无数次,一边念叨一边捻着腕上佛珠,一不留神出了声,“劝赌必赢嘞。你们三位输了莫怪……”
“少说些废话!”刘老板拍出一张牌来,“北风!”
清汤寡水地打了三圈多,汉发悄悄清点一下暗屉,还好,只输了五百多,眼看四圈要下地,小心点打,不出现大番,五六百块钱认了。恰好陈所长打电话来,问这边战况如何,说,最迟三点一刻赶到。汉发放了心,对三人说:“都听到了,陈局长一定来。我输了五百多,不赶本了,四圈打完,你们几位喝杯茶,等他……诶诶诶,慢点慢点,魏院长,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魏院长笑笑:“这没得法,有碰要碰嘛。”
原来,恰在金汉发搁下电话时,南家吴校长打出一张五万,汉发坐西,手上刚好是四六万,两张牌拿下来,正要吃进五万,北家魏院长大喝一声:“碰!”拿出两张五万来,笑嘻嘻地摆在面前。
魏院长伸出两个指头,到吴校长门前夹那张五万。汉发忍不住说一句:“碰了五万,你拿什么做将牌的。”
对面刘老板马上接了一声:“清一色不要二五八做将牌,这都不晓得?”
刘老板心里清楚得很,到此时为止,上家魏院长打了七张牌出来,一张白板,一张西风,三张条子,两张筒子。万字一张不见。这张五万一碰,清一色是毫无疑问了。
吴校长也早看出桌上有人攒万字。他手上唯独只有一张五万,一直捏着。你少,别人就多,这是不消说的,牌局铁则。
汉发稍一定神,当下明白,手上这一把牌没用了。四六万是肯定死翘翘,又不能拆开打出去,只能弃局。好在这一局只有两把牌了,熬过去,少输当赢吧。
魏院长碰了五万,打出一张三条,“金三银七”,这样的字,不到最后关头是不出手的,何况他前边还打过五条、八条、九条。局势再明显不过,魏某人的万字清一色已经十有八九了。
东南西三家都盯着剩下的墩子,暗暗盘算,每人还有三张牌,算了,万字是不能打的,他要自摸,是他的手气。
刘老板打出一张红中,是三张开拆的,不玩了。吴校长本是摸一张三六九条就听牌的,偏偏摸到一张一万,桌上未见面,还打个球,把个四筒丢了出去。金汉发手上有五六筒,本来吃进四七筒就等五万来和牌的,现在死了心,不要了。不是不想要,是不敢要。要了就要拆四六万。伸手一摸,晦气,是张红中,啪一声拍在桌上。对面刘老板这一气非同小可,他一直在等第四张红中出来开杠!
魏院长看着一东一西两家的红中,快活得很,也不怕讨人嫌,西边看看,笑一笑;东边看看,又笑一笑,不紧不慢地去摸牌——“碰!”刘老板气冲冲地拍出一对红中来。
魏院长一怔,手缩了回去。“你不是刚打一张红中……”
刘老板脸上表情马上变了,很客气很歉疚地说:“对不起院长,刚才把牌码乱了,看花了眼,现在刚看清楚,原来我碰红中就听牌了。”说着,学魏院长手势,俩指头把汉发门前的红中提拎过来,刚要放进那一对中凑仨,眼睛一转,丢下了,“还是要我的原配吧。”把上一手打的那张红中捡起来,“对不起对不起。”
魏院长有苦难言。刘老板分明是不让他摸牌,跳他一张是一张,但这种打了什么又吃什么打了什么又碰什么的路数,规则上是允许的,还有个术语,叫做“回头一笑”。好马偏吃回头草,无可非议。
幸好他出手慢了一拍,倘若快那么零点一秒,右手中指肚接触到那张牌正要翻开摊下时被刘老板一刀砍断,他恐怕要掀桌子。
那张本该他摸的牌是,一万。
魏院长门前的明张是碰了三张五万,手上暗张是——
九万九万八万七万六万四万三万二万
一万
最可能的和牌是一四万“两头钓”,清一色,自摸,倒下来是:
九万九万九万
八万七万六万
五万五万五万
四万三万二万
一万一万
25番,三家各五百元,不错了。
但魏院长志不在此。他已觉察到吴校长不要万字,如果第四张五万被吴摸到,理论上说,还可能打出来,那么就是——
九万九万
五万五万五万
七万八万九万
一万两万三万
四万六万,五万和牌!
什么意思?
清一色一条龙嵌五万,还是四带一!这且不谈。最难得的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万,五万和牌,又是绝张,断桥会!
这个牌和下来,按金记雅室的规则,叫做“一家干”。满贯大和。本来他这一把可以算出两三百番,那三位每人要开四五千,但牌友们有约在先,100番封顶,也就是一局最多开两千。一般情况下牌局进行到一半以后,很可能有人手上的筹码不够两千,因此又立了这样规矩:桌上只要有一家筹码用光,“一家干”了,马上散伙。这办法可能是从中国足协那儿学来的“突然死亡”,也可能是从中国证监会学来的“熔断”。干了的人净身离桌,其余两家(有时甚至只剩下一家)开两千,散伙,如要再战,大家再买五千筹码。这是人人认可人人遵守的规矩。
这张一万被刘老板跳过了,魏院长虽然不明真相,心中倒也并不着急,他只等那张惊天动地的五万。
这红中还真碰得巧,吴校长摸起来一看,朝刘老板挤眉弄眼一番,把一万很小心地插进去,丢出一张五筒。
轮到金汉发,摸到的那张字让他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居然是,五万!
绝张。
他本该是吃了吴校长的四筒就等那张几乎不可能的绝五万,上一手放过了四筒,幸好整手牌型不乱,估计老吴也是一对四筒拆的?一切都有可能。
接下来魏院长摸到一张东风,看都懒得看,丢了。
刘老板摸到幺鸡,丢了。
吴校长摸到九筒,丢了。
金汉发心中暗骂,你他妈的就不会摸张四七筒打出来?想想这话说也无用,可想而知,他要有四七筒肯定打了。唉,求人不如求己,不信老子摸不到一张四七筒——翻过来一看,偏偏不是。四七倒是四七,一张七条。
桌面上每人还有两张牌,魏院长坐北,还有三张,一四万应该大有希望,当然,最好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梦想居然成真,一张……五万!
九万九万
九万八万七万
一万二万三万
四万六万——五万!
十一张牌,连同三张五万,十四张摊倒在魏院长面前。
清一色,一条龙,绝张,四带一,断桥会……
场上死一般寂静。
吴校长自己的账有数的,只有一千七了,站起身把全部筹码抓出来一丢,起身就走。
刘老板叫了一声:“再买码子吧,不想赶本了?!”
魏院长说话都不利索了:“不要要紧的的,陈陈局长马马马上到……”
刘老板追赶吴校长去了,魏院长去柜上兑账提现,金汉发呆坐在那里,脑子全空了全乱了。
第一个念头是,魏某人出老千。
网上早说过,广东福建那边有一种贴膜,暗中贴在牌上,眼睛一眨,母鸡变鸭,要啥有啥。
但老魏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再不济,也是镇卫生院院长,副主任医师,省市县三级的劳动模范,有头有脸的人,能如此下作?再说,那最后一张五万看了几十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对是原装正品。
第二个念头……没有第二个念头了。心都乱透了。
老板娘上楼来,打断他似有若无的思绪。
“他只要了……一万四千五……”老板娘说。
“嗯?!”
“账算了,吴校长输光,刘胖子输了两千三,算下来你输了两千五,魏院长该赢九千八,连本一万四千八。他只要一万四千五……”
“不是钱的事!”金汉发跳起来狂叫一声。
老板娘不知场上详情,傻傻地说:“我还和他讲客气话,说大家愿赌服输,我们老金不能坏了规矩……你要让一点,多谢了,要就九千六,六六大顺,要就照算,九千八,要发不离八。他却说,最喜欢这个五五五……”
汉发懒得和老婆讲,把那五张五万排在她面前,“你自己看吧。”
老板娘俯身一看,就像麻将场上笑话所说,两只眼睛变成了一对二饼:“这这……狗日的还出千?”
“不是贴的膜,我看了八百遍。”
“那……偷牌?”
“放屁!偷也要有东西好偷哇!哪里偷第五张?”
“那你怎么不说穿他?”
“放你妈臭屁!我自己手上有个五万!他和了四张五万,这麻将桌姓金,我能够说?!那第五张算他的算我的?”
老板娘瘫坐在椅上,抓耳挠腮许久,不知如何是好。
道理是再简单明白不过,老公不会在桌子上弄鬼,魏某人的四张五万肯定有问题——她自言自语,惹来老公又一顿骂:“真是他妈SB!当然是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老婆居然笑了起来:“你说话像干部嘞!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怎么说的?哈哈!”
汉发翻起白眼瞪这婆娘,越看越坚信真他妈是个SB。老话没说错的,痴驴爱叫,痴人爱笑。“滚!下楼收钱去!”
自去年装修一新“二次创业”以来,除掉乙未年腊月三十那天下午,今天,2016年4月10日,丙申年三月初二,是金记第一次不开晚饭留客。一百多天了,座上客常满壶中酒不空,账本上日积月累的数字正向六位上靠近,生意兴旺,前景乐观,谁想得到今天……两口子都懒得提做饭的事,一个在楼上冥思苦想,一个在楼下盼那六桌散兵游勇快快滚蛋。好不容易,应了盼星星盼月亮的老话,天黑下来时,第六桌才算散了伙。老板娘来不及收拾打扫,急急忙又上了楼。
金汉发好像就等着她快来有话讲,张口就说:“我想到一点眉目了。”
“哦?!”
“我们开张一百多天了,楼下的不谈他,楼上这两桌,我记了的,前前后后有十九个人在转。八大金刚八仙过海是铁杆,每天总有五六个要来,再约别人。去年腊月三十,今年初一到十五,都没有空过桌。哪里有这样巧的事,今天这张桌子出了妖怪,那边唱空城计……这两桩事怕是有牵扯。昨天我不在家,楼上出过什么事没有?”
“哎哟我想一想……哎哟!这一说,还真有点名堂嘞!”
“嗯?!”汉发站了起来。
“昨天,这边是你们刚才的班子,陈局长来了的。那边一桌是财管所田所长、金丰公司杨总、移动公司胡经理、农商行张经理,两边都平平静静的。兑码子的时候,田所长和胡经理赢了,也不多,一个两千三,一个一千八。临走时,田所长坐了几分钟,等那几个走后,悄悄对我说,以后他不和杨总打,约人的时候注意。”
“嗯?”
“他说,今天是他自己赢了,不想多说,要是输了,他不依的。”
“究竟怎么的?!”
“他说,打到最后一把牌,输赢是定了的,他赢两千六,也不在意了。杨总和了最后一盘,碰六条的‘对对和’,这个牌就有点搞不懂。”
“有什么搞不懂?”
“田所长说,他自己手上有一对六条。”
“啊!?”
“不过他又说,反正那一把牌15番只开了三百,落袋两千三,心满意足了。再者说,牌打到最后,都昏头昏脑了,说不定是哪个把六九条看花了眼……只是,说归那样说,他一定怀疑杨总出老千,搞出第五张六条来。所以又说,别的都不谈,天知地知,以后不和杨某人玩就算了。”
“你这臭婆娘!”汉发恨不得掀了桌子,“昨天怎么不讲?”
“你在外头喝得像头死猪了回来……”
“赶快清牌!赶快清牌!”
汉发明白,一定是两边的牌弄混了!这边多出一张五万,那边多出一张六条!如若所料不错,这边肯定少一张六条,那边少一张五万!
电门打开,机器好一阵转,片刻工夫四个墩子拱了出来。汉发一看,背板是红的,双手一拨拉,推了进去,说:“出妖怪的是蓝牌。”
机器又转,片刻,又拱出四墩蓝色背板的牌来。
两口子慌手慌脚一一推倒,条筒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张一排——
买了个表!真是五张五万!
马勒戈壁!真是三张六条!
二话不说,两口子飞快进了对面那间房。汉发已经心中有数,那副蓝牌其实不消看,百分之百是多一张六条少一张五万。
看着面前这桌上三张五万,五张六条,夫妻俩呆若木鸡。
半天,老板娘说:“是哪个砍脑壳的做这种事?幸好昨天这边多一张六条田所长没有发作,今天那边多一张五万是你遇上了,若是……”她的想象力很有限,不知该如何假设可能出现什么更可怕的后果。
“闭嘴!”金汉发呵斥一声,“老子安安静静想一想……”常听开场子的朋友们说,这种事是免不了的,输多了的人,下桌子时偷一张牌走,让你搞不成……这不对,这个问题不是那个问题……把两边的牌搞乱,为的就是让桌子上扯皮翻脸……我日他妈!
汉发猛醒,这是有人要砸场子断财路!
电动麻将桌被人装程序装遥控,早不是新鲜事,业内同仁都心知肚明。一旦被人下了套,轻则花钱赔礼,重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凡事情败露,当事人非伤即残,茶馆老板的日子也不好过。江湖凶险,金汉发岂敢马虎?八张新桌子全是国内顶尖品牌“皇雀”,去年买来时一台一台拆开检查,每台两种背板共272张,八台2176张牌,一张一张校验,应该是万无一失。楼下玩小牌的不必太操心,楼上两桌,外人是不让进的——吴校长说了,金记茶楼虽比不上北京武汉的会所,在我们这小地方也算私密去处了。进场五千元的筹码,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取得资格的。十九个常客,数来数去,大赢家是魏院长吴所长严所长。赢家魏院长应该不会开这个玩笑。大输家是金丰杨总、渔场郑老板,这两个日进斗金的伙计,断不会因为输掉两三万块钱坏了江湖上的名声,再说,汉发心里清楚得很,这两人大多时候是故意输给陈局长张经理他们,周瑜打黄盖的老故事。如此这般,细细想来,这十九个人当中,似乎找不出嫌犯。汉发不放心,对老婆吼了一声:“把那个表拿来。”
这份表册是金记茶楼的核心机密之一,每晚填写,置于暗柜之中。自2015年12月18日,夏历乙未年冬月初八黄道吉日开业以来,每天详记不误。某日某桌某人某人某人某人到,某人赢若干某人输若干,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此时细看一遍,不错,记忆中的情形在白纸黑字上得到印证。登记在册的十九个人,应该都不会有砸场子的动机。
那就……
金汉发把那表格掂量许久,忽地甩到桌上,“给小杂种打电话!”
小杂种即金水,他儿子。这表册是儿子设计打印的。由这表册,汉发联想到“皇雀”也是金水联系购置的!汉发还想到一件事,几天前清明小长假,小杂种回来住了三夜,晚上都宅在楼上雅室。问他干什么,小杂种说,皇雀公司免费提供了一些机器润滑油、清洗剂,他在搞维修保养。弄不好,这件事小杂种恐怕难逃干系!
金水本不叫金水,出生时报的名字是金库。当年金汉发喜得贵子,一时头脑发热,想到金库二字,兴奋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逢人就讲,我儿子这个名字,全中国,加上南北朝鲜,五百年前一个祖宗的金姓人家,恐怕找不出第二个!2005年金库上小学,中心学校的吴校长那时还是小学教导主任,接待报名时大笑,说,这个名字不好。金老板你看,我说句不见怪的话,电视里头老是在讲,哪里金库被盗,哪里金库被抢,这也罢了,还有被炸弹炸了的。不好不好。金汉发如梦方醒,忙给吴主任敬烟,说,正是正是,小伢上学,总是要再起个学名的,吴主任学问大,给他改个名字吧。吴主任把他户口本看了看,哦,98年生的,好!就叫金水。汉发忙问,有何说道?吴主任说,其一,五行上讲,土生金,金生水,此乃顺应天理;其二,水是长流不断的,财源滚滚。金汉发听了,把儿子摁到地下给吴主任磕了三个响头。
金水如今已经是武汉一所高校大一学生。他去年九月入学后,汉发夫妻二人闲得无聊,手里前些年酿酒赚到的一点资金,投资什么都不够也不敢,想来想去,开个麻将馆倒是稳妥。犹豫不决之下,汉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不料瞌睡遇到枕头,金水说,正有人推销国内第一品牌麻将桌。汉发一听,烦了:“你上的什么大学?操的什么心?”金水在电话那一头回答他:“你要我上市场营销系,学的就是这。大二大三大四的,哪个在上课,都被老师差东遣西,推销产品。”汉发无言以对。儿子读这个专业,本就是老头老娘的主意,指望日后金水长流源源不断,现在儿子才读了一个多月,就会向娘老子推销产品了,心想事成,有啥好埋怨好责怪的。
买吧。家中空余面积一算,刚好够摆八台。12月18日开张,冬月初八,八八八,还能不发?
电话打过去,汉发不好明说,拐弯抹角地问:“那个‘皇雀’麻将桌有没有售后服务?”
金水笑了起来:“是不是错了牌?”
汉发大惊:“你——”
那一头电话突然断了,过了一两分钟,发一条信息过来:“要上课了。”
汉发看看表,六点半。小狗日的,武汉才去了半年,就把老子当乡巴佬了?六点半上课?你哄老子?
电话一次一次拨过去,得到的回复一次一次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老板娘听得不耐烦了,说,“怕是你的手机有毛病吧,我来打。”
她拿出手机,点开通讯录一看,嗤嗤地笑。汉发啐道,“真是SB!打电话就打,笑个卵子!”
老婆说,“我这第一个号码是儿子的手机,第二个是他们学生公寓的座机。手机打不通,你不会打座机?”
座机倒是一打就通了。汉发说,“我找303的……”儿子的大名还来不及报上,那边说,“学生在上课。”挂了。
“真的在上课?”
然后……没有然后。直到晚上十点多,电话还是打不通。急得发慌,闲得无聊,汉发捏着手机颠来倒去,心生一念,要老婆给那十几个人打电话,“探探口气,我担心明天情况不妙”。真是怕鬼有鬼,那些家伙个个吞吞吐吐,分明各有心思!更可怕的是,刘胖子阴阳怪气地问,“老魏和牌的时候,我看你神色蛮不对嘞,吴校长说,他也看到了,你捏着一张牌,死死地不松手。老魏那张五万,是不是有点……”
完了。虽说砸场子断财路是谁干的一时还闹不清,但已经被他得手了!四个多月将近赚了10万,推算下去,一年25万跑不掉。就被这张五万打飞了!
快十一点了,夫妻二人和衣而卧,一来担心明天上座率,二来疑心儿子那边可能有麻烦,心烦意乱,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突地,汉发一直捏在手上快捏出水来的手机响了,火急火忙一看,来电显示是027开头的座机号码。
“喂喂喂!”
“我是金水。”
“小狗——哦哦哦,你手机是什么情况?”
“学校把信号屏蔽了。”
“什么?”
“省里有个单位明天借我们学校考试,我们今晚就在上明天的课。移动公司在调试设备,现在这一片信号都没有了,明天上午还要考,手机都打不通。”
“……那个皇雀麻将……?”
“不说了不说了,我排了一个小时队,才排上打这个电话。我很好。明天下午再说……”这时声音压得很低,“有人在监视,不准多说话……”
咔的一声,挂了。老板娘跳下床来,“这不行!儿子在学校只怕有事!你赶快去一趟!”
去武汉方便得很,一百三四十里路,两个小时就到。汉发本想按儿子说的“下午再说”,吃了午饭动身,老婆说,“这不对!我们乡里电话都没有听说打不通的,武汉那样先进的地方,哪里有这种事!上午一定要去!”汉发任何事都可以不听老婆的,儿子的安全他不敢大意,于是天一亮就开车上了路。
到学校时,才九点半,离校门还很远,就知道儿子说的完全属实——周围拉着警戒线,竖着老大牌子,“公务员考场重地,车辆绕行,十一点三十分开放”。这没有什么价钱好讲,汉发只好在路边找个车位停下,关好车门,打瞌睡。一夜未合眼,脑袋一歪睡着了。
一阵铃声把他吵醒,拿出手机一看,“金水来电”。忙说,“我在学校门口。”
“你到武汉来了?——好好好,刚解除屏蔽,我马上来。”
真的马上就来了。汉发拉开车门要儿子进来,在副驾位坐下,劈头就问:“你把麻将换了?”
儿子满不在乎:“是的。”
“我——”换了任何一个人,汉发肯定是”RNM”脱口而出,只是面前对象是亲生儿子,RTM多少年了,骂谁呢?
“你,你搞什么名堂?”只好这样说了。
“老师布置的作业。”
“什么?!”汉发的脑袋在车顶上碰了一记。
汉发的惊诧是可以理解的,那天刘副教授“布置作业”时,金水和他的同窗们也同样大惑不解。
刘副教授要学生们“作一项关于‘皇雀’电动麻将桌的社会调查”。有几十个子课题,抓阄。金水抓到的是,“把136张牌换掉一张,被发现的概率是多少”。
“我不会打麻将。”金水说。
“没让你打麻将。”刘副教授说,“你家里不是有八台‘皇雀’吗?”
“是——您怎么知道?”
刘副教授说:“我什么都知道。你就别问了。清明节放假三天,你回家后找两张桌子,从甲桌上拿一张牌,随机取样,放进乙桌,然后,还是随机取样,从乙桌上拿出一张牌放进甲桌。可知,甲乙两桌总数不变,然后……”
“我那几天回家休息,就在做这个,”金水若无其事地对老爹说,“我把两边换了一张牌,然后一盘一盘清查,看116张中什么时候发觉错了牌点。那天搞晚了,忘记换过来。”
几天前那两个晚上的事,金水记忆犹新。
他搞不懂刘教授布置这作业的用意,他也懒得问,照做就是。他本以为这事很简单——刘教授说得本就很简单,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两张桌子,换一张牌,比如讲,一边拿张五万,换另一边的六条,这一来,一桌有五张五万,三张六条,另一桌就是三张五万,五张六条……”
“这不乱套了吗?”金水不解。
“不怕它乱套。”刘教授笑道,“一副牌136张,实战只用上116张,另外20张是弃墩。这多出的第五张牌,如果码在弃墩里,就发现不了……”
“不可能吧?肯定会发现的。”
“对,肯定会发现的。我现在就要你统计一下被发现的概率。”
刘教授规定的操作方法是,弄乱一副牌后,一次一次清点136张,共100次,看那多出的第五张牌,有几次在116张中,几次在20张中。
“有病吧?”金水心中暗想。但又马上否定。他知道刘教授在干什么。刘教授是“皇雀”公司首席顾问,听一位大四学兄酒后失言,刘教授承接“皇雀”公司委托,这几年一直在研发专供北上广及沿海地区高端会所使用的麻将桌,那些地方一场牌几十万输赢,一张牌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也可以让人倾家荡产……
“你手爪子痒?!”
“做作业嘛……”
“我RTM!”汉发终于有了发泄对象,在素昧平生的刘副教授身上出一口恶气,“你们老师教这……?”
“市场调查,”儿子说,“Marken research,简称MR。说了你也不懂。”
“你今天一定要说清楚!”
金水摇摇头,“不能说。”
“这书不能读了!”汉发拧动钥匙,车子箭一般冲向学校大门。
金水还来不及拦阻,汉发已循着一个多月前带儿子来报到的熟路开到了市场营销系办公楼前。
“你——你想找刘教授?”儿子战战兢兢地问。
“刘教授?他是个什么屌?老子的钱是交到你们系里财务室的!要他退钱,这书不能读了!”
汉发哪知道这市场营销系的大门也好比戏台上官府衙门,不是随随便便好进的,门口站着两个保安,一人举旗一人拿电棍,挡住去路。
僵持半天,举旗的保安拿出对讲机,不知找什么人说了几句,过了几分钟,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推开大门出来了。那女人走到车边,轻轻敲了敲车窗,“请问您是学生家长吗?”
汉发也算跑过码头的人,懂得些礼数,知道不能对这女人发脾气的,便客客气气地说:“是。旁边的是我儿子,在营销系,一年级,叫金水。”
女人隔着驾驶室这边窗户玻璃看金水一眼,很温柔地说:“金水同学,你回教室去好吗?”
金水认得这是学生处彭处长,哪敢顶撞,乖乖地打开车门,出来说了一句:“彭老师,我爸没别的意思……”
“这你别管了。”彭处长挥挥手让金水赶快滚。看着金水向教学楼那边走去,彭处长拉开驾驶座这边车门,“请金先生到楼上谈谈。”
“五万!”噗的一声,金汉发把个大信封扔在老婆面前。
“这是……”
“桌子卖了。”
“嗯?”老板娘想拿起那钱袋点点数,被老公一巴掌打去,“放下!”
“你拿回来不是给我的?”
“……我……”汉发在沙发上躺下,“见了鬼了!”
老婆恋恋不舍地盯着那钱袋,忽想起老公去武汉的原由,慌忙问:“儿子在学校里……?”
“赚了三万块钱!”汉发狠狠地说。
老婆一听,不对头,才说的五万块,怎么又成了三万?
“明天关门。”汉发还是那副腔调,狠狠地又说了一句。
“关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皇雀公司按两千五回收桌子,八台,两万块。”
“还有三万呢?到底是什么……”
“封口费。”
“嗯?”
“你懂不懂什么叫封口费?还问个卵子!”
“哦哦……”
“这五万块钱,儿子的学费,我们的开销,凑合过一年够了。看看别的门路再说。”

李国胜,中国作协会员,湖北作协全委会委员,天门市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螺蛳湾》,中短篇小说集《愉快的车祸》《白墨》。多篇作品在《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转载。另有话剧《倒海翻江》发表,民族歌剧《茶圣陆羽》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