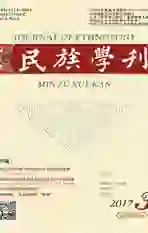土司研究取向的新视野
2017-07-20李良品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703004
[摘要]自2013年至今乃至一定时段内,土司研究取向呈现出一种新视野,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土司机构与职衔研究方面,土司机构利益的谋取、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监控,将成为新常态;第二,土司制度研究方面,土司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土司制度的终结、土司制度的专项制度研究,已成为新的取向;第三,土司区治理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区的国家治理、土司区的地方治理、土司区的边疆治理等呈现新视野;第四,土司文化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文化的理论、土司遗址、土司衙署(庄园或官寨)等方面呈现新视野。对土司研究取向视野作回眸和前瞻,以期深化土司相关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土司研究;研究取向;研究新视野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2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BMZ017)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李良品( 1957-),
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历史文化、土司制度与文化。重庆 涪陵408100
自2013年至今,是土司研究的鼎盛期。不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4年批准17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民族研究》等4家刊物创办“土司研究”专栏,而且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期刊论文620余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70余篇,主办国际国内土司研究学术研讨会8次,将土司研究推到极致。可以说,近年来土司学界无论是课题立项,还是研究成果,均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研究态势,尤其是土司研究取向呈现的新视野,值得学界高度关注。本文拟就土司研究取向呈现的视野作回眸和前瞻,有助于深化土司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土司机构与职衔研究取向呈现的新视野
元明清时期西南各地土司在道德引领、民族融合、乡土秩序构建、民族宗教文化传播、民族历史变迁、民族关系促进、家族经济社会发展、汉族官吏与土司政权互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内容无疑是专家学者们在以往研究中津津乐道的主题。随着土司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重视土司、土司机构与职衔的分类、土司机构与职衔的作用等内容逐渐演变为高度关注土司机构利益的谋取、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监控等方面的探讨。具体来讲,这方面研究取向在如下三个方面呈现出新视野:
(一)土司机构利益的谋取
研究表明,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日臻完善,它主要由土司承袭规则、土司朝贡方式、土司赋役制度和土司军事征调等多条线索以及中央政府直管、流官政府监管、军事卫所节制等纵横交错的网状交织而成。帝国凭藉这一体制,或以文明向化形式,或以武力征剿方式促使各地土司在帝国体系中进行“向内充实”。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采取部分国家权威逐漸让渡给土司,使国家权力逐步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1]明清时期各地土司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流官政府在一些具体事务的博弈中千方百计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加之各地土司具有进京刺探情报、攀附中原文化、结交汉族文人、吞并其他土司、行贿地方官员、指使民众劫掠等“手眼通天”的看家本领,所以,包括水西安氏土司在内的一些土司叛服无常,中央王朝难以驾驭。[2]未来的研究取向应在土司机构利益谋取的方式、手段、成因、影响及正当性、合法性等方面着力。
(二)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
土司机构的权力主要包括土司在其辖区内和宗族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这一问题研究已逐渐引起关注,有的学者或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帝国王权对各地土司权力的管控,或从“土司阶层的内部结构及运作”中探讨土司宗族社会为土司权力结构的整合,或从土司机构的权力赋值[3]、“权赏”关系[4]、权力绩效[5]等方面研究该问题。土司机构权力的获取,或通过积极朝贡和服从征调来获取政治权威,或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不一而足。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十分欠缺,目前仅涉及土司家族内部的运行机制。在未来研究中,要深入探讨土司机构的权力赋予、权力构建、权力义务、权力传承、权威象征、权力丧失、权力制衡以及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运行机制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区域治理、边地治理等问题的勾连。
(三)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监控
各地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化是国家控制地方土司势力扩张的主要手段,明清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控制土司机构的权力,不仅为土司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法制统一的制度基础,而且为实施改土归流奠定了中央权威基础。已有研究表明,元明清中央政府历来重视以法律手段对土司机构权力实施监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元代的土司制度不够完善,实施监控相对宽松;明代土司制度较为全面系统,法律监控力度逐渐加强,故《土官底簿》中经常出现某土司“若不守法度时换了”的说法即可佐证;清代土司制度十分完备,对土司的法律监控更加严苛,如清朝对各地土司机构的法律控制就是从承袭、朝贡、征调、奖惩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目前学界仅有方悦萌[6]的博士论文对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监控有所涉及。未来应该从土司的职衔制度、承袭制度、朝贡制度、征调制度、司法制度、奖惩制度等方面研究元明清中央政府是如何对土司机构的权力实施法律监控?以便探索出中央政府运用国家法律体系对各地土司机构权力实施有效监控而产生一定绩效的规律。
二、土司制度研究取向呈现的新视野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国家体制下治理西南、中南及西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推行的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它完全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如果从1930年葛赤峰提出“土司制度”一词并展开研究以来,土司制度研究已走过了启蒙期、低迷期、快速发展期、高潮期、鼎盛期等五个阶段,专家学者们就土司制度的概念、起源、成因、完备、评价等进行了不懈地研究,有些问题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近年来,土司研究学界已从过去的中国土司制度史的梳理、土司制度评价逐渐演变为土司制度历史地位与构成、土司制度的功能与终结、土司制度内蕴的承袭制度、朝贡制度等方面的深入探讨,有的专家就缅甸和越南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与伯克制度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土司制度研究取向新视野呈现在三个方面:
(一)土司制度的结构与功能
从学理层面和制度本身看,元明清时期我国土司制度应该由国家成文制度、各地土司颁布的制度以及土司区民间制度三个部分共同构成。[7]一定程度上看,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不仅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理论功能,而且具有工具性、稳定性等实用功能。可以说,从学理层面诠释土司制度的结构与功能至今还是空白。
(二)土司制度的终结
土司制度究竟终结于何时?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甚至引起争鸣的问题。至今至少有四种说法:一是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说,二是清末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说,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说,四是1958年最后终结说。杨庭硕先生先后发表《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等論文,基本上认为辛亥革命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8]笔者倾向于这种观点,因此撰写《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一文,可以算得上是对杨庭硕先生这种观点的回应。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后我国政体制的更替、民国政府土司义务的解除以及各地土司特权的丧失,无疑成为土司制度终结的重要标志。[9]其实,土司制度终结的缘起、过程、方式、路径、作用及影响等问题均有值得深究的空间。
(三)土司制度的专项制度研究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内蕴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教等方面的具体制度,涉及土司职衔、承袭、朝贡、征调、赋税、奖惩、教育等内容,是一套系统而综合的“制度集合”。目前学界对各种专项制度均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不够深入。如对于土司制度下的土兵制度的基本要素(诸如军事组织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军事指挥体制、军事后勤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军事法规制度等体制和制度)的研究虽在笔者的《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制度与军事战争研究》[10]一书多有涉及,但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土司承袭制度是土司制度中的核心内容,研究土司的专家学者对于土司的承袭程序、承袭文书、承袭次序与范围、承袭信物、承袭法规等均有一定的研究,但有两个问题未曾涉及:一是对于承袭制度中的世袭、应袭、袭职、承袭、袭替、保袭、准袭、告袭、请袭、听袭、借袭、代袭、冒袭、争袭、夺袭等名词概念的内涵界定、方式、区别、作用及影响等问题;二是对于土司承袭过程中形成冒袭、争袭、仇杀、战乱等弊端,中央政府采取的处置办法。只有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元明清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的驾驭与控制。
此外,土司制度研究还存在诸多空白:一是土司制度实施过程中如何体现国家统一与地方自治,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之间如何互动、调适、博弈,二是新设土司的程序与袭职的手续究竟如何运行,各地土司在朝贡与征调过程中如何有序进行,中央政府、地方流官政府如何有效控制各地土司,三是元明清三朝实施土司制度的预期目标、治策设计与施行效果究竟存在着哪些时空动态性和区域差异性,这些问题都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三、土司区治理方面研究取向呈现的新视野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江应樑《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和《清代之土司制度》、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黄奋生《边疆政教之研究》等论文以及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的专著,都将全国土司区(包括滇西地区)的治理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特别是佘贻泽在《中国土司制度》一书中自觉将土司区治理与国家政体走向连接在一起考虑,他说:“我国自民元以来,以民主政体相标榜,二十年国民会议所通过之约法,以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根本。……是则在行政完整及国家建设上,值得注意之事也。”[11](P184-185)凌纯声在《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文中同样提出:“土司制度演变至今,实已成为部落而封建兼备之制,以土司之虚名。实行部酋之统治,较之盟旗之外藩旗制,有过之无不及。目下中国政治统一,此种‘不叛不服之臣,当不能使其继续存在,听其逍遥于政府法令之外,急应加以改革,令其就范。但改革土司制度初步,应将土司政治列入边政范围。盖因土司之官为世职及其分配土地统治人民之制度,异于内政而同于盟旗或政教制度,且其所在地域,亦多远处边陲。应以土司划归边省与中央专管边政机关直辖,使土官不得借口为土司而自处于法外。又令各省土司情形虽多特殊,推行改革固可因地制宜。或仍村旧制,或改弦更张,各种设施。各地亦可不必划一,然不论其地在近边或在远缴,及其环境如何特殊,石第一步应达到,政权必须统一于中央。”[12]凌纯声在该文中将明代土司按照地域的不同,分为内地土司、腹地土司、沿边土司和边外土司四种。其实,在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其举措也不尽一致。土司区治理的研究历来是土司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2013年至2016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看,其主要研究取向十分注重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土司制度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改土归流与社会治理等主题;发表的学术论文又主要集中在土司治理方式、治理策略以及土司与边疆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等方面。因此,笔者认为,土司区治理三个方面研究取向呈现的新视野为:
(一)土司地区与国家治理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土司地区的治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地方流官政府、各地土司政权、社会基层组织、土司辖区民众则在中央政府“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政策指导下共同参与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迄今为止,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这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应该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研究国家治理下土司制度的缘起、发展、嬗变与改土归流的历程,二是探讨国家治理下土司制度内蕴的职官、承袭、贡赋、征调、升迁等共性制度,三是对元明清时期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土司制度作比较研究,四是深入探讨土司制度实施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五是探究土司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国家治理能力。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是王朝与地方实力强弱消长、国家治理能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治理土司地区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土司区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的研究应注重几个问题:一是探讨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不同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动因、条件、进程、类型、特点、规律,对比明、清两朝在推进改土归流过程中的异同及地区差异;二是探讨明清时期实施改土归流过程中围绕中央政府对原土司区治理的宏观制度设计与具体路径选择,探明国家治理结构、功能、制度、方法、运行等五大基本内容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是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下中央政府对原土司区在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开发、民族关系、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宗教事务等方面的社会重构,从而探明国家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围绕地方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四是分析改土归流实施之中和实施后原土司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理效能。
(二)土司区的地方治理
这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对土司区的治理,二是流官政权对土司区的治理,三是土司政权对本辖区的治理。宋娜针对有关问题提出了她的看法:在“家国同构”政治模式下,中央政府实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之策,以“礼治”和“安抚”为主,土司家族内部在提倡孝道、保证家族内部稳定的情况下,积极朝贡纳赋、奉调出征,以使土司政权的“合法性”固若金汤,以巩固土司政权在辖区内的统治地位。[13]土司政权对本辖区内治理的研究学者目前仅限于周智生、谭志满、韦顺莉、贾霄锋、赵秀丽,吉首大学硕士生李西玲研究最深,她以忻城莫氏土司明清时期的地方治理为个案,认为忻城莫氏土司主要从土司政权建构、辖区内地方法规制定与实施、土地的多种分配方式、办学兴教鼓励科举考试等方面对忻城土司辖区进行社会治理。这些举措既保证了土司辖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土司文化的兴盛繁荣。[14]针对流官政权如何治理土司地区,郗玉松认为,清朝雍正年间,土家族地区仅用八年时间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流官群体执掌土家族地区政权后,加速实施土家族土司区的治理,他们通过严惩违法官吏、打击地痞、保护商旅等举措,维护了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通过清除积弊、廉洁行政、雇佣民工、详定夫价等措施,提高了流官管理土家族地区的效能;通过捐资助教、设置义学、修筑城池、疏通河路、设舟便渡等公益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和谐。这些地方治理举措对当今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15]
(三)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
对于这个问题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实施土司制度过程中对边地土司及边疆治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8年啟动了国家重大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经过6年的努力,该项目于2014年完成,在23部专著中,有11部专著与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密切相关,特别是成臻铭的《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方铁的《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与土司区治理研究正相关,如成臻铭的《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一书,其下编完全是探讨元明清三代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既考察了元明清时期西南土司区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又对西南土司区疆域变动、边疆政治稳定的经验与教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总结。[16]云南大学硕士生朱强以民国时期德宏土司为个案,认为当时的边疆治理既有对清代边地土司治理的继承,呈现出时代特点。民国政府采取调整行政区划、设置行政机构、大力改善交通、发展学校教育等方式,逐步削弱德宏地区土司势力,强化中缅边疆的控制。[17]二是边地土司对辖区的治理。孔含鑫和吴丹妮认为,在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主导下,元明清中央政府利用边地土司治理边疆,这是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边地土司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往往遵循“因其俗而柔其人”的原则,其本质是延续和发展元明清中央政府文化治边策略。[18]可以说,土司制度研究与历代边疆治理相联系,充分体现了土司学界的学术自觉。
土司区治理研究至今存在巨大的空间:一是元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土司制度对土司区采取了哪些治理政策、方略、结构、模式、机制、措施,二是元明清中央政府治理土司区有什么特点、规律,三是元明清中央政府治理土司区的过程中有无善治,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效果?有哪些正面的影响,四是内地的边地土司区、邻国边界的边地土司区、跨国的边地土司区的治理与土司辖地的变化对我国疆域的外扩及内缩究竟有什么影响,五是在推进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元明清中央政府治理土司区中能提供哪些有益借鉴,上述问题是未来研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
四、土司文化方面研究取向呈现的新视野
由于土司文化内容丰富、价值重大、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因此,土司文化研究也颇受学者的青睐,其研究成果颇丰。从1996年到2012年以前对这方面研究的情况看,学界主要的关注点有五个方面:一是对土司文化理论的探讨,二是对土司文化互动的研究,三是土司遗址的探讨,大多从历史渊源、选址、文化特点等方面着笔;四是对广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云南南甸土司衙署建筑、建水纳楼土司衙署、维西叶枝三江土司衙署的旅游形象设计与传播策略探讨;五是土司文化与旅游开发的研究成为学术聚焦点和兴奋点,特别是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等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如赵秀文深入田野考察,并运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结合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文化资源重点探讨鲁氏土司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涉及鲁土司的衙署建筑、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教育等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并从连城镇概况、规划理念、规划布局等方面提出旅游开发的构想,有一定参考价值。[19]自2013年以来,随着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推动以及申遗的成功,土司文化研究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内容如下:
(一)土司文化理论研究
从学术理论的视角深入研究土司文化,主要集中在2016年,李世愉、李良品、成臻铭、彭福荣、罗维庆等做出了较大贡献。李世愉先生认为,土司文化不仅产生于推行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司时期,而且与土司制度密切相关。[20]李良品不仅对土司文化作了内涵界定,而且提炼出土司文化多元性、丰富性、民族性、不可再生性等四个特点,归纳出土司文化蕴含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教育价值、艺术价值等多种价值。[21]成臻铭认为,土司文化的结构应该包含心态、行为、制度、物态“四要素”,且内含炎黄文化、中华帝国家国观念、小区域“官家”文化等内容。[22]彭福荣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考察了土司文化[23],认为土司文化是由制度、政治、教化、民间文化等方面构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区域性、民族性、等级性、政治性、伦理性等特征。[24]罗维庆提出“土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阶段性反映,家族文化是土司文化的组成部分,移民文化是土司文化的外来补充”[25]值得关注。戴玥琳认为,四川甘洛县田坝地区的彝族土司文化具有官方文化、家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属性。[26]上述研究表明,对土司文化产生背景的提出、内涵的界定、构成的总结、特点的归纳、价值的提炼,均是土司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土司遗址
龙先琼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认为永顺老司城不仅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过程,而且也是维护多元民族文化的主要标本和历史样板。[27]其余专家学者或探讨土司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或讲述土司遗址的调查过程和结果,或研究文化空间重构与土司遗址旅游,探索土司遗址的保护管理规划。吴侔卫则以海龙屯土司文化遗存为个案,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土司文化遗存与地方互动的问题,并提出较有建树的学术思想:第一,发展地方文化应充分尊重历史,第二,保护土司文化是开发利用的前提,第三,发展地方文化需要多方资源整合。[28]王献水提出,对永顺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应以活态保护理论为基础,在进行细节性评估的基础上,从文物保护工程、协调地区经济、非遗考古工作等方面进行具体评估与分析,还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和学术理论与实践运用的思考。[29]对土司遗址价值的归纳、文化空间的探讨、后申遗时代土司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等,均是近年来土司遗址研究的热门话题。虽然我国尚有诸多土司城遗址(如湖南省保靖县洛浦土司故城遗址,贵州省黄平县岩门司城垣,云南省景东县卫城遗址等),但遗憾的是土司研究学界和地方政府对这些土司城址的关注者寥若晨星。
(三)土司衙署(庄园或官寨)
据《中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与土司相关的遗产名录》载,我国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衙署、庄园或官寨较多,分为国家级、省级或其它级别。国家级有13处:贵州省有毕节市大屯土司庄园等2处,云南省有南甸宣抚司衙署等7处,广西有忻城县莫土司衙署1处,四川有马尔康县卓克基土司官寨等3处;省级的有6处,湖北宣恩县施南宣抚司土司皇城,贵州省道真县真安州城垣,云南省陇川县邦角山官衙署等3处,四川省丹巴县巴底土司官寨等。[30]这些文物是我国不可多得的财富。在以往的研究中,专家学者主要探讨了土司衙署园林历史发展、土司衙署建筑文化与建筑特色、土司衙署及周邊街区保护规划、土司城衙署平面尺度设计方法以及土司城衙署区建筑遗址复原等问题。姬刚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测绘法,在对南甸和孟连宣抚司衙署建筑群的空间环境构成、建筑形态表征、衙署营造思想、各部建构艺术等方面的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透彻分析出两座土司衙署建筑所体现的地区性、多元性文化特征和文化内涵[31],具有新意。
笔者认为,土司文化研究取向的新视野应聚焦在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土司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特点、价值、作用以及与文化旅游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二是注重后申遗时代土司遗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政策、模式、机制、措施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三是在对甘肃永登鲁氏土司衙署、贵州省毕节市大屯土司庄园、云南南甸宣抚司署和建水纳楼长官司衙署、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四川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等不同民族的土司衙署全面维修、有效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打包,以“中国土司衙署”名义申报第二轮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论证。
参考文献:
[1]蒲瑶.帝国边缘的权利与社会——茂州羌族土司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5.
[2]刘砚月.“内在边陲”与权利博弈:十六世纪贵州土司的变迁研究——以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为中心[D].南京大学,2013.
[3]曾超.永顺司的权力赋值研究[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5).
[4]曾超.酉阳司权赏问题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
[5]曾超.酉阳司权力赋值绩效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6,(6).
[6]方悦萌.清朝前期对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统治[D].云南大学,2015.
[7]李良品,吴晓玲.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构成——学理层面的诠释[J].三峡论坛,2016,(3).
[8]杨庭硕.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3).
[9]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J].吉首大学学报,2015,(5).
[10]李良品.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制度与军事战争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11]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M].正中书局,1944.
[12]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J].边政公论,1943,(11-12),1944,(1-2).
[13]宋娜.论“家国同构”格局下的土司治理方式——以播州杨氏土司为考察中心[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2).
[14]李西玲.明清时期忻城土司地方治理的研究[D].吉首大学,2016.
[15]郗玉松.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社会治理研究[J].山西档案,2016,(4).
[16] 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7]朱强.民国时期的德宏土司与边疆治理研究[D].云南大学,2015.
[18]孔含鑫,吴丹妮.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J].青海民族研究,2016,(3).
[19]赵秀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D].西北师范大学,2007.
[20]李世愉.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2).
[21]李良品,袁娅琴.土司文化的界定、特点与价值[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4).
[22]成臻铭.论土司文化的结构[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5).
[23]彭福荣.乌江流域土司文化述略[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1).
[24]彭福荣,李娟.也谈土司文化的内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4).
[25]罗维庆.土司文化的边际界定[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2).
[26]戴玥琳.凉山彝族土司文化探究——以甘洛县田坝地区为例[D].中央民族大学,2015.
[27]龙先琼.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遗址——以永顺老司城为对象[J].吉首大学学报,2014,(3).
[28]吴侔卫.文化遗存与地方互动:海龙屯土司文化遗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D].西南大学,2015.
[29]王献水.土司遗址的活态保护——以老司城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6.
[30]李敏,等.土司系列遗产的国内外同类遗产的对比分析[J].中国文化遗产(土司遗址申遗专辑),2014,(6).
[31]姬刚.云南土司司署建筑形制及其文化内涵研究——以南甸和孟连宣抚司署为例[D].昆明理工大学,2013.
收稿日期:2016-12-24责任编辑:许巧云